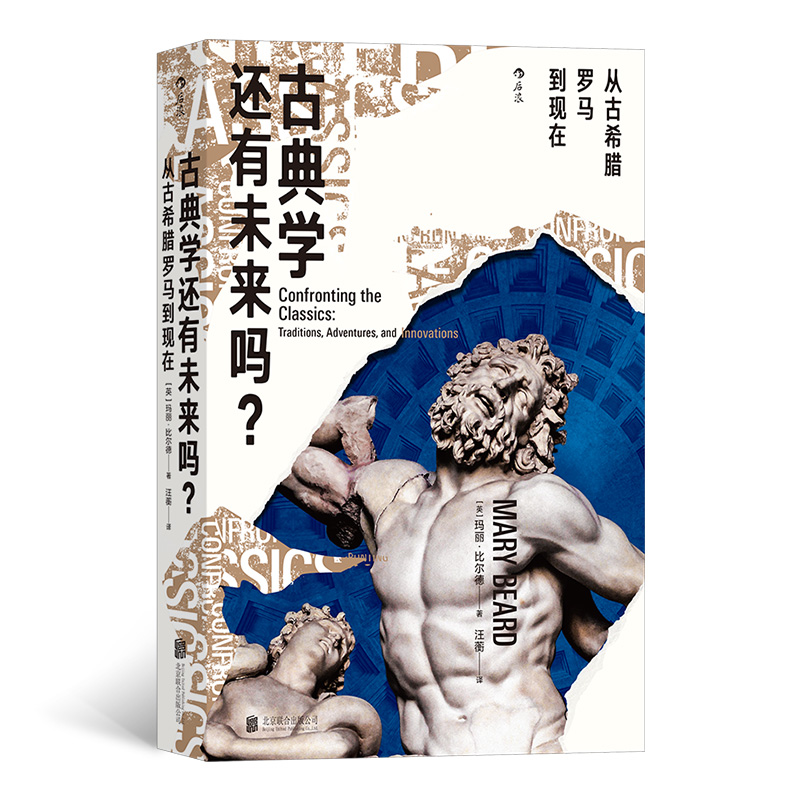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联合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7.20
折扣购买: 古典学还有未来吗?从古希腊罗马到现在
ISBN: 97875596683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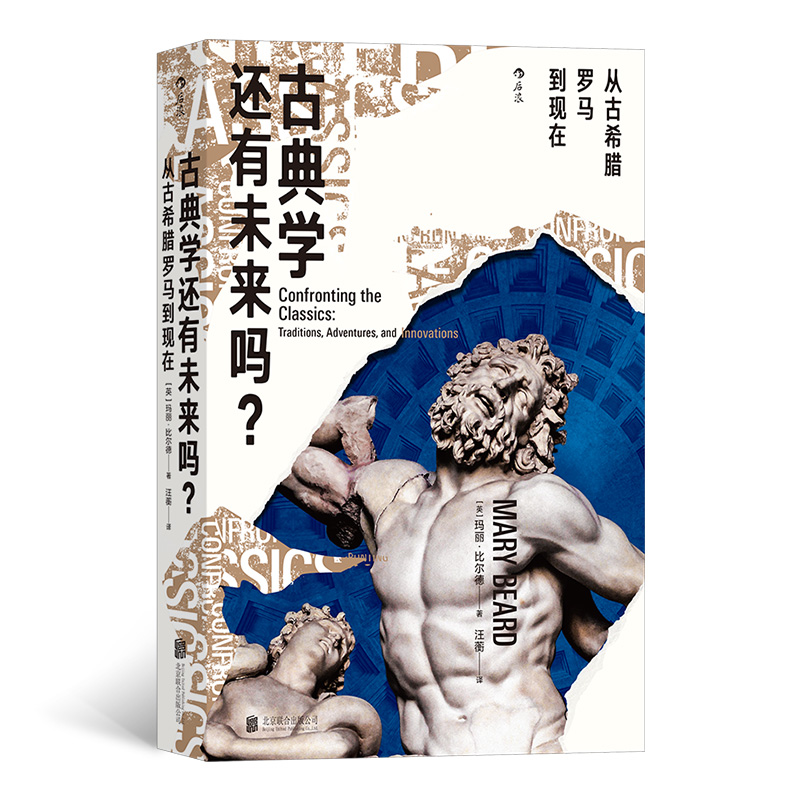
著者简介 玛丽·比尔德( Mary Beard),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由于她对古典文明研究做出的长期贡献,2018年受封爵士。她长期担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古典学编辑,她的博客“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广受欢迎,并与英国广播公司合作拍摄了多部与古罗马和古代文明相关的纪录片。主要著作:《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其中《庞贝》一书荣获2009年沃尔夫森历史奖。 译者简介 汪蘅,自由译者,北京大学英语系硕士,译著包括《美国创世记》、《缅因一年记》(待出)、《思想的革命》(合译;待出)等。
8 到什么时候? 公元前43 年12 月7 日,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遭到谋杀:他是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共和自由间歇性的捍卫者、专制制度声如雷霆的批判者。他最终被马克·安东尼的走狗追捕并刺杀,安东尼是统治罗马的军人集团的成员,西塞罗最后的令人目眩的辱骂辞所攻击的主要牺牲品:那是超过12 篇称为《反腓力辞》的演说,模仿3 个世纪前德摩斯梯尼对马其顿的腓力发出的几乎同样猛烈的攻击。这场追踪蜕变为一场复杂的,偶尔喜剧性的捉迷藏游戏,西塞罗难以决断是躲在庄园等待在劫难逃的敲门声还是尽快从海路逃离。最终刺客在他前往海边的舆轿里追上他,割开他的喉咙,将其头颅和双手打包发给安东尼及其妻富尔维亚,以示行动完成。这可怖的包裹抵达时,安东尼命人将这些遗骸展示在罗马的广场上,钉在西塞罗曾发表过许多激烈的长篇大论的位置;但在此之前,据说富尔维亚把头颅放在腿上,打开他的嘴巴,拽出舌头,摘下头发上的发簪,将它戳了又戳。 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之前的百年内战中,斩首及随之产生的装饰品对罗马一线政治人物来说是某种职业风险。安东尼本人的祖父的头颅据说就曾在公元前1 世纪初一场大屠杀中为盖乌斯·马略的餐桌增色。西塞罗一位表亲被割下的头颅(用西塞罗的话说,“还活着且在喘气”)被呈给独裁者苏拉。在更为巴洛克风格的情节中,不幸的将军马库斯·克拉苏的头颅在帕提亚宫廷某次上演欧里庇得斯《酒神的女信徒》时充当过演出道具,克拉苏在公元前53 年败于帕提亚人手下,这是罗马最惨烈的军事灾难之一。有的罗马人在装饰祖先宅第的胸像那典型的头肩风格和诸多模特最终的命运之间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联系。公元前61 年,“伟人”庞培的凯旋式队列也曾抬着他的巨大头像在罗马穿行,后来这被看作其死法的征兆:公元前49 年9 月在埃及海滩上,他的头被割下并被“腌渍”(安东尼·埃弗利特[Anthony Everitt]在他的西塞罗传记中如此坦率表述),以便献给尤利乌斯·恺撒,他于数月后抵达了亚历山大城。 富尔维亚暴力对待西塞罗被割下的头颅的故事,含义超过了罗马政治生活中常规的施虐癖。她嫁给了西塞罗的两个头号死敌(先是令人不快而魅力超凡的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他曾迫使西塞罗短暂流放,自己却被西塞罗一名心腹谋杀;之后是安东尼),现在她得到了自己的、女性的复仇机会。她用发簪刺破他舌头时,攻击的正是定义了政治程序中男性角色的那种能力—而且是西塞罗的专长。同时,她将一件无害的女性饰物转化为了破坏性武器。 西塞罗被谋杀并分尸的纯粹恐怖促成了这一事件后来在罗马文学和文化中神话般的地位。他的死亡成了罗马学童练习演讲术和名流雄辩家在晚餐后表演时的流行主题。学习演讲的人被要求对神话和历史中的著名人物提出谏言,或在众所周知的过去的罪行中选边站:“在谋杀雷穆斯的指控中为罗慕路斯辩护”;“劝告阿伽门农要或不要以伊菲格涅亚献祭”;“亚历山大大帝应否进入巴比伦,尽管有不祥之兆?”最流行的两种练习在无数罗马教室和晚宴上一再重复,包括建议西塞罗应该或不应该为保全性命而去请求安东尼宽恕;如果安东尼饶他一命的条件是要他烧毁所有作品,是否应该接受。在罗马帝国的文化政治中,这些问题有良好判断——安全地让旧共和秩序最虽败犹荣的支持者之一对阵所有人都逐渐视为代表专制制度不可接受的面貌的那个人;并在生杀大权的野蛮力量面前权衡文学的价值。罗马的评论家几乎一致相信西塞罗之死堪为楷模,这一点也很光荣。不论人们如何指控他一生中其他方面自私、摇摆不定或怯懦,每人都认为在这件事上他的表现堪称壮举:他从舆轿里伸出裸露的颈项,平静地要求暗杀者把活儿干利落(此后英雄们皆如此行事)。 对于西塞罗政治和写作上的其他成就,人们的评判就显得大起大落了。有些历史学家将其看作罗马在内战中越陷越深并最终落入独裁统治的背景下传统政治价值观的能干的代言人。其他人则谴责他用空洞的口号(“有尊严的和平”“社会秩序和谐”)应对罗马帝国面临的各种划时代问题。19 世纪,提奥多·蒙森在对西塞罗不断变换效忠对象(最终成为他号称憎恶的独裁者的傀儡)一事进行反思时,称之为“毫无远见的利己主义者”。埃弗利特的传记《西塞罗:动荡的一生》则将其刻画为理智的实用主义者,赞扬他“明智灵活的保守主义”。对启蒙运动学者来说,其哲学论述乃理性之灯塔。伏尔泰讲过一则不同寻常的故事,罗马使团前往中华帝国朝廷,给皇帝念了一段西塞罗的对话《论占卜》(详尽剖析了占卜、神谕、算命等活动)的译文后,方才赢得这位怀疑主义的皇帝的赞赏;而“图利的责任”,也就是他有关职责的专著 《论责任》(De Officiis),是许多17 世纪英国绅士的伦理手册。但这仰慕未能挺过智识领域中亲希腊主义的崛起;19 世纪和20 世纪多数时候,西塞罗的哲学—现代版本共6 卷——被认为不过是更早期希腊思想衍生的汇编,如果还有点儿价值,也只是因为提供了古代之后散佚的希腊资料的线索。埃弗斯特一有机会就给他做无罪推定,但就算是他也只能在这儿夸他“推广了天才”,并无创新,不过是“成熟的”综合者。 然而西塞罗职业生涯中有一件事,历来比任何事情都招致更多争议,那就是公元前63 年他任执政官期间对所谓喀提林阴谋的镇压。对西塞罗而言这是他最光荣的时刻。在之后的人生中,他差不多一有机会就提醒罗马人民,公元前63 年他曾单枪匹马拯救国家于危亡。他还试图以一首三卷本史诗令其成就不朽,诗名为《论执政官》。诗歌只有片段保留至今,如今最出名的是其中一句,往往被看作是挨过黑暗年代的拉丁语打油诗中最恶劣的诗句之一(O fortunatam natam me consule Romam,“啊幸运的罗马,在我任执政官时诞生”,一句押韵顺口溜,听着像是说“罗马城生来运气真好,我当执政官写个小调”)。毫不奇怪,从古代开始,其他人对于罗马人到底该多感谢西塞罗就有不同看法了。 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是位青年贵族,他和许多同辈一样债台高筑,并且因未能赢得选举,获得他认为理应归他的政治职位而感到挫败。公元前63 年夏末,西塞罗通过各种地下消息源获知喀提林正在策划一场革命暴动,要烧掉罗马城,并取消一切债务—这对罗马保守人士来说是真正的恐怖。作为执政官,他将这一消息呈给元老院,后者宣布了紧急状态。11 月初,自称刚刚逃过一次未遂暗杀的西塞罗带着更多可怕的细节在元老院公开谴责喀提林,并实际将其驱逐出城,赶到伊特鲁里亚的支持者那里。一个军团被派去对付他们——喀提林在第二年年初死于一场战役;还留在罗马的同谋遭到围捕并在元老院一场激烈讨论后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依据是紧急权力法令。西塞罗耀武扬威朝着罗马广场上等待的人群喊出仅仅一个词,一个著名的词——“vixere”(“他们活过”——即“他们死了”)。 这些囚犯的命运立即成了一桩著名公案。公元前1 世纪最尖锐的政治争论之一(自此在其他政治体制中也往往如此)便是关于紧急权力法令的性质。应在何种状况下宣布紧急状态?戒严法、防止恐怖主义法案,或者用罗马人的话说—元老院最终法令,究竟允许国家当局做什么?立宪政府中止其人民的宪法权利,在何等程度上方为合法?在本案中,处决无视了罗马公民得到合法审判的基本权利(尤利乌斯·恺撒本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当时他典型地灵光一闪,在元老院主张全无先例的终身监禁的判罚)。尽管西塞罗慷慨激昂,尽管他依赖紧急权力,他对那些同谋者的处理注定自食其果;4 年后果然应验,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控诉他未经审判便将罗马公民置于死地,并以此为据将其短暂流放。西塞罗在希腊北部备受煎熬时,克洛狄乌斯把刀子插得更深:他推倒西塞罗在罗马的宅子,代之以一座自由女神的圣祠。 西塞罗对喀提林阴谋的处置上还悬着其他问号。许多现代历史学家——无疑还有当时一些怀疑主义者——已在思考喀提林到底对国家构成了怎样的威胁。西塞罗是白手起家的政治家。他没有贵族背景,在罗马顶级精英中只有个摇摇欲坠的位置,置身于号称家世可直接追溯到罗慕路斯时代的人(或者像尤利乌斯·恺撒,可追溯至埃涅阿斯和维纳斯女神本人[ 根据《埃涅阿斯纪》,女神维纳斯之子、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逃到意大利海岸,之后在此立足,成为罗马人的祖先。恺撒号称是埃涅阿斯后裔。])之中。为了保证地位,他需要在一年的执政官任上弄出点水花。能对一些有威胁的蛮族敌人有一场辉煌的军事胜绩是最好的:他做不到(西塞罗不是个军人),需要换个方式“拯救国家”。这就很难不怀疑喀提林阴谋处于“茶杯里的风波”和“西塞罗的臆造”之间的范围内。喀提林本人可能是目光远大的激进分子(取消债务原本可能正好是罗马在公元前63 年需要的);他也同样可能是无原则的恐怖分子。我们现在无法分辨。但很可能他是被一名渴望一战——也渴望自己的荣光——的执政官迫使着走向暴力。换言之,那场“阴谋”是经典两难的典型例子:是心腹大患,还是说整件事是保守派的编造? 不只历史学家认为西塞罗和喀提林的故事引人入胜。至少在过去四百年中,戏剧家、小说家、诗人、画家和电影人都探索过喀提林阴谋的模糊之处,有的讲述高贵政治家拯救祖国免于毁灭的英雄传奇,相应也有遭到误解的梦想家被反动势力扳倒的浪漫悲剧。本·琼森(Ben Jonson)[ 本·琼森(1572—1637),英国剧作家、抒情诗人、评论家。]的《喀提林》写于火药阴谋[ 1605 年11 月5 日,有人试图炸死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炸毁议会大厦,终止英国政府对天主教徒的迫害。阴谋未遂。]仅几年之后,耸人听闻地描画了其反英雄,指控他强奸、乱伦、谋杀:在琼森笔下的冥界里,卡戎需要整个船队来运送喀提林的牺牲品。过冥河。但他的西塞罗是个喋喋不休的讨厌鬼:以至于第一次演出时,不少观众在他对元老院没完没了地斥责喀提林时受不了离场了(喀提林作为答复的奚落之词——“粗鄙的口舌之徒”——肯定会让人想起富尔维亚对西塞罗说话部位的可怕攻击)。易卜生的第一部剧作《喀提林》则完全相反,在1850 年以笔名发表的这出戏中,西塞罗彻底缺席:他压根没有出现于舞台,也几乎没有被提到名字。相反,易卜生对1848 年革命的兴奋之情尚未消退,将喀提林刻画成魅力超凡的领袖,绝望地挑战周遭世界的腐败——结果在最后一幕中和他高贵的妻子一道在血淋淋的集体自杀中死去。20 世纪出现了这个故事的更多版本,从W. G. 哈代(W. G. Hardy)异想天开的喀提林与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的姐姐的情事(《让河水倒流》[Turn Back the River],1938),到史蒂芬·塞勒(Steven Saylor)令人难以捉摸的同性恋主人公(《喀提林之谜》[Catilina’s Riddle],1993)。还有弗兰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颇有希望的电影《大都会》(Megalopolis);本片从未制作,但根据前期宣传,它将未来主义纽约的乌托邦式幻景与喀提林阴谋的主题相结合。究竟怎么做的仍不清楚。 相比罗马政治史上诸多其他逸闻,西塞罗和喀提林的故事一直更为鲜活,其原因很简单:西塞罗的谴责之辞文本尚存。西塞罗将文本付诸流传之前,不可避免编辑过,将尚待处理的细枝末节整理妥当,插入当日或许忘掉的出色俏皮话。尽管如此,在如今所称的In Catilinam I(第一次《反喀提林》演讲)中保留了西塞罗于公元前63 年11 月将喀提林赶出罗马时在元老院说的原话,我们无法指望比这更接近了。其身后名几乎和阴谋本身的一样异乎寻常,尤其开篇那句:“Quousque tandem abutere, Catilina, patientia nostra?”(“喀提林,你到底还要把我们的耐心滥用到什么时候?”引自1611 年琼森让观众极为厌烦的那个版本)。现在这很可能是维吉尔的“Arma virumque cano ...”(“我要说的是战争和一个人的故事”)[ 《埃涅阿斯纪》第一句,译文引自杨周翰译《埃涅阿斯纪》,第1 页,译林出版社,1999 年6 月。]之外最有名的拉丁语引文,依然广为应用、戏仿和改编,其方式显示了对其原意的清晰认识。 其声名可追至古代。学生们的作业包括为西塞罗建言是否要祈求安东尼的原谅,他们几乎肯定被要求极为细致地研习这篇罗马修辞经典;很可能已将其牢记于心。从文艺复兴到大约20 世纪中期的西方精英阶层的学生也是如此。因此出现于同一篇演讲第一段稍后部分的“o tempora, o mores”这句口号自然广为流传(常见的翻译是“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字面意义是“噢时代啊!噢道德啊!”)。更惊人的是开头那句话时至今日仍然流行,既有拉丁语也有现代语言翻译,而如今哪怕略为上心学过西塞罗修辞的学生也不过寥寥。这或许与以下事实有关:从18 世纪以来,《反喀提林》第一篇头几段经常用作排版样本的测试文本(现在则用于网页)。也许这让这些词句保留在文化潜意识中某处,但无法完全解释其流行程度。 从非洲到美洲,政治上的困扰仍能方便地用西塞罗的话语表达——只要把“喀提林”换成你自己的敌人的名字就行。2012年匈牙利示威人群挥舞的旗帜上写着醒目的“Quousque tandem”(“到什么时候”)反对执政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党,这只是一长串实例中最近的一个。2001 年,反对党成员之一质问新任刚果总统:“卡比拉,你要滥用我们的耐心到什么时候?”1999 年8 月,《国家报》一篇社论问道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你要滥用我们的耐心到什么时候?”借以指责西班牙首相不愿让皮诺切特受审。不久,巴西国立大学的罢工者冲着校理事会(CRUESP)高呼:“CRUESP 还要滥用我们的耐心到什么时候?” 这句话也被证明能精彩适用于各种政治之外的敌人和情境。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 卡米拉·帕格利亚(1947—)美国女性主义学者,社会评论家。]众所周知攻击过米歇尔·福柯,将喀提林的名字换成了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一位愁闷的情人(沃尔特·普鲁德[Walter Prude])因为必须服兵役而和新婚妻子(艾格尼丝·德·米尔[Agnes de Mille][ 艾格尼丝· 德· 米尔(1905—1993), 美国舞蹈家、编舞家, 沃尔特·普鲁德是她的丈夫。],《牛仔竞技》《俄克拉何马!》和《绅士喜爱金发女郎》的编舞)分离,他写道:“啊,希特勒,你还要糟蹋我们的性生活到什么时候!”这一切的讽刺之处在于,这条标语原本语境的政治动力一直在被颠覆。西塞罗或许成功地将自己写入了现代世界的政治语言之中。但那些词语本是既有秩序的发言人用来威胁异见分子的,如今却几乎普遍反过来使用,成为异见分子对既有秩序的挑战。喀提林可以含笑九泉了。 西塞罗存世作品如此之多——不仅有演讲和哲学,还有修辞论述和数百封私人信件,这使他成为传记作者显而易见的题材。两千年来确有无数人尝试撰写其生平的部分或全部故事。西塞罗本人曾(未果地)试图委托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就其执政官任期、流放和胜利归来写一部记录。西塞罗刚死,撒路斯特(Sallust)[全名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约公元前86—前35/34),罗马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拉丁文文体家之一,以关于政治人物和党争的文章著称。]就写了一篇专题著作探讨喀提林阴谋,将此事件作为共和晚期罗马道德衰败之范例,至今仍具影响。无疑更合西塞罗口味的应是差不多同时由其前奴隶、秘书泰罗(Tiro)所作的传记,还搭配一卷西塞罗笑话集。这些都未能保存下来;但它们几乎肯定隐现于2 世纪普鲁塔克所作的流传至今的传记背后(内有不少笑话)。现代作者们已经接下这一挑战,单说英文作品,近年的频率是每5 年一部新传记;每种新尝试都宣称有某种新角度或某种貌似可信的理由,来说明为何还要为看似已足够汗牛充栋的传记传统再添一本。 埃弗利特的目标开诚布公,就是“恢复名誉”,这是对他认为的对西塞罗政治敏锐性的一贯低估做出的反应:不如尤利乌斯·恺撒聪明,也许如此,但“他目标清晰且差不多实现了;他运气不好”。尽管有若干糟糕的明显拉丁语错误(如果你或者编辑搞不定,干吗非要用拉丁语?),这仍是一部有条有理的传记作品,有时对主题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热情,对共和国晚期更热辣的细节颇具眼光。同时也和现代多数西塞罗传记一样始终令人失望。埃弗利特墨守成规的“返回古代原始资料”的方法一再让他任由那部唯一存世的古代传记提出的传记上和文化上的假设摆布:由此他天真地遵循着普鲁塔克的说法,断言西塞罗出生时他母亲“生产之苦甚少”—这在古代传统中就是神童降生的意思。这也导致他一再试图填补古代资料中不便的空白,或绝望地过度阐释西塞罗自己的话。例如以他流放时的信件为据提出他“精神崩溃”;又凭借他的大量房产要求我们得出“西塞罗很乐于买房子”(就像他不断浏览本地报纸的置业栏目似的)的结论。结果就是几乎不可避免地变成古代文本的拼凑,以常识、猜测和纯粹幻想的线缝在一起。 机会错过了。我们期待的并非又一本西塞罗的“直率”传记;这种已够多了。更为得当的传记应该尝试探讨两千多年来构建和重构他生平故事的方式;我们如何通过琼森、伏尔泰、易卜生等人来学习阅读西塞罗;我们又把什么投入到了这位公元前1 世纪声如洪钟的保守派及其朗朗上口的演讲口号身上,为什么。 一言以蔽之,为什么在21 世纪,西塞罗还这么到处可见?他代表谁?Quousque tandem ?(要到什么时候?) 玛丽·比尔德带你直面古典学的传统与创新。 31篇辛辣书评,带你在古希腊罗马世界探险游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