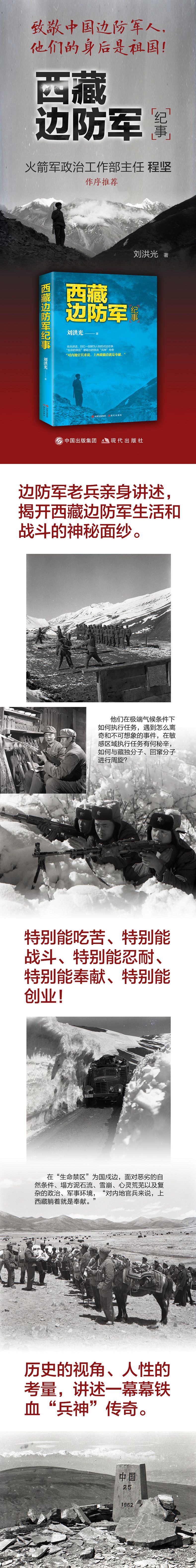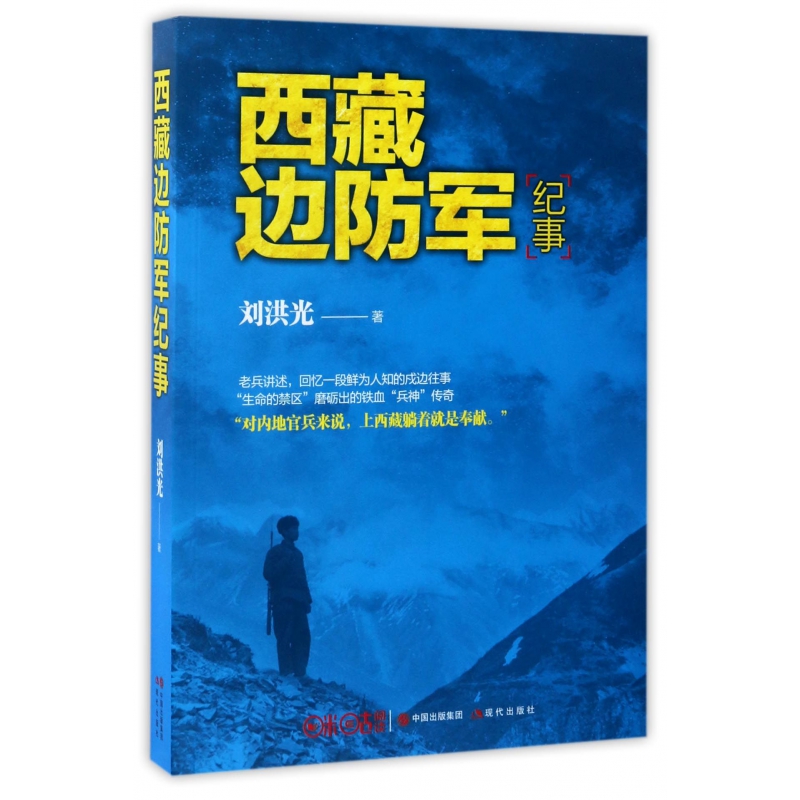
出版社: 现代
原售价: 56.00
折扣价: 38.10
折扣购买: 西藏边防军纪事
ISBN: 9787514359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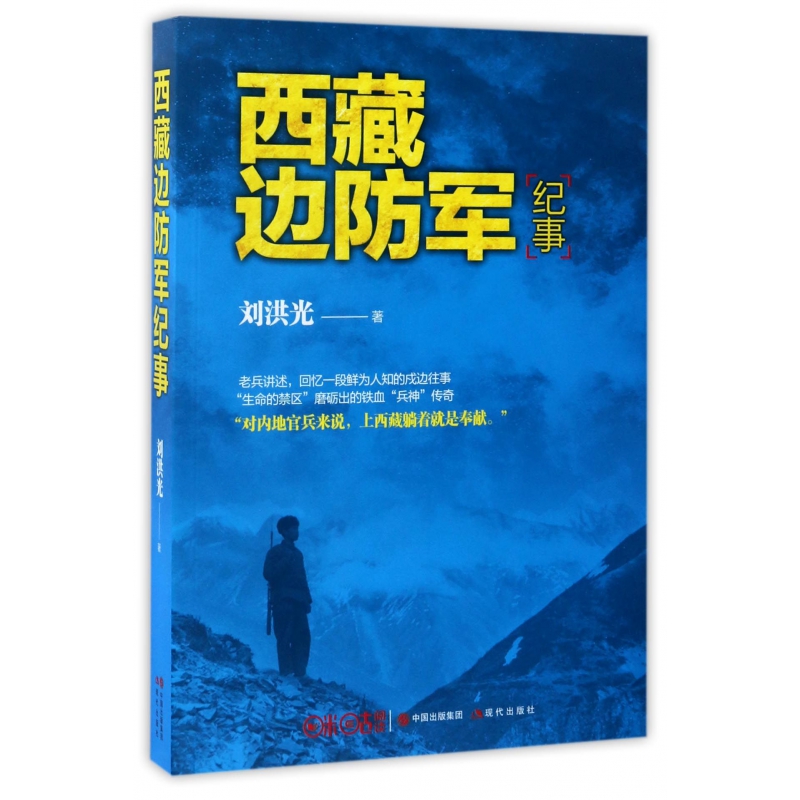
刘洪光,祖籍陕西绥德,1951年生,1969年赴西藏军区边防某团服役,历任战士、通信员、班长、文书、干事。1978年调离西藏军区,任解放军炮兵学院组织处长、政治部副主任,系政委。大校军衔。
过江后,大伙背着背包列队向欢迎队伍走去,我 抢先一步,兴高采烈地走在队列的前头,以期引人注 目。当彼此迎面走近时,我的天哪!眼前的一幕让我 眩晕,滚烫烫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这哪是我心目中的解放军,简直就是《智取威虎 山》中崔三爷的部队从天而降,根本用不着化装。细 细端详,几十个人不成行,不成列,衣冠不整,衣衫 褴褛。有的穿着皮大衣,有的穿着棉袄,不穿外罩, 肮脏不堪,活像叫花子;有的大衣上扎着腰带,更有 甚者大衣面子撕开几个大口子,听任白森森的皮子裸 露在外面,俨如电影里的残兵败将。 绝大部分人军装上缀着补丁,以双肘、两膝和领 口居多,补丁和衣服的颜色迥异,形成鲜明的色差, 太让人不可思议;衣着色调五花八门,有草绿色,有 黄色、浅黄色,也有褐色,还有上下两种不同颜色; 有的不戴领章帽徽,而有的鲜红领章上或褪色或沾上 黑污。 很多人帽檐、衣服领口,尤其胸前两侧几坨黑乎 乎的污垢,非常抢眼。一不小心露出的白衬衣早已不 姓“白”啦;头上皮帽子花样百出,有绒的,有毛的 ,有褐色、黄色、绿色,也有其他颜色,长时间没洗 脏兮兮不堪入目。皮帽子上的毛皱皱巴巴,毛绒脱落 得若斑秃,还凑合着维持现状;脚下穿的翻毛皮鞋上 的毛早已“光荣退休”,溜黑溜黑。鞋带断损后竟然 用细胶皮电线替代,给人以得过且过、混世界的感觉 ;看看他们“苦大仇深”、惨不忍睹的模样让人忍俊 不禁而又揪心裂肺。 由于长期高山缺氧,他们和青藏线上的汽车兵比 不差上下,皮肤黝黑粗糙,脸上、手上的皮脱了一层 又一层。脸蛋红得发紫带些淡淡的蓝色,眼角充斥血 丝,嘴唇干裂;摘下帽子,个个头发乱蓬蓬的像鸡窝 ,不事梳理。当他们粗壮干涩的双手紧握我们手的时 候,心情异常矛盾,不知道说什么好。 从渡口到连队尚有七八百米远,在欢迎队伍簇拥 下,继续迈着整齐的步伐向营房而来,途中有一些不 戴领章帽徽、自称是老乡的不速之客满脸堆笑,使尽 巧嘴簧舌向我们索换大衣、棉帽,寸步不离,不达目 的不罢休,像贴在身上的牛皮膏药,想甩也甩不掉。 虽然内心很反感,但又抵御不住其软磨烂缠,心一狠 ,牙一咬,很不情愿地将帽子和大衣易主。换过来拿 在手里仔细观看,一副脏兮兮的模样,帽檐留下厚厚 一层汗渍,油光光的。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欢迎 队伍中间有即将退伍的老战士,不禁对着屋顶长叹一 口气。 连队没有把我们立即分到各班,而是编成两个新 兵班,单独集中住宿,进行为期一周的适应性学习训 练。环视营院四周,群山环绕,到处是残雪,连队宿 舍除了饭堂、伙房外,一律为木板结构的活动房子, 铁皮屋顶,内部陈设简陋得令人咂舌,和青藏线上的 兵站一模一样,睡的是通铺,一个或两个班一间屋, 仅能满足最低的生活、生存需要。 晚饭前,连长突然推门进来看望刚来的新战友, 面带微笑,穿着一身褪色发白而一尘不染的人字呢军 装,头顶棕色皮帽,脚下那双军用皮鞋油光闪亮,自 我介绍姓邓名中全,四川人,1956年入伍。讲话嗓音 尖细,一脸的络腮胡子,浓浓的眉毛下双目炯炯有神 ,表情刻板,从外表看瘦骨嶙峋,但精气神十足,脸 上隐约带有一股杀气,完全符合我心目中的连长形象 。 连长一只手端着保温开水杯,原地站立,开门见 山地告诉我们高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使初来乍到的 我们明白了许多。突然,连长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将视线转移到我身上。 “伙计,你怎么戴着一顶旧帽子,是不是被老兵 换去啦?”连长嗔怪地问道。 被连长一眼看穿,看来不是今天才有。我自知内 心不够坚强,干了件亏心事,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惶恐地点头称是。 “不像话!不自觉!”连长愠怒地连续说了两个 “不”,并深深地瞪了我一眼,“我看你今后如何过 冬?” 说罢,一个人恼悻悻地转身出了门。 望着连长的背影,我茫然不知所措。 后来才知道,退伍兵也可怜,“从哪里来回到哪 里去”,回到农村能不能填饱肚子、养家糊口还是未 知数。当了几年兵攒不了几个津贴费,也没学到多少 实际本领,有的甚至连套像样的军装都没有。所以, 强新兵所难换个帽子、大衣,是想留个“曾经当过兵 ”的纪念。虽然做法不妥,但也并非“强夺”,况且 是因为与部队有感情才这么做的。 P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