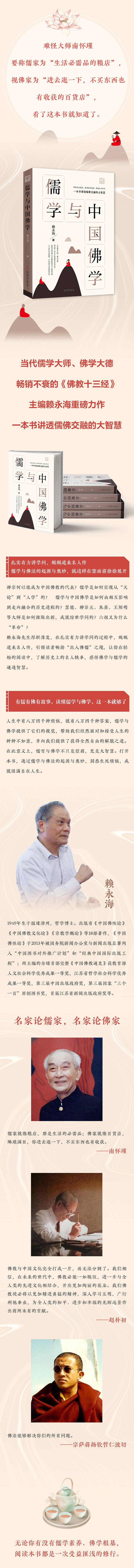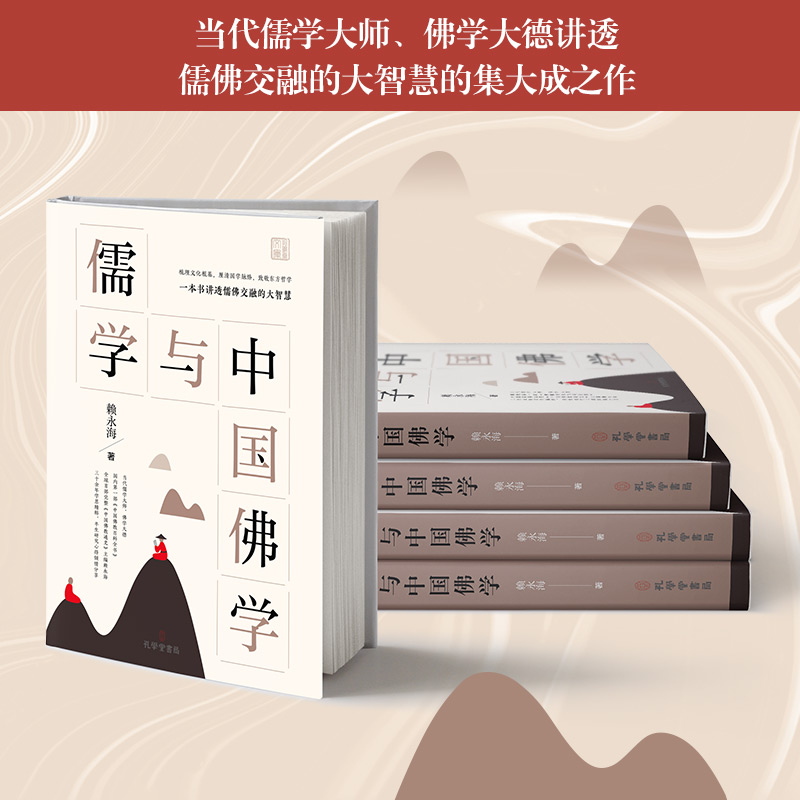
出版社: 孔学堂书局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41.16
折扣购买: 儒学与中国佛学/孔学堂文库
ISBN: 978780770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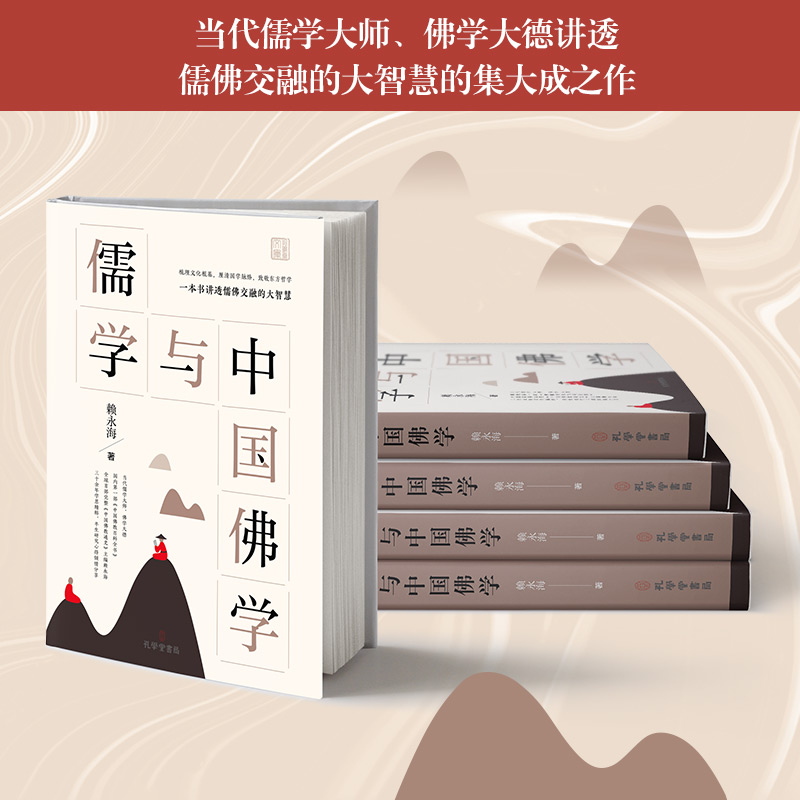
赖永海 1949年生于福建漳州,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儒学学会会长、南京市佛教文化研究院院长、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鉴真图书馆馆长。出版有《中国佛性论》《中国佛教文化论》《宗教学概论》等18部著作,其中《中国佛性论》于2013年新闻出版总署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所主编的全球首部完整《中国佛教通史》获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三届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首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等。
大乘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其修行方法及最终目标(或最高境界)不仅与中国传统儒学有着重大的区别,而且与原始佛教也不尽相同。印度原始佛教基于“缘起”理论,反对一切实体的存在,它视身为五蕴和合之假象或幻影,认为人生的一切痛苦都根源于“五取蕴苦”,要摆脱这种种痛苦,就要历劫苦修,作为最高境界的“涅槃”则是“灰身灭智,捐形绝虑”,亦即死亡之代称;到了大乘佛教,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 由于受到婆罗门教大梵本体、梵我一如思维模式的影响,大乘佛教的般若实相说逐渐孕育出一个抽象的本体。例如,与原始佛教视释迦牟尼为“亦在僧数”,差别只是他比一般僧侣更有修养、更有学问,大乘佛教释“如来佛”为“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来化群生”,亦即佛是“真如”本体之体现;又如,大乘佛教的“一实相印”,就是把实相作为一切诸法之本体;再如,大乘佛教的佛性理论,也把“佛性我”作为一切众生、诸佛的本体。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使得大乘佛教在修行方法上,逐渐地把小乘佛教之历劫苦修变为证悟本体;至于最高境界,大乘佛教则以“反本归极”“与本体合一”为终的。 实际上,当大乘佛教发展到以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为依托之后,其修行方法一定要随之发生变化——因为“本体”之为物,是“无声无臭”“无形无象”的,它不同于某种有形有象的“实体”,如果说实体是可以由“部分”相加而成,那么,再多的“部分”相加也不能构成“本体”,因此,对于本体的把握不可能通过积累“部分”的认识来实现,用佛教的术语说,要“得本称性”“反本归极”唯有“顿悟”,不能“渐修”。诚然,大乘佛教并没有完全否定“渐修”,但是这种“渐修”只能为“顿悟”创造条件,奠定基础,用竺道生的话说,只是“资彼之知”,虽不无“日进之功”,最终目标之实现,则非“顿悟”不可。因此,大乘佛教多以“顿悟”为极致,中国禅宗更直言“唯有顿悟一门,即得解脱”。大乘佛教对于达到最高境界何以要“顿悟”而不能“渐修”曾有过许多颇为深刻的论述,例如,相传为僧肇所著的《涅槃无名论》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心不体则已,体应穷微。而曰体而未尽,是所未悟也。”b这是对“渐悟”说的驳斥,意谓对于本体之体悟,不悟则已,既悟则属全体,不可能这次悟此部分,下次悟另一部分,因为本体是不可分的,或者说“理”是不可分的。对此,竺道生及后来的禅宗更有详尽的论述。 在竺道生看来,所谓佛者,即“反本称性”“得本自然”之谓,而此“本”乃无形无相、超绝言表的,故不可以形得,不可以言传,而贵在得意,因此,道生倡“象外之谈”“得意之说”;又,此本体乃一纯全之理体,是一而不二的,故体悟此本体的智慧也不容有阶级次第之分,而应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可见,竺道生的“顿悟”学说,完全是以本体之理不可分的思想为基础。 至于禅宗,更提倡“经是佛语,禅是佛意”,禅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此中之理论根据,也是把“本来是佛”之“本心本体”视为一包罗万象之整体,对此“本心本体”之证悟,只能“默契意会”“直下顿了”,故禅宗倡“以心传心”“直指便是”,反对在语言文字上讨意度。 总之,不管是竺道生还是禅宗,甚至于天台、华严各宗,尽管它们具体的思想内容不尽相同,但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由于它们都以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为依托,因此,都以“反本归极”“体证佛性”为终的,都把“回归本体”“与本体合一”作为最高的境界,而此一最高境界的实现,又都借助于“悟”,特别是“顿悟”。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儒家的修养理论和最高境界的实现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基础上的。 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是成贤作圣,或者进一步说,是“内圣外王”。而此一理想境界的实现,主要是依靠修养心性。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儒家把道之大原归诸“天”,因此,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圣贤,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知天”,体认“天道”。而要做到“知天”,儒家提出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尽心、知性,则知天”。所谓“尽心”,按《孟子》说法,也就是“存心、养心、求放心”。“存心”者,即是保存“天命”之心性的完美无缺,使“不失其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养心”“求放心”者,实际都是指清心寡欲、克除不正当之欲念。此三者说法上虽略有差异,实际上都是通过一种内省工夫去体认“天道”。 通过内省工夫去体认“天道”的修行方法,儒家“诚”的理论有更详尽的论述。《孟子》曰:“是故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中之“诚”,实是一种作为圣人本性之原的道德规范,亦即“天道”;而所谓“思诚”“诚之”“明诚”,则是一种主观内省工夫,儒家认为,通过这种主观内省工夫,人们就可以由“心”“性”上达于“天道”,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有如《中庸》所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可以说,这就是传统儒家在 修行方法上所遵循的最基本的思想路数及其所要达的最高境界,亦即通过对当下心性的内省工夫,使之一达于“天道”,进而实现“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亦即传统儒学的所谓“诚”,并不像某些人和某些著作所说的那样,本身就是圣人的一种“境界”。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也就等于说天之道即圣人之道、圣人之性,这就意味着,传统儒学的“诚”已具有本体的意义。实际上,这是后儒的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家们的思想,而不是传统儒学的思想,因为,在传统儒学那里,虽然是以“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为依托,但这种“合一”,多少带有二物合而为一的味道,亦即“天道”是源,“人道”是流,“天道”是本,“人道”是末,尽管圣贤可以通过“尽心”“思诚”达到与天道合一的境界,但“天人”并非原本是一体,只是到了宋儒,才提出了所谓“天人本无二,更不必言合”的思想。此中之关键,乃是佛教本体思维模式及其“反本归极”修行方法的影响。 确实,在宋明理学家那里,“诚”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宇宙和道德本体。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在《通书》中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此后,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既把“诚”作为“天之道”,又把“诚”作为一种人伦道德之本体,认为要成贤作圣,最根本的修养工夫,就是要“明诚”。朱熹说:“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诚。”张载也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因得天而未始遗人。”王守仁则说:“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虽然理学家与心学家在强调“自明诚”与“自诚明”上有分歧,理学家讲“自明诚”,注重“道问学”,心学家们讲“自诚明”,强调“尊德性”,但二者都把发明、洞见此道德本体作为最根本的修行方法,把“至于诚”“与本体合一”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这一点,陆王心学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所谓“发明本心”和“致良知”,实际上就是发明此道德本体并进而与此本体合一。这自然使人想起禅宗的“明心见性”。禅宗“明心见性”之旨趣无非要人悟得此“本心本体本来是佛”;而宋儒之“自诚明”也罢,“自明诚”也罢,乃至“发明本心”“致良知”等,也同样是要洞明此作为“天道”“人道”之本体的“诚”或者“本心”“良知”,字眼虽有小异,思想路数却毫无二致,都是强调“明本”“反本”“与本体合一”。 由于宋明理学也把“明本”“反本”作为一家思想之归趣,这就使得理学家在修行方法上也逐渐走上注重证悟的道路——因为对于本体的体会只能采取意会或证悟的方法。对此,朱子有“豁然贯通”之说,陆子更提倡“悟则可以立改”,以致张南轩曾评陆学多类禅扬眉瞬目之机;王守仁说得更直接和明白:“本体工夫,一悟尽透”。实际上,当理学采用了佛教的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和把“明本”“反本”作为一家思想之归趣之后,在修行方法上必定会走上注重证悟的道路。 ◆当代儒学大师、佛学大德赖永海重磅新作,一本书讲透儒佛交融的大智慧 畅销书作家、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内第一部《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全球首部完整《中国佛教通史》主编赖永海三十余年学思精粹,半生研究心得倾情分享,一本书讲透儒佛交融的大智慧。 ◆扎实有力讲学问,娓娓道来名人传,儒学与佛法的起源与奥妙,就这样在您面前徐徐展开 禅宗何以能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儒学是如何实现从“天论”到“人学”?慧能、柳宗元、朱熹、王守仁等大师是如何推陈出新,成就惊世学问?六祖为什么“革命”?在扎实有力讲学问的过程中,娓娓道来名人传,让你在轻松的阅读中,不仅可以了解历史上的名人轶事,感悟佛学与儒学的通透智慧。而且还能透过儒佛经典,勘破世间烦恼,成就圆满人生。 ◆厚积薄发,引领读者畅游“出入佛儒”之境 儒佛砥砺二千年,殊途同归在人间!儒学与佛学是中华文明中的两大支柱,也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资粮。在儒佛经史典籍中藏有温润心灵,唤醒本来智慧的巨大力量,无论你有没有儒学素养、佛学根基,阅读本书,都是一次充满喜乐和感动,受益匪浅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