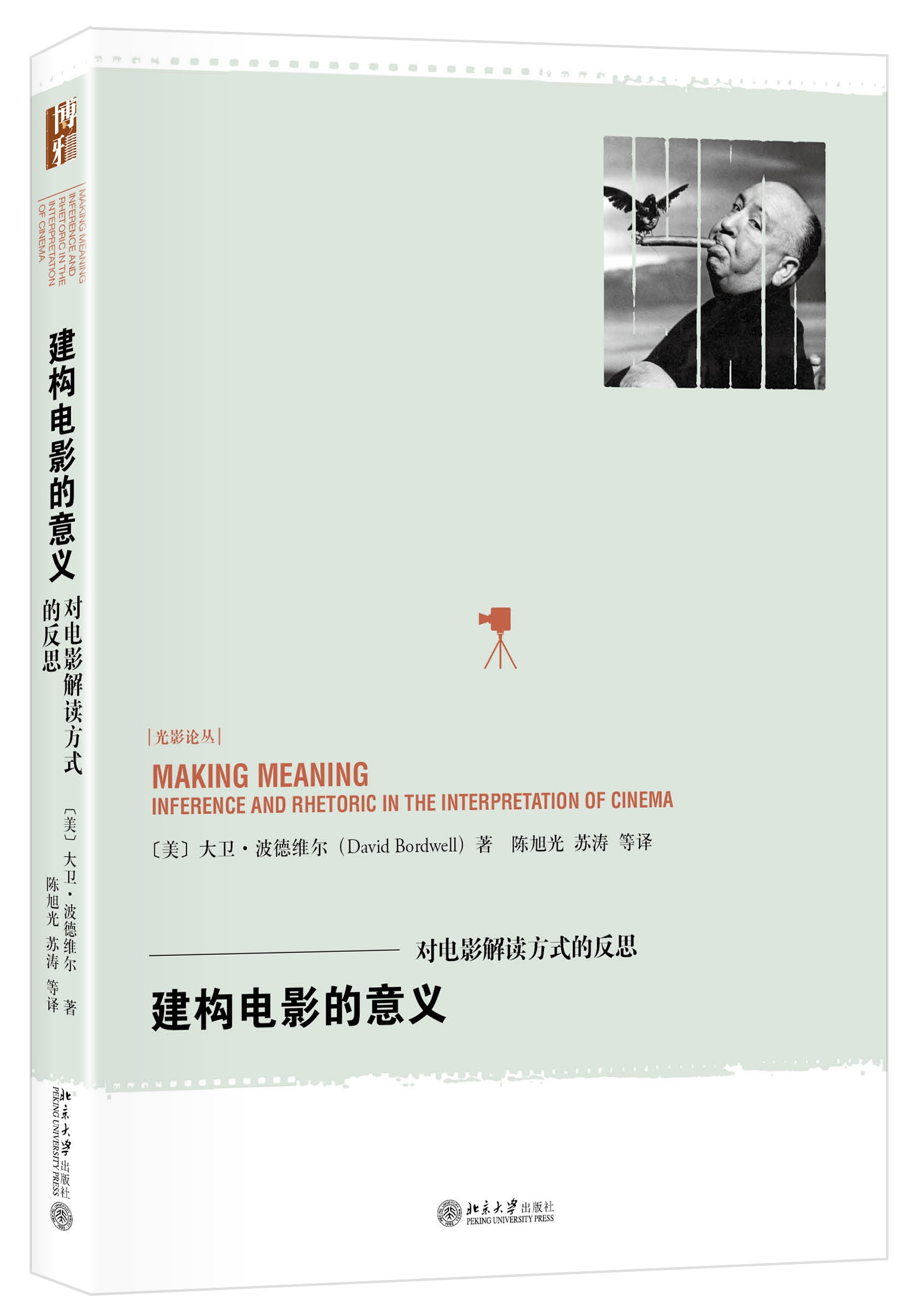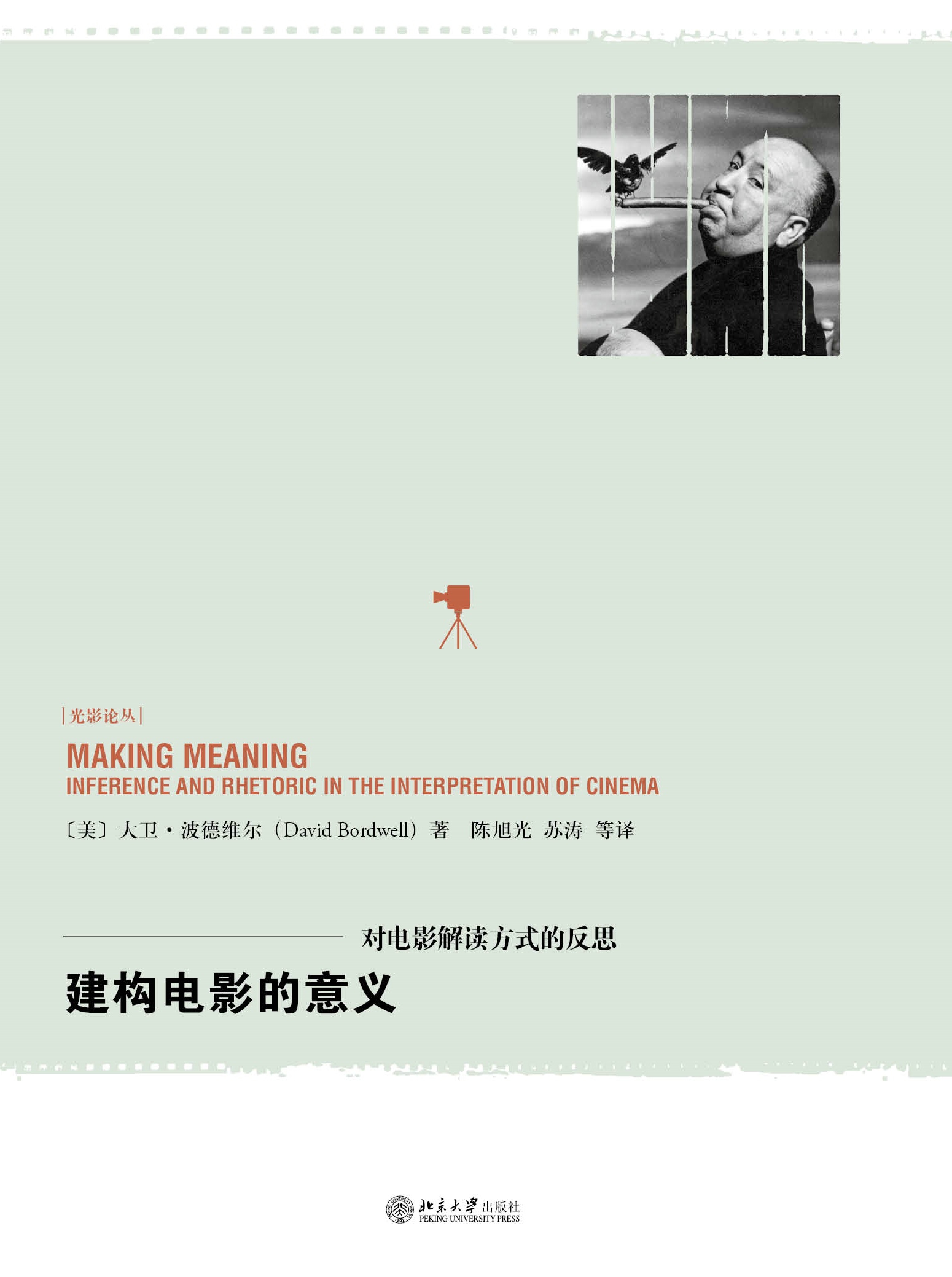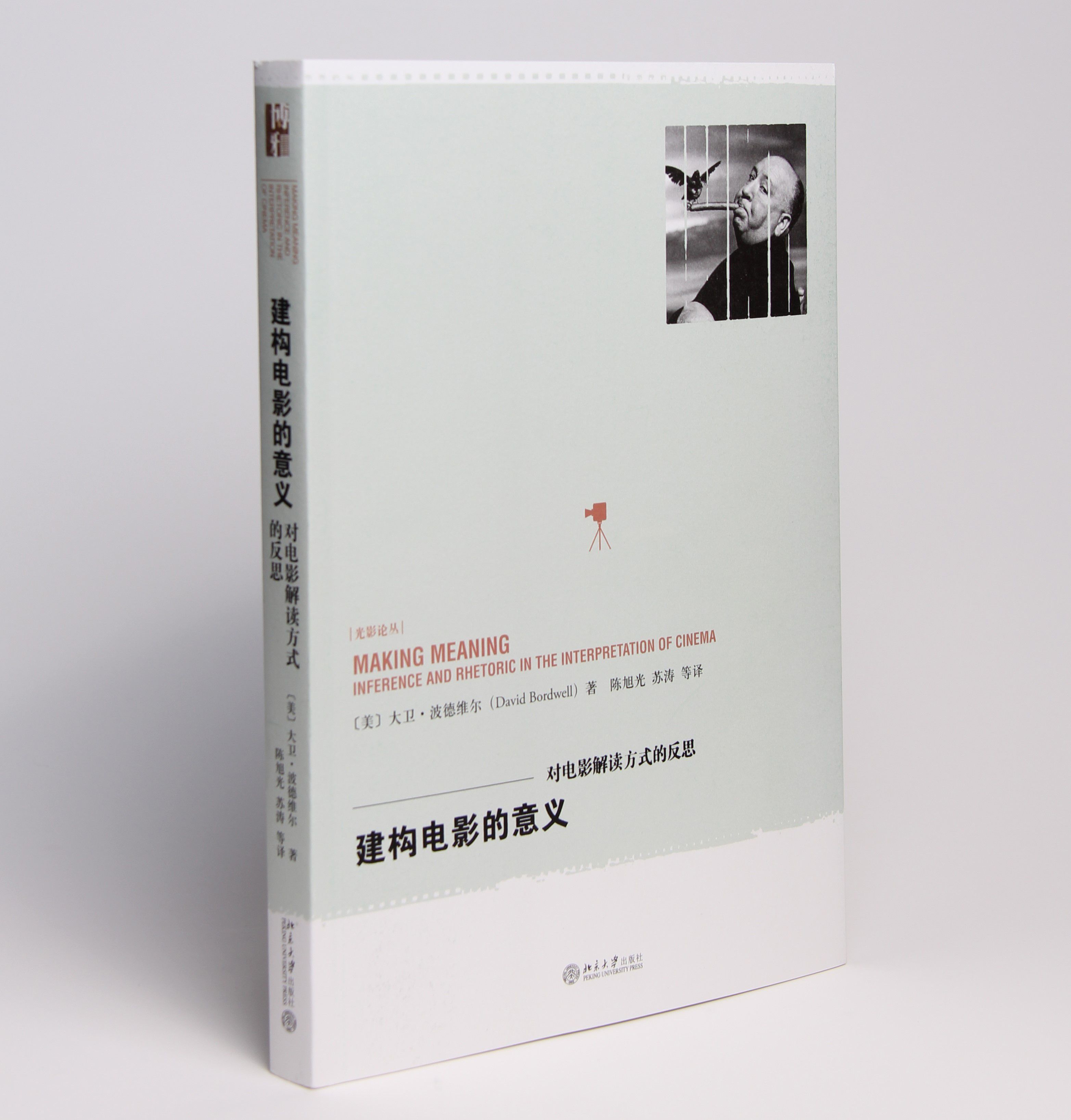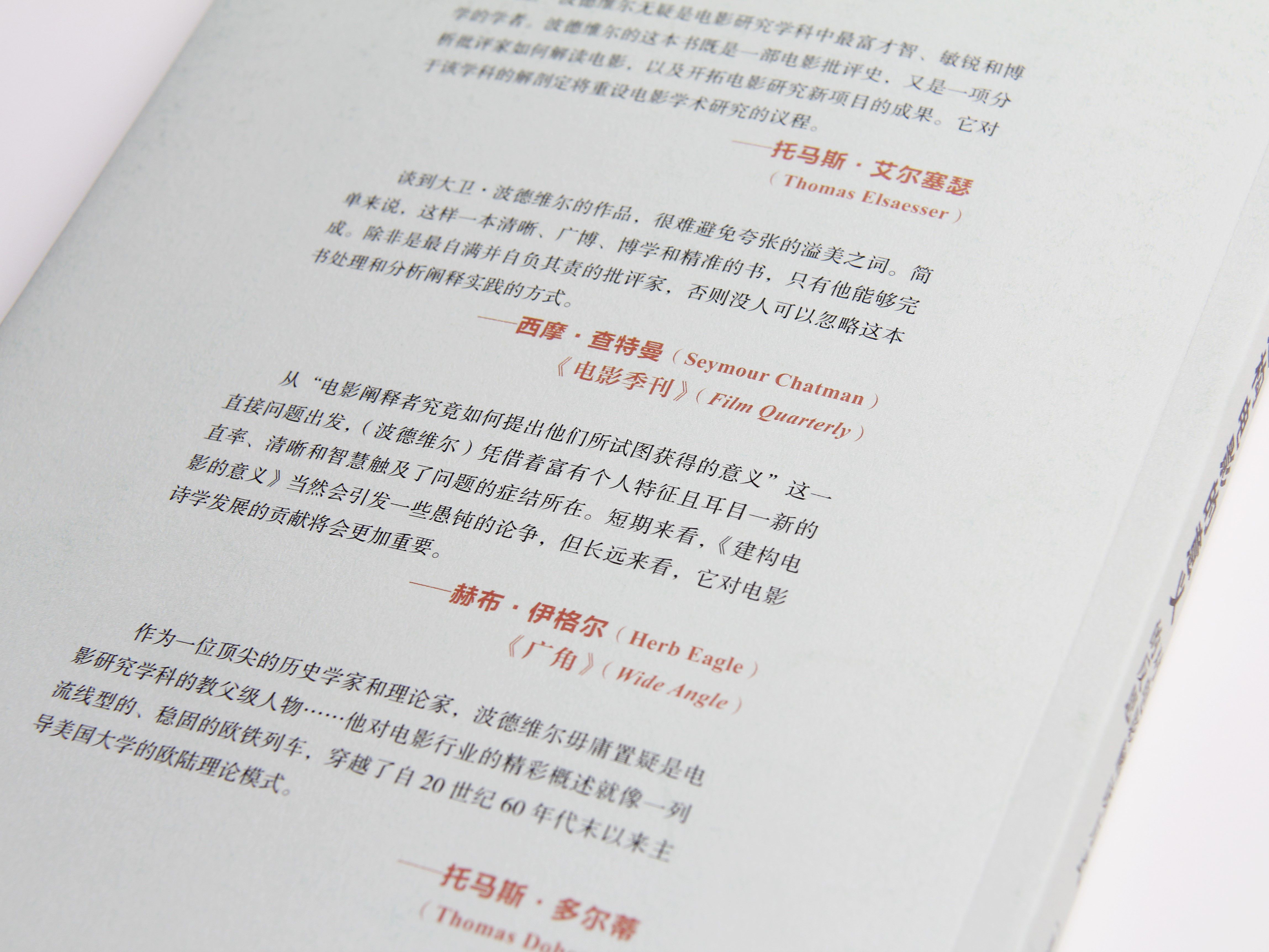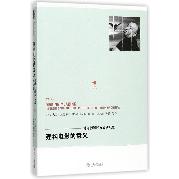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56.00
折扣价: 36.40
折扣购买: 建构电影的意义--对电影解读方式的反思
ISBN: 9787301288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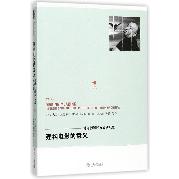
大卫?波德维尔,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电影史家,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学院电影研究雅克?勒杜(Jacques Ledoux)讲席教授,研究领域涵盖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电影史等多个方面,主要学术著作有《世界电影史》《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制造电影的意义:对电影解方式的反思》《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电影诗学》等,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第十一章 为何不要解读电影? 我已设置了很多谜题,它们将让那些专家们花上几个世纪忙于揭示我所指示的意涵,而这就是确保一个人不朽的唯一方式。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Ulysses) 阐释的末路? 阐释可以被视为西方国家仅剩的少数繁荣的行业之一。这是一项多元化事业。待售的文选和特刊因评论方法的日益增多而蓬勃发展。对于大多数学术批评而言,阐释可以说是多元论的一个缩影,多元论又正是二战后的大学们所力保的。“令人印象深刻而又多种多样的电影研究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一则宣传语如此介绍:“值得这本文选集大书特书,以示庆祝。令人陶醉的电影分析与最深远的寓意理论和历史共舞。这是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啊!” 商业在繁荣兴旺,阐释理论方面的书籍、期刊和研究生课程在迅猛增加。如同所有的行业一样,“阐释无限公司”也要做广告,像一位评论家所预示的,电影的黄金时代也将是“好阅读者”的黄金时代:“我认为导致历史唯物倾向的真正原因就是不良的阅读。” 考虑到阐释领域的大量投入,我们不禁怀疑先前的批评学派宣称能超越它的说法。结构主义学说有关“能指”(signifier)的游戏并未降低人们对抽象的、充满意义的“所指”(signified)的兴趣。1966年,在提出“一种内容条件的科学,也是形式的科学”后,罗兰?巴特承认批评“破译并参与了阐释”。 五年之后,他坦承自己在《S/Z》中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优先考虑了文本的“象征性”维度。 正如弗洛伊德以文学批评的观点看待病人的陈述,拉康也将弗洛伊德的案例研究视为文学作品。诚然,众多文学批评家或许正是由于对拉康阐释行为的熟悉(以及钟情于缺失、分裂、矛盾的主体这一不朽的箴言式说法),才被他的著作所吸引。德里达在评论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解读时,使用了常见的图式和程序,正如他用“杜平的图书馆”(Dupin’s Library)的开场描述来引出写作的问题。 类似地,一位解构主义批评家发现《比利?巴德》(Billy Budd)可基于对比的“阅读风格”来区分两个人物角色。 批评家也许坚持认为他揭示的并非意义本身,而是意义的生成过程;并非模糊性,而是模糊性之于文本的必要性;并非文本的含义,而是文本如何表达含义。尽管存在以上差异,评论家通常继续使用一般阐释的策略和手段。最近有人提议,通过将文本视为“阅读构成物”来超越阐释。于是对《金手指》(Goldfinger)片头的金色女郎的讨论就变得极度正统:“金色女郎既迷人,又是一种奖赏,如同主题曲中提到的黄金那样令人渴望获得,而最终她平躺下来,折服于邦德(Bond)的男性力量。对于邦德来说,她是一种深深的麻烦和威胁,因为在她体内蕴藏着金手指代表的去势威胁。” 类似地,我们可以改变研究的目标,选择宣传照片、电影海报、电视节目或主题乐园,并将我们的研究称为“文化研究”,而这仍然不会让程序化、合理化的阐释行业遭受任何质疑。 批评家一旦以阐释作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将这种活动投射到“普通人”或通常被称作“天真的”观众身上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如今,他们也都成了电影的“读者”,属于“阅读群体”或者某个“阅读层次”。通过回应,观众们公开地、有策略地或者是下意识地进行阐释,而专业评论家总是忽略这一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在一开始所评论的术语被广泛使用的历史来源:通过将观众的任一行为都定义成阐释,评论家为其越来越具有启发性的事业确定了修辞方面的保障。 由于阐释的规则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看起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倾向于理论的批评家可能试图将整个事态的立足点放在一些更易被察觉的基点之上。最近的几个实例是威廉姆?卡德伯里和利兰?佩格提出的比尔兹利式(Beardsleyan)美学以及达德利?安德鲁提出的利科式解释学(Ricoeurian hermeneutics)。 然而,这些构建基础的姿态倾向于忽视社会、认知和修辞的过程,尽管这些是让阐释变得与众不同的首要因素。这些作者在他们的理论和评论实践中认为本书中讨论的议题是理所当然的。美学或解释学未必能够揭示电影阐释实践的具体技巧。我在下一节中将讨论,这些技巧将通过历史诗学得到最佳的处理。 此时,阐释还远没有完结。它正开始主导批评事业。但是,这有什么好处呢?我想表明,以阐释为中心的批评的价值在于其具有多种不同的特征。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它的缺点至少是在现在已显得十分突出,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一些新的途径。 一般而言,以阐释为中心的电影批评,组织并规范了各类影评活动。阐释惯例的发展已为电影研究创建了一种传统,这或许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实质性传统。知道如何让电影富有意义是权威人士(如电影学者)操控的主要资源,而倘若没有用解释学规范建立其学术背景,以文本为中心的电影研究也就不可能进入大学,这是毋庸置疑的。 最具创新性的阐释评论的优点无需多言。将文本视作文化张力的症候式呈现的构想,引入了一种强有力的指涉性框架。宣称作者导演的作品之间具有一致性,设想电影院具有“三个视点”,以及暗示类型电影可能构成了电影本质和文化的交叉点,这些观点为影评开拓新视野提供了大量信息。许多范本都值得赞赏,因为它们已经引入了能够重新调整我们的理解的概念模式。它们已经激活了被忽视的线索,提供了新的分类,暗示了新的语义场,并扩展了我们的修辞资源。创新的指涉性框架已使得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艺术作品中值得注意和欣赏的内容。 对于一般的批评而言,应用与扩展现有的语义场、图式与启发法有何好处呢?我认为,它至少起两种作用。一种是驯化(domestication),即对新事物的驯服;当一位批评家发现某部最新的电影文本具有矛盾性对立因素时,他就可以将该电影拉入已知的领域中。驯化能将不熟悉的要归入熟悉的要素里。虽然先锋派们可能会蔑视这种角度的阐释,但这保留了它必要的功能。无法被图式化分析的电影就是无法阐释的电影。 一般批评的第二种作用是异化(differentiation),为已知者重新塑形。为了说明现有的概念模式可以适用于新的实例,评论家常常不得不较之前更准确地区别那些概念模式的方方面面。此外,批评家能从熟悉的语义场中发现新的关系,如同贝洛在《精神病患者》中的发现:女性气质与神经衰弱联系在一起,而男子气概又与精神病相关联。驯化和异化可以重新确认现有的惯例,但它们是通过证明其范围、力量与微妙之处来实现的。 如果科学旨在解释外部现象背后的动作过程,那么阐释基本上无法产生科学知识。具有因果关系或功能性的阐释都不是电影阐释的目标。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文本的知识并非阐释事业最显著的成果。阐释最伟大的成就也许就是激励我们对概念模型作出回应,尽管方式略显迂回。通过驯化新事物和提炼旧知,阐释学派重新激活并修正了理解的一般结构。阐释将我们的感知、认知和情感过程作为基本的主题,但是它采用的是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将其“产出”归因于“外在的”文本。以阐释的方式了解一部电影,就是将其归入我们的概念模式中,从而更充分地掌握它,这通常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的。 我们可以对概念模型如何控制电影批评作进一步的说明。虽然批评家们通常对自身的图式和推理惯例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很希望非正式地探索和比较语义场。阐释者常常认为纯粹的哲学抽象概念和严格的“科学”分析无法捕捉到大脑所能考虑的含义间微妙的相互影响。电影就像小说、戏剧和绘画,成为了展示语义内涵的动态场合。阐释《精神病患者》的批评家并没有证明精神常态和非常态存在于一个连续统一体上,或者男性的凝视是精神受压抑的症状,电影也没有证明更多的内容。批评家和他的读者们都默认此类观念,如虚构的可能性、电影暗示的有趣的语义场并置,以及有效的批评实践。 这种并置可以控制读者的注意力。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常常希望探索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潜在意义。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提到的,语义场与一般人的关注点相关。通过表明不提供明确行为指导的艺术作品能增加思想、感觉和行为方面的重要议题,阐释解答了很多人感兴趣的动机、意向和伦理责任方面的问题。如果批评性阐释产生的不是知识,而是“理解”(Verstehen),那么,或许这是一些批评家认为阐释可以用来检验一种理论的另一原因。而电影也成为了批评家们探索一种理论的语义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场所。 阐释具有的价值也许会被它的缺点和滥用所抵消。我想这就是目前的问题。但是需要赶紧补充一点的是,我并非在暗示阐释会慢慢停滞。结束文学阐释的呼吁至少能够追溯到欧文?豪(Irving Howe)的《这个顺从的时代》(“This Age of Conformit”,1954),并经历了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1964)、杰弗里?哈特曼的《超越形式主义》(“Beyond Formalism”,1966)与乔纳森?卡勒的《超越阐释》(1976)。这些呼吁几乎已经完全被忽视,甚至,它们现在成为阐释机制仪式的一部分。完全抛弃阐释实际上很可能不会影响任何读者,倒是可能被当作推销个人阐释的修辞策略的一种伎俩,而遭人鄙弃。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将要提出的各种原因,忽视隐含或症候性意义的批评家无法全面地对艺术作品的结构或效果做出阐释。不可否认,作为批评家,我发现许多阐释惯例是牵强且没有成效的。双关语启发法通常过分依赖于原子论的局部效应,而对对组和对立系列的强调则经常封闭了电影里意义的范围。对于我而言,将电影院和叙述者人格化都是画蛇添足。虽然这种技巧目前被批评界所认可,但是我会在恰当的时机表明,它们应减少被使用的次数。不过,阐释仍然是批评的重要部分,若将所有的惯例都摒弃,将使得电影研究彻底枯竭。一些图式和启发法—人物角色的人格化、分级语义场的使用,以及对分类模式的偏好—捕捉到了电影的一些重要之处,部分原因是它们符合所有批评学派成员共有的理解观念。在此,我只想指出,如果我们太依赖于这种思考和交谈方式,将解读当作教学和批评写作的基础,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正如许多广为采用的做法,阐释的假设已非常传统。这一点并未被我们当今最具有实验性的批评家充分意识到。看到同时代的诠释者拥抱形式/内容的差异,或解释作品的象征域具有“丰富性、密集型和广阔度” 特点,会让人回想起解析式和症候性批评的假定前提,这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悠久。虽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认为符号是具有内在意义的,但基督教已具有很强的解释学宗教信仰,并寻求福音传道—一种等待被召唤的潜在感觉。 这种传统导致了苏珊?桑塔格所称的“对外形的公然蔑视”(an overt contempt for appearances)。 四十年前,埃利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指出,图像诠释者倾向于将文本的感觉本质裹进抽象的蚕茧里: 上帝在亚当睡着的时候抽出他的一根肋骨,从而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一名士兵穿刺了耶稣的身体一侧,血和水流了出来,同样,这也是十分具有戏剧性的。但是这两件事情在教义上被联系在一起时,亚当的沉睡被解释为耶稣长眠的另一面;亚当身侧的伤痕诞生了人类在肉体上的原始母亲夏娃,同样,耶稣身侧的伤痕诞生了人类精神上的母亲,即教堂(血和水就是神圣的象征)—在隐喻意义的力量形成之前,这些感官的事件都是苍白无力的。 总的来说,相同的趋势也已在电影阐释的历史上表现了出来。 我并不是在老生常谈地抱怨阐释使作品贫乏。标准的反驳是:每一种推理行为都降低了作品的水平,因为如果没有一些观念模式作为中介,我们便无法了解作品。目前为止,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一些观念模式比其他的观念模式更微妙和全面。人们认为文本的特殊性只能通过某种概念的指涉性框架来了解,这是一回事;而坚持认为所有这类框架在力量和精确度上都是对等的,则是另外一回事。许多当前的阐释模式,如有序和紊乱之类的语义对组,或象征和想象,都是十分粗糙的。 诚然,阐释并不一定非得如此粗糙。如果评论家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推测将文本作为比较和探索语义场的一种方式,他也许会对线索的差异比较敏感,以便找出不同语义场的细微差别。在我看来,这种灵活性存在于非常不错的阐释评论中,如泰勒的书籍、巴赞分析威尔斯和雷诺阿的文章以及我已研究的早期关于《精神病患者》的评论。但是随着学术批评的发展,它已装配起一整套全功能的启发法,在电影的标准连接点上切入,并挖掘出可以归入标准库的例子。对语义场的探索只不过激发起一些一成不变的指涉点而已。矛盾对立文本模型(contradictory-text model)曾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新奇性,但是其压抑和被压抑因素之间完全鲜明的对立、对直觉的依赖和标准的散漫以及自圆其说式的剧情说明等缺点已变得十分明显。 这并不是说,对当代批评家而言,任何东西都有意义可寻。实际上,一堆东西所含有的意义可能只有几个。本书的主旨之一是告诉读者,任何阐释行为的结论可能有无限多种,但文本线索、排列和组织这些线索的过程以及分配给它们的语义特征都是非常有限的。总的来说,限制不一定合乎逻辑,却由来已久。阐释是否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应用方式呢?它是否激活了电影中被忽视的部分呢?它是否有助于“最新的发展”呢?这些都是习惯性实践和主导性修辞的限制因素。引用托多洛夫的话,基于阐释将朝电影应该有的意义方向进行推理分析,电影阐释几乎已变得完全“终极目的化”(finalistic)。“对隐含意义的预知主导着电影阐释的方向。” 现在电影中的许多细微之处未被注意,是因为这些细节根本没有进入到预设的阐释视野之内。 更具体的原因是,在近期的电影研究中,阐释者几乎都没有注意到形式和风格(其中,它们遵循弗洛伊德、列维-施特劳斯、拉康和其他“终极目的论”的理论家们有影响力的实例)。电影叙事形式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研究后,电影阐释者依旧继续依赖着非常简单的模式:价值的转换,压抑力量的出现、消亡或持续。同心圆模型(用场景或摄影机的移动来说明剧中人物关系的互动)是理解电影风格的一种粗糙的做法。对于旧的新批评和新的旧批评而言,风格主要是表达意义的一种手段:一扇可以被评论家用于观看体现着语义场的人物角色的窗口,或某个转变的时刻—刻意的摄影机运动、突兀的剪辑点—可以依次被“阅读”。“经典”体系中的连续性表演、摄影与剪辑被视为中立的基础,有时则会被认为具有潜在的象征性(例如,将视线的交集解读为饱含鼓励的眼光),以便让真正重要的意义在对话和行为中产生。电影风格如同19世纪情节剧中的音乐:总是次要而含糊的,只有在衬托其他领域的重点时,它才显得有价值。在当代电影阐释中,风格如果不是自动生发的,就是充当了激发联想的元素。 很明显,理解电影媒介的大多数基本概念并未产生于当代的阐释项目中。阿恩海姆(Arnheim)、库里肖夫(Kuleshov)、爱森斯坦、巴赞、伯奇和另一些人定义了所有批评家仍然采用的电影风格与结构的参数。或许大部分阐释者都认为,形式和风格在如今都得到了很好的理解。这就是让“阅读”滚动前进的有效虚构。电影阐释大量吸收古典美学的内容,却无力回馈分毫。 总的来说,以阐释为中心的当代批评倾向于保守和粗糙,并不重视电影的形式和风格。它大量借鉴其他美学范畴的内容,却不能创造出新的美学范畴。其理论和实践大体而言不会引发争议,也不会带来多少启发。不仅如此,电影阐释还变得令人厌烦。 巴特常常坦白地说他对一般舆论、大众文学和电影中的迂腐的意指感到厌恶。 我们对那些支配文学及学术性电影阐释的可预测的活动行为感到沮丧。对我而言,很可能巴赞、泰勒和戴明、《电影手册》《正片》以及《电影》派的批评将会存留很长一段时间。但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在很多方面十分丰富的电影理论引进了一种批评模式,这种模式在过去十年却变得异常贫乏。我们不需要对血淋淋的恐怖片中的颠覆性时刻进行更多的分析,也不必再对批判主流电影的“理论化”(theoretical)电影大加颂扬,或将最新的艺术电影视为对电影本身及其主体性的沉思之作。回顾往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过翻新的症候式解读恰似独创性的最终喘息。从那时起,我们已经没有了范本,我们生活在一个批评日益平庸的时代,理论也逐渐萎靡。 或许批评家都不顾一切地转向电视、大众传媒和其他文化产品,似乎“阐释公司”的重复性可以通过新的文本再次粉墨登场。 在寻求新颖的过程中,一些批评家求助于拉斯维加斯喜剧的学术对等物:扮鬼脸式的玩笑(依赖大量的斜线、破折号、断句式括号、模糊的引文和造作的双关语)。但是,表面的风光没法掩盖这一事业的空洞。得到学术认可使电影阐释成为一门新学派,建立了一套规则(好莱坞和一些受尊敬的反好莱坞作品)、被接受的事实(理论)、高度规范化的阐释活动以及一些有保障的思想观点。所有这些特征基于对权威的借助。米歇尔?查尔斯曾评论道:“学派是一种思考和表达的模式,其中,所有的认知必须由文本确定,无论它多么不固定或易变;在这个智识领域,对知识加以更新必须经历对文本的重新阅读;在这种体系下,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文本,必定无法产生新的东西(当然包括对权威文本的再阅读)。”没有什么比他的评论更好地描述了当代学术性的电影批评活动。 与文学研究相比,电影研究或许更加狭窄。至少,在若干年前,前者不得不对作者、时代或类型方面作一些经验式的了解。新批评反对学院派的实证主义,不过,电影批评没有可替换的历史性学派传统。高中和大学所教的本质性阐释和“文本细读”很快成为电影研究的主流方法。如今,大多数批评文章隐含的命题知识都涉及一些理论信念和对手边的电影中某些内在特征的描述。这就是“应用”的意义所在,与中世纪的经文诠释相去不远。如此墨守成规的解读或许将成为电影研究走上穷途末路的首要“功臣”。 结构主义和矛盾文本的概念都具有创新的潜力。它们本来可以引发生动而又具有质疑精神的辩论。但是,它们已经融入实用的批评当中,其主张的理论范畴从未与它们有任何关联。这种评论将电影一部部压入相同的模式中,从不怀疑自身做法的正确性。事实上,评论家们可能仍然在享受这一事业,不过这并不能支撑他们继续走下去。毕竟,在1975年,劳拉?穆尔维写道,她的理论力图将娱乐消遣从电影观看中驱逐出去。或许,现在是时候干件更具争议性的事情了:将娱乐从电影阐释中驱逐出去吧! 电影研究教父级人物大卫?波德维尔一部关于电影阐释与批评的著作。 1.电影研究教父级人物大卫?波德维尔唯一一部关于电影阐释与批评的著作 2.视野开阔,脉络清晰而又十分严谨的高品质学术著作 3.西摩?查特曼等多位电影学者强力推荐 4.影视专业学生必备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