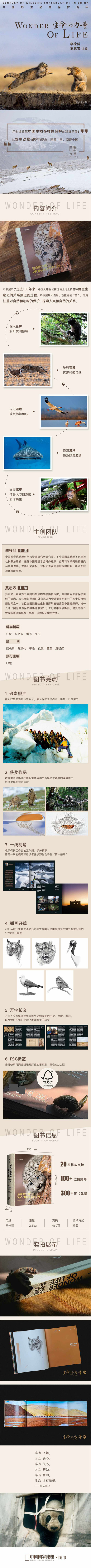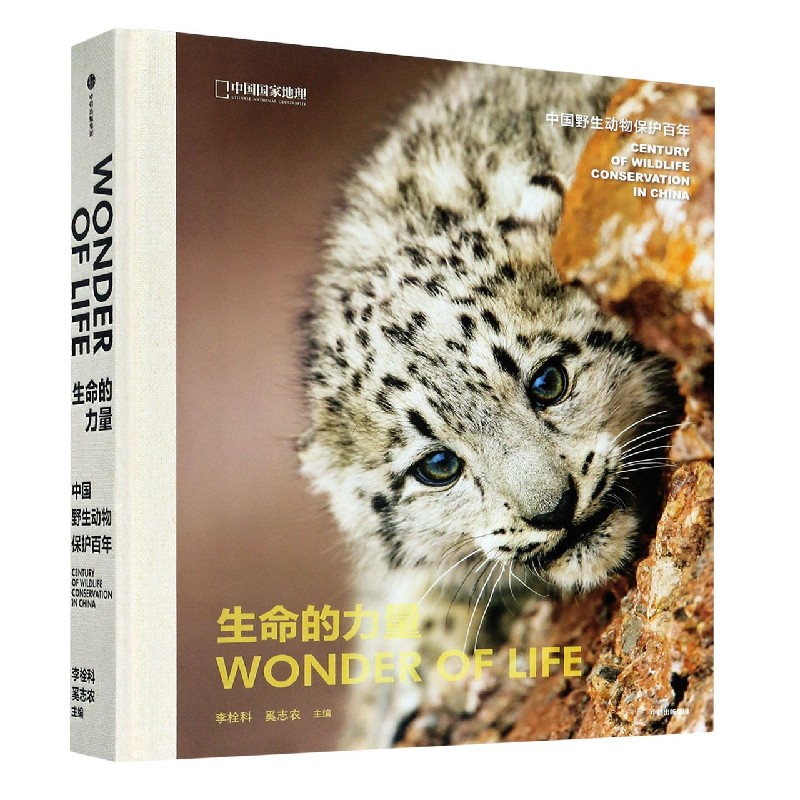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268.00
折扣价: 190.28
折扣购买: 生命的力量(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百年)(精)
ISBN: 9787521719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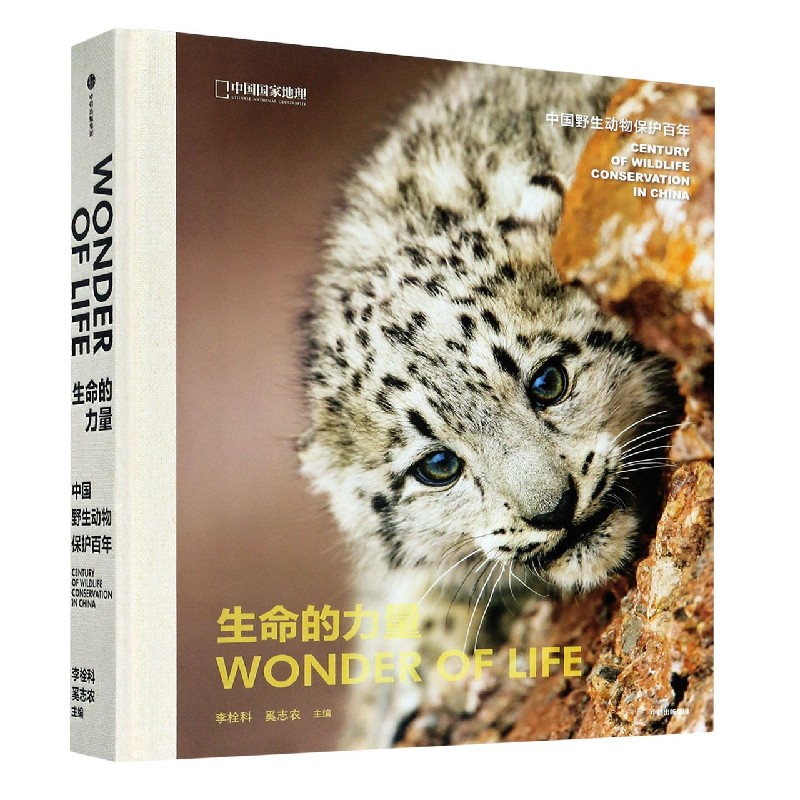
李栓科,男,1964年生于甘肃省平凉,汉族,党员,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曾任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曾长期从事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地区的地貌、第四纪地质环境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90—1993年三次进入南极,并在南极越冬,1995年任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知名野生动物摄影师,野性中国创始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野生动物的拍摄和保护,曾多次为滇金丝猴、藏羚羊、绿孔雀等濒危物种的保护发声,并创办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培养培养中国本土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实践着用影像保护自然的信念。2010年被英国户外杂志评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四十位自然摄影师之一,在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获奖,入选“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iLCP)。2019年1月,受邀担任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自然与环境组的评委。
呵护生命的力量 ◎ 邸皓 生命的力量并非格外强大,当野生动物面对来自人类的持续重压——大肆猎捕、破坏它们的家园时,生态系统难免会濒临崩溃。白暨豚、华南虎的悲剧提醒着我们,贪婪、无视自然法则的人类活动可能会对野生动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进而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带来威胁。生命的力量又是极具韧性的,当人们阻隔威胁、用心呵护,寻找共存之道时,生命便能欣欣向荣。有效遏制捕杀,实施栖息地的保护,大熊猫、朱鹮、海南长臂猿等生灵便从灭绝的边缘被拯救回来。伤害、利用,抑或保护,人类的行为造就了野生动物今天的生存现状;而它们未来的生存与灭亡,也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与行动。 人类对野生动物和自然界的影响如此之大,2019年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以此体现人类对地球做出的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扩张,也伴随着野生动物的退却和消亡。2019年5月6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正式发布了由近150位国际专家联合撰写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这份报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全面评估了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自然世界所面临的严峻现状,根据报告评估,大约有100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威胁,其中许多可能在数十年之内趋向灭绝;人类对陆地和海洋利用方式的改变、捕猎和捕捞等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正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 中国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幅员辽阔的国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赖以为生的家园——海南岛云蒸霞蔚的热带雨林中,长臂猿的长啸在清晨回荡;吉林白雪覆盖的林间,东北虎匿踪潜行;寒风凛冽的可可西里高海拔荒原上,成群的藏羚羊奋蹄奔腾;南海温暖的碧波中,中华白海豚逐浪前行;黄海的滩涂为数以百万计的迁徙候鸟提供补给;川陕甘的山林给了大熊猫最后的庇护…… 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中,人与这片土地上的生灵有着长久的互动,它们早已在中华文化中刻下深深的印记。它们在诗词歌赋中被颂咏,从《诗经》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到汉高祖的“鸿鹄高飞,一举千里”,从《水经注》中“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到辛稼轩的“看天阔鸢飞,渊静鱼跃”;它们的形象装点着人们的生活:幼童穿戴的虎鞋虎帽,恭贺新人喜结连理的鸳鸯锦被,老人寿宴上的松鹤延年图。它们逐渐凝结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仙鹤、猛虎、雄鹰,狐仙、白蛇还有猴王。 先秦至民国:天人合一与近代博物学的传入 自先秦时代起, “ 天人合一” “ 好生恶杀”“万物有灵”等理念就已在中华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设立了对国家自然资源的管理机构,对狩猎等直接影响野生动物的活动有所约束。始自清末的西学东渐使近现代科学、博物学理念进入中国,与传统文化冲撞、融合,重新构建着中国人对野生动物的认知体系。 中国古代产生了许多和野生动物保护相契合的思想。爱护生命是最基础的理念,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荀子》中则引述孔子的话:“古之王者……其政好生而恶杀焉。”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道教都倡导不杀生,不害生。“天人合一”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中国文化中最高的精神追求之一,传统哲学把人伦和天道视为天然同一,通过顺应天道实现人伦。这种追求反映在“顺应天时”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顺从。被儒家奉为行为规范的《礼记》,就明确提出狩猎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不宜过度。 历代君王也颁布了不少护生禁猎的诏旨,如北宋的《禁采捕诏》(公元961年)和《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公元978年)。许多朝代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对野生动物的管理也包含其中。在传说中舜的时代,当时负责管理的人员称为“虞”。此外各朝也设立了供帝王贵族狩猎的苑囿,如著名的上林苑。这些封禁的自然区域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野生动物栖息地。除官方的封禁山泽、法律政令之外,佛教和道教的庙观山林、民间的风水林,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神山圣湖,在客观上都保存了野生动物重要的栖息地。随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农田的开垦和薪柴的消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整体上仍呈缩小的趋势。古代朴素的保护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保护理念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的保护措施也远没有形成稳定的体系。 时间推移至近代,随着科学、博物学兴起,西方的探险家开始在全球搜集、记录动植物,神秘的东方国度自然也吸引了他们的目光。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锁的大门被打开,大量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动植物猎人、商人以及学者带着极大地热忱进入中国进行博物学考察和探险。其中较著名的如英国人罗伯特·斯温侯(Robert Swinhoe),他1854年初到中国,担任领事馆的翻译,但很快就被任命为副领事。随后又先后在厦门、宁波、烟台、上海以及台 湾任领事。斯温侯痴迷于鸟类,几乎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研究和收集鸟类标本上。1863年斯温侯在《伦敦动物学刊》上发表了《中国鸟类名录》,列有454种鸟。俄国军官普热瓦尔斯基于1870—1885年先后在新疆、青海、西藏等地考察,为沙俄攫取资源搜集资料。普热瓦尔斯基在考察期间捕获了大量动物标本,运回沙俄后,俄国科学家将一些物种以普热瓦尔斯基的名字命名,包括普氏野马、普氏原羚等。 这些发现者中最有名的当属来自法国的天主教神父谭卫道(阿尔芒·大卫,Jean Pierre Armand David)。在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三次深入中国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与活体。他是最早发现并描述大熊猫、金丝猴、麋鹿、珙桐等物种的西方人,这些发现轰动了整个欧洲社会。 这些考察和标本采集活动事实上并没有直接贡献于当时的野生动物保护,甚至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资源掠夺性质;另一方面,这些发现也确实增进了人们对中国野生动物的了解,同时也将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博物学带入中国,为中国对野生动物的认知带来全新的角度。 20世纪初,中国本土生物学家、动物学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为中国的动物学研究和随之而来的保护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1920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秉志先生归国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改为东南大学,后又改为中央大学),并在此建立了中国大学中第一个生物系。1922年8月,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在南京成立了,从1922年到1937年,研究所对我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采集的标本总数达12万份左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积累了宝贵的资料。1928年10月1日我国第二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筹建该所是因南京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感到无力顾及北方动植物的研究,建议北平也应建立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工作重点是北方动植物调查,包括华北、东北、渤海等地区的动植物资源调查、采集及分类学研究。除南北二所外,尚有其他研究人员在开展考察研究工作,如著名鸟类学家郑作新先生,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福建等地进行考察,最终在1947年底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鸟类名录》,是当时最全面的中国鸟类资料。 1934年8月23日,以秉志为首的30名著名动物学家在庐山莲花谷组织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并举行了第一届年会,会议还决定创办《中国动物学杂志》,推动了我国动物学研究的进展。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及其他动物学家、生物学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生物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研究人员。这些工作为日后新中国的动物学研究及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掠夺,加上战乱等原因,民国时期中国的自然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以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森林为例,1934年全国森林面积仅有9109万公顷,而在鸦片战争时尚有15900万公顷。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曾尝试通过制定法律等方式对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和管理:1914年北洋政府曾颁布《狩猎法》,又在1921年公布《狩猎法施行细则》,明确提出“各地方官厅,应将该地保护鸟兽之种类,分别列表,各按程序,转报农商部备案,并于各该地面,发禁捕之布告”。同样在1914年由北洋政府颁布的《森林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森林法,北洋政府还制定了适量限量采伐森林的措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森林法》进行了两次修订完善,在鼓励植树造林的同时还设置了专门的森林警察。由于军阀割据、战事频繁、社会动荡、财政拮据等,民国时期的保护整体效果都不太显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全国森林面积仅有828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仅为8.6%。 1949 年以后:野生动物保护起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工业农业基础薄弱,对野生动物的猎捕成为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一种方式,森林砍伐、工农业用地的扩张也在压缩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相对具有计划性的开发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国家较早地建立了第一批自然保护区,并明确发布指示要求保护野生动物,但整体保护工作并未形成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实“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便被提出: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明令珍贵稀有的野生动物需要保护,不得任意猎杀。但野生动物仍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中国人摆脱了百年的贫弱和屈辱,全国上下都充满了奋发强国的建设热情,而危机四伏的国际政治环境也逼着新生政权分秒必争地迅速强大起来。经过战争蹂躏的国家满目疮痍,工业和农业基础都极为薄弱,1949年全国生铁产量只有24.6万吨,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农业方面,粮食产量只有2260亿斤,棉花产量只有880多万担。这样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对野生动物的猎捕也成为一项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方式——捕猎获取的肉食、毛皮,以及鹿茸、麝香等其他野生动物制品,既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够换取外汇。野生动物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来自直接猎捕,还有生存空间的压缩:木材是比野生动物更为重要的自然资源,而大规模砍伐势必会使那些以森林为家的动物流离失所,经济发展伴随着农田、工业和建设用地的扩张,也会吞噬野生动物原有的栖息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开发活动逐步被纳入国家的管理和组织之下: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林垦部主管农业发展和林业资源开发,1951年改组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之后设立了狩猎处管理野生动物狩猎事宜(1956年,还设立了专事森林采伐的森林工业部,两年后并入林业部)。1956年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则主要负责水生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这种由林业和水产(农业)部门分别管理陆生野生动物和水生野生动物的设置一直得到延续。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方面国家明确了对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主要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同时也建立起自然资源开发的组织架构,农(渔)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国营农场、牧场、林场作为主要的基层生产单位,根据生产计划进行猎捕和开发利用。50年代中期开始,野生动物制品由供销社、土特产商店进行统一购买和销售(“统购统销”),野生动物的捕猎和销售大体上是在政府的组织和管理下进行的。这样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显然为国家对这项工作进行管理提供了便利。 20世纪中后期,对于包括野生动物、林业木材在内的自然资源开发,国家提出了“永续利用”的管理理念,即在开发时要保证资源的持续再生,避免过度开发;然而这一理念在实际工作中并未能全面贯彻,特别是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了较大的波折,其中的影响因素众多——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对资源总体和开发状况有准确判断,仍在逐渐建设中的组织管理体系在控制计划实施中也有巨大困难。强度过高的捕猎给许多野生动物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水獭等毛皮动物是捕猎的重点对象,1950—1970年,全国收购野生动物毛皮达28900万张。1955年仅湖北一省就有超过1.4万只水獭被捕杀,毗邻的湖南省收购水獭皮最多的一年则高达25733张。这样高强度的捕杀,加之栖息地丧失等原因,使得水獭在许多曾经的分布区内消失,即使尚有水獭生活的区域,数量也大幅下降:20世纪50年代初期,广东省(含海南岛)一年收购的水獭皮就数以万计,而到1981年收购数量已锐减至不到400张;在东北地区,2000—2010年的水獭记录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92%。 另一些动物则作为肉食来源被大量猎取,蒙原羚便是一个代表。蒙原羚又称蒙古瞪羚,一般也被称为“黄羊”(实际上黄羊是几种体色偏黄的草原有蹄动物的统称,除蒙原羚外,鹅喉羚、藏原羚甚至普氏原羚在其生活区域内也被人称作黄羊),分布于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等地。20世纪 50年代初,蒙原羚仍广泛分布在我国东部草原和西部荒漠草原地区,估计有50万至60万只,其集群迁徙的盛况比之于今天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马迁徙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蒙原羚作为肉食供给遭到了大规模的猎杀。据参加过捕猎的人回忆,当时人们开着大卡车,带着军用步*,在草原上追逐成群的蒙原羚。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黄羊肉”帮助一些区域的民众挨过了饥荒的威胁,黄羊肉出口也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外贸收入。由于中蒙边境上的围栏阻断了蒙原羚的迁徙路线,以及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高强度猎杀,截至20世纪末,我国境内蒙原羚的数量锐减至仅存约8000只,活动范围仅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草原。 科研、教育机构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建设和调整,开展了一系列野生动物调查、研究,极大地增进了对野生动物情况的了解。中国 科学院于1949年组建,并接收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等民国时期建立的研究单位;经过机构整合,1950年成立了中国 科学院昆虫研究室(后发展为昆虫研究所)和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后发展为动物研究所)。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进行了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这次调整整合了高校中的相关学科资源架构,并成立了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学院(今东北林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专门院校,成为之后野生动物研究的重要力量。 梳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百年历程,介绍不同栖息地中代表性物种的经典保护案例,挖掘保护故事背后的科学与人性……影像直击人心,将自然的灵魂与人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