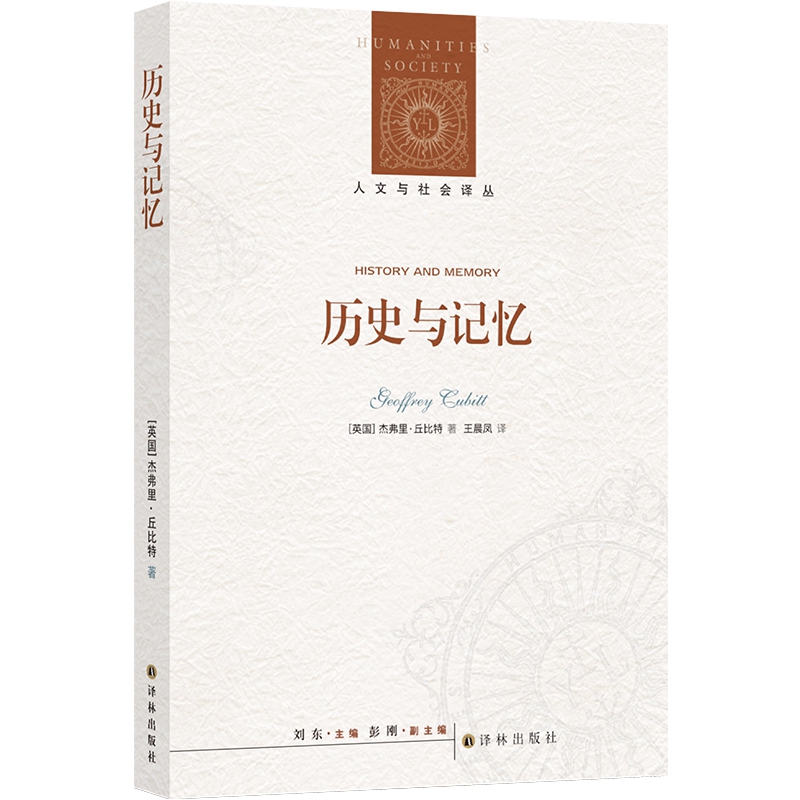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9.00
折扣购买: 人文与社会译丛:历史与记忆
ISBN: 97875447847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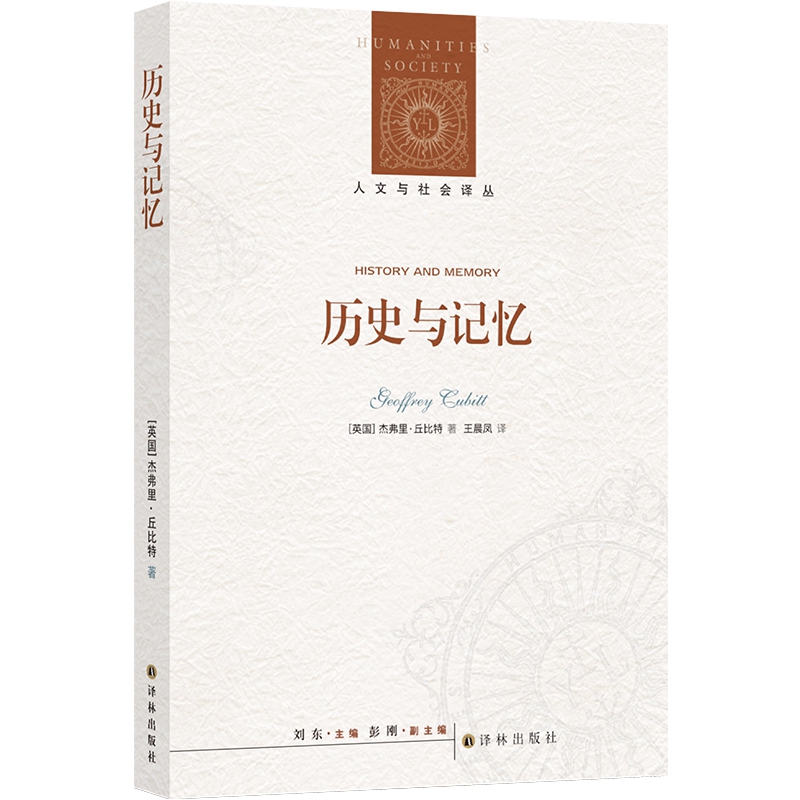
杰弗里·丘比特 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reader),同时任职于约克大学18世纪研究中心和公共史学研究中心。研究兴趣包括19世纪法国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化史,社会记忆诸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表现。
第一章历史与记忆:一种想象的关系 对于安娜·康姆内那(以及其他与她类似的历史学家)来说,是时间造成了遗忘;历史书写却有选择地但也相当明确地预先阻止了它。而当现代历史学家探索其学科在纪念方面的潜力时,他们不认为时间具有显著的作用,也不认为历史书写的职能有那么明确。他们没有将集体的遗忘视作时间将任何没有稳固在书写中(或其他纪念设施,例如纪念雕塑中)的内容扫除出意识的结果,而是至少部分地将其视为政治选择、权力差异、文化倾向的结果。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历史不是自动保存记忆的机制,而是这样一个学科,它所采用的方法和步骤不仅有助于获得记忆,也同样会带来遗忘。他们强调,任何历史叙事都是基于选择的——在保留下一些事情的同时,也在抑制其他的事情;在关注一些群体的发展或利益的同时,也在暗地里(如果不是在明面上的话)排挤另一些看待问题的视角,或将它们边缘化;在宣扬一类记忆的同时,也在阻断另一些回忆的方式。因此,他们在历史中看见的,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工具——一个潜在的解放和启蒙工具,而同时也能用于压迫和控制。简单来说,当现在的历史学家们致力于保存或拯救那些特定的事迹、族群、观点或经历,使其免于遗忘之时,他们会考虑到某种由意识形态建构的遗忘,而在建构这一遗忘时,其他派别的历史书写或许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通常来说,拯救记忆的行为是具有历史编纂学的特点的——它带有历史修正主义或反修正主义的成分。保存关于大屠杀的记忆不仅意味着将其固定在书写中,使其在亲身见证或经历了大屠杀的那代人去世后仍能继续存在,更意味着将其作为记忆的对象来捍卫,抵御大屠杀的否认者所培养起来的对历史的恶意理解。对于口述史家来说,他们的任务不仅是通过搜集和分析口述证词来恢复与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消失的记忆之间的联系,更是揭示出这些记忆——例如工人、女性或受压迫的族群的记忆——是如何被惯常的历史书写中的策略和倾向性所排斥和边缘化的。 下面这个例子或许有助于更充分地说明,关于记住与遗忘的语言是如何表达对这些问题的关切的。根据作者张纯如自己的说法,她的《南京da屠杀》一书即以记忆对记忆的否认为内核。张纯如自己对于1937年日军南京暴行的最初认识来源于关于中日战争的家族记忆,这份记忆是由她的父母——从中国来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传给她的。在海外离散华人(Chinese diaspora)之中重新浮现的记忆,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增强了她作为历史学家对于南京事件的兴趣。她写作一本以该事件为主题的书的最早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明显是纪念性的——“为了给南京数十万个无字的坟墓题上我的碑文”。但她写下这一碑文的愿望并非仅仅来源于她所接触到的记忆表达,更来源于她的震惊:这样的记忆,以及它们所涉及的事件,竟然被战后世界,尤其是日本的主流政治文化和历史编纂传统抑制到了这种程度。她在著作的最后一章试着在谴责的同时去分析这样的抑制机制;整本书所汲取的教训既来自现在能被记起的事件,也来自这样的事件被遗忘的方式。 在一本这样的著作中,“遗忘”这一概念携带着强烈的情感指控。它的精确含义其实往往很难捉摸。张纯如将南京da屠杀称为“二战中被忘却的屠杀”,但她自己的书其实就引用了很多人的证词,对于这些人来说,1937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明显仍然属于在世的记忆(living memory)。“遗忘”所指的是缺乏公众的承认——历史学家创作出关于过去的故事,政治家在演讲中引用它们,教科书把它们教给上学的孩子,公共纪念碑让人们不断想起它们——但在这些故事中,南京da屠杀事件及其受害者却未被给予应有的位置。这不是意识随着时间流逝的消逝,不会因偶然原因被重新想起,而是一种不公正的形式或表达,它大声呼唤着我们去改正。那些人的经历曾被遗忘,对于他们的道义要求,社会有多种方式可以表达认可——经济补偿、财产归还、公开道歉或赎罪,以及惩罚那些对过去暴行负有责任的人——但对于历史学家,这首先意味着,在历史记载中确立正义。 真相、正义和记忆(或对遗忘的预防)长久以来都是紧密交织的概念。补偿和惩罚依赖于记忆;即便是赦免、“原谅和忘却”也依赖于最初的记忆。即便在正义无法(或不愿)对犯罪者施以惩罚的地方,也至少需要记忆去防止错误和伤害落入忘川——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至少从某一立场来看,如果这些事情被忘记了,那么受损失的将是真相本身:“如果大规模罪行的受害人不能留下他们的样貌和名字,如果无人知晓他们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所处的时间、地点以及死亡的方式,那么他们就是在真相的光亮之外,就是被遗弃在遗忘之中。留下的这个世界是不完整的;它的整体性被打破,它的真实性也大打折扣。”詹姆斯·布斯在分析这样的感受时写道。为了给过去一个真实的描述,让这样一些事情不被遗忘不仅被理解为抽象的正义的要求,也被理解为一种更人性的道德义务的实现:切斯瓦夫·米沃什曾说,“活着的人受命于死去而永远沉寂的人:去保存有关过去的真相”。这样一种观点在20世纪得到了深化,因为人们意识到极权政治追求茨维坦·托多罗夫所说的“清除记忆”(the blotting out of memory)的决心;这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删除对先于他们发生的事态的记忆,删除对他们自身罪行的记忆,以及删除这些罪行的受害者的记忆。在战争审判和真相委员会的时代,记忆、正义与历史真相之间的修辞和概念联系被再次反复拿到公共议论的台面上来,不出意外,它们有力影响了一些历史学家谈论自己的学科及其社会功能的方式。另一方面,一些评论家则暗示了可能的“记忆伦理的陷阱”,就什么应该被记住来说,对某一特定理解的遵循,在某些情况下其实很可能是与当下历史准确性或历史正义的要求相矛盾的。 将正义与记忆等同起来的问题之一是,记忆在实际上总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可以有意做出决定,不让一些关于苦难与不公的故事,以及这些苦难与不公的受害者被遗忘;甚至,如果愿意,我们也可以调整我们的历史实践去确保这一结果;但是在为一些人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我们肯定不会为了其他人做出同样的决定。甚至,托多罗夫指出,对“记忆之职责”(例如,与法国战时过往相关的“记忆之职责”)的当代呼吁,所涉及的并不是尽可能详尽地确立关于过去的事实这一愿望,而是“在这些事实中做出选择,并捍卫这种特定的选择,它确保其主角始终要么是英雄、要么是受害者,而不让其他的选择来赋予它们不那么光荣的角色”。换句话说,记忆作为一项道德义务的概念,在运用中总是有所偏颇的,它不仅是要确立应当被记住的内容,也想要固定住回忆的方式。 近三四十年来,记忆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关于记忆,存在着种种纷繁的意象。作者问道:我们是将记忆视为结构性框架、生产性过程,还是一连串图像?是将它描述为已逝的碎片,还是连接过去与当下存在的线缕?是将它比作一张刻印头脑中过去经历的蜡版,还是一间储藏图像的仓库,抑或是一座迷宫、一幅全息图像?在这些意象之间做出的选择,为我们往后的思考设定了轨道。 在历史学界所谓“记忆的转向”(turn to memory)的大背景下,杰弗里·丘比特的这部作品堪称记忆史研究的指导之书。一方面,作者不吝笔墨,大力厘清“历史”和“记忆”这两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术语,为全书叙述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作者本人的专攻领域虽为现代史,在写作此书时却并不囿于一己研究经验,而是在主题遴选上着眼于历史学家的普遍关切,写出一部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值得一读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