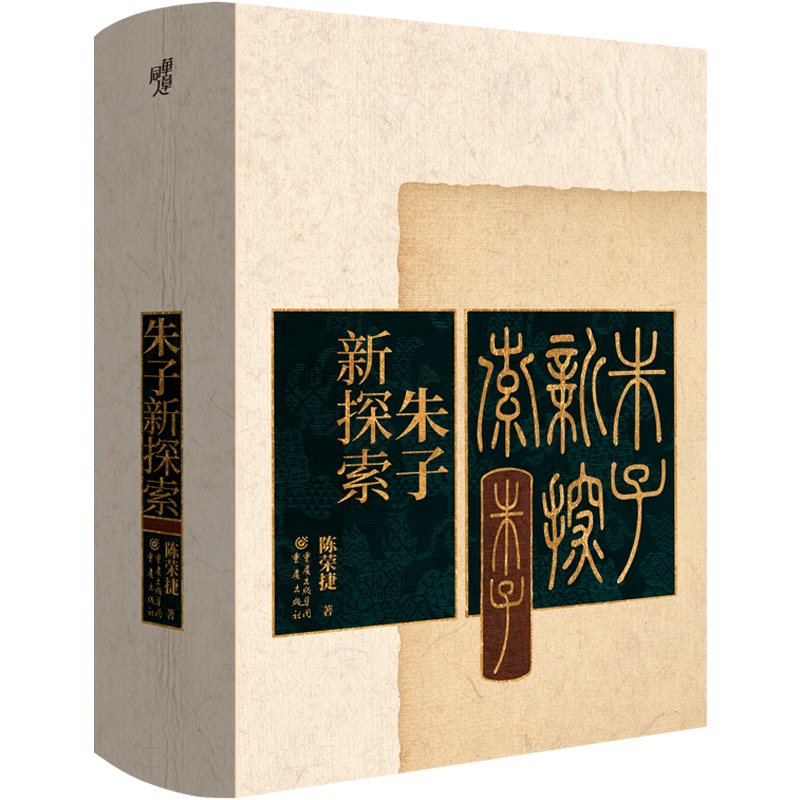
出版社: 重庆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0.80
折扣购买: 朱子新探索
ISBN: 97872291614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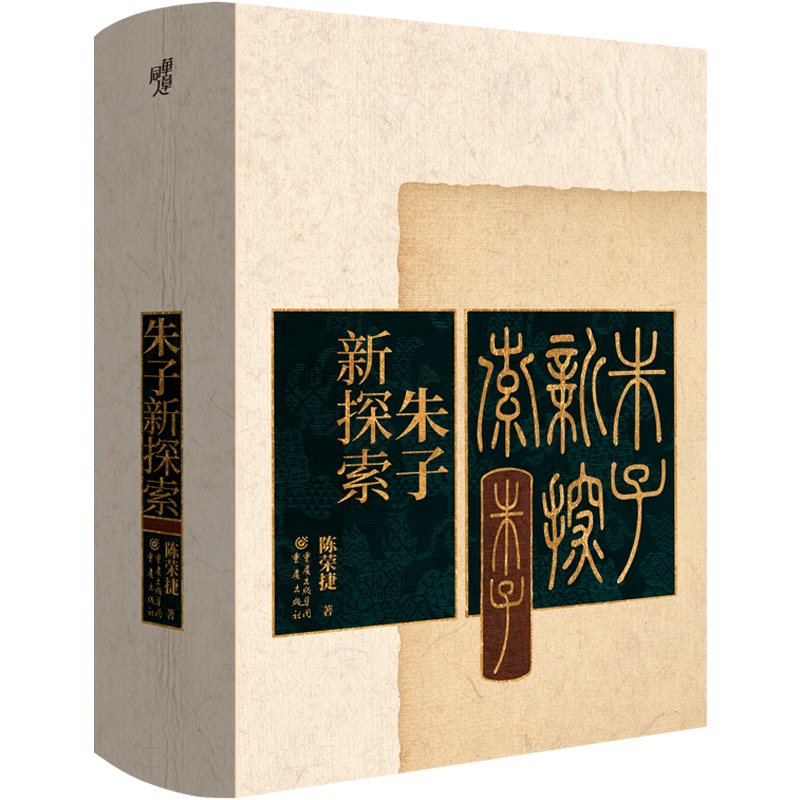
陈荣捷,国际汉学界新儒学研究泰斗,欧美学界公认的中国古代哲学和朱子学研究权威。1901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1916年考入香港拔萃书院,学习英文和中文。1924年岭南学院毕业后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英语系,1926年改入哲学系。1929年以题为《庄子哲学》的毕业论文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相继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夏威夷大学任教职。1943年任达特茅斯学院中国哲学教授,1951年任该校人文学院院长,是当时东方人在美国担任的最高学术职位。1966年自达特茅斯学院退休,被授以“中国哲学和文化荣誉教授”称号。 陈荣捷先生20世纪60年代为各种英文百科全书,包括《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中国哲学词条,被欧美学界誉为“把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大儒”。 陈荣捷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哲学资料的英文翻译。1963年,四部英文译著《坛经》、《王阳明〈传习录〉及其他著述》、《老子之道(道德经)》和《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又名《中国哲学资料书》)在美国出版。《中国哲学文献选编》集十余年之功,英译标准极高,至今无人超越,一直是美国院校教授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 陈荣捷先生1975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思想兼任教授,与狄百瑞教授联合执教哥大新儒学讨论班,直至晚年。1978年被选为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1980年当选为美国“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 陈荣捷先生在生命的后二十年里,将全部的学术关注集中在对朱熹的研究和对朱熹研究事业的推动上。1982年在夏威夷檀香山组织召开“国际朱熹会议”,成为当时世界朱子学术研究的高峰。朱子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有《近思录详注集评》《朱子门人》《朱学论集》《朱熹》《朱子新探索》等,另有作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
【一一七】沈继祖诬朱子六罪 黄榦《朱子行状》云:“沈继祖为监察御史,上章诬诋,落职罢祠。”《宋史·朱熹传》曰:“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又于《胡纮传》云:“独〔隆兴元年癸未(一一六三)进士〕草疏将上,会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继袓以追论程颐得为察官,纮遂以稿受之。继袓论熹,皆纮笔也。”王懋竑《朱子年谱》更详。庆元二年下云:“先是台臣击伪学,既榜朝堂。未几,张贵模指论《太极图说》之非。省闱闻之,知举叶、倪、刘等,奏论文弊。复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见黜落。‘六经’、《语》、《孟》《大学》、《中庸》之书,为世大禁。士子避时所忌,文气日卑。台谏汹汹,争欲以先生为奇货。门人杨道夫闻乡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书告。先生报曰:‘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烦过虑。’久之,奸人相顾不敢发,独胡纮草疏将上,会迁去不果。沈继袓以追论伊川,得为察官。纮以稿授之。继袓锐于进取,谓立可致富贵,遂奏乞褫职罢祠。从之。” 王氏《年谱》乃述洪去芜《朱子年谱》(一七〇〇)。叶公回《朱子年谱》(一四三一)与戴铣《朱子实纪》(一五〇六)内之《年谱》,均早于洪本二三百年,王氏未见。然三本年谱所载全同,只戴本备言叶翥、倪思、刘德秀之名而已。三本所据旧本不一,而毫无差异,则同溯于最早朱子门人李方子所撰之《年谱》,大有可能。(参看页九七“朱子年谱”条)然则沈继祖之奏请落职罢祠,历数百年而绝无异议。 沈继祖疏,最早见于稍后于朱子南宋人叶绍翁(约一一七五—一二三〇)之《四朝闻见录》。此疏读之者少,亟应录其全文,庶可睹其真相: 庆元三年丁巳(一一九七),春二月癸丑,省劄。臣窃见朝奉大夫秘阁修撰提摄鸿庆宫朱熹,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侠,务为武断。自知圣世此术难售,寻变所习,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又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走疏,所至响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贵矣。臣窃谓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恶又不与焉。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昔茅容杀鸡食母,而与客疏饭。今熹欲餐粗钓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熹于孝宗之朝,屡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监司郡守,或有招致,则趣驾以往。说者谓召命不至,盖将辞小而要大。命驾趣行,盖图朝至而夕馈。其乡有士人连其姓者,贻书痛责之。熹无以对。其后除郎,则又不肯入部供职,托足疾以要君。此见于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于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举国之论,礼合从葬于会稽。熹乃以私意,倡为异论。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泽,别图改卜。其意盖欲借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附会赵汝愚改卜他处之说。不顾祖宗之典礼,不恤国家之利害。向非陛下圣明,朝论坚决,几误大事。熹之不忠于国,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谋为不轨。欲藉熹虚名,以招致奸党。倚腹心羽翼,骤升经筵,躐取次对。熹既用,法从恩例封赠其父母,奏荐其子弟,换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为辞免。岂有以职名而受恩数,而却辞职名?玩侮朝廷,莫此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庆。熹乃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熹虽怀卵翼之私恩,盍顾朝廷之大义?而乃犹为死党,不畏人言。至和储用之诗,有“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人间岂容别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说,谓建阳县学风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储用逢迎其意,以县学不可为私家之有。于是以护国寺为县学,以为熹异日可得之地。遂于农月,伐山凿石,曹牵伍拽,取捷为路。所过骚动,破坏田亩。运而致之于县下方,且移夫子于释迦之殿。设机造械,用大木巨缆,绞缚圣像,撼摇通衢嚣市之内,而手足堕坏,观者惊叹。邑人以夫子为万世仁义礼乐之宗主,忽遭对移之罚,而又重以折肱伤股之患,其为害于风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知南康军则妄配数人而复与之改正,帅长沙则匿藏救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而浙东提举,而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齐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说,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夫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夫子圣人之不得位者也,犹能亟去之如是。而况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杀之势,而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诛之乎?臣愚欲望圣慈,特赐睿断。将朱熹褫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盗名者之戒。仍将储用镌官,永不得与亲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宁府追送别州编管。庶几奸人知惧,王道复明。天下学者,自此以孔孟为师,而人小夫,不敢假托凭藉,横行于清明之时,诚非小补。 关于此疏,有数点须说明者。一为疏之年月。疏首云“庆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四朝闻见录》有原注云,“蔡本作二年十月”。据《年谱》,庆元二年丙辰(一一九六)冬十二月落职罢祠。若沈继祖三年二月方奏,则反在落职罢祠之后,而奏内“将朱嘉褫职罢祠”之语为不通矣。朱子《落职罢官祠谢表》明谓二年十二月,则各《年谱》是也。二者本疏明数朱子六罪,《宋史》作为十罪。故王懋竑云:“疏语大罪有六,与《宋史》十罪不合,而《续通鉴》漫采入之。闽本《年谱》,乃据《续通鉴》以改。”所指闽本不知何本。朱子十六世孙朱玉所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一七二二)第一册之《年谱》“褫职罢祠”条下亦作十罪。此亦闽本。则诸闽本均误作十罪矣。然《宋史》谓为十罪,或亦有故。盖沈疏六罪之外,尚举不廉、不恕、不修身、不齐家、不治国之五项恶行,共为十一。《宋史》或只用其十之整数,或以廉恕合计,总数为十,亦未可知。三者选人余嚞上疏乞斩朱子。王懋竑《年谱》备注云:“沈继袓、余嚞两疏,皆不知所据。窃疑为阳明后人依仿撰造以诋朱子者。近人无识,轻以附诸《年谱》中。愚陋至此,亦可怜也。”王氏考识极为精详,惜未见《四朝闻见录》沈继祖疏,而以门户之见,归咎王门。不知王门攻击朱子思想,不遗余力,而于其人格,则无任敬仰,断不至沦为如斯之下流也。 依仿撰造,全在继祖。疏谓“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此指淳熙二年乙未(一一七五)吕东莱(吕祖谦)安排与陆象山(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之会。即据《象山全集》一面之词,参加者七人之中,无一人是朱子之徒。刘子澄(刘清之)亦同调耳。愚又考订此外尚有三人,皆象山门下。是以谓象山聚徒则可,谓朱聚徒则不可。疏谓“除是人间别有天”,乃储用之诗,而不知此乃朱子《武夷棹歌》十首最后之句,与储用无涉也。疏谓“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朱子所娶,乃刘勉之之女而非刘珙之女。刘珙为子羽之子,家素富庶。勉之少富,亦未尝以巨万给其女也。据朱子《刘勉之墓表》,其祖仕至尚书郎中,祖父为朝请郎。即建阳近郊萧屯别野结草为堂。墓表云:“少时家富而无子,谋尽以赀产归女氏。既谢不纳,又择其宗属之贤者,举而畀之。……亲旧羁贫,收恤扶助。”由此可知勉之原是富厚,然勉之非珙也。疏谓“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据《长沙县志》,所藏于袖者非登极大赦之诏令,而乃赵汝愚丞相私人之简札。继祖之虚造,显而易见。疏谓:“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朱子葬母在离福建建阳考亭七八十里之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名寒泉坞,离崇安甚远。疏谓“男女婚嫁,必择富民”,而婿黄榦贫寒至甚。疏谓“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然据愚统计,则门人四百六十七人中,只一百三十三人曾有官职,占百分之二十八。富室子弟诚有之,唯不及全数之半耳。疏谓“四方赂……动以万计”,然朱子取舍极严,其贫乏人所共知。屡次请祠,以求微禄。乾道九年癸巳(一一七三)有旨差管江西台州崇道观,圣旨即曰:“朱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则政府亦早已公认朱子之贫矣。疏谓“绞缚圣像……折肢伤股”,朱子答门人潘时举云:“近日改移新学,复为僧坊塑像摧毁,要膂断折,令人痛心。彼圣贤者尤不免遭此厄会,况如吾辈,何足道哉?”继祖颠倒是非,显而易见。 胡纮与沈继袓之动机,诚如杨道夫所云:“乡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述其经过有云:“胡纮……为监察御史,乃锐然以击熹自任。物色无所得,经年酝酿,章疏乃成。会改太常少卿,不果。……纮以疏草授之继袓,谓可立致富贵。”此疏动机如此,而虚构又如彼,故历来谈落职罢祠者,均不采用,弃如敝屣。但近年大陆学者首次引用。虽对疏中所称,谓为穿凿附会,言过其实,然引朱子《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谓其承认“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朱子果然认罪耶?此则不可不考。 《谢表》云:“谓其习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污行。有母而尝小人之食,可验恩衰。为臣而畜不事之心,足明礼阙。以至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官之地,而改为僧坊。谅皆考核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不虞恩贷,乃误保全。第令少避于清班,尚许仍居于散秩。”大陆学者忽略“谓其”二字,以为朱子自认其罪。实则“谓其”乃述疏中大意,非认罪也。下文即言其目的在于诋诬,欲投诸死地。而朝廷乃保全其性命,诏以依旧修撰清平之职,其非认罪也明矣。查庆元二年丙辰(一一九六)十月继祖上疏,十二月落职罢祠。三年丁巳(一一九七)正月拜命,并上《落职罢宫祠谢表》。在此表中,对于“大谴大诃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初乃“初罔闻知”,继而“甫深疑惧”。某月某日之后,又准告命一道,着了落秘阁修撰依前官,故有《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也。谢表未尝为事实上之辩护,盖事实昭然,无辩白之必要也。 【一二一】孀妇再嫁 五四运动以来,攻击理学者,最喜举程伊川(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语,以攻击伊川,亦即以攻击朱子。以“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为最烈。北京历史博物院特标此二语,以示程颐之残之忍。革命者借此为口号,并不为奇。然以此语代表封建制度之残害妇人,则太过简单。 伊川之言,来自《遗书》。《遗书》云:“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朱子与吕东莱(吕祖谦)合辑《近思录》,采用此段为第六章《家道》之一条,显然有意维持儒家之家庭制度。然朱、吕所采伊川之言,皆以其义理正当,可作行为之范。伊川对孀妇再嫁之问,不答以传统制度,而答以失节问题,且妇之失节亦即丈夫之失节。可知节之问题,乃伊川之中心问题。此问题从孔孟以来,在儒家思想上极是重要。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从此角度观之,则伊川之论,并非特殊。在程朱之伦理系统,此是古今不易之常理。门人陈守(字师中)之女弟作寡,朱子去书曰:“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4之节。此事更在丞相(陈守之父俊卿)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郑鉴)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况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未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5朱子此事不敢直言,必是俊卿欲为孀女再嫁,而朱子则以义为重,亦为名教所关也。 数百年后,汪绂复申此义,且设譬以阐明之。其《读近思录》有云:“孀妇不可娶,以自修君子言之。若市井小人,何能问此?然或疑程子此章之言为过,则程子此言非过也,常理而已。孀妇怕寒饿死而失节,何异于臣怕战而降贼哉?孀妇再嫁,孀妇亦羞之。羞而可为,则亦何不为之有?可以知人道之大防矣。”汪氏从基本问题着想,可谓善于读书。人道之大防,固不止为妇人言也。张伯行极尊朱子,然亦以伊川此言为过,似以朱子为不应采用者。故其所著《近思录集解》删去此条,而以伊川“兄弟之爱”7一段代之。此处抛龙转凤,从来未经有人发觉。伯行可谓不识程朱矣。 或谓妇人须忠于一夫,而男子可续娶,岂非不平之甚耶。应之曰:“此诚是矣。”当时制度如此,朱子亦遵从之。其答门人李晦叔(李辉)书云:“夫妇之义,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8宋代社会制度与二十世纪之社会制度当然不同。然吾人不能以二十世纪之标准,以评定宋代之习俗。亦犹一千五百年后,如实行公妻,而谓吾人在二十世纪之一夫一妻为不道德,不自由也。 或又谓孀妇将死而不救耶?伊川答语,乃依据原则而言。朱子采用此段,亦以其原则之故。至于实际情形,则或有反经为权之必要。此是经权问题,从孟子以来,提出男女授受不亲,而嫂溺则应援之以手,亦成为儒家之中心道德问题。伊川论经权云:“权量轻重,传之合义。才合义,便是经也。”朱子亦云:“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须是合义也。”伊川之父,尝行权矣。伊川撰其父之家传,述其父娶甥女归嫁云:“既而女兄之女又寡。父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又称其父“慈恕而刚断。平居与幼贱语,唯恐有伤其意。至于犯义理,则不假也”。伊川必以其父之归嫁孀妇为合于义理,否则必不于其家传特提此事也。 表面上程颐自相矛盾。朱子门人亦有如是想。故门人问曰:“取甥女归嫁一段,与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答云:“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不能尽”云云,可依汪绂解释。在当时信仰,其理想为孀妇宁死不再嫁,然此极高标准,非普通人所能达到。亦如凡人不应说谎,大纲如此,但人亦有不能尽者。然不害毋说谎之为原则也。 ☆国际儒学泰斗陈荣捷朱子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钩沉中日韩三国史料,全面剖析朱熹的生平、为人与思想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其学说深受后来统治者的欢迎,成为元明清三朝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长达600多年。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广建书院,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皆是由其重建。他也是仅有的一位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 不过,大众对其较为熟悉的却是其提倡的饱受诟病的约束女性的道德枷锁“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是大”……但宋代离婚再嫁的并不鲜见,比如李清照改嫁张汝舟、唐婉再嫁赵士诚,程颐的妹妹也改嫁过。这位曾任帝师、备受世人推崇的大儒为何有如此言论?其本意何在? 朱熹虽身后享尽荣耀,但生前的仕途并不如意,晚年还在“庆元党禁”中被扣上了“伪君子”、“假道学”的帽子,凄凉离世。从饱受唾弃到死后正名,进而备受统治者、世人推崇,或许只有理解了其中的转变所在,才能全面理解朱熹、真正领会其思想。 国际儒学泰斗陈荣捷,是与钱穆齐名的朱熹研究权威,他晚年专注于朱子研究,钩沉梳理中、日、朝鲜三国资料,发掘了大量以往不被注意的新材料,以学者历来所不及论者切入,“言学者所未言”,在85岁高龄时创造完成了《朱子新探索》。其内容不仅涉及朱熹思想中的诸多核心概念如理气、天命、太极、体用,还记述了刻书、传说、贫困、执法、画像、交游等朱熹的日常生活。陈荣捷一生中的大部分学术活动都在美国,其不同的学术环境也赋予了其独特的视角。在《朱子新探索》中,陈荣捷分析朱熹不主张“孀妇再嫁”,认为其本意是“其理想为孀妇宁死不再嫁,然此极高标准,非普通人所能达到”,而且因为宋代没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孀妇出嫁后带走夫家财产,会让幼儿和夫家生活无着落,容易造成社会问题。在朱子之于妇女一节中,幼女夭折,朱熹还特意将此事写信告诉了陆九渊;朱熹对于女儿的婚配也是费尽心思,在婚后还给女婿黄榦写信,请其体谅女儿早年失母,但也请其不可过于纵容女儿,对女儿的爱护之情溢于言表。朱熹在母亲去世后,“日居墓侧,旦望则归奠几筵”,由己及人,再参考宋代社会环境,苛刻而极端的言论似乎不应出自这位大儒之口。其言论是如何被塑造成一种严苛的道德标准的?这其中的疑惑让人不由地去探究。 历代研究朱子的学者多注重其思想言论,忽视或不屑于其私生活。《朱子新探索》却花费了相当的笔墨记述朱熹的日常,甚至包括传说,不是哗众取宠,也“非谓有所发见,只欲彰其密,显其微,提倡激动,扩大研究朱子之范围而已”。《朱子新探索》倾注了陈荣捷十数年之功,行文精悍凝练,书中解决了许多有关朱子的悬案,也澄清了许多后人对朱熹的误会与偏见,无论是对于专业的朱子学研究者,还是对于意欲了解朱熹的普通读者来说,皆是不可错过的启迪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