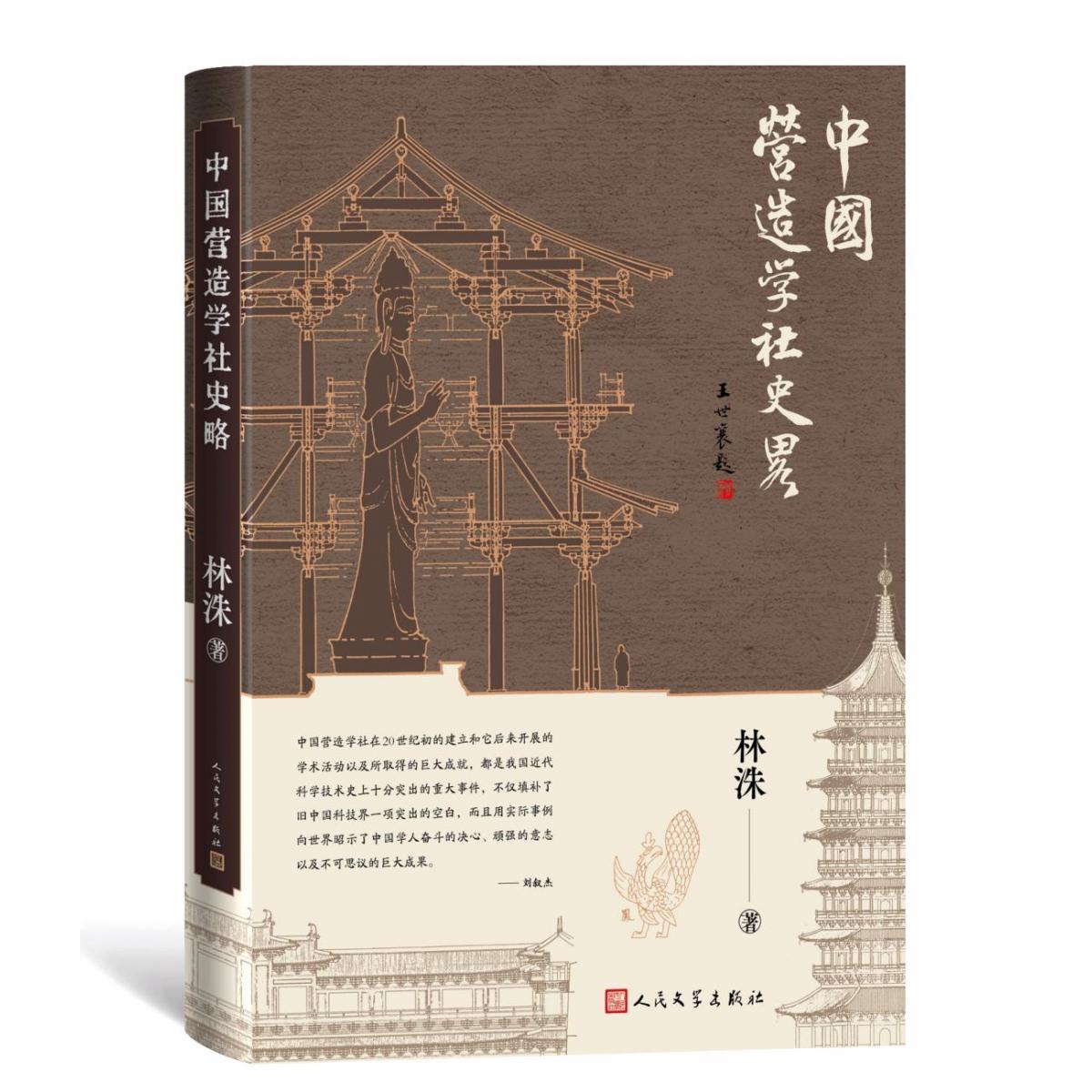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3.60
折扣购买: 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ISBN: 9787020179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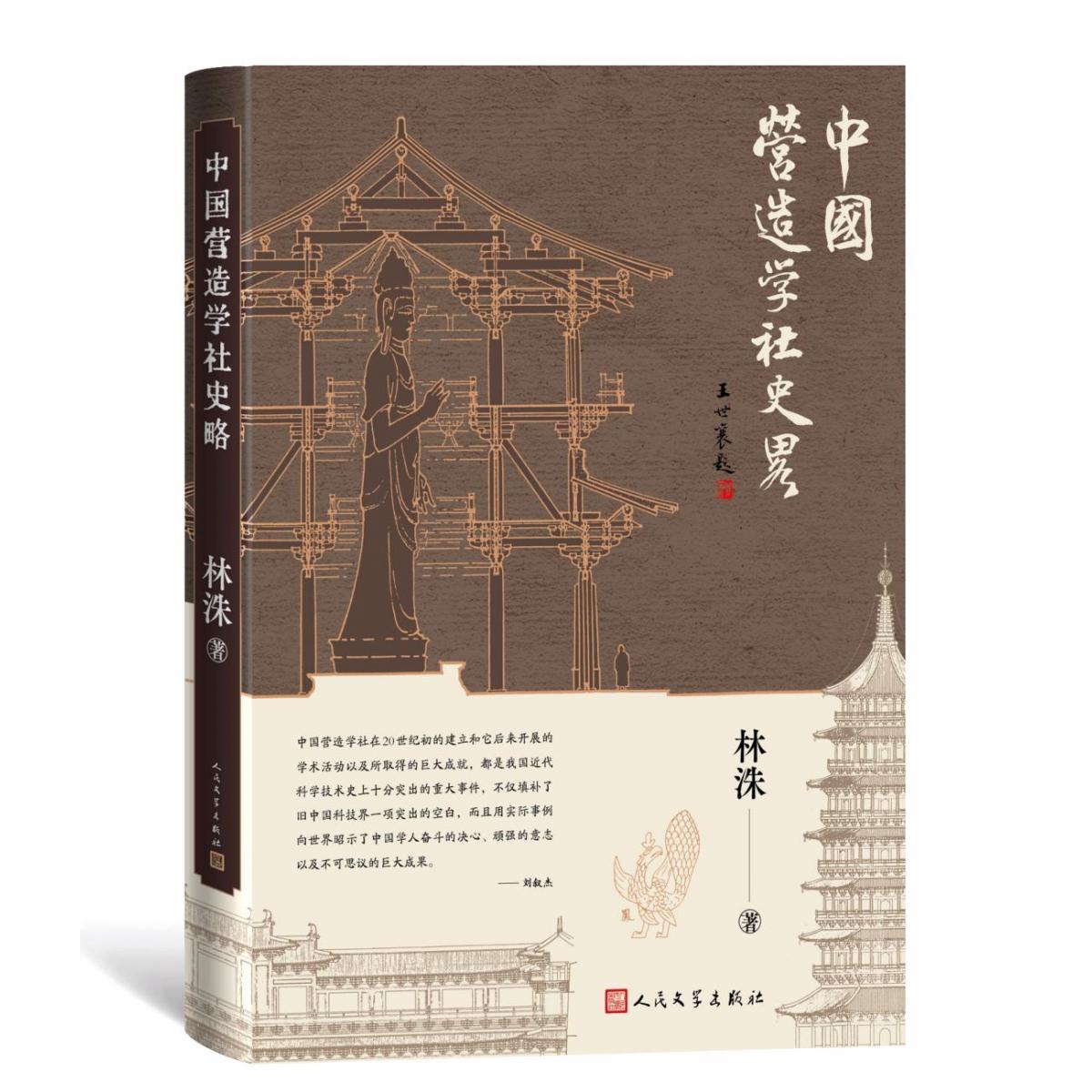
林洙,梁思成遗孀。1928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3年入清华大学梁思成主持的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工作。1962年与梁思成结婚,陪伴梁走过了十一年艰难岁月。梁思成逝世后,全力以赴整理梁遗稿,先后参与编辑《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建筑画集》《梁思成全集》。著有《大匠的困惑》《建筑师梁思成》《梁思成、林徽因与我》,编有《建筑文萃》《未完成的测绘图》《佛像的历史》《梁思成心灵之旅》《梁》《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等书。
第一辑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贵州开阳人,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卒于北京,享年九十二岁,人生历程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这个阶段正是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入大变动的时代。在长达近一个世纪剧烈变动的近代中国社会中,要想出淤泥而不染绝非易事。所以,对朱启钤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把他限制在一个简单而僵化的模式里,而要把他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介。 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地把朱视为“政客”,但他一生的活动绝不局限于政治方面,他是一个杰出的实业家、古建筑专家、文物收藏家,并对髹漆、丝绣等做过深入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是一个多重性的人物,对他的研究,必须注意到他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及他本人的多重性,也就是近代史家称之为“方面论”及“阶段论”的观点。只有从这纵横两方面去观察他,才能通观他的全貌。我对朱启钤先生知之甚少,感谢朱海北先生、朱文极先生对我的热情支持,使我得到了不少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朱本人留下的文字材料太少,限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查阅更多的史料。对朱启钤先生更深入的研究尚有待后人去完成。 朱启钤早年的经历 朱启钤早年丧父,随母寄居在外祖父家,八岁开始读书。1884年,朱的姨父瞿鸿禨视学浙江,朱随母偕妹至杭州探望姨母,住在杭州学使署。瞿见朱聪明过人,特延聘名师张石琴先生教朱习制举文。经一年多的学习,朱于举业无所成就,却对当时的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瞿经过年余的观察,发觉朱是个经世之才,难望以科举进身。果然,朱启钤很早就显示出了他的办事才能,十五岁时,就能帮助办理外祖父的丧事。 1889年,朱十七岁时与陈崧生(曾国藩次婿)的继女陈光玑成婚。婚后自立门户,定居长沙定王台。陈崧生出任英法比参赞时,陈光玑随父出国,生活在巴黎,十岁后才回国。陈给朱带来了不少异国见闻。朱启钤终身坚持一夫一妻,没有纳妾。他的子女们特别是女儿可以自由参加社交活动。这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礼教影响的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可以说,他较早就从陈光玑那里接受了西方社会文明的思想。 1891年至1893年,瞿鸿禨赴四川典试,朱亦随侍左右。四川幅员广阔,学政每年两度科试,瞿须亲往各县典试,旅途既辛苦又惊险,朱乘马随从,调护瞿的起居。瞿亦注意对朱的培养,并每在他批阅案卷时,嘱朱在侧学习,晓以史乘掌故,并令朱试着批复案卷,感到他的批复颇有见地亦中肯。 这一时期,朱结交不少贤俊,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其中,尤以同幕唐才常最是知交。朱的岳父留给他不少驻外时的杂记书籍,朱从这些读物中得出“西人以制造致富”这条路,因而认为中国也应走“以制造致富”这条路。可以说朱很早就树立了后来诸多爱国志士提倡的“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想。他与唐才常经常交谈,深感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强国富民”。直到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朱又佐瞿鸿禨督学江苏时,还常与张劭希、杨笃生、章士钊等私购变法维新书籍,互相传习。可以说,朱的一生始终抱着实业救国的信念。不管他是短暂地担任蒙务局督办,或任京师巡警厅厅丞,或任交通部总长,或任内务部总长,直到任中兴煤矿总经理,他都没有放弃办实事、发展工业、强国富民的信念。 瞿鸿禨通过在四川两年多对朱的考察,认为朱有非凡的办事才能,虽难从科举进身,但若登仕途,不难自发。因此,瞿在1893年离任四川之时 ,出资为朱捐了一个小官。 1894年朱到泸州盐务局印鉴所任职,他的家属也迁居泸州。 1896年朱调管灌口水军兼救生红船事,后又调专管云阳大荡子新滩工事,这是他接触的第一个工程。1897年云阳工地失火,朱住的草屋被烧毁,他幸免于难。工程竣工朱回到家中,不久夫人陈光玑病故。由于朱在工地曾遭火灾,妻子也病故泸州,因此朱的母亲不愿再留居四川,于是东归。是年秋,朱娶续室于宝珊夫人。 1898年瞿鸿禨按试苏松、太仓地区,朱又随侍左右,并随瞿进京,被引荐给朝廷,派他到江苏任职,其家属也迁到苏州。1899年朱在上海出口捐助局任职,又合家迁居上海。 1900年义和团起义。朱母傅太夫人病故,朱奉母灵柩回长沙。1901年在长沙守丧。 1902年朱送姨母(瞿鸿禨夫人)入京,这时瞿已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政务处大臣,后又任外务部尚书,地位显赫。瞿留朱在京。1902年由瞿推荐入路矿总局任职。不久,奉张文达派任译学馆提调。1903年升译学馆监督,于是全家迁来北京。 1904年经徐世昌介绍,朱与袁世凯相识,随后即辞去译学馆职,候政北洋。 1905年朱赴津主持天津习艺所工程。1905年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廷大为震惊。袁世凯乘机插手北京警政,奏请设巡警部。1906年,巡警部设立,经袁保荐徐,世昌任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朗为左侍郎,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朱任京师内城巡警厅厅丞,后又调外城巡警厅厅丞,创办京师警察市政。 当时巡警制度在国内尚无先例,创业艰难,从体制到各项条例的制定,均由朱亲自拟定。为了管理首都的治安,他每天骑马巡视京师内外。当时市政也归巡警厅管理,他开始注意北京的街衢市容。这为他日后任内务总长时,着手北京的市政建设打下了基础。同时,朱创始的巡警制度日后也被全国各省市成立的巡警警察机构奉为圭臬。 1907年瞿鸿禨被清廷罢相归里,朱亦自请开缺,居长沙一年。 1908年袁推荐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徐奏调朱任蒙务局督办。朱在上任之前先赴日本考察殖民政策,次年回国深入蒙区调查,看到兴安岭以南地区资源丰富尚未开发,因而拟定“筹蒙要策”,计划移民边区,开发地区资源,发展边区城镇,想促使人烟稀少的边区得以繁荣。经济发展了,可由地方拨款供边防军的军费,从而巩固连续,加强国防。计划中列举应办之事二十余项,并附金融机关之组织及局务筹款办法。可惜,这项计划未能实行。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官,徐世昌亦调离东三省改任邮传部尚书。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封建社会,朱自然也被迫辞去蒙务局职。1910年朱到徐世昌主管的邮传部任丞参,兼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筹建山东泺口黄河桥工程。 山东泺口黄河桥工程,在当年是一件大事,黄河下游河床淤积了很厚的沙砾层,桥墩基础必须采用沉箱法施工。这种技术当时在国内尚属最新技术。朱对这一工程自勘察设计直到施工,事无巨细,均一一亲自过问。桥墩基础施工时,他亲自下到沉井中去视察土层情况,沉井中氧气不足,十分憋闷,上得岸来正在喘气,有人从旁呈上一封电报,原来是家中来电报喜,长孙朱文极降生了。 1911年袁世凯东山再起。1911年至1912年,朱任津浦铁路督办。1912年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即任朱为交通部总长。 1915年朱启钤在内务总长任内又兼了一任交通总长。前后涉足铁道事业五六年的时间,成为老交通系的重要成员之一。交通系是北洋军阀统治下政府中的一个重要政治派系。它虽不是公开的政党,却具有左右政局的势力。交通系之所以能成为一派政治力量,是因为它把持全国的路权,掌管全国路、电、邮、航四政,并设有交通银行,管理四政专款及全国汇兑,掌有一定的财权,其中又以路权最为重要。民国初年,京汉、京奉、津浦三路开始运营,获利较多。铁路收入亦多留用军费、政费。同时,有了路权便可以铁路为抵押向外国大量贷款,以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北洋政府就是因为它控制住了交通系,从而绝大部分经费由此而来。 1912年,交通银行逐步扩展,取得国家银行的地位,交通系进而染指国家财政,呼风唤雨,左右政坛。老交通系的领袖人物有梁士诒、叶恭绰,前者总揽交行金融,后者总揽路政。任过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及董事的有梁士诒、曹汝霖、张謇、周自齐、朱启钤、陆宗舆、叶恭绰、徐世章、汪有龄、周作民、蒋邦彦、孟锡珏、任凤苞、施肇曾、方仁元、钱永铭…… 这些人均与朱有交往,其中梁士诒、叶恭绰、徐世章、周作民、孟锡珏、任凤苞、钱永铭等后来都是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并为学社研究经费或解囊或奔走,其中尤以叶恭绰与朱关系最为深挚。 朱任交通总长时期,除已建成的京汉、京奉、津浦三线外,从全局考虑计划再修筑四条主干线以贯通全国:一、宁湘线,自南京至长沙并延伸至贵阳;二、同成线,自大同到成都,使四川丰富的物资得由陆路运出,避开三峡之险;三、浦信线,自浦口至信阳;四、陇海线,自东海至兰州。 朱计划的这四条线是很有眼光的,也是他实现“实业救国”的基础建设。但是,腐败的北洋政府将大量的铁路经费用于军、政。这个庞大的修路计划,仅陇海线东段开工,其他均未实施。同成线自宝鸡到成都段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修成。 1913年至1916年,袁世凯任大总统职,任命朱启钤为内务部总长。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6月病逝,朱亦引咎去职,移居天津。 如何看待朱启钤的早年经历 1906年至1916年,朱启钤跟随徐世昌、袁世凯十年,这也是朱被后人诟病的一段历史。因此,我们也不能不认真对待朱的这一段历史。朱的亲友们出于对他的爱护,亦常为他开脱。如叶恭绰曾说:“袁用他,实际是把他当作瞿的人质。”朱的秘书刘宗汉先生也认为:“袁对他终究是有芥蒂的,在任用中又有时把他放在最容易受伤害的地位。……如果讨袁军胜利,他自然便成祸首,而袁的嫡系亲信都得到保护。”按这个说法,似乎认为袁之用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嫡系。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均有欠妥之处。 20世纪初,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已基本形成。当时任军机大臣的瞿鸿禨与袁的矛盾也逐步深化。清廷实际掌握军权的荣禄已被袁世凯以入拜为门生等各种手段拉拢过去,结为死党。袁想如法炮制拉拢瞿,先示意愿列为瞿的门生,被瞿以万不敢当却之。继之,又托人询问可否换帖结为兄弟,瞿又婉言辞谢。袁意识到瞿不可能被他收买,因此立即警告他的死党奕劻必须把瞿赶出军机处,否则“日后必受其害”。1907年,赵启霖参奏载振、奕劻受贿丑事,举朝哗然,西太后大怒,下令查办。载、奕被袁设法包庇过关。赵启霖是军机大臣瞿的同乡,袁认为赵的参奏是受瞿的指使。因而参奏案一结束,袁立刻发起反击,以一万八千两银子收买御史恽毓鼎,要他参劾诬陷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清廷遂将瞿开缺。至此,瞿袁之争,以瞿鸿禨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后人根据瞿罢相后,朱亦自请开缺为由,认为朱是瞿党无疑;对瞿下台后,朱为瞿的政敌服务,有所非议。但笔者却有些看法,仅供参考。 一、朱不是瞿党,至少不是瞿的死党。尽管朱在青年时期(二十岁)就追随瞿的左右,但瞿始终没有重用他,他一直只是个小官。直到1902年,朱(三十岁)由张文达之荐当了译学馆的提调,转年升监督。名声虽好听,但译学馆是个没有政权、财权、军权的清水衙门。这个差事远远涉及不到瞿、袁的政争。尽管朱曾为瞿传递过文件,也仅仅是因为他和瞿有亲戚关系而已。有人根据瞿罢相后,朱自请开缺为由,认定朱是瞿的人,这个理由也是不充足的。在封建社会,仅仅因为是同乡、亲戚而受株连是常见的。朱当时任京师巡警厅厅丞,这么重要的职务很可能被清廷视为瞿“阴结外援”的一分子,因而他自请开缺,这只能说明朱是很有头脑的聪明人。尽管瞿、朱在政治上没有很深的瓜葛,但瞿毕竟是最早提携他的人,因而朱在瞿失败后,暂时退出政坛,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认为袁用朱是把他当作瞿的人质的说法,更是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朱并非瞿的子或孙,也不是养子。从《朱启钤自撰年谱》来看,朱、瞿的关系与感情并没有密切到能当瞿的人质的地步。 二、袁世凯为人的阴险毒辣及政治上的卑鄙诡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而逐渐被人们认识的,特别是他直接指使的几起重大谋杀案,只有在他死后才可能被彻底揭露。 我们且看看20世纪初袁世凯的表现:他编练北洋新军,被誉为懂得现代兵法的军事家。政治上他投机立宪,以“开通风气”自诩,连上奏折,侈谈立宪。1907年,立宪运动达到高潮,他也成为立宪“急进派”,被视为宪政运动的中坚。他还力主新学,联合张之洞两次上书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在他管辖的直隶,几年之内就办了高等学堂五所,中、初等专业学堂及习艺所一百三十三所,中学及女子学堂六十七所,小学校四千三百四十四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他还令周学熙办理实业,先后在天津创设铁工厂、考工厂、商品陈列所、国货售品所、种植园,并在各县办工厂分厂,设直隶工艺局。1906年,又开办滦州煤矿公司,扩大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袁的这些赫赫政绩,不仅使外国人对他“刮目相看”,甚至相当多的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也被他所蒙蔽。瞿、袁相比,自然袁比瞿更能讨好世人,更能吸引朱启钤这个胸有大志、想要干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并与朱的“以制造致富”的想法相一致。 三、袁世凯是个重才、识才且会用才的人。当徐世昌把朱推荐给袁时,袁肯定已通过他的情报网对朱进行调查并已对他有个基本的估计。否则,袁不可能仅仅为了表现自己的“雍容大度”而重用他。1904年冬,徐正式向袁引见了朱,这次见面,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互相赏识。这在1936年朱写的《朱启钤自撰年谱》中可以看到。1936年,袁已去世二十年,按说朱对袁已无任何顾忌,但朱仍在年谱中写上“光绪三十年……冬,以天津徐公之荐,受项城袁公知”。这里朱用了一个“知”字,这就说明了朱、袁会晤的性质及对朱的重要性。这一个“知”字,也概括了朱与袁的全部关系。就在朱、袁见面之后,朱辞去译学馆职,以“候政北洋”,于次年赴天津主持习艺所工程。实际上习艺所工程只是一个暂安之处,袁是准备重用他的。果然,1906年,机会来了。徐世昌出任巡警部尚书后,朱即升任京师巡警厅厅丞。至于袁对朱是否存有芥蒂呢?可以说,袁对他手下的人,个个都存有戒心。 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在政府部门尽可能安插他的亲信、嫡系。在他任临时总统及大总统期间,国务总理一直由他的亲信担任,如唐绍仪、陆徵祥、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徐世昌等。各任部长也都是他的嫡系。仅仅为了同革命党人妥协,他才把一些次要的部门让给同盟会会员和进步党人,如梁启超一度任司法总长,宋教仁任农林部总长,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等。其他,如财政、交通、军队这些要害部门的大权袁是紧紧抓住不放的。对他的下属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嫁祸于人,更不可能去“保护”他们。 袁内阁第一任总理是唐绍仪。唐本是袁的亲信,辛亥革命后加入了同盟会,以“调和南北”自居。在任总理期间,推行责任内阁制,为袁所忌,当年就被迫辞职,代之以表面上无党派的陆徵祥。不久陆就被赵秉钧接替。赵秉钧是袁一手提拔的人,对袁感激涕零,死心塌地为袁卖命。1913年,赵因参与谋杀宋教仁案被迫调离。1914年,赵对袁派人刺死杀害宋的案犯应夔丞有不满情绪,袁得知后立刻派人将赵毒死灭口。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也是袁的心腹,且他利用任财政部次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的职务,为袁筹措大量活动经费,深得袁的依赖。人称他是袁的“财神”。但是,梁好包揽把持,利用秘书长职权,在北洋政界培植个人势力,形成颇有影响的交通系,又为袁所忌,袁遂下决心把他撵出总统府,派为税务处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