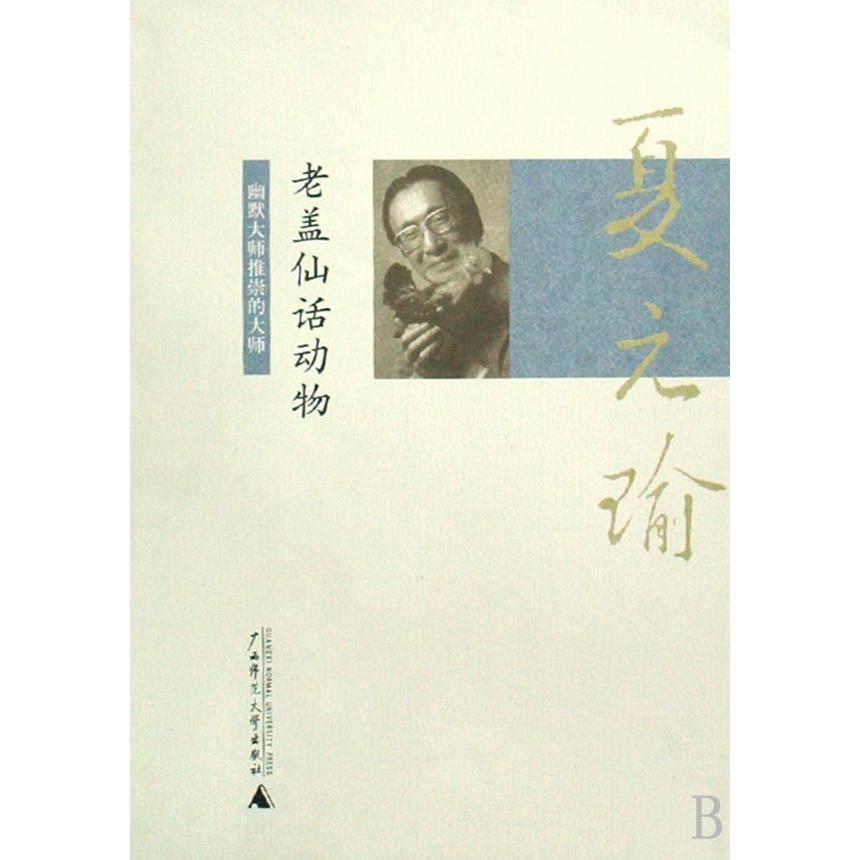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33.00
折扣价: 20.80
折扣购买: 老盖仙话动物
ISBN: 9787563375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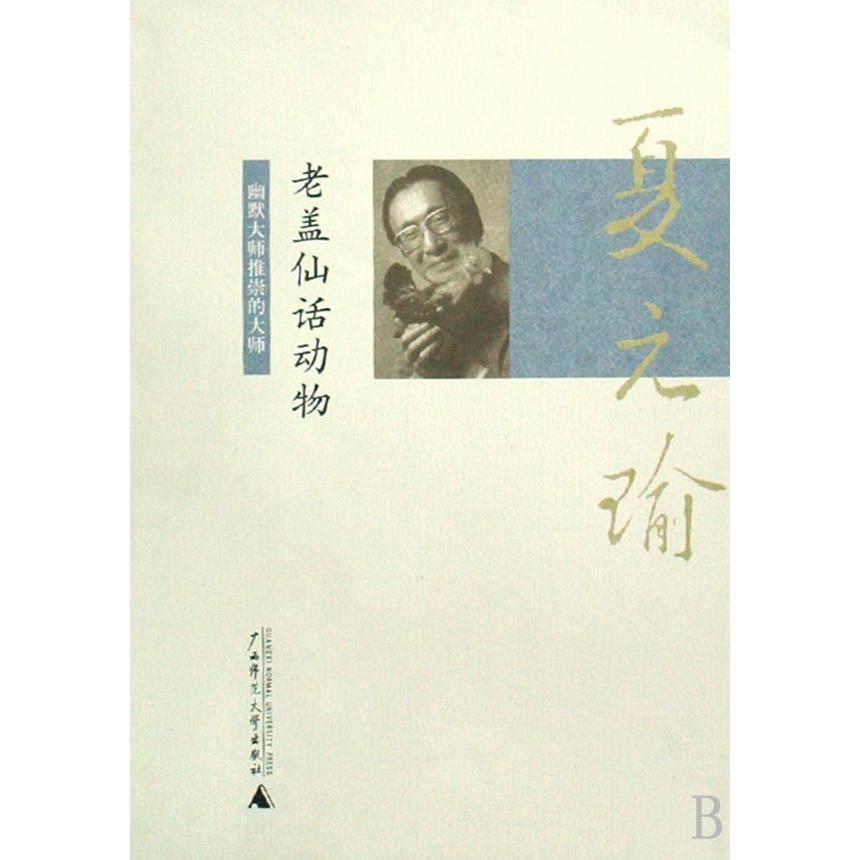
夏元瑜(1909—1995),祖籍杭州,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其父夏曾佑为著名史学家,其兄夏元瑮为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早年负笈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后赴日本深造。曾为北京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园长,南迁台湾之后,任过公务员,制过动物标本,当过大学教授,做过电视名嘴,评过“金马奖”。退休后专注于爬格子,人称“老盖仙”,遂文名胜过本业,成为“左手拿刀、右手执笔”的幽默大师,与至交唐鲁孙共被视为台湾文坛奇人。夏元瑜作品堪称当代幽默文学代表,毕生著作二十余部,均脍炙人口,其新书在台湾曾出版一周即再版。此次推出的“夏元瑜幽默精选”为其作品首次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结集出版。 一般所谓的“盖”,指“吹”“侃”得天花乱坠。“老盖仙”夏元瑜却自道:“‘盖’不是吹牛,吹牛就像违章建筑,会被取缔。‘盖’是引而申之,言之有物,且字字有所本。”夏元瑜的“盖式幽默”,杂糅着老北京的京味逗趣与台湾的综艺化诙谐,善以“无论说古论今,总是不忘适时幽自己一默”的自嘲自讽,将世间诸般烦恼、不顺,在莞尔一笑中释怀、解压,可谓嬉笑中透着乐观哲学。
前些日子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题目是“伦敦市里的野生动物”, 内容不错。譬如原来在悬崖峭壁上营巢作窝、生儿养女的荼隼,竟然拿高 楼的窗户口当作悬崖,在那儿落了户。它们也真聪明,先经过不少日子的 观察,单挑了个永不打开的窗台来做安身之所。若干的野鸭、秧鸡也全飞 到公园里去,英国人对野生动物很知爱护,绝不去骚扰它们。有一次一对 小鸟在一个电话亭上做了窝,而且孵了蛋,于是竟无人敢进去打电话。美 国公园里的松鼠跑出来向客人要吃的,又何等地好玩儿。要是在台北,少 不得抓了来关在圆形铁丝笼里来卖,再不然剥了皮做标本。野生动物别说 在市区里走投无路,就是藏在中央山脉里也老命难保。英国人也不是不打 猎,打是有一定的地方和季节,以及限定的种类。最大的不同是洋人为了 消遣,中国人为了赚钱。前者的死亡率不太大,而我们的办法是赶尽杀绝 。现在三年禁猎以来,野生动物的日子又好转了些。 想起从前在北平的时候,市区里可有不少野鸟。有的是根本在城市里 长久住家,多少代的老住户。另有不少是有季候性的,春秋来临的流动户 口。那些老住户,平日也没人去注意它们,好像自古相传,毫不足奇,没 人提它。我可不然,因为天性爱野物,对老虎固有兴趣,对乌鸦也照样地 喜爱。要说起北平城里的乌鸦来,数量着实可观。正因为古城里百年大树 很多,您要是站在故宫后面的景山中峰上往全城一瞧,真是满城苍翠。那 些特老的大树散处各地,有的在人家院子里,有的在冷巷里,马路边可没 有。那些老树高有二三丈以上,乌鸦——北平俗称老鸹,大概以其鸣声聒 聒之意——全在大树上作窝,有时一株老树上有好些个老鸹窝,可是各家 的光线和通风,比现在的公寓强多了。它们不用钢筋水泥,可是从没瞧见 老鸹窝被狂风吹下来过,很值得建筑家参考研究。它们虽散居全城,可是 有个共同的公约,遵守千百年而不渝。每天东边一透白,不知哪一只全城 的鸦长就醒了,理理羽毛,先跳出窝来,然后“聒”的一声中高音,接着 就冲天而起。它老人家振臂一呼——想是鸦语说大家出发吧——全市各街 各巷的乌鸦就全跟着起来,于是全城的鸦众都在空中集合。最怪的,我由 幼而壮只见它们成千上万地从北城向南郊而去,从未见鸦群一清早向北飞 过。老鸹是有品德的鸟,您院子里要是晒点香肠腊肉的话,甭担心它会来 不告而取。 到了黄昏之后,天擦黑儿了,老鸹又遮天蔽空地回来了,你鸣我叫, 彼此高谈一天的得意之事,不知飞到哪儿才解散,然后各自回家。它们的 菜单很广,翻翻垃圾,清理掉无数的将腐或已腐的食物,吃了也决不得肠 炎,对环境卫生有不少功劳。 北平市内的乌鸦有三种,最大种全长有四五十厘米,大嘴,嘴尖略略 有点弯,一身黑羽,闪着暗蓝的金属光泽。另一种大鸦是白嘴根子的,因 为这种鸦的嘴根上的刚毛最易传染疥癣,就脱毛变白。第三种是小形的, 全长二十五厘米左右。在郊外有种体大而白颈白腹的老鸹,咱们叫它白脖 子老鸹。据说当初清太祖一天兵败,藏人树洞中,飞来了一只老鸹往洞口 一站,明朝兵追来一瞧,洞口有鸦,想来其中必然没人,就上别处去找了 。太祖出洞,赏了这只救驾的乌鸦一个玉环。乌鸦没处可放,赶快套在脖 子上,从此成了这个白脖子的品种。还有体小灰腹的寒鸦。更有一种大红 嘴、大红脚的红嘴鸦,嘴细而弯,体窄长,很不易得,我半辈子只得到过 一对死的。 俗语说“天下的老鸹一般黑”,形容某一行的人全有相同的毛病。其 实很不对,不但白脖子老鸹和寒鸦不全是黑的,而且在正常的大嘴鸦中也 有变白的,虽不能欺霜赛雪,它褪色有如旧的牛皮纸似的,少得很,物以 稀为贵,也很值钱。 我瞧着任何动物全有三分秀气,各臻其妙,细看老鸹也觉得很有些可 爱之处,一般俗人没有慧眼不大领略得了。以此眼光来看世人,于是觉得 坏人也有些好的地方,丑人也有些美的部分。今年老夫年逾七旬,揽镜自 照,很以为左额的那一块青记真有张大干泼墨山水的意思,脑门上的那几 条皱纹也不亚于齐白石的笔法,仅可叹俗人不能欣赏耳。 曾有一次,城外的朋友逮了一只老鸹送给我,我欢喜得很。先给它脚 上系了一根细绵绳,拴在椅背上。野鸟被捉之后,往往宁愿饿死首阳,也 不肯吃那嗟来之食。它则不然,不拘荤素,无不笑纳。我俩同住一屋,宾 主十分相得。于是把那根细绳儿也取消了,以免有损它的自尊心,而碍友 谊的进展。解开之后,它也不跑,和我平起平坐,有时我看书或做工的时 候,它竟飞到我肩膀上,往下瞧瞧我干些什么。外国电影中演个女巫,一 定要配只乌鸦,其实这有何难。一两个月之后,有一天下晚儿,它站在我 肩上,我在院中散步(北平房子的院子大),正碰上大群老鸹鼓噪回城。它 抬头一望,激发本性,在我脑袋顶上啄了一下,一声长鸣举翅升天,人群 而去。我虽惋惜,可也庆幸它恢复自立生活,不再在孟尝君门下当食客了 。它临去时的啄我,也正是它说:“拜拜了!” 崇效寺的牡丹开过,北海公园的荷花也结了莲蓬,中山公园正举行菊 花展览,真是四季名花不断。我看了回来,吓了一跳,老朋友竟站在我房 门口等我,看了我,马上飞到我肩上。我素来爱说话,立刻寒暄一番。它 虽没回答,可是另一声鸦叫发于对面南房的屋檐上。我一瞧,还有一只老 鸹。它可有点怕我,不敢下来,而且叫之不已。我肩上的老朋友只好舍我 而去,飞上房檐,和那只乌鸦一齐飞了。 哦!我明白了,它结婚了,和新夫人一块来看看老朋友,很够交情。 也没准儿他想带着太太全住到我家里来,我住的虽是陋室,究竟比老鸹窝 强些,至于伙食当然比垃圾胜过万倍。不过那位鸦太太不爱这种新环境, 也许觉得平白地添出一位公公来怪讨厌的,不赞成此举。 台湾乌鸦极少,有一电影中用了几只乌鸦,翅破尾残,一看便知是笼 中之物,别说为妖,连活命都难。它实在是极聪明的鸟儿,今日垃圾成灾 ,正应当多培养它们。 笔者——老盖仙夏氏——平常为文虽不免有点盖性,可是言及动物决 不乱盖,实话实说,以广爱物之意。 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