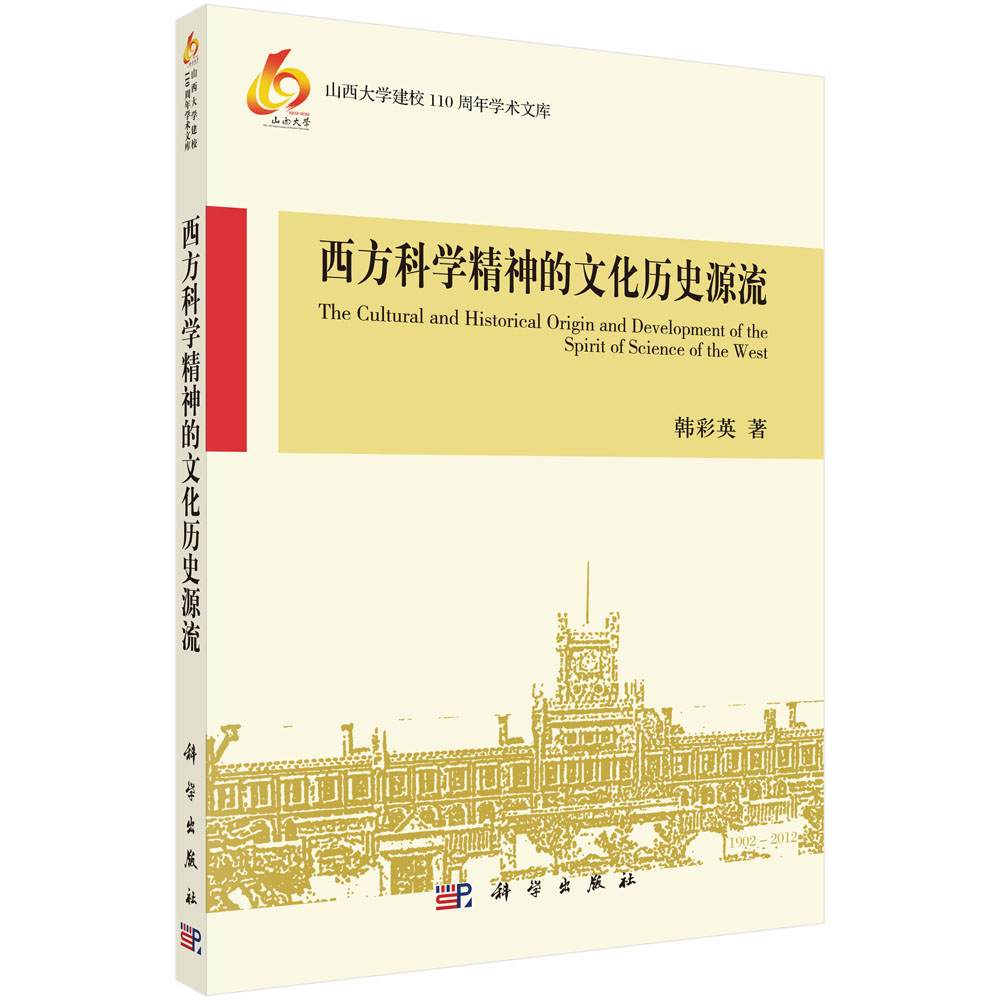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61.60
折扣购买: 西方科学精神的文化历史源流
ISBN: 9787030340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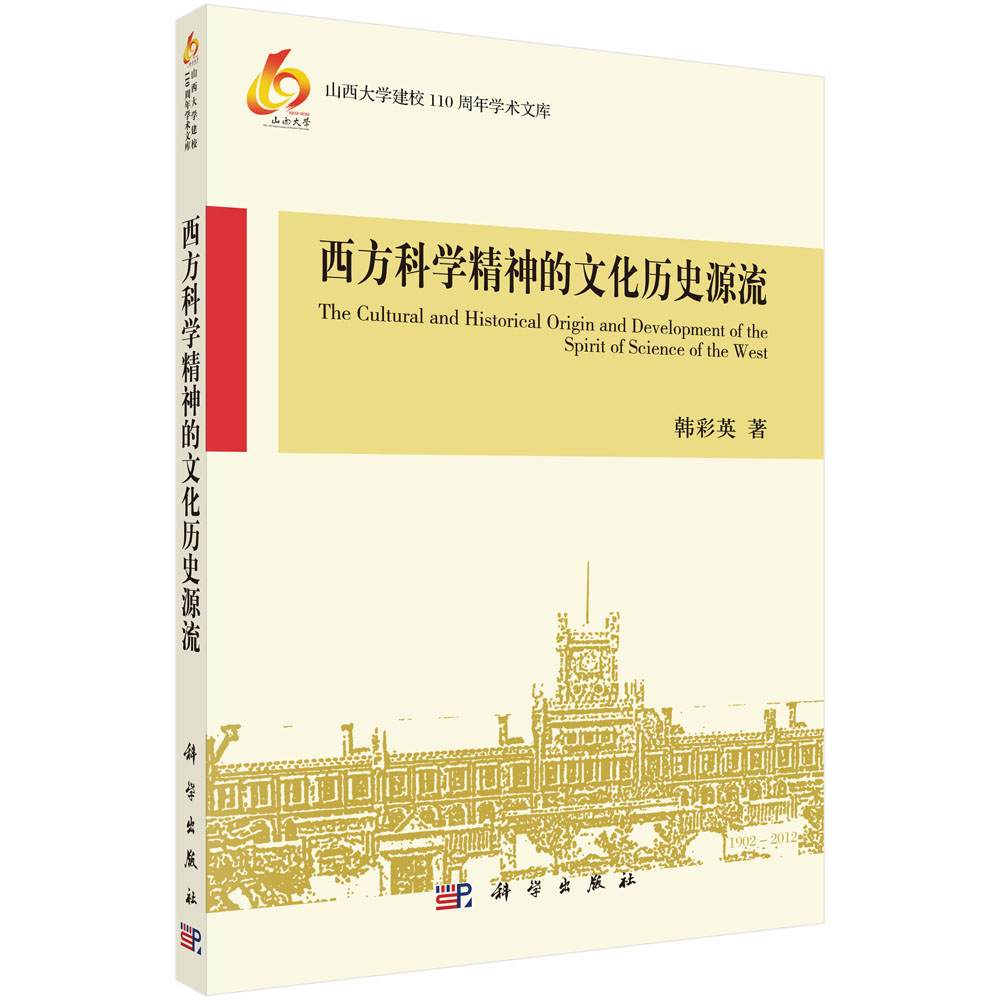
绪论
—、理解科学的动力和困难
近代以来,科学逐步成为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主流。科学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以及使人无法拒绝的吸引力,改变了人类的心智,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它就成为国力的象征、文明程度的象征。最迟从19世纪开始,科学作为一种学术类型,成了社会人文学科建设竭力模仿的模式;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它的境界成为世俗社会生活的渴望,它的实践者则成为世人竞相推崇的典范。如今的科学,其影响几乎无处不在。科学文明巳然是全人类共同崇尚的文明,科学文化巳然是全人类唯一普适的文化。如今的科学巳经赢得它应该得到的崇高地位。
就在科学家以自己的科学研究活动不断地塑造科学新形象的同时,哲学家以及社会和文化学者也在试图透过科学的外在形象来揭示它的内在精神实质。然而,尽管我们每个人心目中似乎都有关于科学的形象理解或者“概念图画”,但却无法说清楚它的完整形象。即使是非常专业的学者,也只是从某个或者多个维度给我们描绘科学的“分析性的”形象,而不是全景式的“图画”。数百年来,最为常见的就是关于科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特征的哲学“形象”描写,当然还有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以至于文化学等学科维度的诸多不同理解。
这就造成当学者们试图回答“科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至今也未能给出可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权宜之计只能是给科学以具体的特征描述。进而,当学者们面对“科学精神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就更加难以给出一个恰当的定义。因为比起“科学是什么”这样较为单纯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蕴涵诸多的现实迷茫和更多的价值考量。科学的高速发展使人无法仔细跟踪,技术与科学的混淆更使人向它投以批判和反思的目光。
尽管我们总是无法说清“科学是什么”、“科学精神是什么”,但科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精神影响力总在与日俱增。这就不难理解,热爱科学的人们总想对它有所了解,而且总是试图对它的“精神”做出真切理解。我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就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出现过两次讨论科学精神的热潮。
二、国内外科学精神研究概况
“科学精神”对于学术界一直是一个内涵不太确切、外延不太明朗的概念。绝大多数学者只是依照自己的理解来言说“科学精神”,或者是囿于片面维度的价值建构,或者是充斥过度自由的个人感想。总体而言,“科学精神”作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被言说的对象,是学者们关于这一概念的形形色色的“所指”或者“外延”重合而成的研究领域。“科学精神”这个概念所指向的就是整个科学领域(包括科学知识体系、科学研究活动和科学社会建制)中的根本因素、关键要素和所蕴涵的核心价值。这是一个由国内外为数众多、志趣迥异的学者们共同建构起来的概念和研究领域。
1.国外科学精神研究概况
历史地看,关于“科学精神”的论述,早在古希腊哲学家理解世界、构建知识体系的思想理论活动中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在其《形而上学》中专门论述从事“哲学”研究必备的条件。①作为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精神论说,在中世纪中晚期初露端倪。例如罗吉尔 培根(Roger Bacon,1219—1292)主张基于经验、以实验方法来构建关于自然的“新科学”。
随着近代科学革命的展开,欧洲大陆出现关于“科学精神”议题的专门论述。在那个“革命”的时代,关于自然知识、关于获取自然知识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哲学论述层出不穷。其中,哲学的方法论进路比较系统地体现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数学主义两种富有生命力的进路之中。弗兰西斯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新工具》和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哲学教程》典型地代表从经验主义到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追求,而笛卡儿(Ren6 Descartes,1596—1650)的《谈谈方法》则代表理性主义者和数学主义者的科学理想。笛卡儿哲学奠定了近代认识论的基础,也形成了关于科学精神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以马赫为首的批判学派哲人科学家基于对近代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反思和历史批判,揭露了近代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路的褊狭,阐明了科学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既要保持张力又要力求平衡的观点。
现代西方的科学史家(如萨顿(George Alfred LeonSarton,1884—1956)、页丹皮尔(W.C.Dampier)、莱昂 罗斑(Leon Robine,1866—1947)、林德伯格(D.lindberg)、米歇尔 塞瑞斯(Michel Serres)、爱德华 格兰特(Edward Grant)、约翰 亨利(johnHenry))、历史学家(如霍伊卡(R.Hooykaas))、思想史家(如梅尔茨(john Theodore Merz))、哲学家(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和实证主义哲学家),以及哲人科学家(如马赫(Ernst Mach,1836—1916)、彭加勒(JulesHenri Poincare,1854—1912)、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著述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科学精神”问题。
虽然这些哲学人文社会学者和科学家对于科学精神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是就“科学精神”的总体建构,尤其是历史变迁而言,国外还没有展开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而且,除了在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和规范结构方面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外,其他观点都非常零散、杂乱。
2.国内科学精神研究概况
我国学者对于科学精神的研究比较关心,付出了更多的热情和智慧。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俊彦就对科学精神给予了热切关注和精湛研究,他们从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方面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科学精神的要素和实质,并做出了恰当的理论表述。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启改革开放实践。伟大时代造就科学的春天,再次激起国人的科学热情。在全国上下日益重视科学的氛围中,学术界再次开始关注科学精神问题。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当代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科学精神,发表的文章数量不少,但总体而言,只有极少数学者的研究具有新见解,绝大多数著述流于泛泛之论,其学术水准让人实难恭维。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两位研究者。吴国盛在《科学的历程》中,无论是在特定时代的精神要素结构方面,还是在历史演进的线索方面,都对科学精神把握得较为到位,可惜只是滞留在了附带议论层面,未能展开系统论述。李醒民先生在30年的研究中,广泛研读国内外关于科学精神的文献,深人研究哲人科学家之科学精神集中体现者,详细论述了科学精神的诸多方面,从而形成了他关于科学精神之构成要素和结构的基本观点:
科学精神以追求真理作为它的发生学的和逻辑的起点,并以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构成它的两大支柱。在两大支柱之上,支撑着怀疑批判精神、平权多元精神、创新冒险精神、纠错臻美精神、谦逊宽容精神。这五种次生精神直接导源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它们紧密地依托于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从中汲取足够的力量,同时也反过来彰显和强化了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它们反映了科学的革故鼎新、公正平实、开放自律、精益求精的精神气质。科学精神的这一切要素,既是科学的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也成为人的价值,因为它们提升了人的生活境界,升华了人的精神生命,把人直接导向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生命,也是人的生命。①
目前,国内外还缺乏关于西方科学精神源流的全面而系统的专门研究和“全景式”梳理。绝大多数论述要么是关于科学精神某种维度的研究(如巴什拉的认识论维度的研究),要么是断代史式的研究(如爱德华 格兰特的《近代科学的中世纪基础:宗教的、制度的和智力的语境》),要么是关于某位科学家的研究(如柯瓦雷(Alexandre Koyre,1892—1964)的《牛顿研究》)。关于西方科学精神的起源、形成、发展,还没有比较详尽和系统的论著,有关论述散见于哲学史、思想史(包括科学思想史)以及哲人科学家的研究文献之中。
亚历克斯 罗森堡(Alexander Rosenberg,1946—)指出:“在西方世界,存在着某种特别的东西,它导致了科学的出现,科学的起源也表征了独特的西方文化的价值。西方文化和科学的特点彼此使得对方得以产生,这一直是这两个领域的学人值得讨论的问题。”②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我们国家对于科学及其精神实质认识的现状而言,关于西方科学精神之文化历史源流之研究,对推进国内学术界的科学精神研究,增进国人对科学及其精神实质的全面理解,提高国人的科学素养和精神素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研究的方法论路径和主要目标
李醒民先生指出:“科学文化是人类化的一种形态和重要构成要素,是人类的诸多亚文化之一。科学文化是科学人(man of science)在科学活动中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态度,或者是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遵循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态度。”③时至今日,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化业已达成共识,而且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解和研究需要更多地仰仗这种学术眼界。这种文化哲学观念事实上规定了科学精神研究最为基本的方法论路径。
科学是人类文化整体中演化、分化出的文化类型,似乎它与文化整体一直处在文化意义上的一致性与差别性辩证统一的演进中。仅就两者关系而言,科学文化对于人类文化整体是吸取与反哺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并不是一种异类的文化,虽然它在一些本质属性上与其他人类文化存在差别性,但它毕竟是“人”的文化,有着“人”的文化所共有的东西。无疑,“科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各种亚文化之一,不用说具有人类文化的共性。”“文化的一般特征,或多或少都能在科学文化中窥见。”①事实上,即使在古代文化中就已经蕴涵(自然)科学的一些文化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于科学来说还十分浅陋。在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近代科学革命之前人们在对自然的认知实践中,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制度和伦理规范中,已经包含近代科学的一些精神要素。这不仅在认识论意义上,而且在方法论意义上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胡塞尔曾指出:我们想要赢得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就必须“通过对历史的整体的批判地理解”,就必须“依据这一对整个统一过程的回顾进行一场认真负责的批判”。②萨顿也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③
无疑,仅凭科学知识体系本身我们无法领略科学精神要义,或者说,仅从科学知识体系本身而来的关于科学的禀赋和禀性的理解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如果仅囿于科学研究活动之行为实践和科学共同体之社会建制本身,既无法真正廓清科学精神的全貌,也无法真正把握科学精神的真谛。这是因为,如果把科学从其得以产生和赖以发展的文化历史语境(cultural-historicalcontext)中剥离出来,孤立地进行分析考察,这种认识论视界本身将不可避免地遮蔽一些科学精神要素。诸如实验、观察、测量器具和研究活动之行为这些外在的物质形态呈现,以及科学共同体之社会建制的表面的社会关系表征,既不可能全然显现科学之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精神特质,也不可能全然显露科学不可或缺的、与其他文化共有的精神气质。其结果往往会仅将异质于其他文化的特质说教,甚至仅将视科学为物质“力量”之信念,看成是科学的“圣经”,以至陷于科学万能论或者科学方法万能论的泥淖,使科学万能论和科学方法万能论在自己的理论视界中弥漫,从而郁结极端的“科学主义”情结。即使是一些试图理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关系的人文学者,甚至标榜要理解人文文化乃至其他文化的其他学者,也未能真正消弭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决然分离(而且或多或少存在对立)的文化意识形态樊篱。一些试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