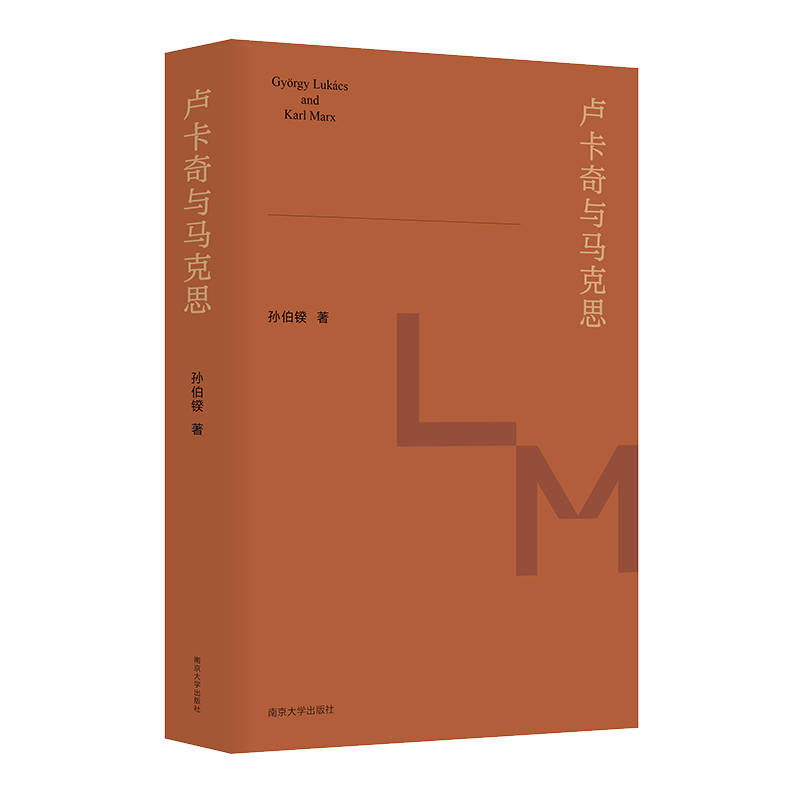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大学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5.66
折扣购买: 卢卡奇与马克思
ISBN: 9787305264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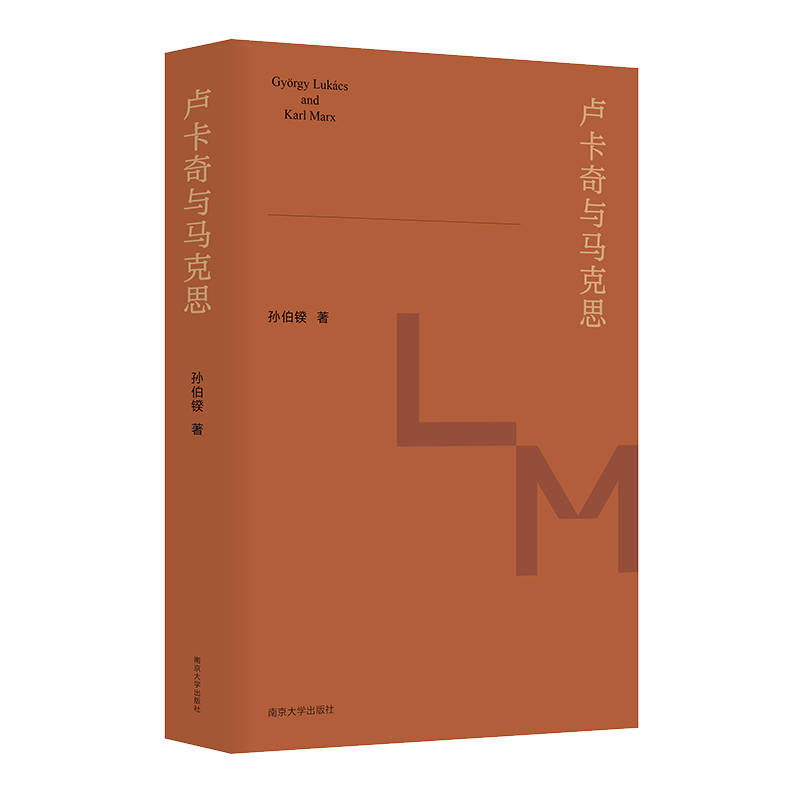
孙伯鍨(1930—2003),江苏泰兴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成员。出版著作《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卢卡奇与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第一章 物化和异化 一、 卢卡奇关于物化问题的基本思想 物化和物化意识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一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二是与之相适应的物化意识。从卢卡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基本思想有以下七点。 第一,物化和物化意识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是历史现象,不是自然现象。 第二,他认为物化和异化是一回事,物化即异化,没有把物化和异化区别开来加以研究。这一点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认为物化有两种:一种是指劳动的对象化,另一种是指异化。异化是指生产者的劳动在社会规定性上的物化,亦即社会关系的异化,而对象化则是指劳动在其自然规定上的物化。 第三,卢卡奇认为,物化、异化的结果造成了一个存在于人之外的第二自然。这个自然以其和人相异化、相外在的自然规律的形式来支配和主宰人的活动。第一自然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卢卡奇没有加以否认。正因为它是存在于人之外的,所以它的规律对人来说是异在的,既不是人们自己所创造的,也不为人们的活动所改变。所以人只能以直观的方式去把握它的规律,却不能达到一种超越自然规律的自由。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历史是人们自己所创造的,就其是人的创造活动的产物这一点来说,它本质上具有人的行为特征。可是在商品生产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存在作为社会活动的结果,却失去了人的行为特征,变成了一种不是由人的活动所控制,反而支配和主宰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的第二自然。从这一点来说,人的社会活动的结果就变成了类似于第一自然那样的第二自然,也以其独立于人的自然规律来支配人们、主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只能像对待第一自然那样以直观的、抽象反思的态度来面对这类规律。而以这种抽象、直观的即形式理性主义的认识方式所把握的规律,最多只能给人们提供可以利用的机遇,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不能达到和保障真正的自由。 第四,异化导致了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首先是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的对立。一方面是作为自然规律而与人相异在的客观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是和这种存在相对立的主体意识。从本来的意义上说,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作为活动的产物,它应当是主体活动的一个因素、一个层面。现在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第五,由于异化而产生的社会历史中的二元对立,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就表现为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意识中的二律背反表现为思维形式和概念内容的完全脱节,表现为自在之物的非理性和不可克服性,表现为人们对总体性把握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和割裂。所以在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哲学上便是自在之物的问题。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恰好是这个社会的不可克服的物化和异化状态的真实写照。康德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在认识论上重视数学和数学化的自然科学,以为认识的本质就在于使对象符合构成这类精密科学之基础的直观形式和先验范畴。所有这些认识的结果在知识宝库中都表现为抽象的、形式理性主义的东西,理性变成了一堆脱离内容的抽象形式和公式。能够融入这种抽象的理性容器的就是可知的,不能融入理性之中的就是不可知的、非理性的内容,即自在之物。这样一来,能够被认识的就只是对象的形式。形式主义的、抽象反思的认识方法造成了内容与形式的脱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主要就表现为这种数学化的形式主义:把客体和对象变成形式上可以计算、可以预见、可以推论的东西,经济学、社会学以至法学等等都在广泛地运用数学和计算技术。在这些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中,人们只要求数学和形式推理的合理化,把一切都变成可以统计的对象。这就出现了卢卡奇在本书中借用韦伯的研究成果来描述的那种情况,甚至人也成为被计算的对象。 第六,因此,卢卡奇认为必须突出实践的观点。卢卡奇提出实践的观点首先是同抽象反思的观点相对立的,因为抽象反思只涉及对象的形式。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差别就在于单纯的理论只涉及对象的形式方面,它是抽象反思的规定,把对象只当作可以从经验上加以直观的异己的存在物。社会生活不同于自然过程,它必然既能从形式方面又能从内容方面加以把握,而这样的把握方式只能是实践。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实践的把握高于理论的认识,认识论首先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因为这个实践不仅创造了历史,而且改变着历史。 第七,与此相联系,卢卡奇进一步认为,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是认识社会历史的唯一正确的原则。总体性原则一方面是把人们的活动、行为看作一种总体性的实践,是作为总体的主体性即阶级的实践,而不是单独的个人实践。而作为这种实践结果的社会存在也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卢卡奇提出辩证的总体性原则,把它作为把握社会生活的一个方法论原则,这是有创见的。因为只有立足于这种辩证的总体性原则,才能把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和有机构成的整体去认识、去把握。由此获得的理论,作为一种创造和变革历史的行动着的人们的主体意识,才能和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为实践。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卢卡奇把改造社会历史的阶级实践和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区别开来。所以,他早期提出的实践概念,并不包括生产劳动。这是因为认识自然不同于认识社会,他认为人们不能提出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因为从总体上把握自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把握自然界总是先搜集材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找出其局部的规律,这是反思认识的一种逐步拓展的前进过程。但是对于社会的认识则不能如此。认识社会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就必须从总体上去把握它,而不能局限于把握它的局部规律,满足于建立关于社会的局部性体系。他认为在认识社会问题上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态度,他们把社会规律当作自然规律来认识。在卢卡奇看来,由此获得的规律是物化、异化的规律。人们越是贯彻它,就越是会强化这个社会。二是改良主义者的态度,他们主张对社会进行局部的变革,满足于一点一滴的改良,而不是从总体上进行革命,因此对资产阶级社会也不要求从总体上去把握。三是卢卡奇所主张的总体性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一致,坚持把资产阶级社会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和生理过程去认识。他认为,在总体性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无产阶级实践,这种实践的目的是彻底地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卢卡奇的这种观点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卢卡奇提出总体性原则既可以从认识上来理解,又可以从实践上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认识和实践的一致。正因为总体性认识是总体性的,所以必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在历史起源上。社会生活中的物化现象、二律背反等等,所有这些都要从历史起源上去加以把握,必须弄清其历史的生成与起源,就是说必须把它们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理解,在静止状态下是无法理解的。二是总体性或整体性。通过发现中介范畴和联系环节的办法,把一切貌似对立的现象理解为一个统一整体的有机构成因素,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生活中的二元对立,即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他认为在社会历史中不应该有不可认识的、非理性的彼岸世界的存在。卢卡奇的这个思想最终所要证明的就是这样一点,即必须建立主体与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在历史中的统一。他认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不能超越历史的范围来考虑和解决。因此,自然的问题是被置于《历史与阶级意识》所讨论的问题范围之外的。 从根本上讲,卢卡奇的物化和异化理论脱离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卢卡奇相对照,马克思在异化和物化问题上的看法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