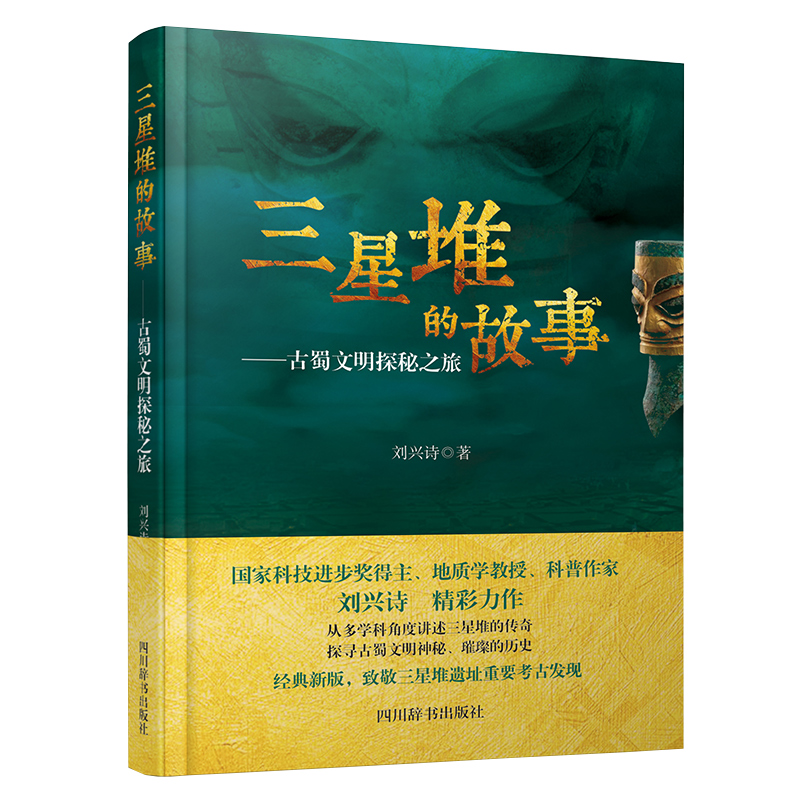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辞书
原售价: 39.80
折扣价: 27.46
折扣购买: 三星堆的故事——古蜀文明探秘之旅
ISBN: 9787557908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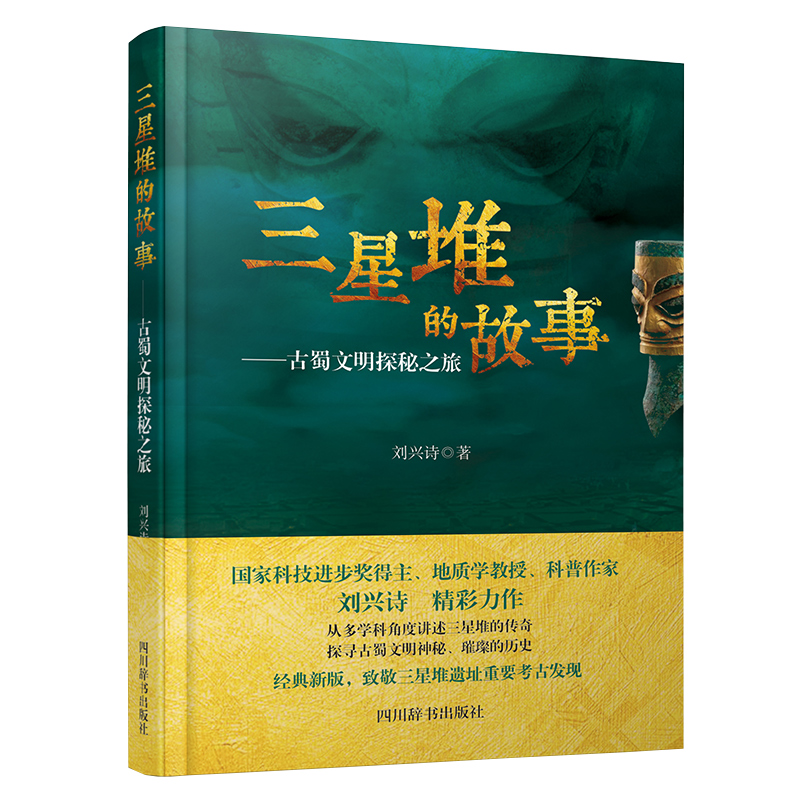
刘兴诗,男,1931年出生,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大学、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等校任教,地质系教授、史前考古学研究员、果树古生态环境学研究员,中国第一代科幻小说作家。194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在境内外出版近300本书。美术片《我的朋友小海豚》获意大利第十二届吉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荣誉奖、总统银质奖章;童话作品《偷梦的妖精》获第一届海峡两岸中华儿童文学创作奖;还曾获第一届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共获奖100余次。
写在前面的外行话——代序 写这本书,有些不胜惶恐,好像应聘人怀里揣着街边买来的一张假文凭,面对着人事科长冷冰冰的目光。也不胜激动,颇有运动员(中国男足除外)有幸登上奥运会领奖台的感觉。 为什么惶恐? 因为在下毕竟不是考古专业的科班出身,说得直白些,纯粹外行一个。面对深奥的考古科学,所知并不多。正如在下一个好友,一位当代四川考古学界的泰斗,手指在下的鼻子,大喝一声道:“你娃不懂!” 听了这话,在下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简直像是吃了豹子胆,也半开玩笑回敬说:“你娃也不懂!”他听了一怔,随后大家哈哈一笑。差距,尽管有差距;朋友,照旧是朋友。友谊地久天长,不是什么力量都可以损伤的。 为什么我敢这样说?难道真的不知天高地厚,脑袋进水发疯了? 不用说,这是开玩笑,不能当真的。可是从某种意义而言,似乎也可以算是有恃无恐。 我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出身,学科体系属于理科,距离文科范畴的考古学,似乎相距十万八千里。有什么把握,胆敢向考古界的内行叫板?如果要较真,依仗的就是自己的专业本事。搞科学研究避人锋芒,不从正面交锋,而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又有什么不可以?翻一翻《孙子兵法》,就是这样说的。休道黑旋风李逵势不可当,来、来、来,浪里白条张顺邀请你下浔阳江玩一下水。 话说到这里,需要说几句有关学科发展的题外话,来作为开场白吧。 一、科学研究不能关门 科学研究不能关门,科学发展必须开放。 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涉及许多领域,和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在别的兄弟学科协助下,才能共同努力开拓更加广阔的视野,使研究更加深入,顺利进入更高的层次。无视相关学科的联系,只顾自己走独木桥,势必影响本身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试看埃及研究金字塔,并不设置任何限制,干脆称为“金字塔学”,各种五花八门的学科都可以自由介入。笔者就曾经在许多场合大声疾呼,建立我们自己的“三星堆学”“金沙学”。抛弃传统的门户之见,彻底敞开大门,诚心诚意欢迎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研究。 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一些相关学科对古蜀文明的研究成果,的确曾被一些自视正统的学者不屑一顾。 是的,如果完全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不是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仔细反复论证,自我怀疑检验;而是抱着急于求成的态度,仅仅凭着脑瓜灵机一动冒出的什么奇思妙想,抓住一点就无限扩大,只择取对我有利的材料,拒绝不利材料,迫不及待地通过新闻媒体或者在网上宣布有什么震惊世界的伟大发现,生怕别人不知道,害怕有人抢了头功,这种做法,的确不值一哂。让这些幻想家去自我陶醉吧,不必耗费精神和他们纠缠。君不见,如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的确存在。 有人曾突发奇想,认为自己的家乡四川盐亭一带,曾经坐落于“四川盆塞海”之上,那里的一个个孤立的丘陵都是“群岛”,并进一步发展为“远古联合国”的“高度文明”,并说那里和非洲都是古人类诞生的源地。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贸然宣布这样的“伟大发现”,且不准别人议论半句,叫人怎么信服?当然啰,这样的玩意儿另当别论。只要不当真,茶余酒后说说也无伤大雅。别人要说,就让他去说吧。 话说回来,针对现在我们要谈的古蜀文明而言,如果不是信口开河,而是从严谨的科学态度出发,以相关的科学知识介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能统统都一棍子打死。常言道,兼听则明。百家争鸣得有雅量,对不对? 须知,当今已是科学飞跃发展的21世纪,不再是几百年前夫子们论经说道,一切以一本经书为准的时代。不同学科协作研究探讨,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古蜀文明研究是否应该认真考虑,在传统的金石学和文献学的基础上,真诚地请进来、派出去,多方面地引进其他学科的支援? 出于这个原因,笔者曾经在《成都商报》的支持下,根据三星堆鸟类图谱,事先请教了一位因病不能同行的鸟类学家,组织了几位青铜冶炼学、金属切削学、建筑学和医学的专家,打着“多学科研究三星堆”的旗号,前往三星堆考察,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力图以此打破僵局,开展轰轰烈烈的多学科研究活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活动无疾而终,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跨学科研究是当前一个潮流,愿有关方面能够真正重视。我这个人老是不安本分,就是有点“乱来”。常常不按照旧小说的描写或者京剧开锣后的规矩,摆出堂堂之阵,双方架住刀枪,通名报姓后,兵对兵、将对将地正面厮杀。而是野里野气,喜欢像魏延献计一样出奇兵,把一门学科输入另一门学科,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样做虽然碰过钉子,但也尝过一些甜头。 请让我说一说,尝过一些什么甜头吧。 我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西天山,有一片野生苹果林。过去中国、苏联园艺学界一直未能解决其来历问题,不过,一般认为在全球性的第四纪冰期时代,这里有可能是一个物种的避难所。 我的两个好友,新疆农业大学钟骏平教授、伊犁园艺研究所林培钧所长,召唤我去试一试。我除了吃苹果,分得清红苹果、青苹果,哪里懂得这门学问,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可是碍于朋友的情面,不得不硬着头皮打鸭子上架。心想,此事绝对不能从自己根本就不懂的什么果树基因学、遗传学等方面入手,必须另辟途径方能奏效。左看右看,看出一个症结所在。过去长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专家们太专了,思路过于狭窄,没有拓宽视野。我何不反其道而行之,绕过果树本身,来一个大包围?反正自己是外行,错了也没有关系,有什么好怕的?想不到思路一放开,运用自己熟悉的古气候学和古环境学等方法介入,居然一下子把问题破解了。这里并不是避难所,而是第四纪冰川活动的一个中心,野生苹果其实是在冰川消退了之后,从中亚平原迁移过来的。 这是一个国家自然基金的重点项目。我面对的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却也是很重要的子课题。论文发表后,获了奖,把老林喜欢得不行,立刻聘我为果树古生态学研究员。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哈萨克斯坦农科院闻讯又专门把我请去。他们的一个果树研究所所长,是该国总理的“毛根朋友”(四川方言,从小长大的朋友),亲自到边境迎接,海关关长又代为填单并宴请,来回一切免检,好像是VIP式过海关。我研究了一下该国境内西天山同样的问题,如同旧小说里火头军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一样,我这个火头军也扬眉吐气,一箭定了中亚的西天山。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果树古生态学研究员这个职称是侥幸“蒙”来的,并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能耐,还得处处夹着尾巴做人。不过说起来,这就是多学科研究的好处。 呵呵,说白了,我有什么能耐,不过是像脑筋急转弯,你没有想到,我侥幸先想到了而已,一点也不值得吹牛。为什么在这里提起?就是以此为例,说明科学研究不能走独木桥,试一试多学科配合也许更加有效。 再说一个例子。我这个地质汉子,居然和史前考古学沾了边,也得到一个研究员的称号。 那是发现北京猿人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在世时,布置给首都自然博物馆馆长周国兴的一个任务,深入研究柳州白莲洞遗址,这也是一个国家自然基金的重点项目。老周负责古人类研究,约了童恩正负责文物研究,我负责洞穴地层研究,我们仨号称“白莲洞三剑客”。裴先生去世后,贾兰坡先生继续领衔。经过多年工作,我们取得了海内外学界公认的成就。 1994年课题结束,在柳州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在下有幸成为包括贾兰坡、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安志敏两位院士,以及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主任吕遵谔、周国兴在内的中方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协助周国兴主持会议,负责现场考察讲解。那一次建立了一个考古文博单位,贾兰坡担任名誉馆长,周国兴担任馆长。因为在下从第四纪地质学切入白莲洞和其他遗址的研究得到肯定,就在会议上颁奖并授予我一个研究员的名分,算是和考古学沾了一点边。这也是把一门学科运用于另一门学科的收获。 我的确不懂金石学的精髓,甚至连懂皮毛也说不上,不能就具体的文物标本鉴定多说一句话,对古典文献相对也不够熟悉,不能与真正的考古学家们相比,真的是“我娃不懂”。但是在下的专业研究方向是第四纪地质学。从上述例子看,也和史前考古多少沾一点边。 什么是第四纪?大致说来,就是人类发生、发展的最新地质时代。种种人类文明统统发展其间,岂有和考古学没有半点关系之理? 在第四纪地质学中,在下平生研究的内容,就主要包括古气候、古地理环境等。我的一个最主要的科研基地就在四川盆地及其邻侧地区,古蜀文明就诞生在此时此地。从这个角度介入史前考古研究,要说是“外行”,也真有些“外行”;要说是“内行”,就毫不客气地可以算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内行”了。加以地质学和其他杂七杂八学科方面的浅薄基础,所以我才有底气叫板,向那位老友半开玩笑、半认真,放肆地回敬一句“你娃也不懂”了。 说到这里,我十分怀念已故的四川考古学界前辈冯汉骥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伊始,他就不耻下问,一再召唤不才,共同研讨一些问题。甚至在当年率领全体弟子,嘱我带路到资阳人化石地点考察,向大家介绍情况。 他的高徒童恩正更是我的铁哥们儿,不仅一起写科幻小说,还总是在专业工作上并肩作战。他的许多论文常常首先给我看,叫我出主意、挑毛病。他还派了两个得意门生,如今都是四川地区考古学科的骨干人物,不辞辛苦地骑着自行车,大老远从四川大学前来我所在的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前身)进修第四纪地质学。 我和恩正最后一次到野外并肩考察,是他在去世前不久从美国回来。当时由其高徒之一,现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陪同,一起前往研究新津宝墩古城遗址,他诚意征求我的意见。 现今的王毅院长和金沙博物馆副馆长朱章义也虚怀若谷,十分尊重其他学科的研究,保持了冯汉骥先生与童恩正以来的传统,令人十分感动。 我十分怀念冯汉骥先生和童恩正,期望有机会能够像配合他们一样,和现在的四川考古学界有更多的精诚合作。再一次充当马前卒,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和研讨有关问题,扩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创一条新的路子。如果建立起开放的“三星堆学”和“金沙学”,岂不很好吗? 二、对“一家之言”的看法 学者著书立说,自然要树立自己的“一家之言”。 不过,我常常想,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一家之言”又起什么作用。 也许在下毕生从事地质学研究,花岗岩看多了,完全变成花岗岩脑袋,活脱脱“化石”一个。对于“一家之言”的问题,有些顽固得近于不开窍的想法。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不用说,是破解一个个问题,推动研究工作一步步深入发展。 在不断摸索探讨的研究工作中,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想法,这就是“一家之言”了。问题在于一个个“一家之言”,只不过是在研究某个问题的过程中,一时产生的某种说法而已。一旦问题弄清楚了,就应该拨云见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在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里,显得特别重要。 当然啰,在一些人文科学范畴内,也不一定这样。例如一些文史哲的研究,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强求一致。 请让我再说一遍。“一家之言”的目的,是为了多方探讨,最终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树立个人的权威以及其他。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我信奉一道数学题只有一个答案,绝对不会华罗庚得出一个答案,陈景润又得出一个答案。虽然有些迷茫的古史或者其他问题有多角度探讨的空间,在讨论的领域内,提出不同的“一家之言”,可以活跃思维,有助于从多方位探索问题的实质根源。但是在某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上,例如我在后面将要讲到的三星堆铜、金、玉的来源,以及几千年来古气候发展阶段等问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常常告诫学生和助手,在一些问题面前,只有对和错两个答案。错了,就错了,不能只顾自己说得圆就心安理得,千万不要以什么“一家之言”掩饰自己的错误。学术研究属于公众,绝非个人名利场。对于一个科学问题,只能越研究越清楚,不能把明知错误的观念也混淆其间,树立错误的“一家之言”。这样不仅对现在没有好处,也为后学者开了一个恶劣的头。一些不谨慎的后学者就会把我们的错误意见,作为“前人学说”来继承发展。这看起来热闹非凡,实际上却是越来越混乱,甚至于不可收拾了。试问,这除了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对科学研究有什么好处? 话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次申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并不是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多方面探讨,不同意见也可以活跃思想。但是某些十分具体的问题,常常就只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自己如果碍于面子,不敢承认错误,洋洋得意于什么“一家之言”,那简直就是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三、“三个敢于”,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我常常对学生和助手说,科学研究和做人,都应该坚持“两个严谨”“三个敢于”,就是严谨的科学态度、严谨的科学方法,敢于设想、敢于怀疑、敢于认错。 “两个严谨”说的是,研究态度必须端正。不能以出风头为目的,抓住什么点子就不放,无视已有的科学事实,千方百计维护自己,凭着一点认识就轻易下结论。研究过程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不能以自己脑瓜里的一点主观成见,代替实验室分析以及其他科学手段,极其轻率地发表意见。 “三个敢于”说的是,可以放开思想去设想,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境界,脑瓜里冒出一个新奇念头就沾沾自喜。还必须认真怀疑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从不同角度审视甚至否定自己,进入第二个境界。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必须公开承认错误,不能姑息自己,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也是第三个境界。 辛辛苦苦得来的设想,萦系了自己许多美好的向往。一旦放弃,甚至公开认错是极其痛苦的,似乎没有面子。其实,面子这个问题最害人,一害科学,二害别人,三害自己。正确的态度是一旦发现错误就立刻认错,这才是最有面子。我自己常常这样做,举一个例子吧。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前一个多星期,一批地球物理勘探专业的1978级学生,毕业30年后回来。见到他们后,我如释重负,一个特殊的心愿可以完成了。 30年前,我曾经带领他们在银厂沟附近的小鱼洞后坝沟考察,一个问题讲错了,给了他们错误的概念。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他们居然有大半个班回来,真是让我大喜过望。我把他们带到野外现场(想不到几天后,这里就发生大地震,我们住的旅舍和合影留念的地方,统统化为一片废墟),第一件事就是站起来,向他们认错道歉,重新作出正确解释。 在这样的场合,他们感到非常惊愕。一个现在已经成为自然资源部一个部门负责干部的女生说:“那一次您的讲课,我们还记得很清楚。其实,现在您不必旧话重提,我们也不会过多思考这件事的。” 她说得对,我不说也没有关系。说出来,会破坏了他们的美好回忆,还影响了教师的威信。但是我必须这样做。我过去说错了,现在就必须当着学生认错,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教师向学生认错不丢面子,隐瞒自己的错误才是最可耻的,才最没有面子。 我在这里说这段话,就是表明态度。如果在这本小小的书中有什么错误,我一定公开承认。让我们抛弃个人的一切私心杂念,把这个课题探讨得更加清楚吧! 看来,科学研究也应该“一大二公”才好,共同为探明一个真理而奋斗,勇于探索,也勇于放弃。而不是百般维护自己的观点和地位,树立自己的威信和“一家之言”,哪怕是错误的。 我这样啰里啰唆说这一大通,哪像什么文字简洁的序言,简直就是正文了。然而我认为也许这比一段正文还重要,因为在这里强调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一是科学研究不能单打一,必须多学科配合;二是科学研究是严肃的,要坚持正确的科学研究态度,它绝非个人树立“一家之言”和扬名的处所。请读者多多理解和批评,谢谢! 我的这个开场白说完了。最后特别申明,我深深明白自己只有几两重,绝对不敢毫不自量地在这里冒充什么专家,也没有半点哗众取宠之意。能说几句就说几句,不能说的就闭口不言。别人说得少的地方说几句,别人说得多的地方就不说。所以这不是一部正规系统的古蜀文明史,而是从人所未见处,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仅仅是自己的一部读书笔记,不敢僭越风雅自诩“学说”。只是希望完成多年来的心愿,尽力推动多学科研究,抛砖引玉,盼读者诸君明察才好。有机会也期望能够让考古专家们随便看一眼,如果能屈尊提一点意见,那就不胜荣幸了。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下明摆着是外行,就不必过于畏惧高高在上的行家里手了。由于这是一种试探性的研究,我又是门外汉,肯定有许多不当之处,还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如果我错了,决不以什么“一家之言”而逃避,一定公开承认错误,决不文过饰非。 成都理工大学“八〇翁”刘兴诗 汶川大地震后三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