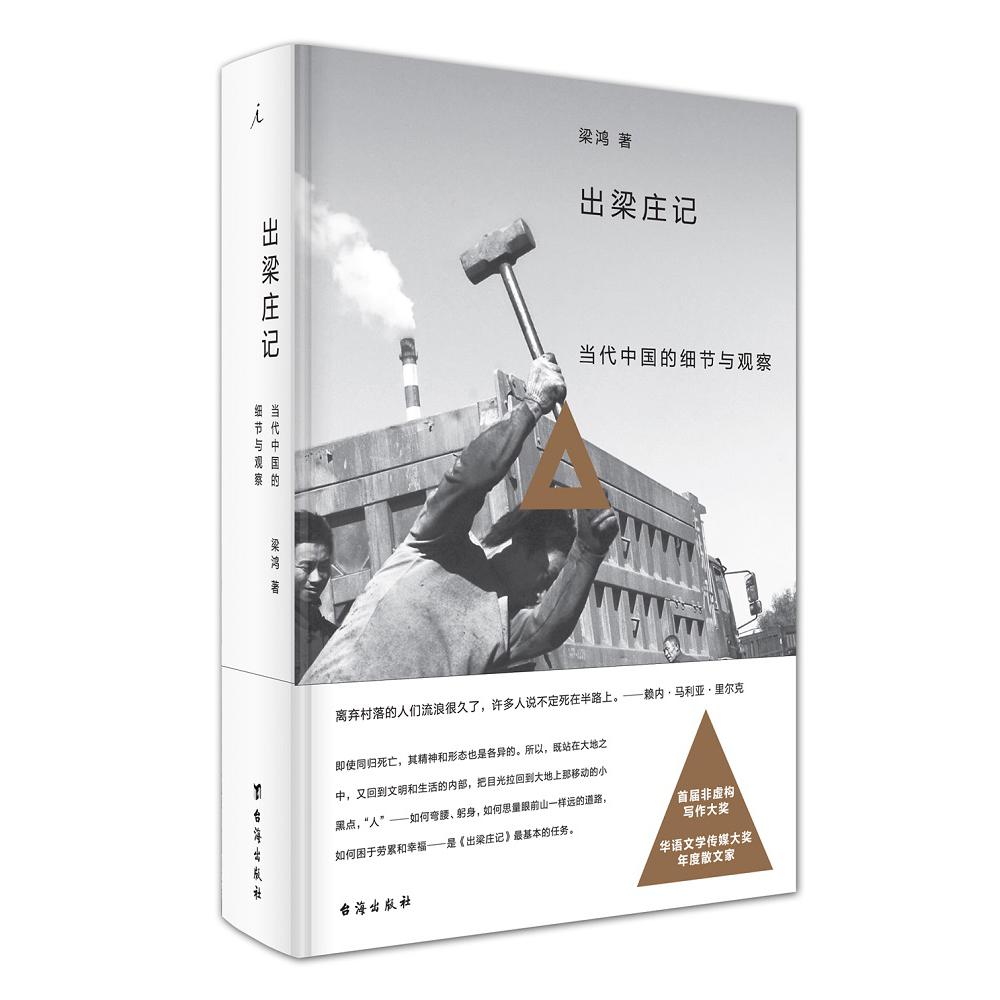
出版社: 台海
原售价: 72.00
折扣价: 44.70
折扣购买: 出梁庄记(精装新版)
ISBN: 9787516809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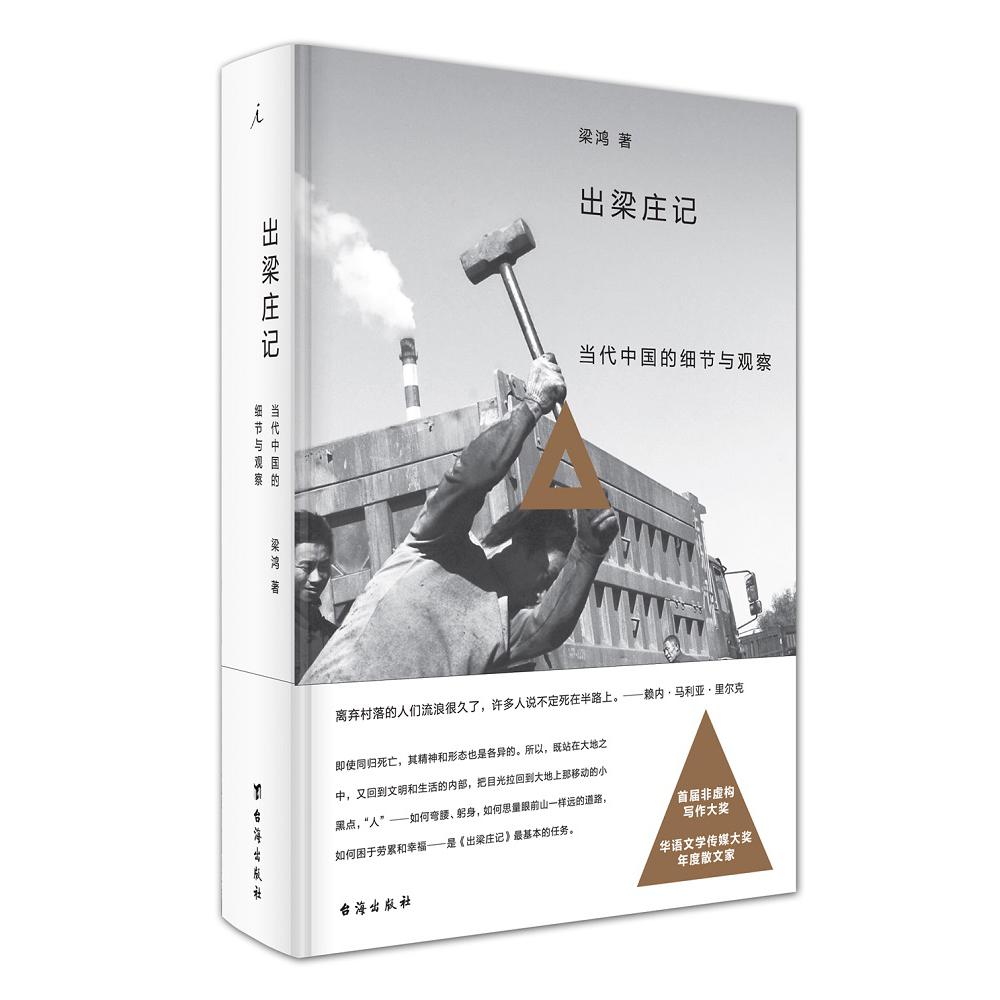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著有文学代表作《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神圣家族》等;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首届青年作家以及《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等。
闲话 2011年的夏天,穰县持续暴雨。湍水又涨了。 暴雨之中,浊浪滚滚的湍水把连接南城和北城的两座石桥冲得摇摇欲坠。有好几天时间,河水漫过石桥,河岸两边的树也终于抵挡不住洪水的力量,纷纷倒在了河中。大水过后,石桥重又露出水面,石基已经有些动摇,护栏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一辆农用车在过桥的时候掉了下去,车毁人亡。政府在桥边立了一个鲜红的牌子:“禁止车辆来往。” 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又一具尸体挂在桥边不远处那裸露的交错的树根中。尸体被捞了上来,特征如下: 男性,50—55岁,枯瘦,头发、胡须皆长至颈部,嘴巴塞满泥沙,牙齿全无,腿部溃烂。 死者被拍了照,贴在各乡镇派出所的广告栏处。很快,有人传回信儿来,那死者好像是梁庄的梁军。梁军,和我同辈,他们兄弟三个,大哥是兴,他是老二,老三已记不起名字,是一名惯偷,常年坐监狱。兄弟三人都是单身汉。他们的姐姐接到信儿,赶紧往派出所跑,看到照片,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跟随而来的兴哥却沉着脸,一言不发,拨开同去的村里人,一个人先回家了。随后,派出所让他们去城里停尸处认尸,兴哥死活不去。任谁劝说,只是坐在梁庄小学他那借来的房子里,抽着纸烟,挠着花白头发,一动不动。 兴哥不去,尸体就无法确认。毕竟,他是最直系的亲属。况且,经过长期饥饿的洗礼,与人隔绝的孤独和河水的浸泡,那尸体确实具有模糊性。他们的姐姐偷偷去城里认尸,哭了一场,因为弟弟不认,也不敢擅自确认。更何况,真的确定下来,火化还要花钱。最后,民政局出资火化了尸体,以“无名尸”结案。 关于梁军如何淹死,梁庄人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饿昏了,栽到了河里。2008年我最后一次在田埂上见到军哥时,他已经是流浪汉,靠捡垃圾为生。在和我对视的时候,他陌生的、惶恐的和躲避的眼神曾让我颇为迷惑。也许是天生愚笨,他捡到的东西并不多,也卖不到什么钱,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几个月都没人看见他,大家并不在意。也有人说,可能是去河边捞东西吃,淹死的。还有人说是晚上睡在堤岸上,被冲下去的。不一而足。 至于兴哥为什么不去认,大家的看法倒非常一致。一旦认了,军哥就要被销户。作为户主的兴哥,要遭受两重损失:第一,军哥的低保不能再向国家要了;第二,军哥的地他也不能种了,一亩地呢。现在,军哥虽然不见人影,但也没有人能证明他死亡,国家就不能随便销户,兴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种弟弟的地,吃弟弟的低保了。 我回梁庄的时候,军哥的尸体刚刚火化,关于这件事的闲言碎语正在村庄密密流传。梁庄人对兴哥的行为很是看不惯,有责备之意,但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道德评价。是兴哥太穷了?他,和军哥在村庄都太微不足道了?抑或是他那未老先衰的花白头发,他孤苦一人的生活让梁庄人的同情大于批判?不管怎样,这仍然是本埠新闻里的重要事件。梁庄人边重复地说了多遍的观点,边摇晃着脑袋,表示着不可思议。 在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兴哥拒认军哥只是梁庄的小闲话,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闲话。小闲话只是个引子,是戏剧里的丑角,是一部小说的过渡,是草蛇灰线,最后拉扯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目标和指向。 建昆婶的小儿子红伟的房子就盖在梁庄新老公路的交叉口,这个交叉口是进出梁庄的主要通道。红伟前几年从深圳回来,盖了房子,又贷款买了一个货车,搞起了运输。红伟好客,村里人,或是邻村去吴镇赶集的熟人来回的时候都会到他家坐下喝会儿茶,聊聊天,说会儿闲话。也因此,以他家为中心,辐射周边几家,成了梁庄新闻传播中心。 我回村庄的时候,一群人正坐在红伟家的大门口,两个小桌子,一桌在打牌,另一桌在喝茶,七八个小孩子各自一堆儿散落在周边的沙堆旁玩耍。红伟在他那辆大货车下,叮叮当当地修补。 初看到我,大家仍然是一脸的怔忡,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我打招呼。在接触到他们眼神的一瞬间,我发现,他们对我还是陌生的,就好像我不是梁庄的闺女,好像我从来不曾回来过,我从来都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过交集。 或许,事实也是如此。2008年和2009年那几个月的村庄生活,即使在我,也很遥远且模糊了。对于梁庄的乡亲们而言,那几个月甚至连涟漪都没有泛起,这样的来来去去太多了,政治、经济、亲人,都是自管自地来了又走,走了再来。 一刹那的陌生之后,我这些哥、叔、婶、嫂、爷的表情马上变得丰富起来,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和我开起玩笑来。人群逐渐围拢过来,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嫂子、婶子、奶奶,看着我,不断地感叹,又一次提到我早已去世的母亲,慨叹“麦女儿”人有多好,如果活着该多有福气。麦女儿,我母亲的名字,她那一辈的梁庄人都这样叫她。 红伟家左边斜对面,旧公路的另一边,是已去世的光河的大房子。院子一角的刺玫、月季、大丽花,在夏雨的不断浇灌下,正肆意开放,繁密的花朵把枝条压得朝向四面八方伸展。大门上贴着黄色的对联: 迎新春倍思亲人 贺佳节缅怀前辈 德高望重 光河是绝食而死的。在死前的两个月,他就拒绝进食。他每天斜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口,仿佛在期盼着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看,眼神空茫,没有焦点。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一直这样一个姿势,直到虚弱得不能动弹。光河的老婆花婶把一个吸管插到光河的鼻孔里,每天用针管注入流食。只有此时,光河才把头转过来,绝望地看着花婶,他拒绝吞咽,可是,吸管直接进入他的胃里,他无力抗拒。梁庄人都说,他是在等着他惨遭车祸死去的一儿一女来接他。这座宏伟的、用赔偿钱盖起来的房子,是他宝贝女儿和儿子的象征。他每天躺在儿子和女儿的心脏里,悲伤地怀念他们。据说最后半个月,他忽然又想活了,拼命地吃东西,每天乞求花婶给他弄东西吃。他吃完就吐,吐完再吃,吃完又吐,最后,还是死了。2010年11月21日,光河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1. 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出梁庄记》精装新版重磅出击——此次精装新版对图文进行了全面修订,增加梁鸿新序《给父亲》,并特邀陆智昌老师操刀设计,重磅出击。《出梁庄记》是作家梁鸿继《中国在梁庄》之后,集中书写离开梁庄进城打工者生存状态的非虚构作品。作家走访了10余个省市、采访340余人,以近200万字图文资料整理撰写而成。《出梁庄记》因其纪实性、文学性和社会性已成为国内非虚构文学的经典代表作。 2. 当代乡村与中国最完整的文本《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首次集合出发——《中国在梁庄》叙述的是作家与她的故乡,而《出梁庄记》则是中国的细节与观察。在梁庄,望故乡;出梁庄,见中国。在梁庄的本地人与出梁庄去外地的打工者原是不可割裂的统一体。此次关于“梁庄”最完整的文本,即《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本书首次集合出发。从“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乡村与中国最真实的形象。 3. 附赠别册《梁庄》,特别收录关于“梁庄”议题的经典阐释——《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出版之后,围绕“梁庄”及其承载的“乡土中国”“当代中国”“乡村纪实”等话题不绝于耳。别册《梁庄》即收录了社会各界关于“梁庄”议题的经典阐释,包括《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出梁庄,见中国》以及作家本人关于“梁庄”议题的反思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