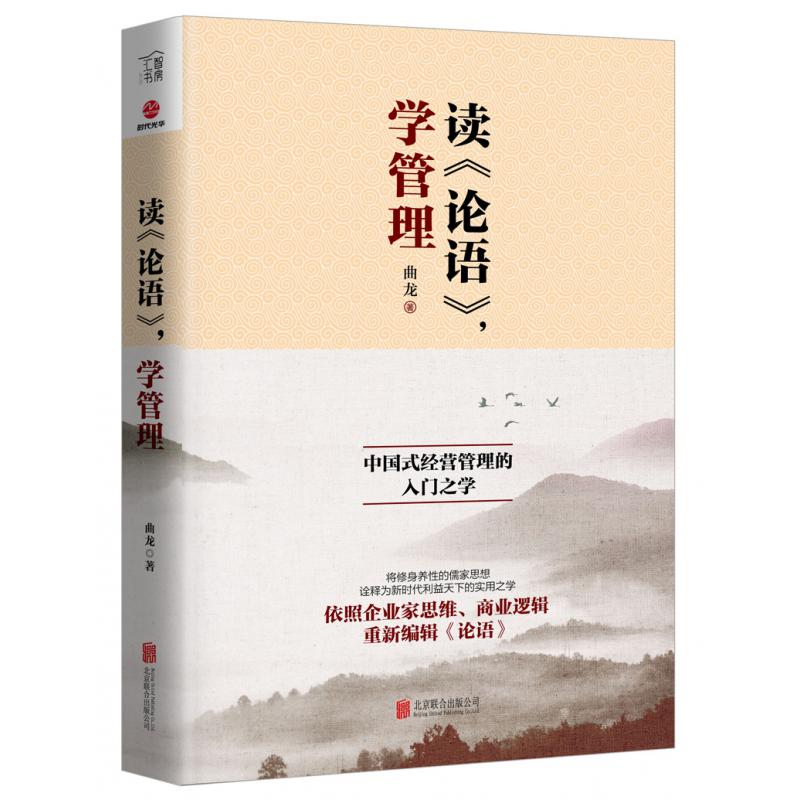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联合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0.80
折扣购买: 读《论语》,学管理
ISBN: 9787559622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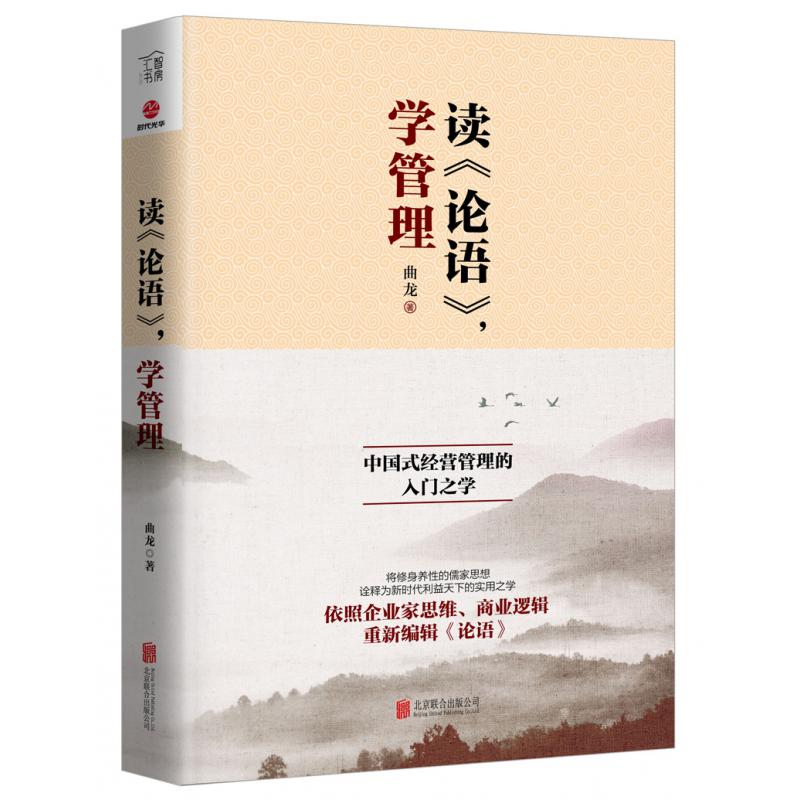
"曲龙 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国学基础严谨扎实。10年世界500强外企高管经历,10年民营企业营销总监经历。他能将儒家学说的经世致用,解读为现代企业经营的实际;能将晦涩难懂的古文,理解为通俗易懂的故事;能将国学智慧中奥妙难测的元点,阐述为实学实用的工具模版。"
"第 一 章 《论语》是可以重新编辑的 儒家思想,只是从近代开始不合时宜了吗 众所周知,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苦难令我们的知识精英阶层开始反思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儒家思想,并将近代的积弱不振归结为儒家思想的僵化、保守和平庸。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大家认为儒家思想不合时宜了一百多年。 童年时,我对于美术作品的记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板报墙上的一只特写的大钢笔尖,插穿了“孔二扁头”挣扎扭曲的身体,或是一只大脚拧踩着孔子,旁白写着“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一时开放风气的纪录片《河殇》,对我们的黄河文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也是唱衰看低的。 其实,中国人大力批判孔子,是附骥于*本对儒家思想进行全盘否定和**批判之后的。十九世纪中叶,*本和中国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的困扰。*本的知识精英们在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政治体制的同时,也对比、看到了衰落的中国在列强面前的脆弱和委曲求全,自此便认定西方文明是一种*为**的文明,儒家文明则属于半开化的文明,而儒家思想*是落后以致*朽了的思想。*本否定儒家的思潮,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后来,他们成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主力。如钱玄同断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就连鲁迅先生,也认为“中国书越少读越好,*好是**不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当时的批判,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背景下,具有合理性。儒学是人学,以人为出发点来看世界,强调人间伦理的礼仪**。若是“过度解读”了,过于注重礼教仪式,就变得唯心而教条了,会漠视外在世界的独立性,妨碍了对于外在客观世界的研究,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十九世纪中叶,正是我们急需正视外在世界、以科学角度来理解物质世界的时代,从“过度解读”的角度来讲,南宋时期崛起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就已经是不合时宜了,其后的阳明心学“心外无物”偏执于另一端,也同样不合时宜。 或许,我们可以以商业模式应该具有的创新性打比方。当市场发生变化,消费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商业模式却还沿袭着以往的经验不作改变,漠视外在变化,而不是面向市场来改善产品和服务、改进营销策略、变革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此时,你的商业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变化下的消费需要了,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会被竞争对手淘汰。但是,全盘否定的批判对于孔子也是不公平的。如果说儒家后世“礼教”的僵化思想压制了人们对于外在物质世界的研究,那我们否定孔子,似乎是将儒家后世门生的错误,怪罪到了儒家始祖孔子的头上。何况,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蒙者伏尔泰,还被称为“西方孔子”。可见,孔子的思想与西方现代文明和世界现代文明并不相悖。 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前后,在学习了西方的营销思想、经营理论、管理哲学后,中国企业发展迅猛,开始批量地进*世界五百强。大家才发现,论及中国企业的持续经营之道,还是要回头来寻找我们自己的文化根源,应该重新发现儒家思想的价值。就企业经营管理而言,西方理论如现成的**一般,拿来就可以用,拿来就好用。但是,要想玩得好,还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理解,玩出自己的**套路。儒家学说好比中医养生,治于未病,等到病发,再用中医疗效就慢了。西方学说,是西医治病,治于已病。病发时,用西医疗效*快。所以,在企业经营实际的*常,就要注意用儒家思想来养生,企业经营才能走得健康,走得长久。 讽刺的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学习儒家思想之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时,市面上**欢迎的书籍,竟也是*本人写的,比如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稻盛和夫的《六项精进》。一方面,说明了*本人对于《论语》的学习理解具有实践性、入世性的特质。另一方面,反观我们的学习,大多还停留在大学教授或国学专家讲解字面语义,大家由此而“修身养性”的阶段。我们*多的是将儒家思想供奉于“象牙塔”之中,缺少将之平凡化于*常工作、生活的实践研究中。 从理论研究、实践应用而言,如果不能一以贯之地解析儒学“仁爱动机、举止礼仪、执中而用”的一生二、二生三的逻辑关系,就不能将儒家思想哲学化、系统化,进而实用化于企业经营的实践之中。类似的研究需要学术专家的考据训诂,需要一些企业家朋友的实践心得,*需要具有哲学思维的学者们条分缕析地进行研究,才是合时宜的。 如果希望能真实地感*儒家思想,*好是亲自读一读《论语》。读《论语》时,你会发现一个在朝时礼仪很严谨、家居时又很放松,甚至是活泼可爱、自带萌点的老夫子形象。比如着急找工作,被子路误解时赌咒的“天厌之天厌之”;比如和子贡谈及自我实现的“沽之哉沽之哉”;比如面对冉有退朝时酸溜溜的“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比如不多给学生妈妈粟米还唠叨“君子周急不继富”;比如多给学生粟米“以与尔邻里乡*乎”;比如为厚葬颜渊的越礼行为而辩解“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等等。 俗语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从表面来看,是孔子在说仁,而孟子在说义。那我们二十一世纪说什么?还是延续说“仁义之道”?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了?“仁、义、礼、智、信”是西汉时董仲舒总结儒家学说归纳出的“五常”。其中,孔子谈“仁”*多,因为“仁”是“五常”的原点,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初心,是动机,如果以动机而不是以相对客观、独立的标准来判断是非,将所有问题统统归结为道德问题,是有些粗俗的。 到了战国时期,也许孟子认为只谈动机是不现实的,就谈义,谈君王的具体行为,谈仁政之于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产生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未之有也”的执政理念。 到了汉朝,董仲舒总结了儒家思想的“五常”,其中特别强调“礼”,“礼”不仅对当时政治伦理的建设**实用,还由此奠定了汉唐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体系。 宋明理学的发展,吸收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人要依附于天理,开启了近千年的“礼教”。当时的“天理”,若是偏向于“格物”那样外在物质世界的独立性还好,可惜陷入了“致知”的唯心理解之中。不过,宋明理学强调的“格物致知”,也算是一种实践出真知的科学精神,注重事实、注重事物内在逻辑的联系。明朝时,***的心学吸收了佛家禅宗的思想,主张以人为主的“知行合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强调人作为主体的主动作用。阳明心学,有“智”的萌点,***个人也是儒家“智”的代表,但是儒家思想里的“智”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综上,可以理解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经过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朱熹的礼、***的智,到了现在,是“智”和“信”并存的时代了,是儒家思想信实可用、发扬光大的时候了。 如此,理性认识儒家思想的发展变化,理性分解儒家思想的“五常”,就合时宜了。 儒家思想,能一以贯之地“简单理解”吗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这几年在潜心研究国学。一次闲聊,一个年长的朋友问我,研究儒家有什么心得?我刚说了几句,他打断追问道:“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表述吗?”我想了想,说:“不能!”若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就不能叫“博大精深”了,或者不能算是一种思想体系了。一种思想体系,一定是要回答*基本的三大**问题的:世界是如何的?我们人类是如何的?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如何?这哪里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少也要三句话。这个年长的朋友语重心长地说:“你还是读得不够细致啊,儒家之道不是一以贯之的‘忠恕而已’吗?”我字斟句酌地回答:“这个忠恕,孔子自己说过,其弟子曾参也总结说过,的确是儒家思想的原点。但是如果理解简单了,容易理解成宽容忍让没有原则,就等同于佛家的‘忍辱’之道。所以也就难以理解孔子说的‘以直报怨’的直、‘不教而杀’的杀、‘君子贞而不谅’的不谅,难以理解他为何一任‘摄相’就诛杀少正卯,难以理解他为何两次辞职离开鲁国。”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等同于“忠恕”之道的“以德报怨”,是老子以柔弱胜刚强的说法,原话是“报怨以德”,而孔子的原话是:“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再看看孔子说的:刚、毅、木、讷,近于仁。可见,孔子是一个有原则有力量的人,忠恕之道也是有原则有着方正之相的“腔调儿”。而且,就仁爱而言,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不同,和佛家的慈爱也不同。思想,看似无形,如风或如空气,只有通过它附着的现象,才能看到它、认识它。思想,是要有条件地来描述的,看似凝练实则简单地概括,是一种“投机取巧”的伪命题。 所以,理解儒家,不仅要知道这个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要知道这个“忠恕”之道,一以贯之着什么?一以贯之的扦子上是羊肉串还是*脆骨,或者只是烤韭菜?我一直习惯于用佛法的“体、相、用”观,来看待和总结万事万物。我对《论语》中儒家的思想,也做了“体、相、用”三层观的总结: 1.儒家思想的体,也就是核心思想,是忠恕之道,也是仁爱之道。为何我将忠恕作为儒家思想的根本呢?原因一在《论语》里。“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还有一处,“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原因二则是《说文解字》里关于忠和恕的解释:忠,心在中央不偏离;恕,如心,将心比心。所以,儒家思想的“忠恕”,不只是向内的宽忍,还是向外的以人比人、以礼比礼,意思就是推仁成礼。“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说明了“忠恕”的根本意义。 儒家的仁爱之论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可以看出,尽管没有地域的限制,但仁爱的对象、方式是有区别的。所以,儒家之爱又被称为“伦理之爱”。 2.儒家思想的相,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现实表现,是要恢复“周礼”。 儒家认为,作为个人,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治国则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君子之间的纷争应该是“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其实,孔子是用“礼仪、礼让”代替了管理之法,以此来建立理想化的君子国。当然,孔子也知道以礼治国的艰难,所以《论语》里有:“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儒家思想,以礼约束行为规范的形式就好像是公约,而法家思想,以刑罚约束行为规范,就*像是法律。 3.儒家思想的用,也就是行为原则,可以概括为“中庸”之道。中庸不是平庸,而是持中而用,就像是高空走钢丝时需要手持平衡杆的中部一样。孔子认为做人做事不能偏激:“*乎异端,斯害也已!”“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儒家的中庸之道类似于佛家二见不住的“中道”。禅宗三祖僧璨大和尚在《信心铭》里有言:“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 ”“二见不住,慎勿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 在将近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论语》中体现的儒家思想可以称为原始儒家思想,其后的汉儒经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皆由此发展而来。所以,我们也可以将《论语》视为儒家思想的本体,将其他不同阶段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儒学发展视为其不同阶段的表象。 我们要复兴儒家思想,不能将“阳明心学”、*本的“稻盛和夫”作为学习的本体,它们只可以作为参考的“相”。我们应该将原始儒家思想的精髓与现代商业社会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发展出现阶段的“新国学、新儒学”。 《论语》里,孔子教诲子夏,“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此处的儒,到底是什么意思?儒,原为商朝时主管祭祀的官员,也被称为“祝人”。周灭商后,制度有所改革。孔子又说:“周鉴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此两句话说明了孔子的儒家精神,是进化而不是守旧,是有社会之用而不是自得其乐。另外,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也说明了孔子的儒家精神不是只为某一特定阶层的封闭服务,而是面向所有大众的开放思想。孔子曾说“不知生,焉知死”“祭神如神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等非迷信思想。我们可以从中理解孔子的儒家精神,它具有“现实性、唯理性、开放性、进化性”的特点,是一种强调现实的人生道德,是一种爱在人间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强调伦理之道的入世哲学。因此,新时代的儒家精神,也要具有我们新时代的“现实性、唯理性、开放性、进化性”的特点,才能承担起社会价值观的主体作用。 《论语》里的孔子形象很丰富,言谈举止也很活泼。从一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孔子极具现实感的“君子儒”精神。《论语·阳货》中,“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叛乱的公山氏召请孔子,孔子思前想后,觉得他盼望已久的“复周礼,行王道”的时机已到,便动了出仕之心,欲应召前往费邑。弟子子路得知老师的念头后,很不高兴,说:“没地方去也就算了,何必要去叛乱的公山氏那儿呀?”孔子道:“你以为他召我去,又哪里是毫无目的?如果能重用我,让我得以行仁义之道,或许我也可能在鲁国的东边,建立当年的周一样的功业呢!”紧接着,孔子又对子路解释道:“周文王和周武王,就是分别起家于丰邑和镐邑,*终得天下而王。现在费邑虽小,与丰、镐二邑比起来,不也差不多吗? ”(《史记·孔子世家》: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并没有那种表面意义上的“忠一君,爱一国”的所谓“高洁”,而是带着一些“英雄无论出处”的功利性和“复兴周礼,普惠大众,普利天下”的抱负。"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不可否认的是,《论语》等国学著作容纳了诸多精华,在新的时代依然值得一看。曲龙先生所著的《读,学管理》深入浅出地将《论语》与现代商业思维、企业管理结合在一起,为古老的著作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且为现代企业家管理企业、发展商业做出了诚恳建议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