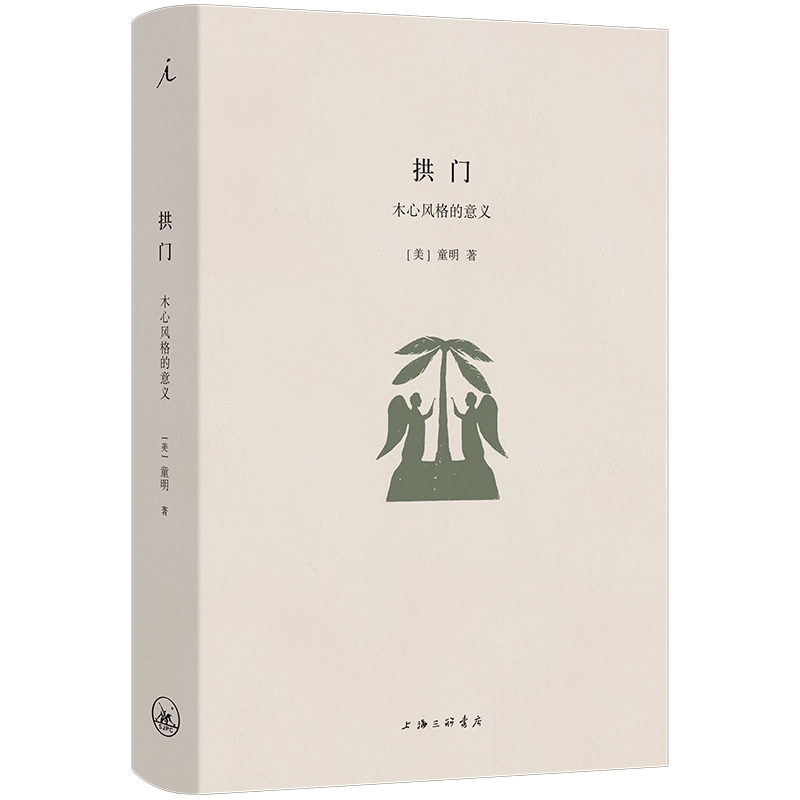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三联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2.90
折扣购买: 拱门:木心风格的意义
ISBN: 9787542685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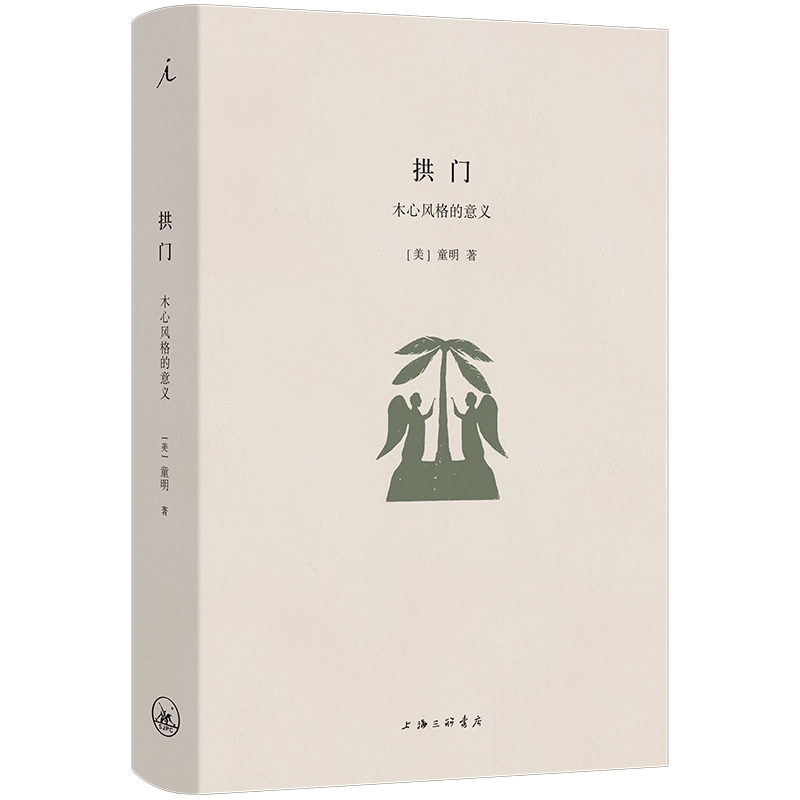
童明,马萨诸塞大学英美语言文学博士,西安翻译学院特聘教授,加州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八十年代初任联合国纽约秘书处译员。 主要著作有:《美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英语增订版,2008),《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修订版,2019),《解构广角观:当代西方文论精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编有木心精选集:《木心诗选》和《豹变:木心短篇循环体小说》。英语译有木心小说:An Empty Room: Storie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11)。
《拱门》选摘之一 反复有人说:“越是民族性的,就越有世界性。” 是的:具有民族性的,在有些情况下具有了世界性。 又不然:许多具有民族性的,并没有什么世界性的意义。 鉴于几百年来是欧洲文化在世界上占有领先地位,是否可以说:东方(如中国)文化只有在与西方文化相似时才有世界性? 否。与西方文化的相似或不相似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似或不相似之处,能否使东西方发生历史的、实质的关联。 比如,李商隐的诗在回忆中将过去现在将来做多种的组合,早已具备了“意识流”的一些特征。又比如,佛经中的“阿赖耶识”早已指向潜意识、无意识。但李商隐的回忆性诗艺和“阿赖耶识”,在历史上并没有在东方形成意识流派或心理分析学说,也没有对西方文化造成影响,因此没有形成所谓世界性。它们在世界上悄然隐退,对东方民族文化日益觉醒的世界意识,倒是有警戒的作用。 东西方文化只有在同一时空内产生对话和理解,才具有世界性。这不仅适用于东方的西学,也适用于西方的东学。西方东学中的某些褊狭见解,如属于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某些偏见,那是反世界性的。 所谓世界性,不是指相同,而是指相通。相通,可以有分歧,可以不同。相通时有张力,方显得世界精神的博大精深。 各文化之间的相通,最难得的媒介,是对当下的时空具有超常领悟力的某些个人。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经过这种超常悟性的整理,本来没有联系的有了联系,原先比较原始的涵意经思想的折射而获得新意。木心的《遗狂篇》就是此种悟性(美学思维)的实例和象征。 《拱门》选摘之二 我是木心作品的第一个英文译者。因为美国大学的工作繁忙,我一直在工作之外找时间一篇一篇翻译。译作先发表在美国的《北达科他文学季刊》《柿子》和《没有国界的文字》等文学期刊。木心去世之后的2013年,英译本的《SOS》(即《豹变》首篇,未收入英译本)在纽约的《布鲁克林铁轨》杂志上发表,当年10月获得 Pushcart文学奖的提名。英译本的《林肯中心的鼓声》和《路工》则发表在美国的《圣彼得堡季刊》。这些都是木心身后的事。 2006年前后,我和木心在纽约的文学代理人向 New Directions 出版社提交了十六篇的完整译本。这是一家负有盛名的文学出版社,早年出版过庞德和艾略特的诗歌。那里的编辑部收到稿件后很快通过决议,表示愿意出版,却只肯采纳其中十三篇,并不说明为什么不收入《SOS》等三篇。我们向出版社解释:那三篇是小说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希望收入。出版社没有回复。我们坚持,对方继续沉默。一耽搁就是几年。我们都有些郁闷。文学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乔伊斯为了出版《都柏林人》,从1905年到1914年前后向出版社十八次交稿,最后方能如愿。可是,好事非要如此磨人吗? 木心的健康每况愈下。我们同意退一步,向出版社妥协。含十三篇的英译本于2011年5月出版后,各书评机构好评如云。此书幸好在木心去世之前出版了,给了他不少的宽慰。 2010年夏,我带清样去乌镇。木心双手接过,显然很兴奋:“来来来,让我看看这些混血的孩子。”翻看一阵之后,木心缓缓说了一句:“创作是父性的,翻译是母性的。”我心里一热。 2011年夏天,再去乌镇,见木心案头和书架上摆上一排排崭新的小开本《空房》。如果当时出版的是完整的《豹变》,那就完美了,但生命中完美的事并不多。 我喜欢木心,推荐木心,看重他的艺术品格和精神。许多人都喜欢木心的俳句,觉得好玩,幽默,机智。我也很喜欢木心好玩的这一面。但他还有另一面。《豹变》里的故事,虽然有好玩的字句和片刻,基调却是透着力的凝重。木心喜欢冷处理,他冷淬过的诗句,常常带我们走进生活中熟悉的阴影,行走间却感到一丝温暖,为之鼓舞,受之启示。我想,木心是要让我们知道,爱和生命意志是艺术的本质,也是生命的意义,这是我们在黑暗中唯一的光源。 2011年英文版《空房》出版后,我在美国产业工人的网站读到一篇书评,说西方一些作家看似写得精致,却不像木心的小说给人以真实的力量。书评说,木心有“一种精神”。我急忙打电话转告木心,他连连说:“对,对呀,我们是有精神的。” 我和木心相遇相知,在体验艺术品格和精神之中加深了友谊,于是彼此都感受到了:生存虽然苦,命运却可以精致而美妙。 1993年8月的一天,我从美国西岸飞到纽约,兴冲冲前去拜访木心。他已经搬过几次家,那时租居在杰克逊高地的一栋连体屋里,门口正对路口的交叉处。我下午时分到达,木心早站在门前的楼梯上眺望,见我到了,快步走下来。我们热烈拥抱。 木心兴奋时,眼里闪光;沉思时,眼睛像午后的日光暗下来。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不停地谈话,东西南北,话题不拘大小。 木心的屋子呈横置的“山”字,“山”字中间的一横短下去,是间很小的厨房兼餐厅。进了门,前面的小间算作客厅,一张桌,两把椅,右面墙上是红字体的王羲之《兰亭序》拓片;穿过通道,经中间的厨房,后面一间就是卧室。我们一会儿在前厅,一会儿在中间厨房。晚上在后面就寝,他睡床上,我睡地铺,继续说话,直到睡着。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木心半开玩笑地说:“童明呀,你再不回洛杉矶,我要虚脱了。” 第二天傍晚,在街上散步,我重复着这两天谈话的亮点,木心突然说:“人还没有离开呢,就开始写回忆录了。”两人就不再说了,沉默良久。此后我一直在心里写回忆录,久而久之,反而不知如何落笔。 谈话平缓时如溪水,遇到大石头,水会转弯,语言旋转起舞,荡出浪花。第三天晚上,十一点半左右,坐在前面小厅里,话题进入平日不会涉及的险境,话语浓烈起来,氛围已然微醺。这时,街对面的树上有一只不寻常的鸟开始鸣唱。木心打开门查看,我也看到了,是一只红胸鸟。我顺口说:“是不是红衣主教(red cardinal)啊?”后来,我向熟知鸟类的美国朋友请教,他们说不是,应该是某种模仿鸟。 模仿鸟无非是模仿两三种曲调,而这只红胸鸟可以变换五六种曲调,居然有solo的独唱,还有duet的和声。这是天才的羽衣歌手,还是天外之音?最不寻常的是,它叫得如醉如痴,一直激昂到凌晨三点,等到我们躺下了,才转入低吟。梦里还能听到它。之后,我再也没有听过这样的鸟鸣。木心也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也是我们共享的唯一的一次。 木心说,我们的谈话触及了人类历史的险境,或许就要触动另一个维度。这样说,有些神秘,有点暗恐,但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解释了。 木心很在意这只红胸鸟,诗句里几次提到。我和木心一起亲历了那晚,知道整件事的不寻常,却无法向别人转述。木心向丹青他们转述,再传出的叙述也有些走样儿了。准确地说,那不是一只鸟,是来自神秘世界的信使。 我写这篇序,断断续续的,难免想到那个夏天,想起我对木心的承诺,似乎又听到了红胸鸟如醉如狂的鸣唱,不舍地把它留在记忆里,反复聆听,慢慢回味,突然间我意识到:木心已经不在了。心里,一大片空白。 翻开书,又听见他谈笑风生,就像那只红胸鸟,来自彼岸,归于彼岸,一个和我们的时空交集的时空。 2016年圣诞前夕 ★ 大家都在“读木心”,为此,陈丹青出版两种听课笔记《文学回忆录》和《木心谈木心》,童明写出一册文学批评集《拱门:木心风格的意义》—— 谁是童明?木心美术馆馆长陈丹青说:“这些年谈木心的场合,大家已经习惯是我出来讲。其实,应该童明来讲。我们两个和木心是将近30年的‘老朋友’。可是童明在加州教书,不容易过来。木心去世以后,他有课,也没法过来,他非常悲痛……木心在纽约,生活上的事情找我,交税啊、办杂事啊、进城啊,都找我。文学上的事情,木心从来是找童明谈。” ★ “文学无国界”,木心之所以拥有一批英语读者,也是因为先有了一位首要译者叫童明,到晚年,木心酝酿一部诗集,题词即“献给童明”—— 1985年,经纽约同胞介绍,童明结识木心。1989年,童明将木心小说列入世界文学课讲授,受到欢迎。2011年,童明翻译的木心短篇循环体小说An Empty Room(即《空房》)在美国出版。童明说:“我和木心相遇相知,在体验艺术品格和精神之中加深了友谊,于是彼此都感受到了:生存虽然苦,命运却可以精致而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