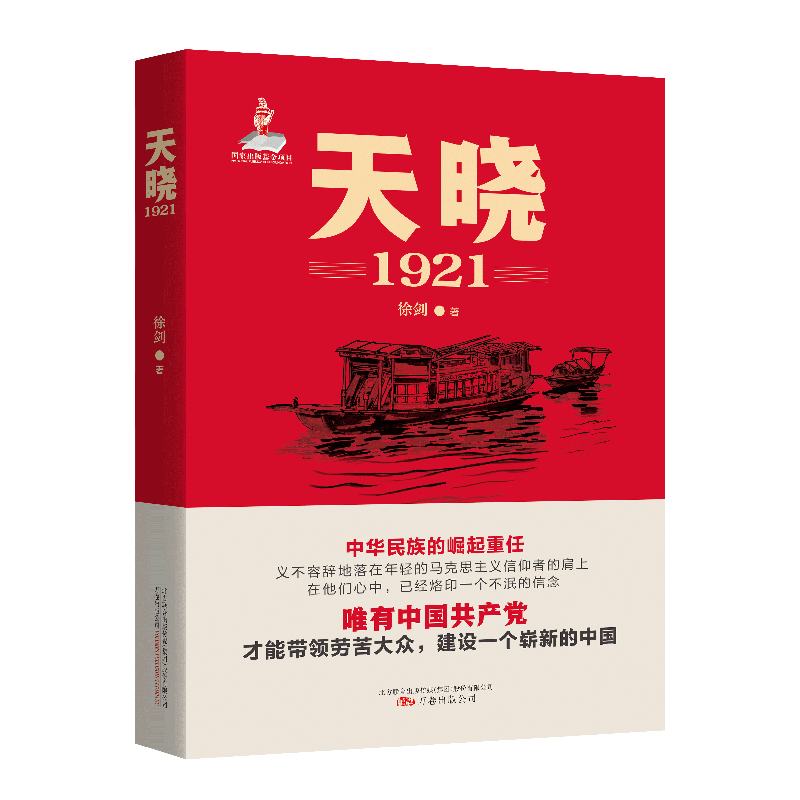
出版社: 万卷出版公司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天晓——1921
ISBN: 9787547058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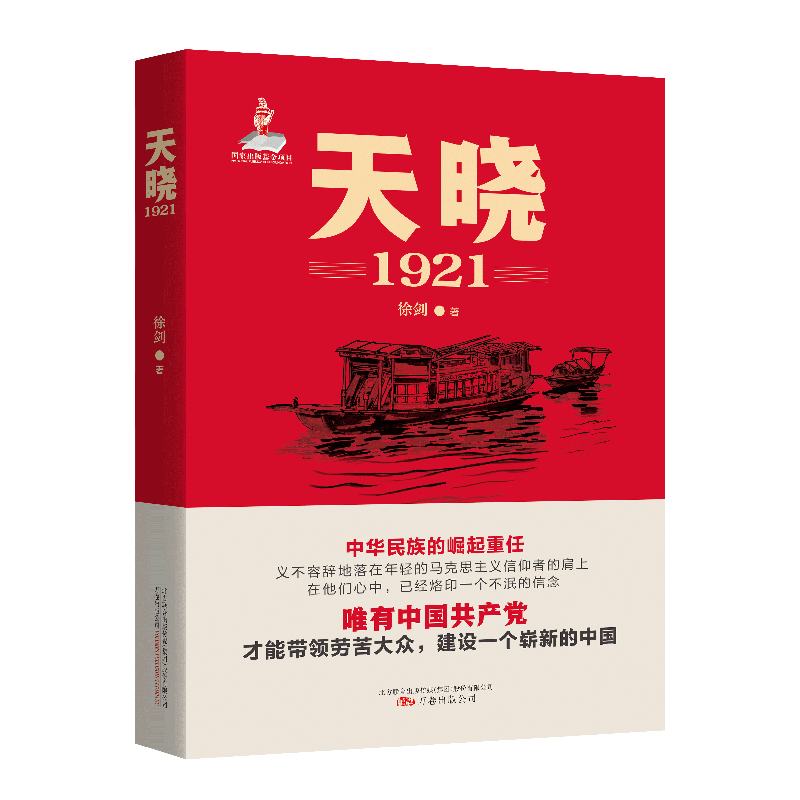
徐剑,云南省昆明市大板桥人,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创作一级,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出版文学作品700余万字,曾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中国好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全国、全军文学奖,被中国文联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家。
将近黄昏了,天有些暗淡,好像要下雨了,上海城郭上空,不时惊雷响起,轰隆隆的声音,从遥远的地平线传来。 王会悟放了一天哨,天将向晚了,这些男人们的会议越开越长,那个外国人马林,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李汉俊和刘仁静换着给他做翻译,看来这会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瞧,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下楼看了好几次,都不见小叔子的动静。李书城去南方前交代过她,对于汉俊的事,一概不许过问,她谨遵夫训,复又折回楼上去了。 天黑下来,不会再有人来干扰了。王会悟得回到渔阳里2号,她的晚饭还没有着落呢,于是起身匆匆走了。那是7月30日晚上8点的会,马林将要发表演说,与会代表围着长方形的大条桌落座。周佛海请假了,说自己闹肚子,腹痛大泻,正独自躺在博文女校的地铺上。 各位代表,开会吧!张国焘刚宣布完,那一扇半掩的后门,忽然被推开了,闪进一个陌生面孔,是一位中年男人,身着长布衫,朝一楼的客厅扫视了一圈,仍站着不走。众人惊诧。 “先生,你找谁?”李汉俊站起身来,问这位不速之客。 “对不起,我找错地方啦。”男子说完转身便走了。 “刚才这人说了什么?”马林很机警,用英语询问李汉俊。“他说找错地方啦。”李汉俊也用英语回答。 “有情况,散会。”“砰”的一声,马林将拳头重重地擂在桌子上。他毕竟是老地下工作者了,有着丰富的城市秘密斗争经验,说,“这是一个包打听,一定返回巡捕房报告去了,大家立即从前门撤退,会期再定。” 会场发生一阵小小骚动,大家立即起身,卷着文件和本子,从前门蜂拥而出,三三两两,穿过林荫道,各奔东西。他们也不敢再回博文女校了,再集合的地点是渔阳里2号的陈家,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在这里应对。 陈公博当时为何不走?他在《寒风集》中说:“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预警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马林的判断极其准确,那个陌生人去巡捕房搬兵去了。代表们刚撤走一会儿,十几个武装巡捕和刚才那个包打听就闯进了李汉俊哥哥的家。 李汉俊因为牺牲得早,对于巡捕房搜查之事,未留下只言片语,但陈公博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刊在《新青年》杂志上,虽然隐掉了他参加中共一大之事,但是因离那个时间较近,比较贴近当时的事实。他写道:“……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横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是英国人。那个总巡有点儿疑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国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懂。那个侦探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儿误会。我于是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地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已经检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是不少,既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社会主义者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法国总巡训完话,收队走了,扔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个人长舒了一口气,好险啊,险些酿成摇篮中共的一场大劫。陈公博说,自那天始,他在上海和杭州活动,他的身后始终有三两个鬼影尾随。 这场突如其来的搜查,因了马林非同一般的危机预警而化险为夷,但是每个与会代表对这场有惊无险的撤离皆记忆犹新,经年之后,纷纷付诸文字。可是一场秘密之会,何以受到巡捕房的搜查呢? 其实这一切,又皆与马林有关。马林刚一踏上沪土,他的行踪便受到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的共同监视。此人系危险人物!荷兰王国外交部早已经照会英、法、日、德和中国外交机构。从这一年春天马林在维也纳被捕,然后登船驶往东方,他的行踪就被沿途各国及殖民地总督府所“眷顾”,他到上海住于何处,接触些什么人,皆在各国警方互通情报之中。马林对此也早有察觉,并采取反侦探的措施,让人代转信件和收发电报,但是他还是无法隐匿个人的行踪。日本著名中共党史研究者石川祯浩曾翻阅过日本警视厅《外秘乙995号中国共产党上海的行动(1921年6月29日)》(收于《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内称“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与会”。时间被误报成了6月30日,但地点却确凿无疑:“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就在法国巡捕房检查过的第二天,《民国日报》刊登了法租界当局的一条取缔集会的条例:自8月1日起,凡集会须于四十八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的许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法租界巡捕房因获悉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匆忙制定的一个应对之策。日本警视厅未说情报来源何处,但是法国总巡搜查李书城家时,将陈公博当成日本“社会党”人,可见其情报并非空穴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