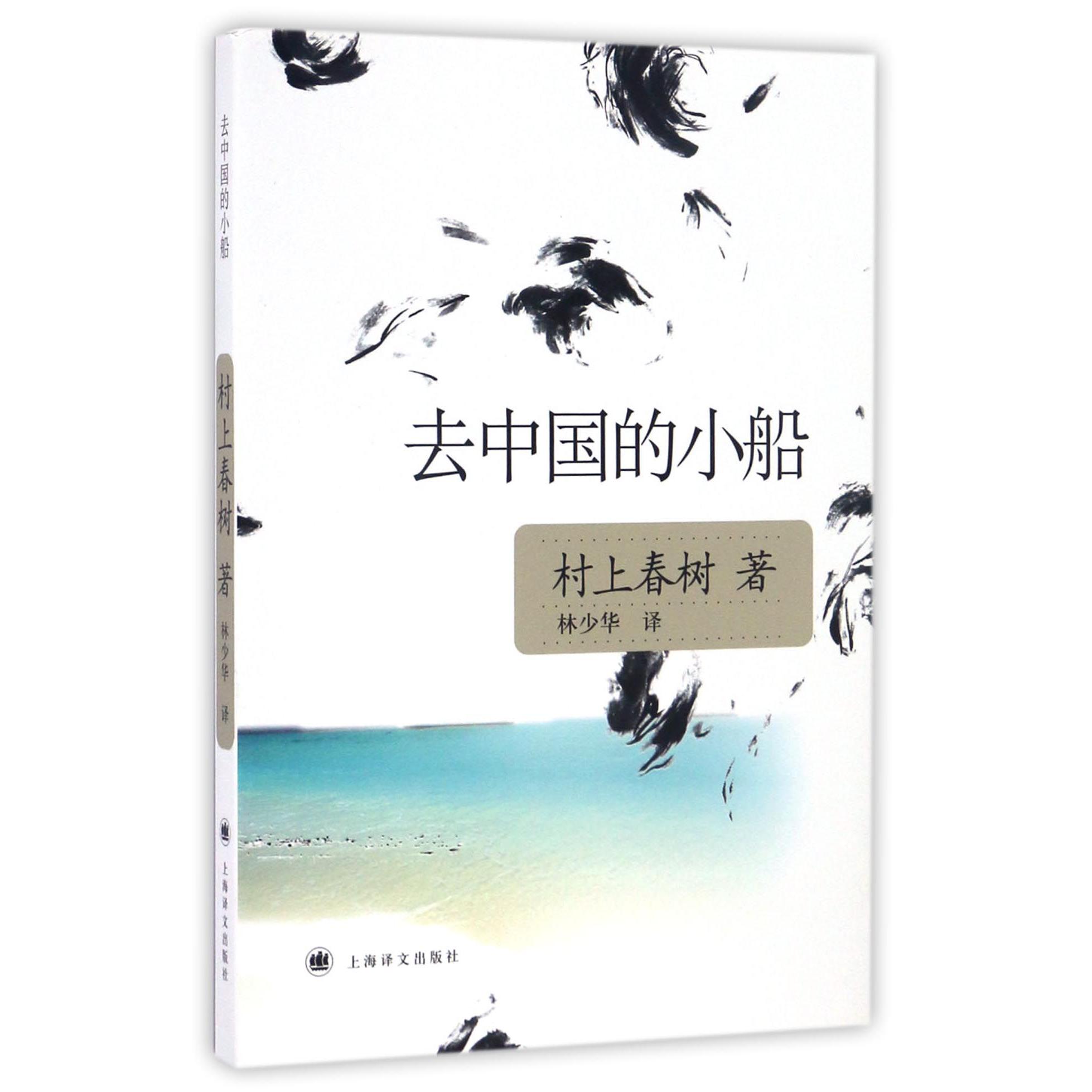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25.00
折扣价: 15.00
折扣购买: 去中国的小船
ISBN: 9787532746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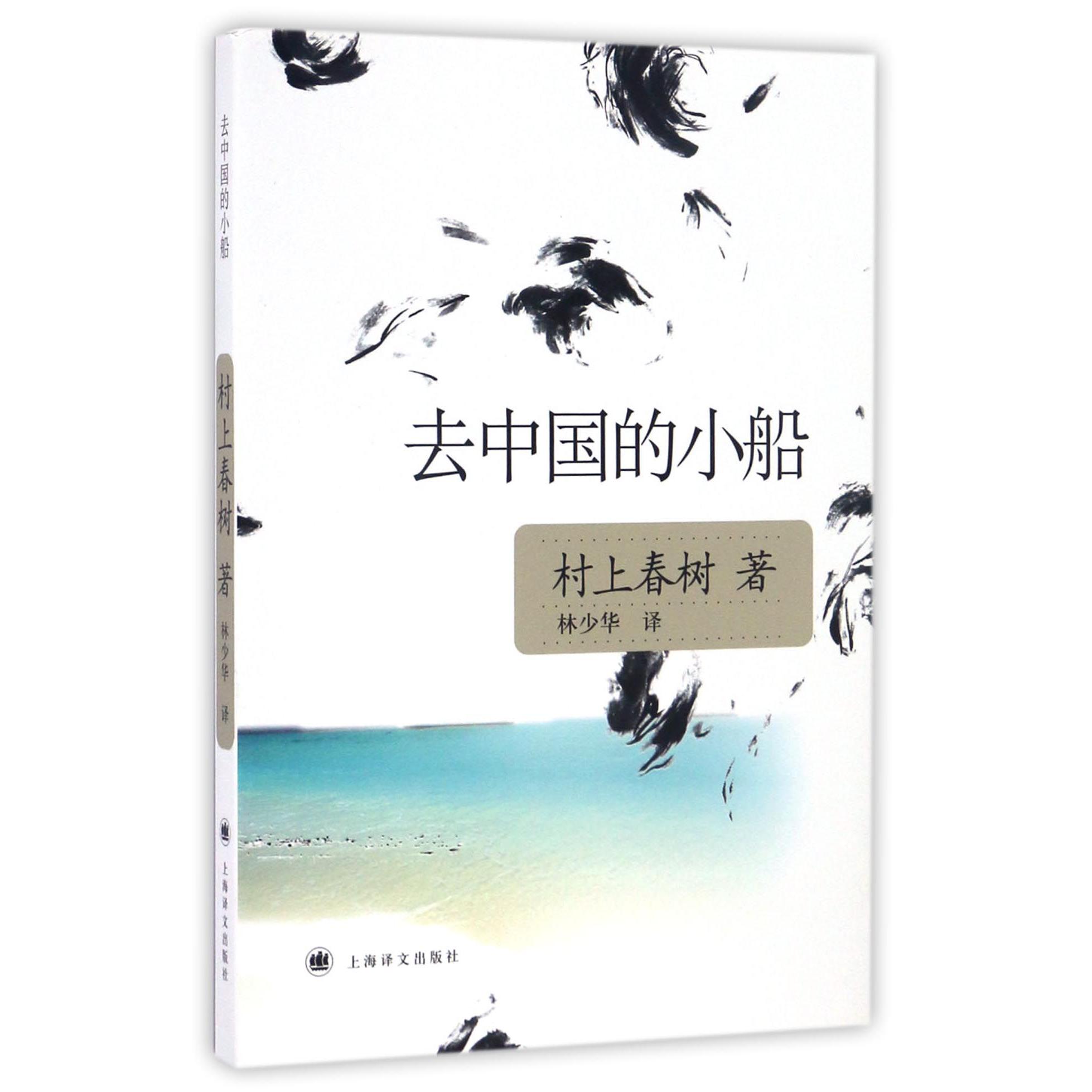
村上春树(1949—),*本**作家。京都府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1979年以**作《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等。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个**和地区,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
出乎我朦胧的预想,中国人小学外表上与我们小 学不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清爽得多。又黑又长 的走廊、潮乎乎的霉味儿等两个星期来在我脑海中随 意膨胀的图像根本无处可寻。穿过别致的铁门,一条 花*簇拥的石板路画着舒缓的弧线长长地伸展开去。 主楼门正面,清冽的池水光闪闪地反射着早上九点的 太阳。沿校舍树木成行,每棵树上都挂着一块中文解 说板,有的字我认得,有的不认得。主楼门对面是被 校舍环绕的运动场,状如天井。每个角落分别有某某 人的胸像、气象观测用的小白箱、单双杠等。 进得楼门,我按规定脱鞋,走入规定的教室。明 亮的教室里排列着正好四十张开启式小桌,每张桌上 用透明胶粘着写有准考证号码的纸片。我的位置在靠 窗一排的*前边,就是说这教室里我的号数*小。 黑板崭新,墨绿色,讲桌上放着粉笔盒和花瓶, 花瓶里插一支白菊。一切都是那么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墙上的软木板没贴图画没贴作文。或许是故意取下 的,以免干扰我们考生。我坐在椅子上,把笔盒和垫 板摆好,托腮闭起眼睛。 过了约十五分钟,腋下夹着试卷的监考官走进教 室。监考官看样子不超过四十岁,左腿有一点点跛, 在地板上抬腿不大利索。左手拄一根手杖,手杖是樱 木做的,很粗糙,颇像登山口土特产商店卖的那种。 由于他跛的方式显得甚为自然,以致唯独手杖的粗糙 格外显眼。四十名小学生一看见监考官——或者不如 说一看见试卷,顿时鸦雀无声。 监考官走上讲台,先把试卷放于桌面,继而“橐 ”一声把手杖靠在一旁。确认所有座位无一空缺之后 ,他咳嗽一声,瞥了一眼手表。接着,手像支撑身体 似的拄在讲桌两端,直挺挺地扬起脸,望了一会天花 板。 沉默。 每个人的沉默持续了大约十五秒。紧张的小学生 大气也不敢出地盯视着桌上的试卷,腿脚不便的监考 官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的一角。他身穿浅灰色西装 白衬衫,打一条转眼即可让人忘掉色调花纹的很难留 下印象的领带。他摘掉眼镜,用手帕慢慢擦拭两侧镜 片,重新戴回。 “本人负责监督这场考试。”本人,他说,“试 卷发下以后,请扣在桌上别动。等我说好了,再翻过 来答题。差十分到时间时我说*后十分钟,那时请再 检查一遍有没有无谓的差错。我再说一声好了,就彻 底结束,就要把试卷扣在桌上,双手置于膝盖。听明 白了么?”沉默。 “千万别忘记先把名字和准考号写上。” 沉默。 他又看一次表。 “下面还有十分钟时间。这个时间我想给大家讲 几句话,请把心情放松下来。” 几声“吁——”泄露出来。 “我是在这所小学任教的中国老师。” 是的,我就这样遇上了*初一个中国人。 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人。这也难怪,毕竟那以前 我一次也没遇到中国人。 “这间教室里,”他继续道,“平时有和大家同 样年龄的中国学生像大家一样刻苦学习……大家也都 知道,中国和*本,两个**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 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对 吧?” 沉默。 “不用说,我们两国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 相似之处,既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 沟通的地方。这点就你们的朋友来说也是一样,是吧 ?即使再要好的朋友,有时候也不能沟通,对不对? 我们两国之间也是一回事。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 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这 是……**步。” 沉默。 “比如可以这样想:假定你们小学里有很多中国 孩子来参加考试,就像大家坐在这里一样,由中国孩 子坐在你们书桌前。请大家这样设想一下。” 假设。 “设想星期一早上,大家走进这所小学,坐在座 位上。结果怎么样呢?桌面到处乱写乱画满是伤痕, 椅子上粘着口香糖,桌子里拖鞋不见了一只——对此 你们会有何感觉呢?” 沉默。 “例如你,”他实际指着我,因我的准考号*小 ,“会高兴吗?” 大家都看我。 我满脸通红,慌忙摇头。 “能尊敬中国人吗?” 我再次摇头。 “所以,”他重新脸朝正面,大家的眼睛也终于 看回讲桌,“大家也不要往桌面上乱写乱画,不要往 椅子上粘口香糖,不要在桌子里面乱来。明白了吗? ” 沉默。 “中国学生可是会好好回答的。” 明白了,四十个学生答道。不,三十九个。我口 都没张开。 “注意:抬起头,挺起胸!” 我们抬起头,挺起胸。 “并怀有自豪感!” 二十年前的考试结果,**早已忘了。我能想起 的,唯有坡路上行走的小学生和那个中国老师,还有 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 那以后过去了六七年——高三那年秋天,一个同 样令人心情舒坦的星期*下午,我和班上一个女孩走 在同一条坡路上。我正恋着她,至于她对我怎么看则 不晓得,总之那是我们的初次约会,两人一起走在从 图书馆回来的路上。我们走进坡梅正中间一家咖啡馆 喝咖啡,在那里我向她讲起那所中国人小学。听我讲 完,她嗤嗤地笑了起来。 “真是巧啊,”她说,“我也同**在同一考场 考试来着。” “不会吧?”P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