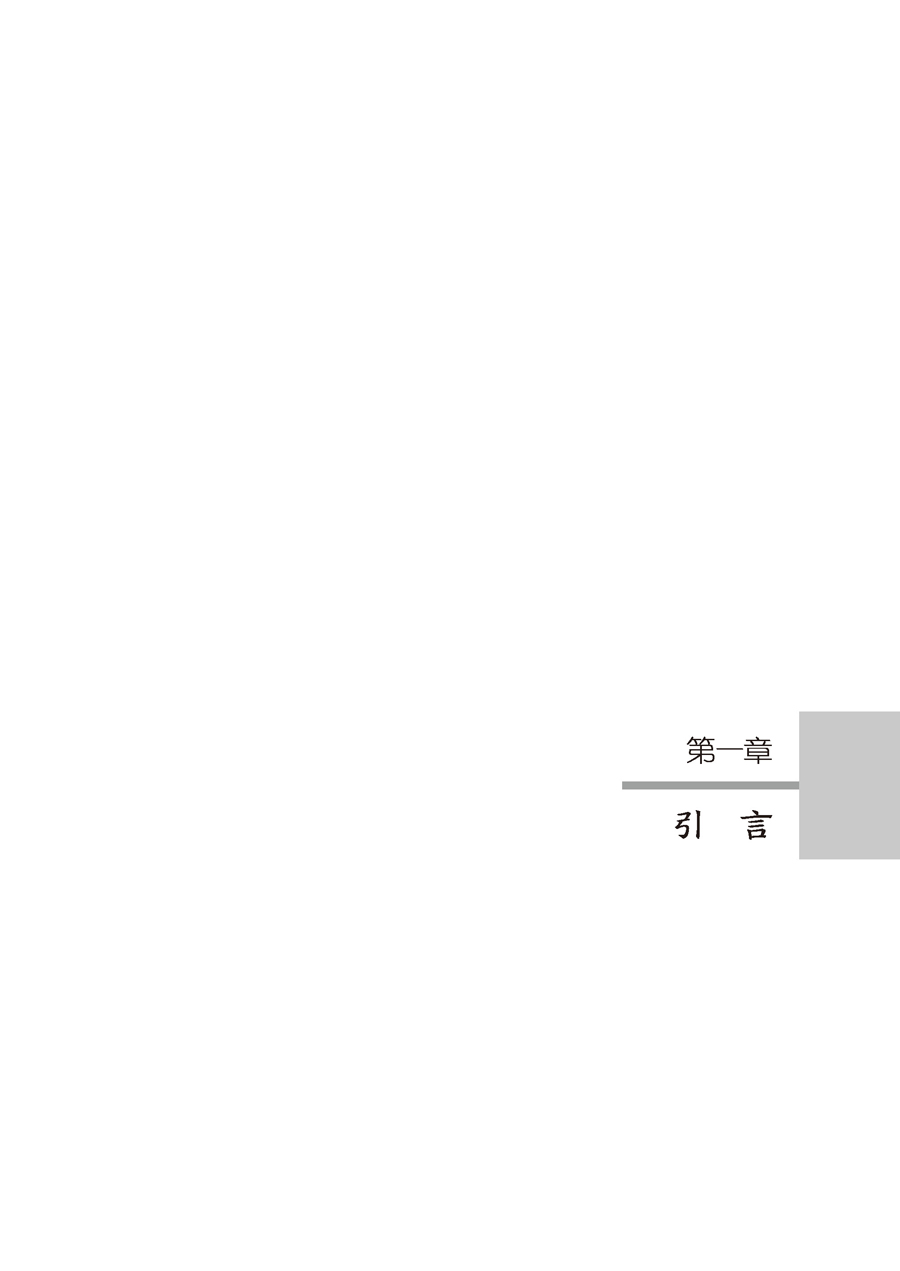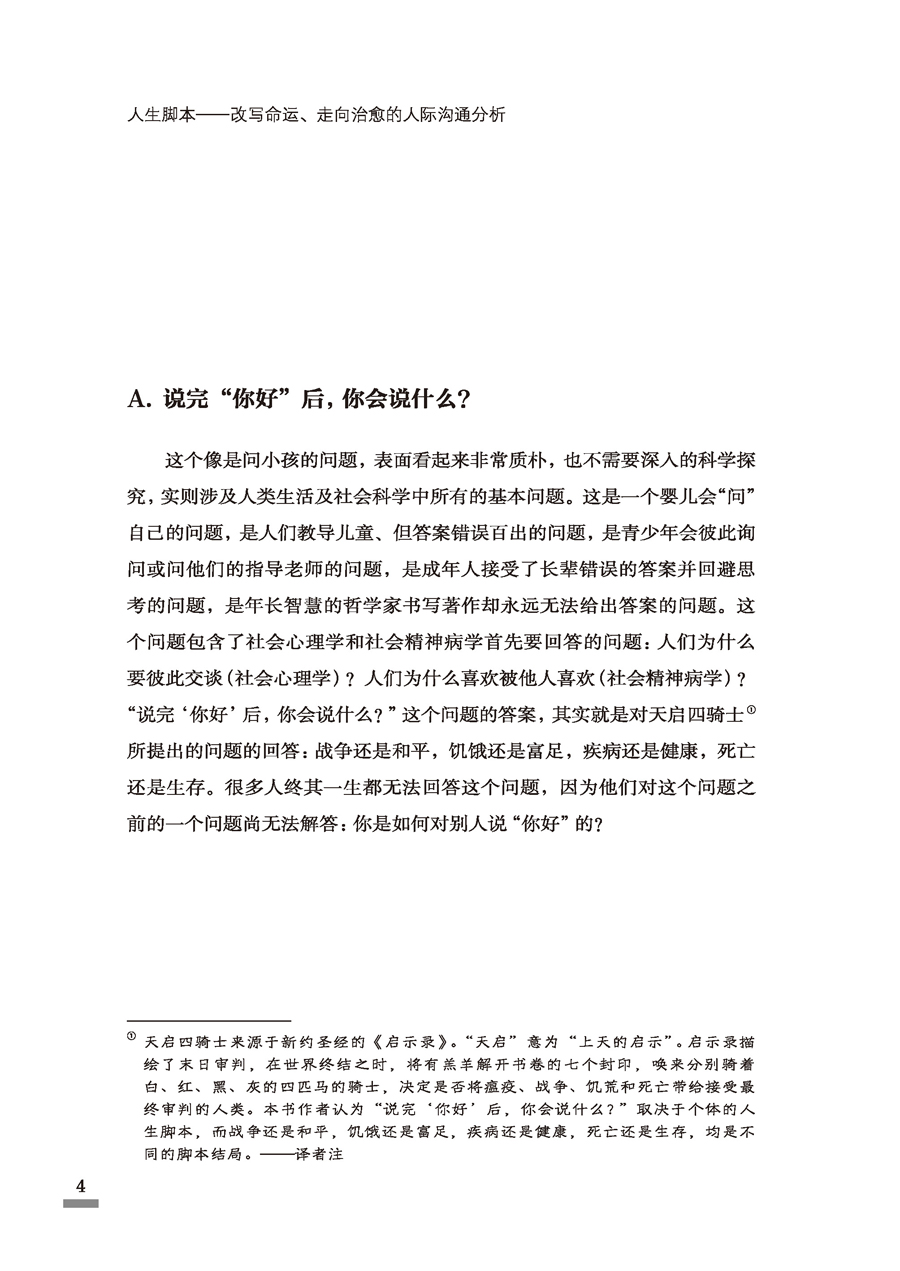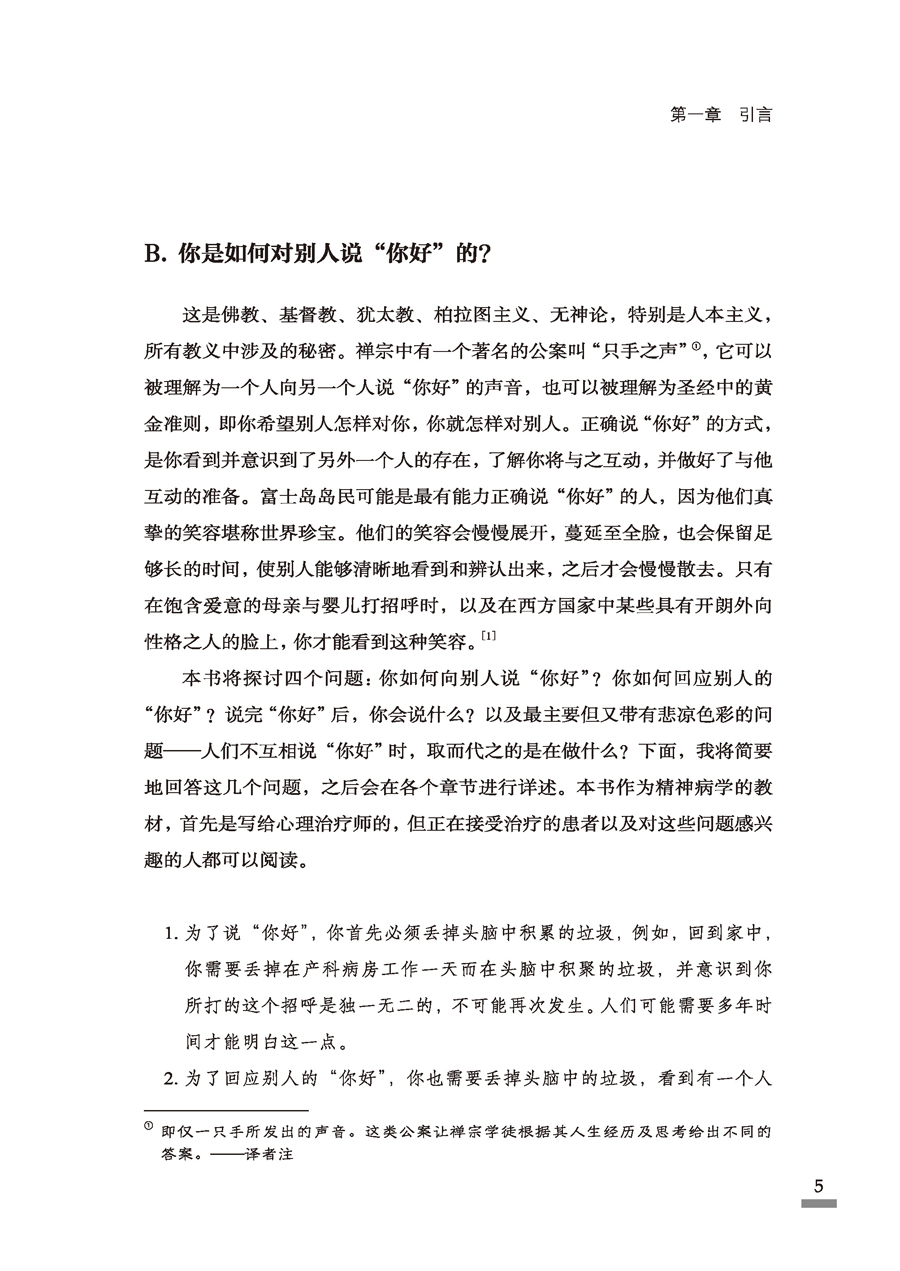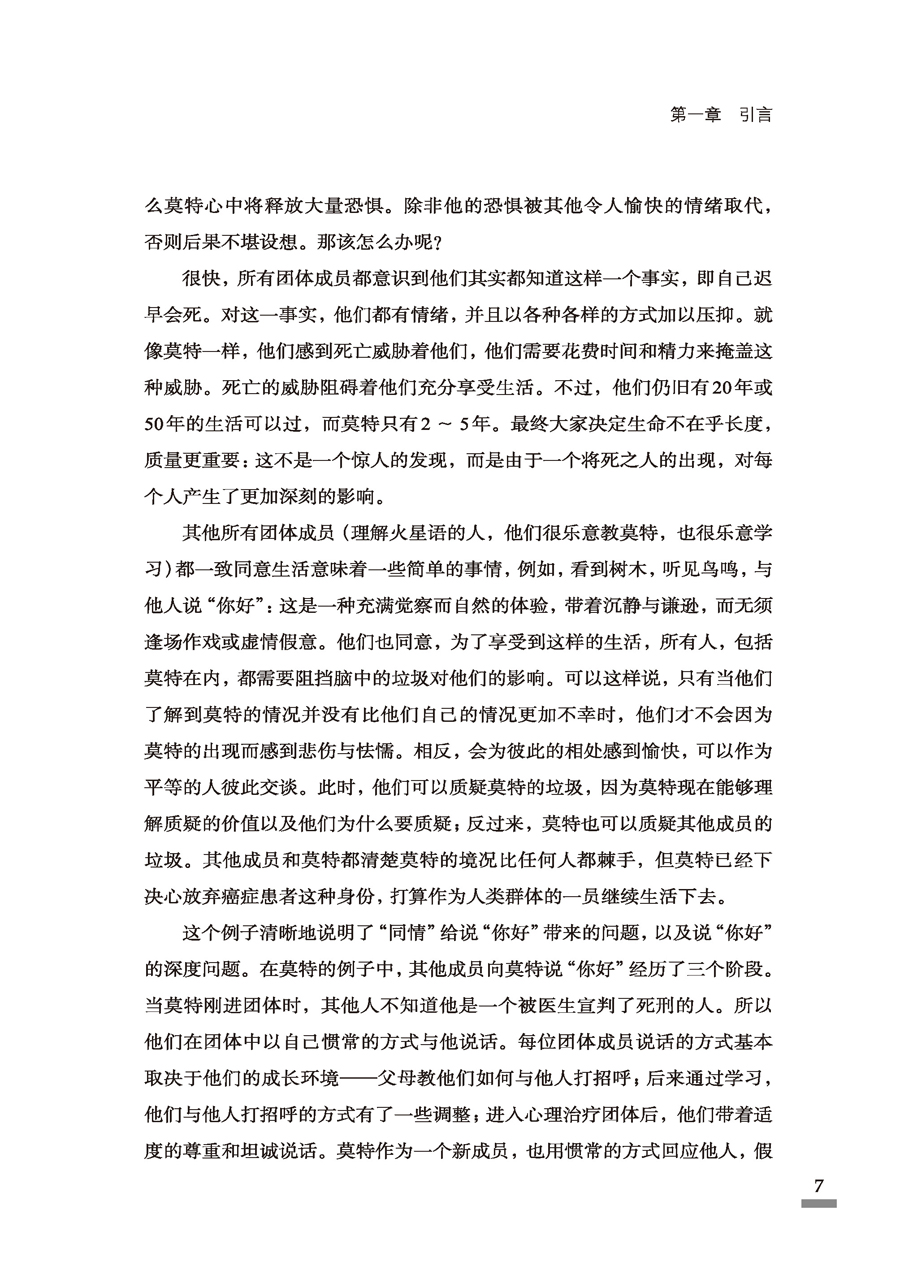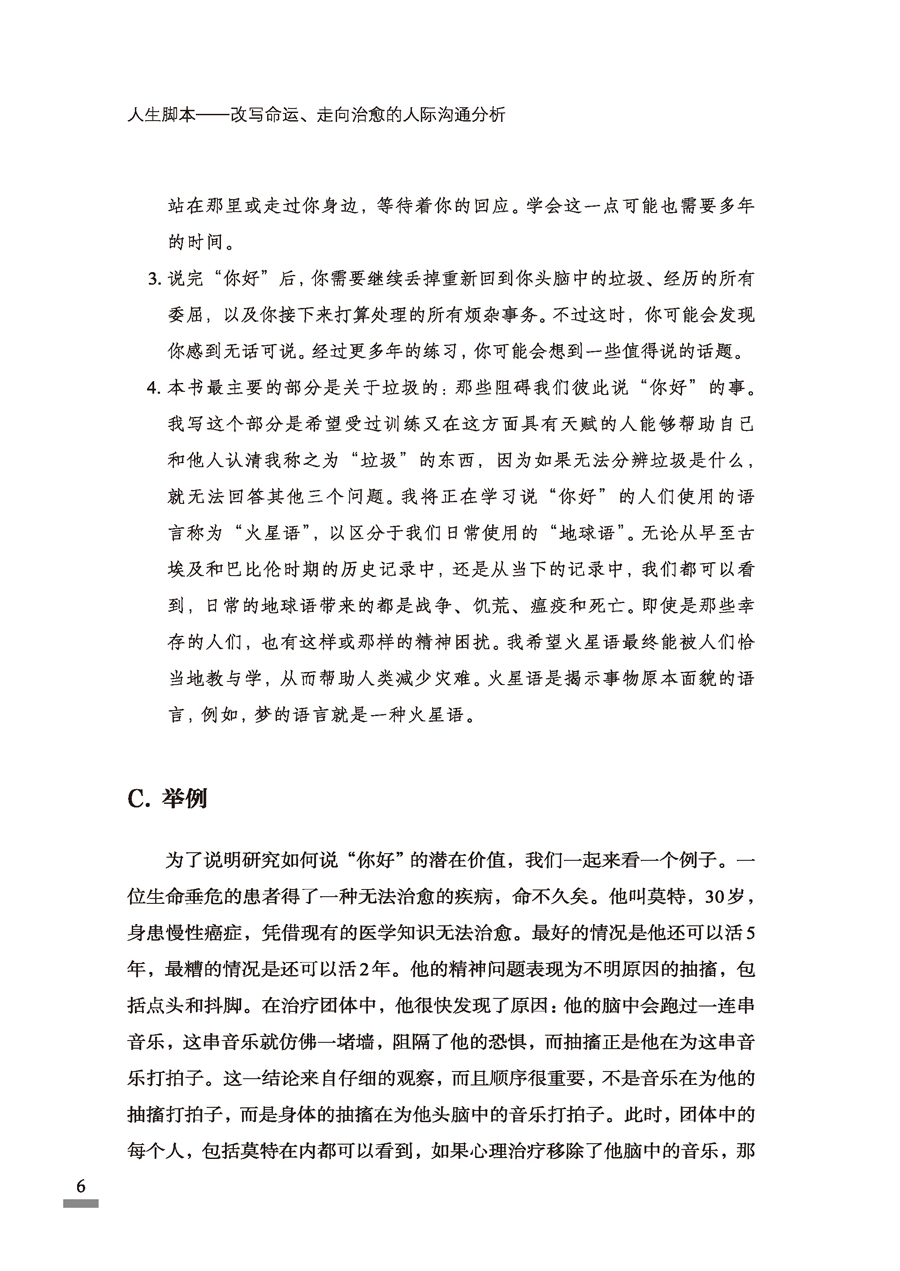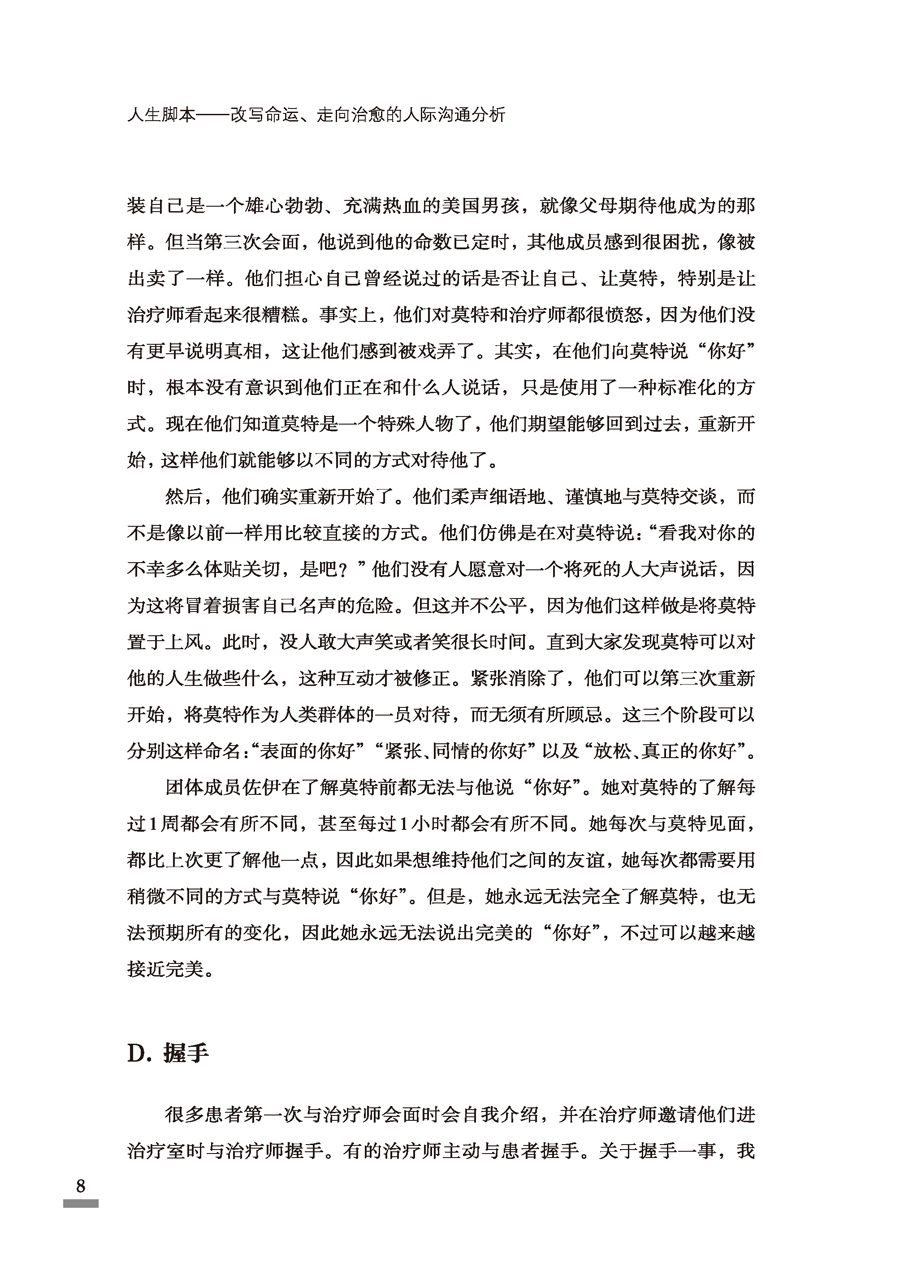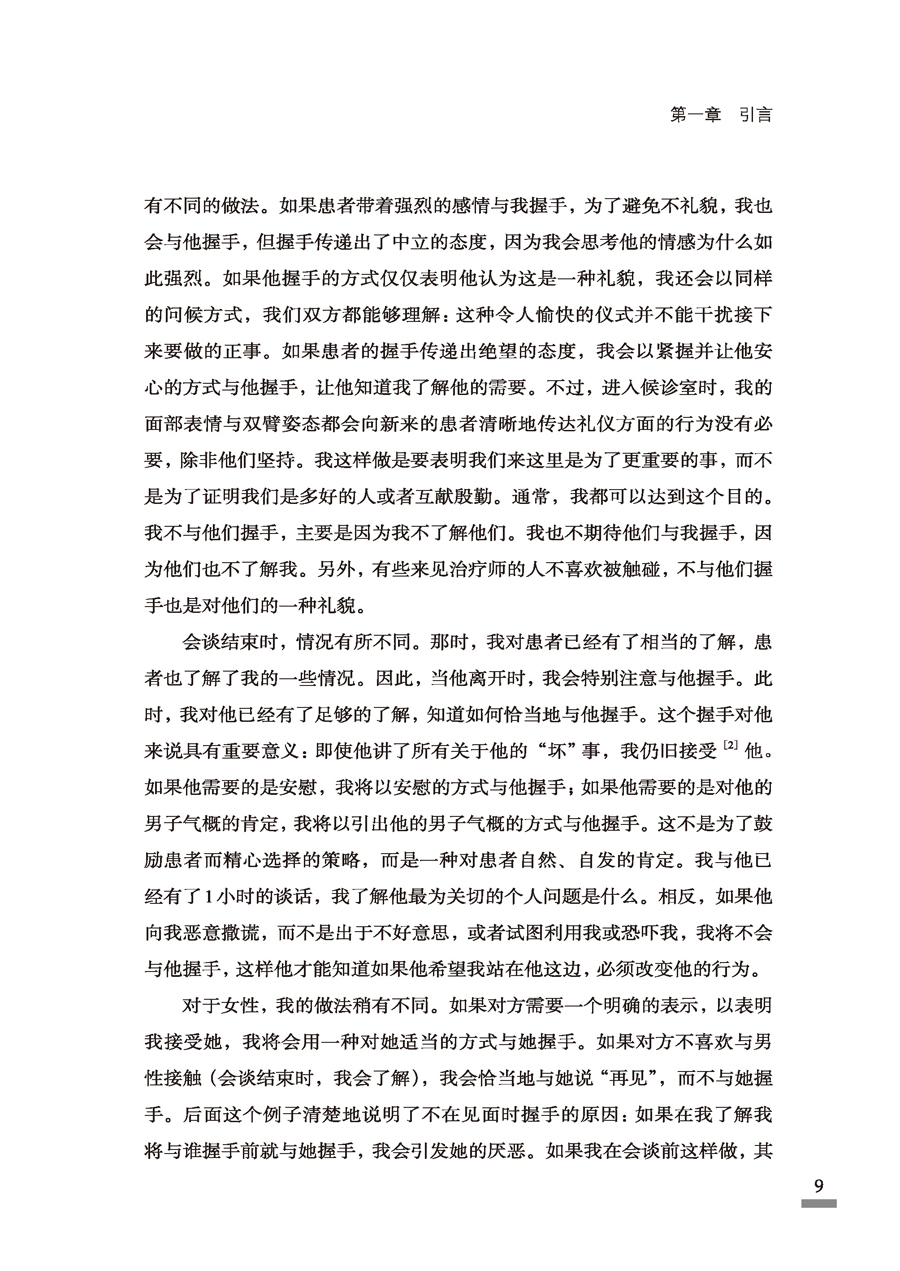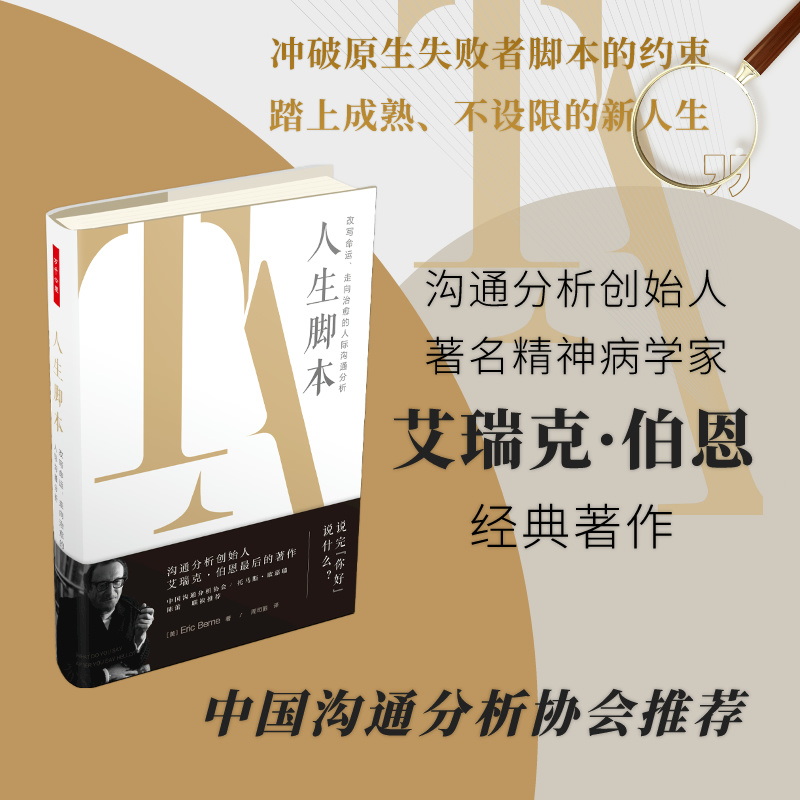
出版社: 轻工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6.40
折扣购买: 万千心理.人生脚本:改写命运、走向治愈的人际沟通分析
ISBN: 9787518434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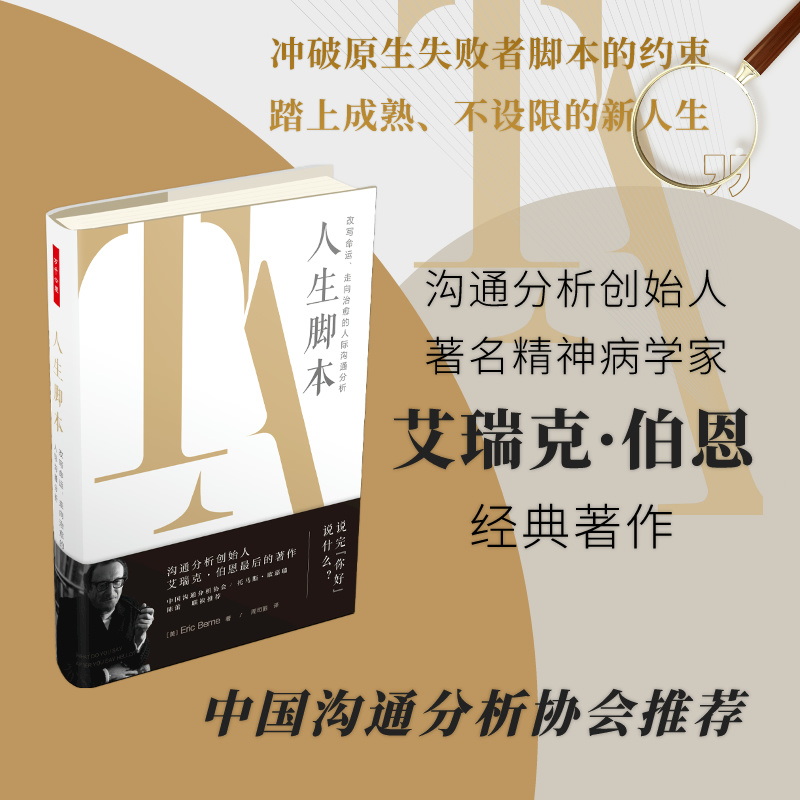
??作者简介 ?? ??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 1910—1970) 美国精神病学家。早年学习精神分析,后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沟通分析心理治疗流派。其沟通分析治疗体系在心理治疗、教育、管理以及各个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的工作领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 ?? ??译者简介 ?? ??周司丽 中华女子学院应用心理学教师和研究生教研室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咨询心理学博士,国际沟通分析协会认证沟通分析师(心理治疗方向)和沟通分析教师及督导师(受训中),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和注册心理师。
?A.说完“你好”后,你会说什么? ?? ??这个像是问小孩的问题,表面看起来非常质朴,也不需要深入的科学探究,实则涉及人类生活及社会科学中所有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婴儿会“问”自己的问题,是人们教导儿童、但答案错误百出的问题,是青少年会彼此询问或问他们的指导老师的问题,是成年人接受了长辈错误的答案并回避思考的问题,是年长智慧的哲学家书写著作却永远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了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精神病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彼此交谈(社会心理学)?人们为什么喜欢被他人喜欢(社会精神病学)?“说完‘你好’后,你会说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对天启四骑士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战争还是和平,饥饿还是富足,疾病还是健康,死亡还是生存。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之前的一个问题尚无法解答:你是如何对别人说“你好”的? ?? ?? ??B.你是如何对别人说“你好”的? ?? ??这是佛教、基督教、犹太教、柏拉图主义、无神论,特别是人本主义,所有教义中涉及的秘密。禅宗中有一个著名的公案叫“只手之声”,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你好”的声音,也可以被理解为圣经中的黄金准则,即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别人。正确说“你好”的方式,是你看到并意识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存在,了解你将与之互动,并做好了与他互动的准备。富士岛岛民可能是最有能力正确说“你好”的人,因为他们真挚的笑容堪称世界珍宝。他们的笑容会慢慢展开,蔓延至全脸,也会保留足够长的时间,使别人能够清晰地看到和辨认出来,之后才会慢慢散去。只有在饱含爱意的母亲与婴儿打招呼时,以及在西方国家中某些具有开朗外向性格之人的脸上,你才能看到这种笑容。[1] ??本书将探讨四个问题:你如何向别人说“你好”?你如何回应别人的“你好”?说完“你好”后,你会说什么?以及最主要但又带有悲凉色彩的问题—人们不互相说“你好”时,取而代之的是在做什么?下面,我将简要地回答这几个问题,之后会在各个章节进行详述。本书作为精神病学的教材,首先是写给心理治疗师的,但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以及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阅读。 ?? ??1. 为了说“你好”,你首先必须丢掉头脑中积累的垃圾,例如,回到家中,你需要丢掉在产科病房工作一天而在头脑中积聚的垃圾,并意识到你所打的这个招呼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再次发生。人们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明白这一点。 ??2. 为了回应别人的“你好”,你也需要丢掉头脑中的垃圾,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或走过你身边,等待着你的回应。学会这一点可能也需要多年的时间。 ??3. 说完“你好”后,你需要继续丢掉重新回到你头脑中的垃圾、经历的所有委屈,以及你接下来打算处理的所有烦杂事务。不过这时,你可能会发现你感到无话可说。经过更多年的练习,你可能会想到一些值得说的话题。 ??4. 本书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垃圾的:那些阻碍我们彼此说“你好”的事。我写这个部分是希望受过训练又在这方面具有天赋的人能够帮助自己和他人认清我称之为“垃圾”的东西,因为如果无法分辨垃圾是什么,就无法回答其他三个问题。我将正在学习说“你好”的人们使用的语言称为“火星语”,以区分于我们日常使用的“地球语”。无论从早至古埃及和巴比伦时期的历史记录中,还是从当下的记录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日常的地球语带来的都是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即使是那些幸存的人们,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精神困扰。我希望火星语最终能被人们恰当地教与学,从而帮助人类减少灾难。火星语是揭示事物原本面貌的语言,例如,梦的语言就是一种火星语。 ?? ??C.举例 ?? ??为了说明研究如何说“你好”的潜在价值,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命不久矣。他叫莫特,30岁,身患慢性癌症,凭借现有的医学知识无法治愈。最好的情况是他还可以活5年,最糟的情况是还可以活2年。他的精神问题表现为不明原因的抽搐,包括点头和抖脚。在治疗团体中,他很快发现了原因:他的脑中会跑过一连串音乐,这串音乐就仿佛一堵墙,阻隔了他的恐惧,而抽搐正是他在为这串音乐打拍子。这一结论来自仔细的观察,而且顺序很重要,不是音乐在为他的抽搐打拍子,而是身体的抽搐在为他头脑中的音乐打拍子。此时,团体中的每个人,包括莫特在内都可以看到,如果心理治疗移除了他脑中的音乐,那么莫特心中将释放大量恐惧。除非他的恐惧被其他令人愉快的情绪取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该怎么办呢? ??很快,所有团体成员都意识到他们其实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自己迟早会死。对这一事实,他们都有情绪,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压抑。就像莫特一样,他们感到死亡威胁着他们,他们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掩盖这种威胁。死亡的威胁阻碍着他们充分享受生活。不过,他们仍旧有20年或50年的生活可以过,而莫特只有2~5年。最终大家决定生命不在乎长度,质量更重要:这不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而是由于一个将死之人的出现,对每个人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 ??其他所有团体成员(理解火星语的人,他们很乐意教莫特,也很乐意学习)都一致同意生活意味着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看到树木,听见鸟鸣,与他人说“你好”:这是一种充满觉察而自然的体验,带着沉静与谦逊,而无须逢场作戏或虚情假意。他们也同意,为了享受到这样的生活,所有人,包括莫特在内,都需要阻挡脑中的垃圾对他们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只有当他们了解到莫特的情况并没有比他们自己的情况更加不幸时,他们才不会因为莫特的出现而感到悲伤与怯懦。相反,会为彼此的相处感到愉快,可以作为平等的人彼此交谈。此时,他们可以质疑莫特的垃圾,因为莫特现在能够理解质疑的价值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质疑;反过来,莫特也可以质疑其他成员的垃圾。其他成员和莫特都清楚莫特的境况比任何人都棘手,但莫特已经下决心放弃癌症患者这种身份,打算作为人类群体的一员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例子清晰地说明了“同情”给说“你好”带来的问题,以及说“你好”的深度问题。在莫特的例子中,其他成员向莫特说“你好”经历了三个阶段。当莫特刚进团体时,其他人不知道他是一个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的人。所以他们在团体中以自己惯常的方式与他说话。每位团体成员说话的方式基本取决于他们的成长环境—父母教他们如何与他人打招呼;后来通过学习,他们与他人打招呼的方式有了一些调整;进入心理治疗团体后,他们带着适度的尊重和坦诚说话。莫特作为一个新成员,也用惯常的方式回应他人,假装自己是一个雄心勃勃、充满热血的美国男孩,就像父母期待他成为的那样。但当第三次会面,他说到他的命数已定时,其他成员感到很困扰,像被出卖了一样。他们担心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是否让自己、让莫特,特别是让治疗师看起来很糟糕。事实上,他们对莫特和治疗师都很愤怒,因为他们没有更早说明真相,这让他们感到被戏弄了。其实,在他们向莫特说“你好”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和什么人说话,只是使用了一种标准化的方式。现在他们知道莫特是一个特殊人物了,他们期望能够回到过去,重新开始,这样他们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了。 ??然后,他们确实重新开始了。他们柔声细语地、谨慎地与莫特交谈,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用比较直接的方式。他们仿佛是在对莫特说:“看我对你的不幸多么体贴关切,是吧?”他们没有人愿意对一个将死的人大声说话,因为这将冒着损害自己名声的危险。但这并不公平,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将莫特置于上风。此时,没人敢大声笑或者笑很长时间。直到大家发现莫特可以对他的人生做些什么,这种互动才被修正。紧张消除了,他们可以第三次重新开始,将莫特作为人类群体的一员对待,而无须有所顾忌。这三个阶段可以分别这样命名:“表面的你好”“紧张、同情的你好”以及“放松、真正的你好”。 ??团体成员佐伊在了解莫特前都无法与他说“你好”。她对莫特的了解每过1周都会有所不同,甚至每过1小时都会有所不同。她每次与莫特见面,都比上次更了解他一点,因此如果想维持他们之间的友谊,她每次都需要用稍微不同的方式与莫特说“你好”。但是,她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莫特,也无法预期所有的变化,因此她永远无法说出完美的“你好”,不过可以越来越接近完美。 ?? ??D.握手 ?? ??很多患者第一次与治疗师会面时会自我介绍,并在治疗师邀请他们进治疗室时与治疗师握手。有的治疗师主动与患者握手。关于握手一事,我有不同的做法。如果患者带着强烈的感情与我握手,为了避免不礼貌,我也会与他握手,但握手传递出了中立的态度,因为我会思考他的情感为什么如此强烈。如果他握手的方式仅仅表明他认为这是一种礼貌,我还会以同样的问候方式,我们双方都能够理解:这种令人愉快的仪式并不能干扰接下来要做的正事。如果患者手传递出绝望的态度,我会以紧握并让他安心的方式与他握手,让他知道我了解他的需要。不过,进入候诊室时,我的面部表情与双臂姿态都会向新来的患者清晰地传达礼仪方面的行为没有必要,除非他们坚持。我这样做是要表明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更重要的事,而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是多好的人或者互献殷勤。通常,我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不与他们握手,主要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也不期待他们与我握手,因为他们也不了解我。另外,有些来见治疗师的人不喜欢被触碰,不与他们握手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礼貌。 ??会谈结束时,情况有所不同。那时,我对患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患者也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因此,当他离开时,我会特别注意与他握手。此时,我对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知道如何恰当地与他握手。这个握手对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即使他讲了所有关于他的“坏”事,我仍旧接受[2]他。如果他需要的是安慰,我将以安慰的方式与他握手;如果他需要的是对他的男子气概的肯定,我将以引出他的男子气概的方式与他握手。这不是为了鼓励患者而精心选择的策略,而是一种对患者自然、自发的肯定。我与他已经有了1小时的谈话,我了解他最为关切的个人问题是什么。相反,如果他向我恶意撒谎,而不是出于不好意思,或者试图利用我或恐吓我,我将不会与他握手,这样他才能知道如果他希望我站在他这边,必须改变他的行为。 ??对于女性,我的做法稍有不同。如果对方需要一个明确的表示,以表明我接受她,我将会用一种对她适当的方式与她握手。如果对方不喜欢与男性接触(会谈结束时,我会了解),我会恰当地与她说“再见”,而不与她握手。后面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不在见面时握手的原因:如果在我了解我将与谁握手前就与她握手,我会引发她的厌恶。如果我在会谈前这样做,其实是对她的一种侵犯和侮辱,因为我强迫她出于礼貌触摸我,并接受我的触摸,而这是违反她的本意的。 ??在治疗团体中,我的做法类似。刚开始时,我不会说“你好”,因为我已经整整1周没有见到团体成员了,我不了解我正在对怎样的人说“你好”。一个轻松或兴奋的“你好”对那些在两次会面中发生了一些事情的人来说十分不恰当。但是在团体会谈结束时,我会非常重视与每个团体成员说“再见”,因为此时我了解了我正在与怎样的人说“再见”,以及应该如何说“再见”。假如一位女士的母亲在上次团体会面后过世了,而我在见面时与她愉悦地说“你好”,这对她似乎不太合适。她可能会原谅我,但我没有必要让她承受种负担。在会面结束时,我会知道如何在她处于哀伤的情绪中与她道别。 ?? ??E.友谊 ?? ??在社交情境下,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交朋友是为了获得安抚。对于朋友,根据他们的准备情况或需要,说“你好”和“再见”的方式可以从公开的握手到大大的拥抱。有时,为了避免过度投入,我们也会用微笑表示。但是人生中比必须交税还要确定、和人终将一死一样确定的是:你越早结交新朋友,你越快拥有老朋友。 ?? ??F.理论 ?? ??对于说“你好”和“再见”的事暂时讨论至此。“你好”和“再见”之间发生的事涉及另外一个理论框架。关于人格与团体动力,也是一种治疗方法,被称作沟通分析。为了更好地理解后续的内容,首先需要了解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 ??若你发现人生仿佛原地转圈,或者逃不出命运般注定上演的剧情,或许沟通分析理论的创始人、著名精神病学家艾瑞克·伯恩的回答会让你豁然开朗。 ??我们早在童年时就形成了某种人生脚本,它是我们潜意识中一生的计划。而设定了输家脚本的人会践行“失败者”的角色,走向某种消极的人生结局。 ??但是,经过沟通分析式的省察,人生脚本在当下即可改写,冲破原生脚本对命运的束缚,迎来“彻底的治愈”,踏上真正成熟而不设限的新生。 ??伯恩在他最后的这本著作中,详细介绍了脚本是什么,如何形成和发展,有哪些深刻的类型,以及在临床治疗中应该如何做。无论是从事心理治疗、咨询、教育、组织发展和商业活动的专业人士,还是希望获得个人成长的读者,都将从这本经典著作中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