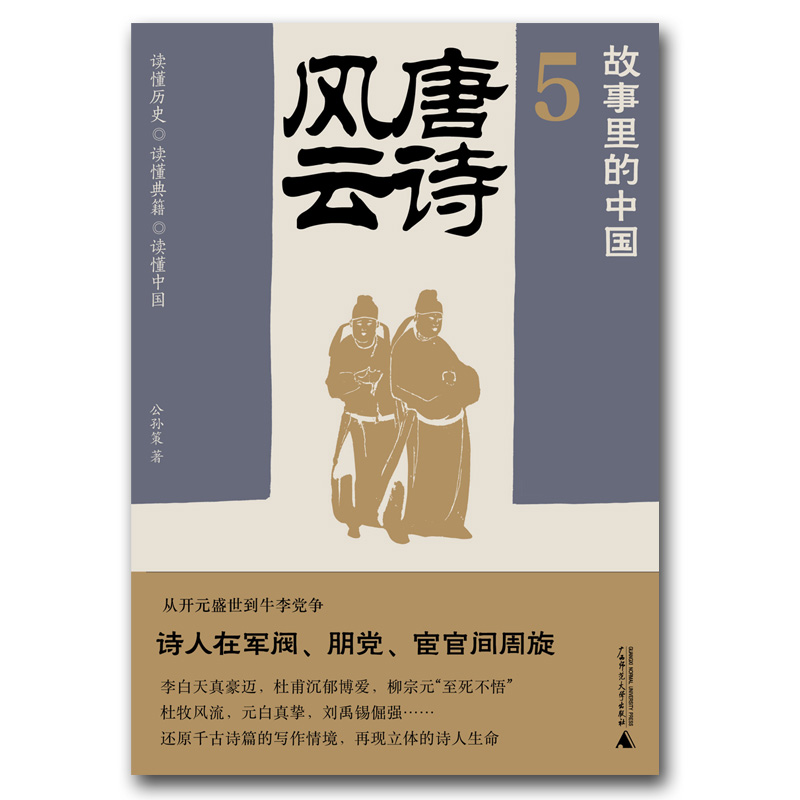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30.70
折扣购买: 故事里的中国(5唐诗风云)
ISBN: 9787559862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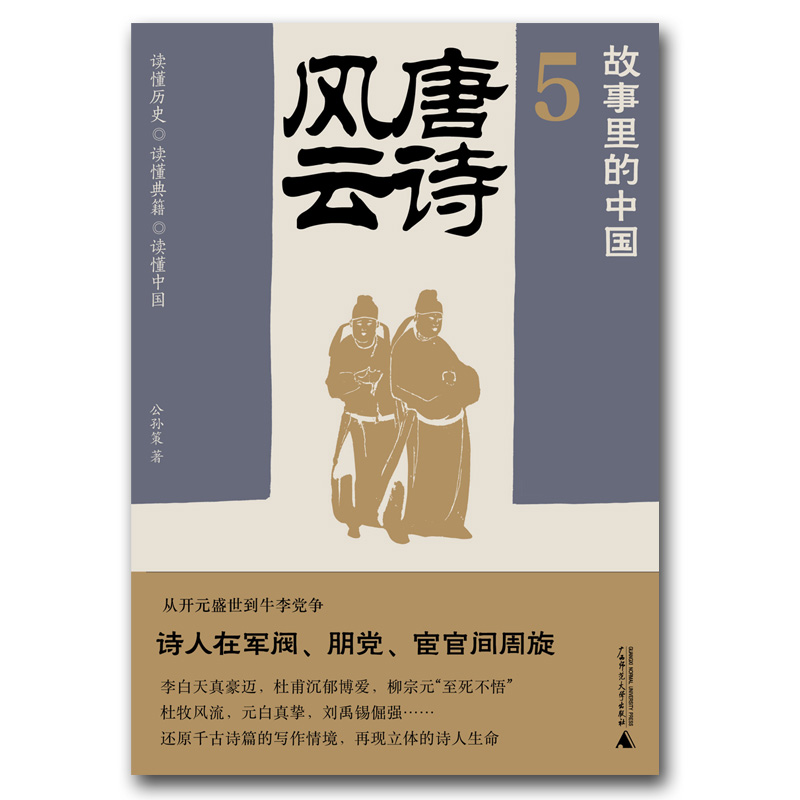
公孙策,本名陈哲明,台湾知名专栏作家。曾任“中时报系”记者、主任、副总编辑,台湾《新新闻周刊》总经理、副总编辑。代表作有《公孙策说名句故事》《公孙策说唐诗故事》《史记经典100句》《战国策经典100句》以及“公孙策说历史故事”系列等。
"这里选的两个故事,就真的是“故事”,不是历史,故事主角都是虚构的,分别是两位女侠:红线和聂隐娘。故事里还有些神鬼法术的元素,情节都很好看,也常被现代人改编称电影电视作品。如果拿现在的通俗文学作比,应该可以说是“爽文”吧,都是比较憋屈的一方,借助会法术的女子令强势的一方拜服。而这两位展现神通的人士都是妙龄女性,也很有趣。 ——编者按 大唐女侠:藩镇割据下的文人想象 红线盗合 仆固怀恩先被逼反,再被剿灭,引起各藩镇的寒心,尤其是安史旧部的河北四镇。 所谓河北四镇,包括:昭义节度使薛嵩,治所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治所在幽州;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治所在魏州;成德节度使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治所在恒州(今河北正定县)。 薛嵩、李怀仙、田承嗣、张忠志都是安史降将,他们心知肚明,仆固怀恩是朝廷“剿贼功臣”尚且有此下场,何况自己是“贼人余孽”!自己的存在全靠武力支持,所以对扩充军队不遗余力。精锐健卒选为卫士,称“牙兵”;最精锐的蓄为“养子”,名称不一,这些军士只效忠主帅,心中没有国家。而藩帅之所以这么做,另一个原因是害怕被刺杀。 藩帅相互刺杀,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红线盗合”。 河北四镇中,最嚣张的是田承嗣,兵力最弱的是薛嵩。 薛嵩为求奥援,只好跟左近镇帅结亲,薛嵩的女儿嫁给田承嗣的儿子,薛嵩的儿子娶了滑亳节度使(治所滑州,今河南滑县)令狐彰的女儿。 田承嗣患了“热毒风”的病,每到热天就发作,因此经常自言自语:“如果能够调到太行山的东边镇守,一定可以多活几年。”目标就是并吞薛嵩的地盘—如此一位亲家,比敌人还危险。 田承嗣在牙兵中挑选武艺高强的三千人,称之为“外宅男”——“男”就是儿子,亲生儿子在内宅,“外宅男”就是养子,他们的任务就是守卫内宅,每晚派三百人值班。 薛嵩知道这个亲家不怀好意,日夜忧闷,经常唉声叹气,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天晚上,辕门已关,将要起更,薛嵩仍无法入睡,拄着手杖在庭心踱步,跟随在身边的是个名叫红线的婢女。 红线问主人为何心烦? 薛嵩叹了口气说:“此事关系本州安危,不是你能管得了的。” 红线说:“我虽然地位低微,却自信能够替主人消愁解忧。” 于是薛嵩将情况告诉了红线。 红线说:“这件事不难处理,主人不必忧愁。请允许我走一趟魏州,此刻一更天动身,五更天就可以回来复命。请大人准备好一封问候信、一个官差、一匹快马,其他的事等我回来再说。” 薛嵩闻言,大吃一惊,说:“想不到你是位奇人,我居然都不知道!可是,万一事情弄僵了,会不会反而更加速致祸?” 红线说:“我此行必定成功,请主公放心。” 说完,红线回房整装,出来只见她头上梳个乌蛮髻,插一支金雀钗,身穿紫色绣花短袄,系一条青丝腰带,足下穿一双快靴,胸前挂一柄龙纹匕首,额上书写太乙神名,向薛嵩拜了两下,倏忽就不见了。 薛嵩回到书房,一个人喝酒等候。平时他酒量不过几杯,这夜却连喝数十杯不醉(紧张啊!)。忽然听到军营中破晓的号角声响起,又听到窗外有一片树叶飘落(紧张啊!)。却只见人影一闪,原来是红线回来了。 薛嵩执起她的手,问:“事情成功了吗?” 红线说:“不敢辱命。” 薛嵩:“没有杀伤人吧?” 红线:“不至于那样,我只带回田亲家翁床头一只‘金合’(用来装东西的有盖容器)而已。” 薛嵩询问经过情形。 红线描述:“夜半子时前三刻到了魏州城,穿过好几重门岗,进入田亲家翁寝室,只听到外宅男鼾声如雷,看见士兵在庭心巡逻。我一直进到床帐跟前,田亲家翁睡得正熟,头靠犀皮枕,枕边露出一柄七星剑,剑的前面有一只打开的金合,金合里有纸写着他的生辰八字和北斗神的名字,上面覆盖着香料和珍珠。我从睡着的侍女们的头上,将簪子、耳环都拔下来,再把她们的短袄、长衣都系结在一起,她们如病如昏,没有一个人惊醒过来。我便取了金合回来。” 薛嵩听完,立刻修书,派人送去给田承嗣,说:“昨夜有客人自魏州来,说他在田大帅的床头拿了一个金合。我不敢留下,恭敬地封起来,送还给您,望请收下。” 使者奔驰一整天,入夜才赶到魏州,敲开城门,请求接见。田承嗣很快就出来,拿到金合,胆战心惊,差点跌倒在地。 第二天,田承嗣派出使者,带了三万匹绢、三百匹名马,还有其他珍贵礼品,送给薛嵩。并且回信说:“我的脑袋蒙您厚恩才得保留,从今以后,我会改过自新,不再自招灾祸,为您奉毂(车后随侍)挥鞭(车前驾御)。那些外宅男,已经让他们解甲归田了!” 消息传出,一两个月内,河北、河南各节度使纷纷派使者来与薛嵩修好。而红线在任务完成不久,就向薛嵩请求“归山”。薛嵩设宴为红线饯行,席间节度从事(中高级的幕僚)冷朝阳作歌,薛嵩亲自唱歌送别。 送红线 冷朝阳 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销百尺楼。 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 冷朝阳其实就是《红线传》的作者,红线盗合是杜撰的故事,但可以体会冷朝阳身处薛嵩幕府的心情—多么期待能让田承嗣“胆战心惊,为薛嵩奉毂挥鞭”啊! 实际的发展却是,薛嵩死后,昭义军内部分裂,最后被田承嗣并吞,之后就只剩“河北三镇”了。 聂隐娘 田承嗣吞并了昭义军,唐代宗遣使奏问,田承嗣置之不理。代宗生气了,动员河北、河南九路节度使,加上淮西诸镇,会讨魏博。田承嗣一面分道抵御,一面上表请罪,再用计离间各路人马,造成成德军与幽州军互攻,诸镇围攻魏博不了了之。 平卢节度使(治所淄川,今山东淄博市)李正己掠得魏博一部分地盘,乃上表为田承嗣说项。唐代宗无心追究,只想息事宁人,乃诏复田承嗣官爵。但是如此姑息养奸作风,反而使得各藩帅愈发骄纵。 代宗驾崩,太子李适继位为唐德宗,在位第三个年号用“贞元”—口气很大,意在重建贞观与开元盛世。但事实上,他不但没能振衰起弊,且因本身不具实力却妄图削藩,而逼反诸镇,一度在朝廷之外,出现“四王”“二帝”,他本人更狼狈逃出长安。 事情的起因,是几位藩帅相继去世,他们的子、侄自立为节度使。包括前文提及的田承嗣去世,其侄田悦继任;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卒,其子李惟岳自命为“留后”(代理节度使)要求朝廷任命,德宗不准。于是田悦与李正己联合李惟岳公然造反,但李正己不久即病卒,其子李纳干脆不理朝廷,任命自己为平卢节度使。 德宗闻变,决定大举讨伐,派李晟率领神策军进讨,并诏令各镇出兵,联合进剿。官兵剿乱初期成果辉煌,可是各镇打了胜仗后,都想要领有新地盘,德宗不准所请,由朝廷另派节度使,却逼反了几个原本支持朝廷的藩帅。 局势逆转,叛军击退政府军,四镇会盟,一齐称王: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共推朱滔为盟主。 德宗征调驻防在西北的泾原(今甘肃泾川县与宁夏固原市一带)兵马,增援前线。这些边兵经过京师长安,原本满怀期待会得到朝廷赏赐,不料当时国库空虚,竟一无所给。 负责供应军粮的京兆尹王翃,提供的食米中甚至掺有沙子,这下子军队哗然,开骂:“吾等将赴战场效死,吃都吃不饱,如何以微躯拒白刃!听说宫中琼林、大盈两库充满金银布帛,我们何不取之,以图富贵!” 兵众鼓噪呐喊,回头攻向长安。长安城防措手不及,乱兵涌入,一片大乱,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 乱兵在长安城内找到一位老长官,曾任泾原节度使的太尉朱泚,朱泚正是叛军盟主朱滔的哥哥,当天就进入皇宫即位称帝,国号“秦”,后来又改为“汉”,并派出使节,封朱滔为皇太弟。 朱泚亲自领军攻打在奉天的唐德宗,不能取胜;在东方作战的李怀光、李晟率军西归勤王,朱泚不敌,退回长安。 唐德宗这时下了一道历史上著称的《罪己诏》,除了深自检讨(自责“朕实不君”),并赦免东方叛军(四王)。 罪己诏颁下后,王武俊、田悦、李纳三人主动取消王号,上表谢罪。只有中途加入叛军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不奉旨,反而在汴州称帝,国号“大楚”—这时候,天下有三个皇帝:大唐皇帝李适、大秦皇帝朱泚、大楚皇帝李希烈。 唐德宗宠信的权臣卢杞与李怀光不睦,使得李怀光一度跟朱泚联合。但朱泚与李怀光旋即翻脸,李怀光一怒而走, 渡河袭据河中。 形势再度逆转,神策军李晟与浑瑊克复长安,朱泚逃走,被部将诛杀,人头献至长安,德宗也回到京城。不久之后,李怀光也兵败自杀。 唐德宗问宰相陆贽:“东方之贼该怎么办?” 陆贽说:“诸藩气夺势穷,必有内变,可以不战而屈。” 于是政府军采取稳扎稳打战略,下令四方州镇“合围封锁”,不积极迫进。果然,李希烈众叛亲离,被部将陈仙奇毒杀。 德宗回过神来,开始秋后算账。 在德宗流亡奉天期间,长安城内的士人有对朱泚谄媚拍马屁的,也有心向故主却不敢明言的。最忠烈的一位是太常少卿樊系之,他受命起草朱泚的即位册文,心里不想写,可是又不敢不写,怕连累亲族。结果他在写完以后,仰药自尽。 樊系之的朋友严巨川为此感慨: 建中四年十月感事 严巨州 烟尘忽起犯中原,自古临危道贵存。 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 落日胡笳吟上苑,通宵虏将醉西园。[ 上苑:上林苑,西汉皇帝林园。西园:东汉皇家御花园。皆是以汉喻唐。] 传烽万里无师至,累代何人受汉恩。 当时有一位“风情女子”李季兰,上了很多诗给朱泚, 全是阿谀之辞。德宗将她抓来,责备她说:“你怎么不学学严巨川的诗呢?”下令当庭扑杀。 这就是“有心振作”的唐德宗作风:没有实力却躁进惹来叛乱;平定叛乱却又姑息养奸;姑息藩帅却只会对弱女子开刀。于是乎,藩帅就更嚣张了。藩镇之间,为了抢地盘,派刺客行刺的事件,更屡有所闻。有一个唐人传奇(小说)以这一段时期为背景,那就是《聂隐娘》。 聂隐娘是魏博大将聂锋的女儿,十岁时被一个尼姑带走,五年后又被送回来。隐娘对父母述说这五年的经历: “师父带我到一个大石穴,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学登山爬树,渐渐觉得身轻如风。一年后,用剑刺猿猴,百无一失;后来刺虎豹,也能割下它们的头取回。三年后,能飞,用剑刺鹰隼,绝不失误。天天练剑,师父最初给的一把二尺长的剑,已经消磨掉五寸。” “第四年,可以大白天在大街上刺杀一个人(那个人恶贯满盈,死有余辜),没有任何人看见。第五年,师父叫我去刺杀一个残害人民的大官,我伏在他屋梁上,直到深夜才提着他的头回来。师父问:‘为何这么" "我们认识大唐,好像总是先看到文艺、学术、风格气度。读杜甫的诗,哪怕读到他笔下惨淡的真实生活,也首先被诗歌高超的修辞感动。读《祭侄文稿》,哪怕了解其背后满门忠烈的悲壮故事,也首先被这幅书法作品的气势震撼。哪怕知道李白的打架斗殴经验,也首先与他诗歌的豪迈激越联系。好像先有文学艺术的大唐,而真实的大唐历史是诗歌的注脚。 公孙策先生的《唐诗风云》这本书刚好反过来,他把历史中的大唐放在前景,而文学艺术常常是诗人仕途的副产品。安史之乱爆发,皇帝离开京城,其他人蠢蠢欲动,李白恰好上了永王李璘的“贼船”,遂写几十首《永王东巡歌》;后来因为这次站错队获罪被流放,又写了《上三峡》;流放途中得到赦免,才有了我们倒背如流的《早发白帝城》。那为什么加入造反队伍这么大的罪都能获得赦免,则是多亏郭子仪说情。 郭子仪才是真正“改变历史”的那部分人,也是本书的一个关键人物,在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吐蕃入侵等大事件中,他都立下战功。跟着藩将捣乱的回纥军队一看郭令公来,都不打了,下马拜服。他也屡次被夺兵权,但下次朝廷有困难还是毫不犹豫地上马。这本书讲了很多郭子仪这样的人,包括《祭侄文稿》所祭的颜季明与其父颜杲卿,还有冲出重围搬救兵不成又冲回去与城池共存亡的南霁云,等等。他们的品行,夹在昏庸的皇室、野心勃勃的军阀、勾心斗角的权臣之间,与唐诗一样,对后人来说,有万丈光焰。我们看了就知道,历史本身的热血、沉郁、荒唐,有时比诗歌更甚。 除了在讲故事的同时赏析唐诗,书中还选取了《资治通鉴》、新旧《唐书》等史书中与本书故事有关的段落,同样辅以注释,我们在读故事、学历史的同时,顺便还温习了古汉语,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学历史、学语文、练习作文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