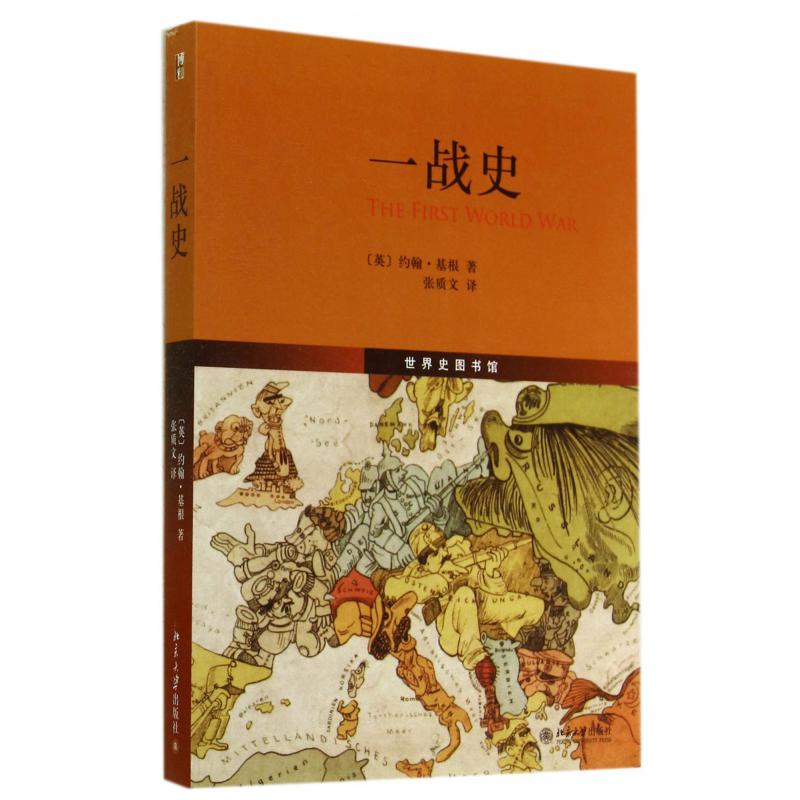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72.00
折扣价: 51.12
折扣购买: 一战史/世界史图书馆
ISBN: 9787301245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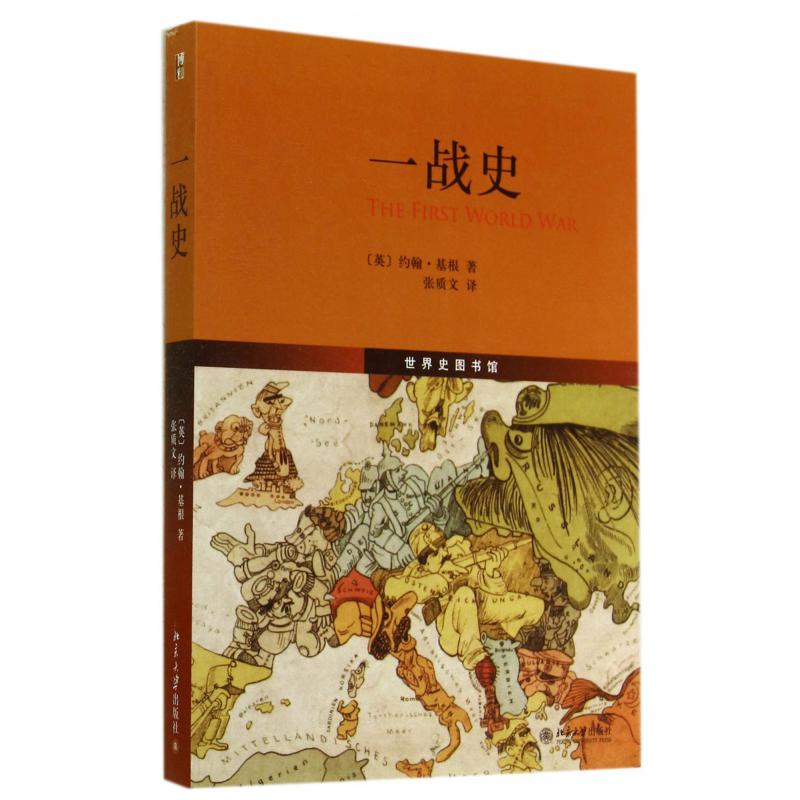
约翰·基根(John Keegan)是伦敦《每日电讯报》防务主编,曾多年任英国桑霍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高级讲师,并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和瓦萨尔学院历史学教授;与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霍华德并列为二战后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权威。《战争史》与《战斗的面貌》(The Face of Battle)是其最重要、最著名的著作。
到1915年春,1914年冬季所有参战军队的进攻力 量消耗殆尽——在东线只比西线晚一点点——这给欧 洲带来一条新的边境。这一边境的性质与战前那些老 式、松散、往来自由的边境大为不同。战前,人们在 寥寥无几的海关口岸通行,无需护照,或是在其他任 何地方往来,也不需要正式手续。这种新的边境与罗 马军团在边境的堡垒(limes)类似,是一种把巨大的 军事帝国与外部世界分隔开来的土木工事构成的壁垒 。确实,从罗马以来,欧洲从未有过类似的东西出现 ——查理大帝统治下没有,路易十四统治下没有,拿 破仑统治下也没有——直到未来三十年后冷战爆发前 也不会再次出现。 然而,不同于罗马边境的堡垒和铁幕,新的边境 既不标志社会边界,也不标志意识形态边界。它只是 防御工事而已,既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分开了 交战各国。这样的防御工事此前曾经存在,尤其是在 美国内战中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半岛战争中,威灵 顿在葡萄牙修建过类似的工事;它也在巴尔干战争中 伊斯坦布尔外面的恰塔尔贾(Chatalja)出现过;17和 18世纪,沙皇军队在西伯利亚草原也曾修建这样的工 事(长砦,Cherta lines)。但1915年欧洲的新边境 在长度、深度和布置上都是无与伦比的。从波罗的海 的梅梅尔(Memel)到喀尔巴阡山的切尔诺维茨,从比 利时的纽波特到弗赖贝格(Freiberg)附近的瑞士边境 ,土木工事形成的界限延展接近1300英里。1870年代 美国牧场发明的铁丝网出现在这里,到春季,已在敌 对双方的战壕之间排列成行。地下掩体也出现了,英 国人称之为“防空壕”(dugouts);此外还出现了通 往后方的支援和后备堑壕。然而,在本质上,这条新 的边界是壕沟,挖掘得足够深,能够保护人,足够窄 ,使炮弹难以击中,每间隔一段距离后转弯,挖出横 道,以便分散爆炸的冲击波、碎片或是弹片,并防止 进入战壕的敌人以火力控制太长的距离。在潮湿或是 多石的地面,战壕很浅,而在前方设置较高的护墙, 用泥土,常常是沙袋建造。土壤越是干燥和适于建造 工事,就越不需要用木材或枝条编织物建造的“护墙 ”支撑战壕内壁,地下掩体也就越深;这些开始时只 是作为最靠近敌方的战壕侧面上用来保护入口、避开 飞进来的炮弹的“刮痕”,很快发展为很深的掩体、 向下延伸的楼梯;德国人最终在阿图瓦和索姆的白垩 土中挖到了30英尺或是更深,在最凶猛的炮击中岿然 不动。 但是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战壕体系。不同地方,不 同战线上的样式各不相同,设计取决于地形的特点、 部队相对于空间的比例——西部高,东部低一一和战 术准则,还取决于决定了战线停止在哪里的战斗过程 。在1915年东线宽阔的无人区,分隔敌对双方前线的 空间可能达到三四千码宽。在克拉科夫以南的戈尔利 采和塔尔努夫(Tarnow)之间,即将来临的大规模奥德 进攻将发生在这里,“只有一条狭窄、连接也不好的 壕沟,前面有一两股铁丝网,而通往后方的交通线常 常是在开阔地上……而且也常常没有预备阵地”。相 比之下,西线的无人区一般宽两三百码,常常更窄, 有些地方只有25码宽。紧张的战壕战甚至导致双方修 建了“跨国的”铁丝网障碍。尽管障碍带——先是串 在木桩上,后来使用固定时不会发出喧闹锤击声的螺 旋桩(screw:pickets)——仍然很窄,到1915年春 ,铁丝网大量出现。50码深的密集障碍带是稍后一些 年发展出来的。在前沿阵地的后面,英国人尝试挖掘 一条“支援堑壕”(support 1ine),与第一条距离 200码,更远的400码处常常还有一条“预备堑 壕”(reserve line)。这些不同的堑壕由“交通壕” 连接起来,后者同样也挖出横道,使救助和配给人员 在从后方接近前线时自始至终得到掩蔽。如果概略地 表示,这种布局看起来会与18世纪攻城工程中由坑道 连接的“平行堑壕”很像。然而,当战壕遭遇洪水、 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下,或者在战斗中落入敌手,所有 图表式的整洁都很快荡然无存。总有新的战壕被挖掘 出来以“改善”战线或者弥补在战斗中的损失:旧的 支援壕或是交通壕成为新的前线;一次成功的推进可 以把整个战壕体系抛诸身后,可能只有当局部优势转 移到另一方时才会重新启用。而就如第一张航空照片 不久揭示的那样,西线很快成为一个重复的场景和死 胡同组成的迷宫,士兵们,有时候是整支部队很容易 在其中迷路。当在前线的期限结束,一个营将接替另 一个营的阵地时,熟知战壕地理的向导是换防时不可 或缺的伙伴。指向较为结实的战壕和民居遗迹的布告 板同样必不可少;在1914—1915年冬天的伊普尔突出 部,至今仍有被英国士兵命名为电车小屋、巴特西农 场、乞丐寮、苹果别墅、白马酒窖、堪萨斯路口、玩 具屋的建筑的遗迹。 英国人在1914年10月急匆匆赶到伊普尔,以填补 西线出现的缺口,他们已经在那里尽自己最大可能地 把工事挖掘到地下。一个人可以以三分钟一立方英尺 泥土的速度挖掘避弹坑(shelter pit),它或许能够 在半个小时内为一个士兵提供掩体,当它们被连接起 来,就成了战壕。更常见的是,第一个掩体是一条原 有的沟渠或者田间排水沟;当它们被挖深,或者遇到 降雨,这些现成的隐蔽所会积满水,除非下大力气, 否则根本就无法住人,就像第2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 (2ndRoval WelCh Fusmers)1914年10月在伊普尔南 部遭遇的那样:“公路和许多田地以很深的沟渠作为 边界……土壤大多是黏土,或者沙子……连指挥官派 出人手在[防守面对德军的前沿阵地的]掩护部队后面 进行挖掘……C和D[连]分段挖掘带有横道的普通战壕 。A[连]分不同的排进行挖掘……B[连]挖掘一条辅助 战壕……并留下一个排驻扎在那里。其他三个排去往 酒窖农场后面柳树成行的干水渠……并用他们的挖掘 工具进行修补。”12月,在他们接管的邻近一个类似 防区,“24个小时里一直是‘雨,雨,雨!’冬汛来 了,沟渠变成了流入河里的溪流;它是这个排水造出 来的低地国家的主要排水道之一。胸墙东倒西歪;沟 渠造成的战壕里水流湍急,在白天不得不放弃它。” 在皇家工兵部队和从锯木厂来的木头的帮助下,战壕 终于在水线以上重新建好。“在可以听到敌人声音的 地方……在两英尺深的……水里工作的人们……不得 不把[木头]强行插进流动的泥淖里……两个星期的艰 苦劳动建造出一条地面高于正常水线的战壕……在 1917年,它仍然是该防区最为干爽的战壕。” 这条战壕长期存在,这并不寻常;尽管西线即将 陷入僵持,没有多少前线从1914年到1917年一直持续 保持它一开始时的状态。燧发枪团在1915年1月伊普 尔以南利斯河附近一处阵地的经验解释了何以如此… … P192-P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