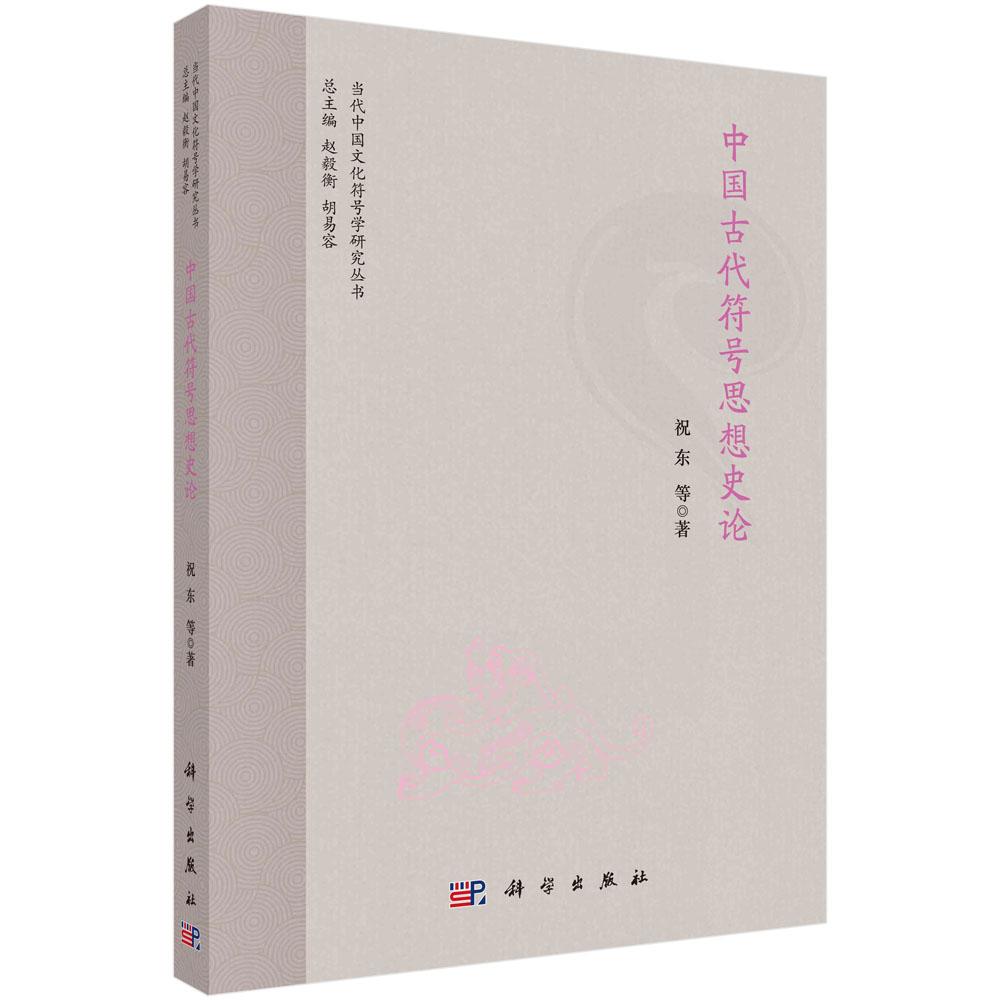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77.42
折扣购买: 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
ISBN: 9787030708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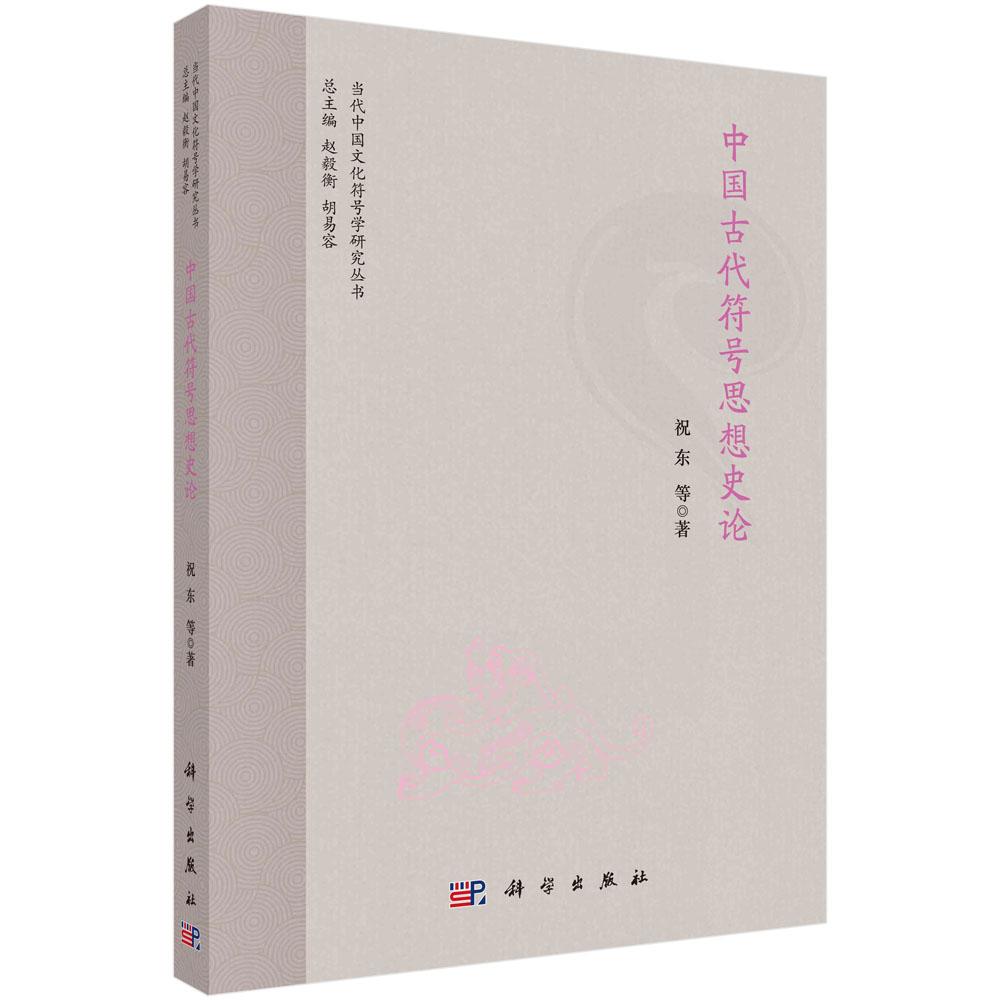
祝东,男,湖北孝感人,博士,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理事,文化与传播符号学会常务理事,国际符号学会(IASS)注册会员,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成员。
绪论
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曾开宗明义地指出:“符号就是意义,无符号即无意义,符号学即意义学。” 这是一个简单而明晰的定义,因为无论是意义的传递还是接收都需要用到符号,任何意义的解释也必须借用符号才能实现。意义即“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之间据以对符号的指涉进行编码和解释的一种既定秩序” 。人类的社会活动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制造意义、规范意义而又不断受意义规约的过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关乎符号,人之所以为人也在于他能制造并使用符号。德国哲学家恩斯特 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他对人的定义还不够完善,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表意活动,还要受到人类社会约定的道德伦理的制约,或者说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符号表意活动,规范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秩序。人类会不断对其表意行为做出伦理反思与调整,以求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和谐共生。
总体而言,符号学可以缕分为三个层面的探讨,其一是在符号与对象层面展开的科学符号学,目标在求真,其二是在符号与内容层面展开的文艺符号学,重点在于求美,其三是符号与主体层面的意义交流与价值规范,其核心为求善。符号学会在科学的、艺术的以及伦理的三个维度上展开,由第三个维度发展而来的即是伦理符号学(Semioethics,又称作符号伦理学)论域。伦理符号学并非以伦理为研究对象,而是符号学研究的一种视域,认为人类的符号活动与生命活动同步,因此要求符号学回到人类符号活动的价值论维度。人类作为唯一能够对符号活动进行反思的动物,必须担负起对生命的责任。现代意义的中国伦理符号学研究虽然起步晚、发展相对迟缓,但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很早就对人类的符号行为进行了反思,他们的学术思想中的确存在着丰富的关爱生命和谐发展、注重人际规约的伦理符号主张。系统发掘中国符号学思想及其伦理价值,不仅能够推动中国符号学思想史的建构,促进中西学术对话交流,更能为当今中国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重建文化表意活动中的价值规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发展的符号学及其伦理视域
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符号表意的学科,诞生于20世纪初期。符号学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的自觉,也即符号学作为真正的学科,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随即向全世界拓展,向各个学科渗透,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方法论。关于符号的定义,国内外学界迄今鲜有一致的观点。符号学开创者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曾经给符号下了一个定义:“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作符号。” 索绪尔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符号进行定义,并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而且这个音响形象主要是声音的心理印迹,并建议保留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另一开创者查尔斯 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也曾经给符号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符号 在再现体(representamen)形式上而言,即对某人来说,在某个方面或某个品格上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该符号在此人心中创造出一个同等的符号或一个发展了的符号。我将创造出的这个称为该符号的解释项(interpretant)。而该符号代表的事物,是其对象(object)。” 也即,符号有一种能代表某一事物的能力。
纵观国内外各种关于符号学的观点,我们认为赵毅衡关于符号的界定比较精当且较易为人理解:“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 赵毅衡用“被认为”替换了前人的“代表”说,其实是将意义的源头回归到解释者一方,意义必须在接收者这里才能得到实现,否则一个发出的符号只能是潜在符号,其意义有待阐释。事实世界广袤无垠,如人类尚未发现的宇宙世界,皆自在地存在着,而人类的意义世界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为人类所认知接受的那部分,也即是人类赋予已知世界以意义的那一部分。从一个完整的符号过程来看,发送者的意图意义经由符号转变成文本意义,然后在接收者这里达成解释意义。人类所有意义的传达解释必然要借助于符号,符号学即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这一界定也适宜于对中国的传统伦理符号学做出合理恰当的阐释,人们使用符号的过程其实也是对符号的一个解释过程,如当人们在用“道义”这种组符号来规范、评判一个人或者社会群体的表意活动时,实际上也是对“道义”这个符号的解释—什么是义(义的内涵),怎样做符合道义,怎样做又是违背道义(道义的外延),这些问题在伦理符号学中将以更细致繁杂的方式展现出来。
要谈伦理符号学,必须先对伦理学有基本了解。伦理学是人类的一门古老的人文学科,其主要研究对象为道德问题,其终极目的是求善。“伦理”一词,在中国文献典籍中,最早见于《礼记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 大意是说,音乐是通于人情事理的,“伦”在《说文》 中被解释为“辈也” ,并且可以引申为同类的辈分、顺序等,其实也就是指人类之间的尊卑长幼等关系,也即人伦,而“人伦”这个词早在《孟子 滕文公上》中就曾出现过:“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学校的目的在于教人明乎人伦,也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从中可以看出所谓人伦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之间的人际意义规范关系,人伦即人的意义是在各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理”在《说文》中的解释是治玉,援引《战国策》所记,郑人谓未琢之玉为璞,理过,也即剖析琢磨过之后,才成为玉,因此,“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 。人伦物理必须经过推敲揣摩,才可以领会,理即可引申为道理、规则等。由是可见,伦理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意义规则。
汉语中的“道德”一词,从伦理学意义上合用始见于《荀子 劝学》:“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意思是说学习一定要达到《礼》所要求的标准才算是到了道德的顶点。“道德”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解释为:“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人们的自律或通过一定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 道德在英语中为morality,意思是习俗或礼仪。综合起来看,道德在中外都是指人类行为的规范准则,对这种规则的遵守应该是自我发自内心的,道德偏重个体的主观认同,而伦理则偏重社会团体的客观规范。也即,道德更多地用于人,偏于主观、主体、个体意味。相较而言,伦理则更具客观、客体、社会团体方面的意味。“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 伦理学通过对人类道德现象的研究,寻找其行为背后的规律法则,从而使人类更加全面地认识自我行为,指导自我发展,为人类提供社会行为的根本性指导。
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沿革,蔡元培的总结颇为精当:“我国伦理学说,发轫于周季。其时儒墨道法,众家并兴。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言始为我国惟一之伦理学。魏晋以还,佛教输入,哲学界颇受影响,而不足以震撼伦理学。” 中国古代伦理学说,发端于周秦之际,此前殷商时期,当然也会有道德现象,但是还没有广泛系统的研究,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诸子百家并争,特别是儒、墨、道、法四家,研究亦颇为深入,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影响亦最大,我们可以说先秦儒墨道法诸子的伦理学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根源,后来的伦理学都可在先秦诸子伦理学说这里找到渊源。汉魏以降,佛教东渐,没有改变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而是改头换面以适应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要求。即便晚清民国以来西学东渐,依然无法根本性地改变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所谓新旧冲突云云,仅为伦理界至小之变象,而于伦理学说无与也”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把握住了先秦诸子伦理学思想,特别是儒、墨、道、法四家的伦理学思想,就基本上把握住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顺流而下,两汉阴阳五行之学、唐宋佛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等,则是流脉,皆受到先秦伦理思想的影响。
伦理符号学是一个新名词,与种族符号学一道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符号学家托马斯 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将符号学发展为“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指出符号与生命相重合,这为符号的生命和生命的符号提供了连接点和观察点;苏珊 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与奥古斯都 庞奇奥(Augusto Ponzio)以及约翰 迪利(John Deely)等学者沿着西比奥克的路径,提出伦理符号学必须以全球视野关注符号域(semiosphere)和生命界以及文化界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流。2003年,庞奇奥与佩特丽莉重提伦理符号学这一术语,旨在恢复符号学对生命的关爱,因为人类的符号活动生命活动是彼此交叠在一起的。 在他们看来,伦理符号学的主要议题是在符号活动与生命彼此交叠这种整体视野中“关爱生命”,在这一主旨之下,佩特丽莉等认为要复兴古代符号学(症状学)致力于生命健康这一传统。西方伦理符号学由人类符号活动转向生物符号活动,注重对其互动关系的考察,凸显的是一种生态意义的伦理符号学思想。显然佩特丽莉的这种伦理符号学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实际,中国传统伦理符号思想自发源起,就关爱生命,注重人际交流的伦理问题,如孔子的仁学说、孟子的性善说、义利之辨等,西方的伦理符号学家们尽管在著作中一再提出整体视野,但他们的“伦理符号学”并未吸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宽广视野和哲理深度,其局限性很明显。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极其注重实践,道德伦理问题于中国先哲而言,不只是知识问题,更是信仰问题和道德实践问题,先秦诸子学和易学皆关注现实和实践,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符号学思想本身就是伦理符号学的进路。
按照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实际,结合新起的伦理符号学关爱生命的研究思想,本书认为,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及其伦理价值的研究,应该是综合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与伦理意义及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现状的一种通过伦理学视域对人类表意活动的规范反思的学术思考,注重以语言文化及其符号系统对人类表意行为的影响来考察先哲是如何用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对社会文化进行规范调整,以及对符号过程的反思。人的符号表意活动必须遵守一定社会中的伦理规范,一定社会内的伦理规范必然影响人的符号表意活动,人类在符号表意活动过程中受到的价值规约,以及传统伦理思想观念在影响人们符号活动时呈现的规律等,这些都是本书需要研究的内容。
二、中外相关研究的回望与检视
现代符号学的兴起虽然是20世纪初的事情,但人类用符号进行的表意活动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与人类生命发展与共。中外符号学思想及相关研究亦源远流长,中国、希腊、印度的古代哲人都曾经对符号表意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诚然,中国古代并没有一门与现代符号学意义相当的符号学研究学科,但是中国古代的哲人确实曾经用符号学的思想方法对社会文化进行过考察,对人类经由符号表达意义及其符号活动有过思考和探索,只是相对缺少理论与方法的自觉罢了。这一理论方法的自觉责无旁贷地留给了当今有志于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研究的学者。对中国传统符号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盛于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代表性学者有李先焜、孙中原等。但他们多是从符号逻辑角度切入,而从文化伦理符号学角度进行观照的学者则相对不多。
作为术语的伦理符号学尽管晚起,但是对相关思想的关注却早已有之。赵元任1926年发表于《科学》的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文章,提出建设一个普遍符号学的设想,并认为里面应有关于“符号好坏的原则”“改良不好的符号,创造缺乏的符号” ,显然这些论域其实都与伦理符号学研究的内容有关。如卢德平言:“很少有人在此基础上做过深入、系统的研讨。” 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关伦理符号学方面的研究一直被忽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重新拾起这条研究脉络,进行此方面的研究。
如李幼蒸对中国传统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发掘阐发,先后著有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Ethical Archetype(1997)、《仁学解释学—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