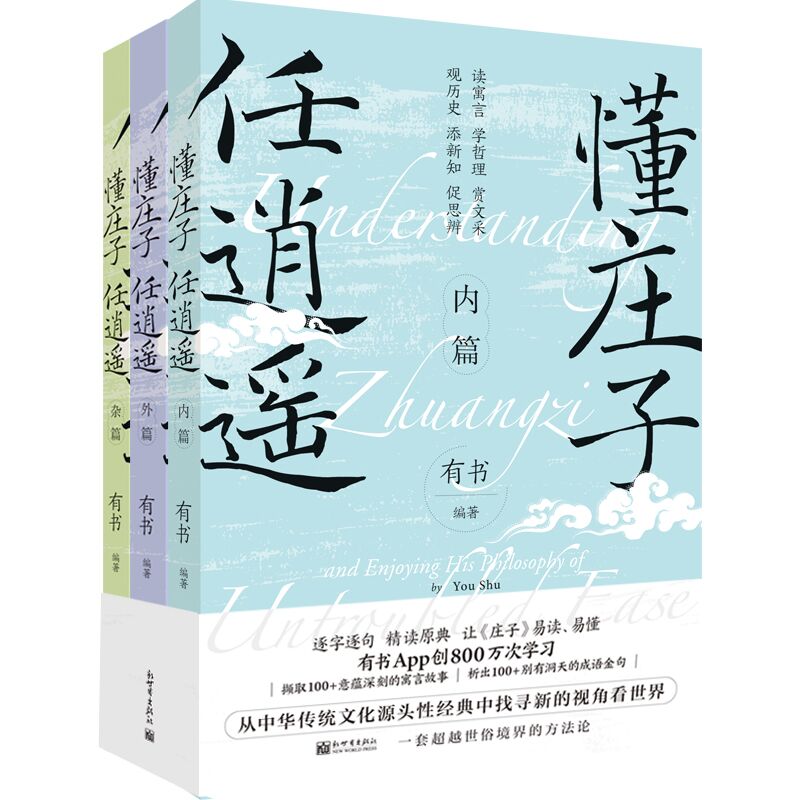
出版社: 新世界
原售价: 115.00
折扣价: 67.90
折扣购买: 懂庄子 任逍遥(全3册)
ISBN: 97875104765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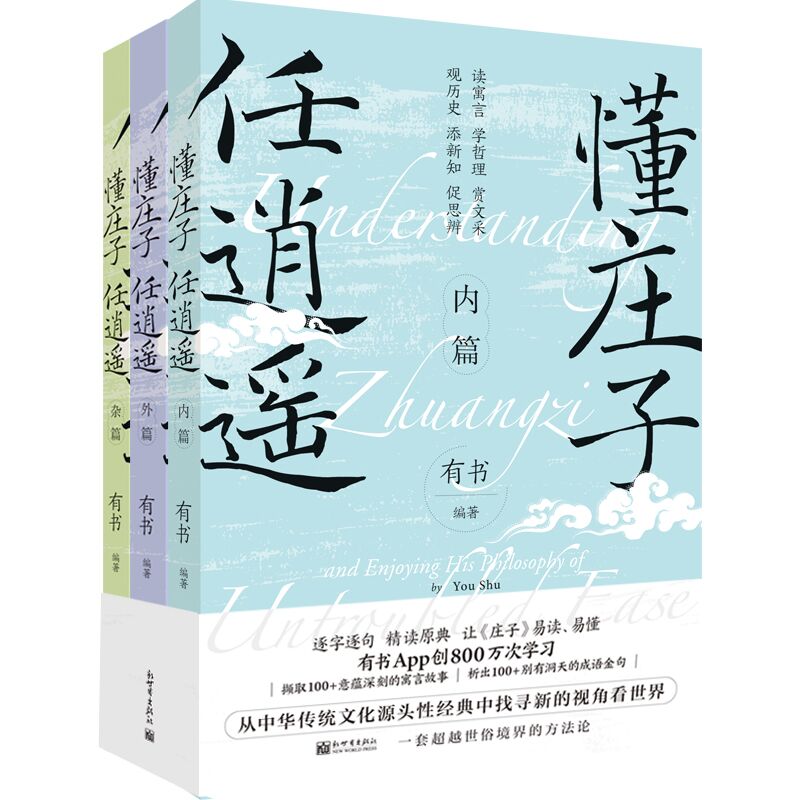
有书,成立于2014年,旗下拥有有书App、有师、有书空间、有书新媒体矩阵等四大业务模块。 有书是颇具影响力的终生教育领创者,致力于帮助人们持续、系统、高效地获取所需知识,让人人都能享受有书相伴、终身成长带来的美好生活。 有书拥有6000万用户,有10万个书友群并遍布于中国100个城市,共读书籍累计阅读次数超过1.5亿次,共读书籍累计阅读人数超过4500万。 已出版畅销书《典籍里的中国》《诗词里的中国》《一读就上瘾的心理学》。
老聃:说话简单点,大家都很忙的 《庄子·天道》中“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原文: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 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故事讲的是,孔子有一天跟学生们说,他想把自己写的书,保存到周王室的图书馆里去。学生子路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听说,周王室原来的图书馆馆长是老子,现在他已经引退、返回家乡了。先生要想藏书的话,不如去找他说说。”孔子一听,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前往拜见老子。 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老子,希望自己的书能入藏,可老子压根儿没搭理他。孔子无奈,开始援引《六经》来解释自己的书有多好,从天到地、从古到今,一五一十地给老子细细说来。 老子实在是不耐烦了,直接打断他,说:“你说得太繁琐了,能不能用一句话,说说你这些书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呀?”孔子说:“主旨就是仁义。”老子说:“请问,仁义是人的本性吗?”孔子说:“是的,君子如果不仁,就不能成就名声;君子如果不义,就不能立足社会。仁义是人的本性,离开了仁义又能干什么呢?” 老子说:“那我再问一句,什么叫做仁义呢?”孔子说:“与万物同乐,兼爱无私,这就是仁义。”老子说:“哎!你这种言论,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性情已经开始迂腐,才需要强调兼爱;因为自私自利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所以才需要强调无私。先生,你是想让天下人都失去养育自身的条件吗?天地原本就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日月原本就存在光亮,星辰原本就有各自的序列,禽兽也原本就有各自的群体。先生如果能仿照自然的状态行事,顺应天地规律去进取,就已经很不错了,又何必如此急切地标榜仁义呢?这岂不像是打着鼓,去追寻逃亡的人,鼓声越大就越追不到吗?哎,先生,你可真是扰乱了人的本性啊!” 在这则小故事中,庄子借孔子和老子的对话,再一次说明了仁义是戕害人性的罪魁祸首!作为一国之君,最应该做的,是尊重天地万物自然的发展规律,以推行“无为之政”为首要理念,而不是以虚假的仁义,来扰乱人类的纯真之情与自然本性。 本篇的篇名,叫《天道》,“天道”与“人道”可以说是先秦时期最为重要的一对哲学概念。早在春秋时期,子产就已经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说法。后来孔子和孟子基本继承了子产的思想,认为天道和人道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人难以把握天道,因此只能大谈仁义礼智,追求可以把握的人道。 而道家在这一点上,选择了与儒家完全相反的方向。道家崇尚天道,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肯定天道,排斥或否定人道,认为天道公平无私而人道卑劣,因此提倡绝仁弃义、绝圣弃智,返璞归真。 庄子及庄子后学,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又做了新的阐述,认为为君之道应效法天道,以天为宗,以自然为用,以虚静、恬淡、无为为根本;而为臣之道应人道,各守其职、尽忠职守——唯有如此,才能映照万物,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国家治理有序的超然境界。就如故事中老子所说的,天地星辰都有自己运行的规律,作为君主,只需要顺应就好了,像孔子一样额外创造出一套体系来控制万物,简直是多此一举、有害无利。 这种“虚静”思想,对中国文艺思潮和文人的创作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作家只有保持虚静的心灵,“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才能达到“心游万仞,精骛八极”(陆机《文赋》)的至高境界;只有精神世界空灵包容,“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秋日》),才能收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的自在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虚静的心态,对于为生活奔波、在城市中疲于奔命的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投身自然,让压力得到暂时的解脱,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安宁,可以调节我们的身心健康。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在谈到庄子玄禅时曾说:“它可以教人们去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慕,或怡然自适,与活泼流动盎然生意的大自然打成一片,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这可能就是庄子带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了! 除此之外,这则故事还告诉我们,讲话要抓住重点,交流要有针对性,故事中孔子喋喋不休地给老子讲述自己著作的重要性,并且援引“六经”内容来阐发自己的学说,整个过程漫无边际,毫无重点,最后老子实在听不下去了,打断了他的发言,让他用一句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犯孔子所犯的错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却无关痛痒,完全说不到点儿上,最后让聆听者产生反感、厌恶的心理。英国剧作家本·琼森说:“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只要你说话,我就能了解你。”(《木材,或关于人与物的发现》) 因此,对于说出口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慎之又慎,尽量不说和主题无关的话题,能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就好,不要长篇大论地扯闲篇儿,这样既节省自己的时间,也节省对方的时间。 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说话方面也是简单明了,单刀直入。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派遣使节、商队携带大量金银珠宝与商品,前往中亚的花剌子模王国缔结通商协定。至讹答剌时,花剌子模总督亦难出见财起意,污蔑商队中有间谍,于是上报国王屠杀了这些人,并侵吞了商品与财宝。 成吉思汗那会儿正全力攻打金朝,没工夫管花剌子模,只希望他们自己把此事和平解决。于是,他致书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只要他交出凶手,此事便可作罢。但摩诃末不仅拒绝了这个要求,还杀死了使臣。这个做法使得成吉思汗勃然大怒,决定攻打花剌子模。他给对方发出的战书,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尔要战,便战!” 这封战书既没有长篇大论的叙述,也没有引经据典的谴责,而是一句话直达中心思想,简单直接地概括了成吉思汗的意图,让人不寒而栗。最终花剌子模被成吉思汗攻占,而这封战书也因为简单明了,霸气外露而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战书之一。英国思想家培根,有一句名言——“说话周到比雄辩好,措词适当比恭维好。”与大家共勉! 士成绮见老子:下者劳力,中者劳智,上者劳人 《庄子·天道》中“士成绮见老子”的故事原文: 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吾闻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观子,非圣人也。鼠壤而余蔬,而弃妹之者,不仁也,生熟不尽于前,而积敛无崖。”老子漠然不应。 士成绮明日复见,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却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圣之人,吾自以为脱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苟有其实,人与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天,士成绮见到老子,开口就说:“听说先生是圣人,我便不顾路途遥远,一心赶来,希望能见到您一面。我走了上百天,脚掌上结了厚厚的老茧,也不敢停下来休息;可如今见到了您,看您也不太像是个圣人啊!您这里,到处都是剩饭剩菜,老鼠满地跑,这足以说明,您生活还算不错;就算如此,你却不愿意收养自己的亲生妹妹,这种行为能算是合乎仁的要求吗?”士成绮的话说完了,可老子就跟没有听见似的,连头都没抬一下。 第二天,士成绮再次见到老子,对他说:“昨日我用言语刺伤了您,今天我已有所省悟,并且改变了先前嫌弃的心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老子这次没有无视他,开口说到:“如果你说的圣人是聪明智巧的人,那么我觉得我并不是圣人。你想把我叫作牛,那么我就可以是牛;你想把我叫作马,那么我就可以是马。如果我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又拒不接受你对我的称呼,这不是犯了两重罪过吗?我总是欣然接受别人给予我的称呼,这种接受是顺其自然的接受,而不是强行的、有目的的接受。” 老子的这一番解释,听上去有点拗口,其实很有智慧。原句“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延伸出一个成语,叫做“呼牛呼马”,比喻被别人骂也好、称赞也好,决不计较。这里的“牛马”没有贬低的含义,就是两个称呼、两个“名”。 庄子在内篇《逍遥游》说过“名者实之宾也”,称呼名号并不总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在二者不相符的时候,实比较重要,而名只是实的衍生品。所以,故事中的老子才说,你愿意叫我什么都行,我都接受;如果我真的如此,那么你这么称呼我,完全没问题;如果我并非如此,那么你只是给我安了一个不重要的“名”,既然动摇不了真正重要的实际情况,所以你这么叫也无所谓。 原文: 士成绮雁行避影,履行遂进而问,“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冲然,而颡頯然,而口阚然,而状义然,似系马而止也。动而持,发也机,察而审,知巧而?于泰,凡以为不信。边竟有人焉,其名为窃。” 士成绮听了这一番解释后,非常羞愧,蹑手蹑脚地走上前来,问到:“我还想再跟您请教一下,修身之道是怎样的呢?” 老子说:“你伟岸挺拔,目光突视,前额高耸,口张舌利,在行动之前故意装作很矜持,一旦行动起来就像箭一样飞出去;你精明又持重,凭借自己的智慧,表现出骄泰自若的神色——别以为我是在夸你,你外在的这些表现,都不是人的真实本性。边境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他们的名字就叫做盗贼。”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士成绮器宇轩昂、仪表堂堂,话里话外全都是仁义道德,好像是正人君子一般,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已经被智巧所奴役,心态也总是随着外物的变化而起伏不定;相比于老子,表面邋遢随意、内心豁达从容的无为君道,士成绮充其量只能算作有为而卑的臣道罢了,所以他才显得格外的渺小与自卑。 这两个角色的对比,其实也反映了儒家与道家对“天人关系”这个哲学命题的不同观点。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有为、臣亦有为,此乃经世致用之道,也就是所谓的人道;而道家却认为,天道尊、人道卑,因此君道与臣道也有尊卑之别,君无为是天道,臣有为是人道。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天道》),因此刑名赏罚只能被天下人所用,而不能被君主拿来统治天下。为臣者,拘于一孔之见,只能是一曲之士,他们的有为也只是负责国家大政的某一个方面,搞经济的就管钱去,学土木的就搞基建,总之,各管一摊儿、互不干扰。而为君者,绝不能像为臣者那样实行有为政治,因为他要统御全局、掌握方向,只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一个在高位俯瞰人间的清虚帝王,才能面面俱到、没有疏漏;如果为君者今天又搞搞经济,明天又管管水利,把臣子该干的活儿都干了,那么,国家也就面临要垮掉的危险了。 孟子有一句名言,叫:“下者劳力,中者劳智,上者劳人”。(《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下层人做体力劳动,中层人做脑力劳动,上层人管理别人。作为中高层管理者,把脑力劳动干成体力劳动,不仅会伤害自己的性命,还会让自己管理的组织处于紧绷状态,累死的诸葛亮就是最好的注脚。按照《三国志》和《晋书》的记载,诸葛亮晚年和司马懿交战时,见司马懿龟缩不出,便遣使求战。结果司马懿不谈军事,而是直接问使者:“诸葛亮每天吃多少饭啊”使者说:“三四升。”司马懿又问:“那丞相管理政务又是怎么样的呢?”使者说:“打二十军棍以上的事情,都要亲自处理”。司马懿听了之后大喜,对身边人说:“诸葛孔明活不了多久了!”(《晋书·宣帝纪》)果然,诸葛亮当月就病故。作为丞相,诸葛亮原本应该高瞻远瞩、掌控全局,而不是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这样做的结局,只有把自己累死。 有句话叫:“君闲臣忙国必兴,君忙臣闲国必衰。”据《明史》记载,末代皇帝崇祯,做事亲力亲为,国家的大事小情全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对手下的臣子也是极其不信任,换了50个大学士、诛杀了7位总督、杀死了11位巡抚,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蓟辽总督袁崇焕——明朝本来就已经危机重重,有加上这么一位勤勉、爱折腾的君主,国家最后一丝气息也难以存续,最终以崇祯自缢而草草落幕。反观明朝嘉靖、万历两位皇帝,不上朝也不处理政务,而是把国事全部托付给戚继光、张居正、海瑞这样精明能干的官员,国家反倒太平无事。如果用儒家经世致用的道理来解释,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讽刺呀! 领导者管得过多,不仅容易对组织的平稳运行造成阻碍,也不利于接班人或者后备干部的培养。同样以诸葛亮为例,刘备死后,姜维北伐时,蜀国能征善战的大将都已亡故,无人可用,只能让原来在关公帐下做书记的廖化做先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诸葛亮没有去刻意培养年轻人。 诸葛亮和崇祯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做事太小心谨慎了,不敢放手让底下人去做事,唯恐别人做不好。这样一来,手下的人就得不到锻炼和施展,自然很难出人才;就算有可造之材,不给他机会,也会把他的才华埋没。 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公式,叫“高层需要胆略,底层需要业务,中层需要人际关系协调。”处在管理层,就要学会授权,管理一个企业,如同建设一栋大楼,如果管理者任何事都要亲力亲为,那么这个企业注定是要衰败的;如果管理者比较清闲,那么说明他善于用人,企业的未来才能光明可期。 庄子说:“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天道》)领导者,就该有领导者的样子,去做自己专属的事情。把控全局,统御战略,为组织的未来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庄子眼中的:“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天道》) 轮扁斲轮:要想技艺“得心”,就得天天“硬手” 《庄子·天道》中“轮扁斲(zhuó)轮”的故事原文: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通“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可,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故事讲的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当时著名的造车工匠轮扁,在堂下制作车轮。突然,轮扁放下锥凿走到堂上,向齐桓公问到:“请问您读的是什么书呀?”齐桓公说:“是记载圣人之言的书。” 轮扁又问:“那圣人还在吗?”齐桓公说:“已经去世了。”轮扁说:“如果是这样话,那您读的书岂不都是古人的糟粕吗?”齐桓公说:“呵,我读的书,你个做车轮的人,怎么随便议论呢?你要是能说出道理就算了,要是说不出道理,我非治你的罪不可!” 轮扁说:“那我就从我制作轮子的角度,来给您解释一下吧。我们做车轮,把榫眼凿得太宽,车轮就容易滑动而不牢固;榫眼凿得过紧,车轮就会干涩,零件难以进入。不松不紧、不大不小,才能在使用的时候得心应手、没有麻烦。这个分寸的把握,用嘴是说不明白的,全凭工匠心里有数。我想明明白白地把这个分寸传授给我儿子,但是他却从我的言语中领悟其中的奥秘。因此,我都快七十岁的人了,还要亲自上阵砍削车轮,实在是没有人能接班呀。同样的道理,古代那些不可言传的学问,也都随着创造者的去世而不复存在了;您现在所读到的书,不过是对一些只言片语的误解罢了!” 其实,这个故事中的轮扁,与之前讲过的解牛的庖丁、粘蝉的老人一样,都是在某一个领域中出类拔萃的匠人。他们因为对所在领域的极致钻研和反复练习,而使自身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触类旁通,领悟到了作用于自己这个领域的道,进而接近了作用于万事万物的自然大道。 庄子通过轮扁对齐桓公说的话,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大道至虚,其中的奥秘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只能自己去亲身感受;想要把握自然大道或者掌握一门知识,只啃书本、只停留在文字学习上是不行的,要在实践中训练技巧、感悟道理,做到“得意忘言”,追求知识本身的真谛,而破除语言文字带来的束缚。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老师傅手把手地指点徒弟玉石该怎么雕、书法大师手把手地教授学生笔划该怎么画,但是无论教得多么细致,学生都不可能马上达到老师的艺术成就,因为“经验”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玉石雕到什么地方该减小力度,笔划写到哪里该考虑收笔,都只能靠自己体会,老师即便说得清楚的,学生也不可能完全吸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其实不只是学习,我们中国人做饭也有“只可意会”的特点。看过中国菜谱的人都知道,在放调味料的时候,出现最多的词就是“若干”“少许”“适量”,这种量词真的可以逼疯外国人,在他们眼中,必须要说清楚盐放多少克、油放多少毫升,否则就不可能做出正宗好吃的菜;而有经验的中国厨师,拿来炒勺就可以直接做饭,问他调味料究竟要放多少,他也只会说“我也说不好,反正就是根据经验放”。正如《庄子·秋水》篇中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一定不是好的东西;真正好的东西,只能靠心灵去感悟。 庄子强调,事物真正的“妙理”是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只有“求之言意之表”“入乎无言无意之域”才能掌握其中的玄妙。如果总考虑雕刻玉石会不会雕坏,那么一定会雕坏;如果总琢磨着字写完之后好不好看,那一定写得很不好看。意兴所至、随意生发才是最好的创作状态,不考虑雕刻的力度,也不在意写字的笔法,完全靠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去创作,往往能诞育出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 书法家王羲之的传世名作《兰亭序》,就是在醉酒的情况下完成的。 那时候的他,写字完全没有章法,笔势完全没有控制,包括字体大小、纸张留白也完全没有构思,只是一股脑地倾泻自己的创作欲,却无意间创造了天下第一行书精品;等到王羲之第二天酒醒后,想要再重新临摹自己这幅作品时,却发现怎么写都没有当初的神韵了,因为此时,他加入了主观意念,刻意还原当时的状态,反而被私心杂念所困扰。 再回到本节讲的“轮扁斲轮”的寓言故事,它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是,无论什么样的技艺,想要炉火纯青,就要坚持训练、孰能生巧。轮扁七十岁了,还亲自制作车轮,除了因为制作轮子的真谛无法用语言传递给儿子,还因为轮扁的儿子自身经验不足、没有达到走进大道的水准。 在《养生主》中,我们讲过“庖丁解牛”的故事,为什么庖丁肢解那么多牛,都没有让手里的刀变钝呢?就是因为他已经熟练到根据牛经络的空隙来下刀,刀刃游走于最柔软的地方当然不会有大的磨损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庖丁进行了刻苦的训练,从最初的“所见无非全牛”,到“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到最后达到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至高境界。因为长久的训练,他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即使不用五官,也可以让双手自动完成宰牛工作,节奏甚至可以和音乐相贴合,显得十分地自然。 在《达生》中,我们也讲过“佝偻承蜩”的故事。驼背的老人拿着涂满胶水的竹竿去粘蝉,最开始在竿子上放两个圆球,不断练习,保证圆球不掉下来,那粘蝉的失误就很少了;后来在竹竿上放三个圆球,再勤加练习,如果还能做到不掉下来,那捉蝉的失误率就只有十分之一了;如果放五个圆球还能保证它们都不掉下来,那粘蝉就一粘一个准儿。这一切也都需要千辛万苦的训练。 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篆刻。有一天,他去拜访一位老篆刻家,老人说:“你去挑一担础石回家,等这一担石头都变成了泥浆,你的印就刻好了。”别人都以为老篆刻家在戏弄齐白石,劝他不要理那老家伙,但齐白石却真的挑了一担础石来,夜以继日地刻着,一边刻一边拿古代篆刻艺术品来对照琢磨。刻了磨平,磨平了又刻,手上起了血泡他也不在意,只顾着雕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础石越来越少,地上的淤泥却越来越厚。最后,一担础石统统都化为泥了,齐白石也练得了一手好篆刻艺术。他刻的印雄健洗炼,独树一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直到现在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的确是这样的,世上没有什么口诀可以让人在一夜之间获得登峰造极的成就,有的只有日复一日的练习和年复一年的实践。语言是无法告诉你成功真谛的,只有坚持和磨炼才是通往艺术圣地的唯一道路。 《天运》 太宰荡与庄子:人要学会变通,不能一味地恪守陈俗 《庄子·外篇·天运》中“太宰荡与庄子”的故事原文: 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 ”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 太宰曰:“荡闻之,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谓至 仁不孝,可乎?”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而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 话说,宋国的太宰荡,有一天去请教庄子对“仁”的看法。庄子说:“仁如果是一种品格,那么虎狼也有仁。”太宰荡问:“怎么讲?”庄子说:“它们父子之间相亲相爱,这不就是仁吗?”太宰荡一听,敢情庄子没明白自己的意思,便说:“我说的是最高境界的仁,请问您怎么看待最高境界的仁呢?”庄子说:“最高境界的仁,是不讲亲情、没有亲近关系的。” 太宰荡大为疑惑,问到:“我听说,没有亲缘关系就不会有爱,没有爱就不会有孝。按您所说,最高境界的仁不讲亲情,更谈不上孝道,那请问这还是仁吗?”庄子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最高境界的仁太崇高了,以至于孝道这种标准根本不以表达它的内涵。这并不是责备和否定孝道,而是说仁与孝根本就没有关系。这就好比,一个人向南行走,一路走到了楚国的都城郢,当他向北看的时候,一定没法看到北方的冥山。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两个地方相距太远了。同样的道理,仁与孝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当一个人已经在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这时候又怎么能用孝与不孝评价他呢?”话说到这里,庄子的第一层意思表达完全了,但是他对仁的理解还不止于此。 庄子接着说:“所以说,用尊重的态度来尽孝,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用爱的态度来尽孝,更难一些。用爱的态度来尽孝,也还算容易;忘记亲疏远近、一律仁爱待人,更难一些。忘记亲疏远近、一律仁爱待人,也没有那么难;使双亲忘记我如何仁、如何孝,更难一些。使双亲忘记我如何仁、如何孝,也还算简单,把天下所有的名利、权势、一切的一切统统忘记,更难一些。忘记天下还不是最难的;让天下人忘记自己的美德与功绩,那才真的叫难呀!” ★从中华传统文化源头性经典中找寻新的视角看世界 ★有书APP创800万次学习 ★逐字逐句精读原典,让《庄子》易读、易懂 ★撷取100+意蕴深刻的寓言故事 ★囊括100+鲜活动人的主角配角 ★析出100+别有洞天的成语金句 ★1套超越世俗境界的方法论 ★1卷让人舒心、安心、静心的通透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