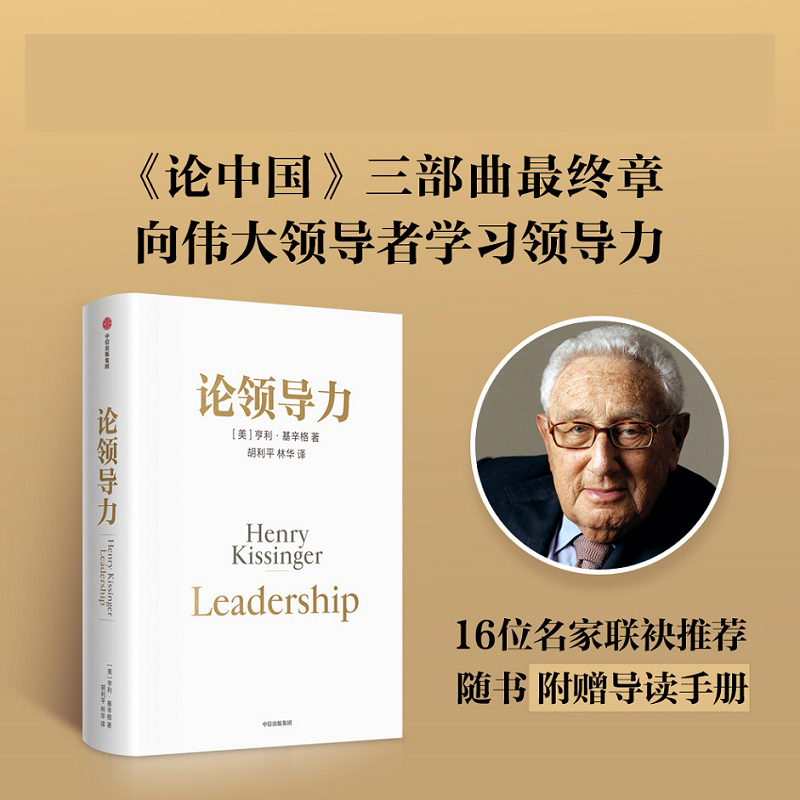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3.70
折扣购买: 论领导力
ISBN: 9787521762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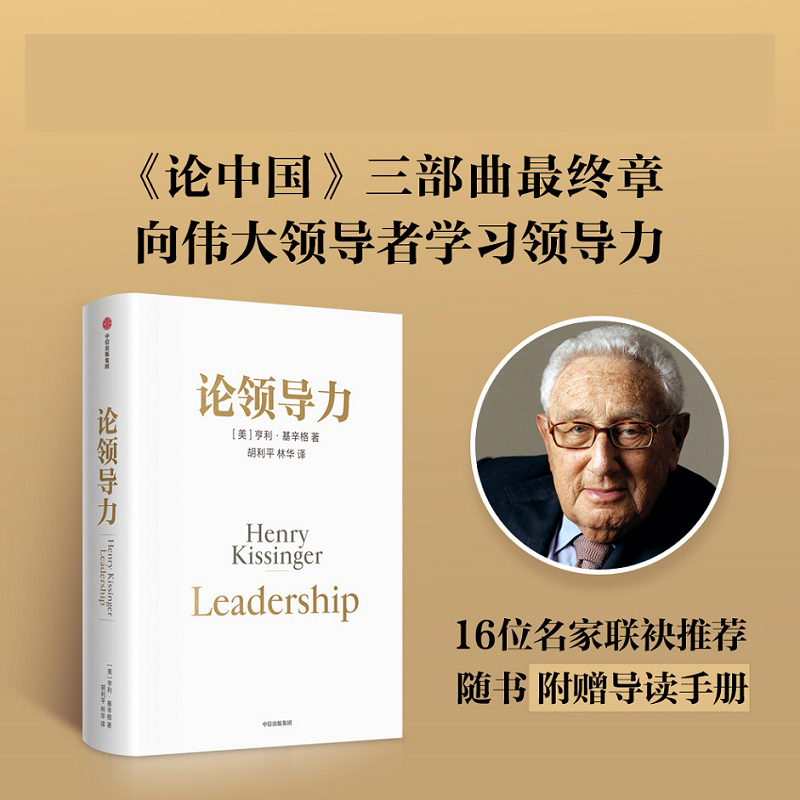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2023) 哈佛大学博士、教授,美国前国务卿 美国知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 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建交开启了大门,为中美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深入的交往。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其主要著作有《论中国》《世界秩序》《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等。
领导力轴线 任何社会,无论是何种政治制度,都处于一种永远的过渡,那是从构成它记忆的往昔向激励它发展的未来愿景的过渡。在此过程中,领导力不可或缺,因为必须做出决策,赢得信任、履行承诺,指出前行之路。人类各种机构,如国家、宗教、军队、公司、学校等,都需要,导力来帮助人们从现有位置努力达到过去从未到过,有时连想都没想过的高度。若是没有领导力,机构会失去方向,国家可能变得日益无足轻重,最终导致灾难。 领导人在两条轴线的交叉处思考问题,采取行动:第一条轴线连接过去与未来;第二条轴线连接长期价值观与他们领导的人民的渴望。领导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分析形势。这要求首先根据本国社会的历史、风俗和能力对社会做出现实的评判。然后,领导人必须在自己的所知与自己对未来的直觉之间达成平衡。前者当然是来自过去的经验,后者则必然无法确定,只能靠想象。领导人就是靠着这种对未来方向直觉的把握来确立目标,制定战略。 领导人若想让自己的战略起到激励全社会的作用,就必须担起教育者的任务,需要宣讲目标,平复疑虑,动员支持。固然,国家按照定义拥有对武力的垄断,但依靠胁迫是领导力不足的表现。杰出的领导人能在人民心中激起追随其脚步的愿望。领导人还必须启发自己的班子理解吃透自己的思想,将其应用于眼前的实际问题。这样一个活力充沛的班子是领导人内心活力的外在表现,与之相得益彰。它能为领导人在前进的征途中提供支持,减轻决策的困难。班子的质量能使领导人如虎添翼,也能令其难成大器。 领导人在履行这些任务中,需要具备勇气和性格这两个重要品质。勇气和性格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需要勇气在复杂困难的各种选项中决定前进的方向,而这要求敢于超越常规;需要强韧的性格坚持沿着选定的道路走下去,虽然在选择之时无法完全看清相关的裨益和危险。勇气在决断时刻能唤起美德;性格能加强对价值观的长期坚守。 过渡时期最需要领导力,因为过去的价值观与机构制度正变得日益无关紧要,值得向往的未来轮廓尚不确定。这种时候需要领导人放飞思想,仔细分析:社会福祉的来源是什么?什么是造成社会衰败的原因?过去的哪些遗产应该保留,哪些需要调整或予以抛弃?哪些目标值得坚持?什么前景无论多么诱人都必须拒绝?还有,社会在危急关头是否具有足够的活力和信心,愿意为了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做出牺牲? 领导力决定的性质 领导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制约。他们的行动受限于稀缺不足,因为每一个社会由于人口和经济原因,能力和影响力都有限度。领导人的行动也受限于所处时代,因为每一个时代和每一种文化都反映着当时普遍的价值观、习惯和态度。以上因素共同界定何为理想的结果。领导人在行动中还要面对竞争,必须与其他力量相争,无论是盟友、潜在的伙伴,还是敌手。这些力量并非静止不动,而是随势而变,各有不同的能力和愿望。此外,形势发展瞬息万变,无法做到算无遗策。领导人必须依靠直觉和当时无法证实的假设来做出判断。对领导人来说,风险管理与分析能力同样至关重要。 领导人在这种稀缺不足、囿于时代、竞争激烈和情势多变的条件下做出的决断是为 “战略”。战略领导力对前行之路的探寻可以比作走钢丝。杂技演员过于胆小或过于胆大都可能摔落。同样,领导人腾挪的空间也非常小,悬在过去的相对确定和未来的模糊不明之间。雄心过大——希腊人称之为狂妄——会落得精疲力尽,而沉迷往昔、不思进取则会逐渐丧失重要性,最终陷入衰落。领导人若想达到目的地,迈出的每一步都必须做到手段与目的相匹配,意图与环境相符合。 作为战略家的领导人面临一个固有的悖论:一旦情势需要采取行动,决策空间最大之际恰恰是相关信息最少之时。等到有了更多的数据,活动余地已经缩小。例如,在一个竞争大国开展战略军备扩充的早期,或一种新型呼吸道病毒突然出现之时,很容易认为这种新现象不会长久,或者按照现有标准可以控制。等威胁到了无可否认或无法消弭的时候,行动范围已经受限,或者是应对威胁的成本已经升至难以承受的高度。一旦贻误时机,便处处掣肘。余下的选择中,哪怕是最好的办法执行起来都很复杂,而且成功了好处不大,失败了却危险不小。 此时,领导人的直觉和判断就变得至为重要。温斯顿·丘吉尔对此非常清楚,他在《风云紧急》(The Gathering Storm,1948)中写道:“呼唤政治家不是为解决容易的问题。那样的问题经常可以自我解决。当力量平衡摇摇欲坠,轻重缓急迷雾重重之时,才是做出能拯救世界的决定的机会。” 1953年5月,一个美国交换学生问丘吉尔,如何做好准备迎接担任领导人后将遇到的挑战。“学习历史。学习历史,”丘吉尔在回答中强调。“历史中蕴藏着治国之道的所有秘密。”2丘吉尔自己对历史深有研究,也撰写过历史著作。他对自己所处的历史长河有着深刻的了解。 历史知识固然至关重要,却还不够。有些问题永远“迷雾重重”,就连博学多识、经验丰富之人也难以看透。历史通过类比给人以教诲,让人看到过去类似的情形。然而,历史的“教诲”本质上是近似性的。能否领悟历史的教诲是对领导人的考验,将其用于自己所处的环境是领导人的责任。20世纪早期的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说,“天生的”领导人“首先是个评估者——评估人、形势和事物……(有能力)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做正确的事”。3此言捕捉住了这项任务的本质。 身为战略家的领导人还要具备艺术家的素质,要能够感知如何利用现有的材料塑造未来。戴高乐在思索领导力的《剑刃》(The Edge of the Sword,1932)一书中指出,艺术家“并不放弃使用自己的智力”,毕竟,智力是“经验教训、方式方法和知识认知”的来源。艺术家在此之上又加了“我们称之为灵感的某种本能的能力”,而只有灵感才能“直接触及自然,才能擦出重要的火花”。 因为现实十分复杂,所以历史真理与科学真理有所不同。科学家寻求可核实的结果。熟读历史、身为战略家的领导人则努力从历史固有的模糊不明当中提炼出可供行动参考的见解。科学实验能证实或质疑以前的结论。科学家能够改动变量,再试一次。战略家却通常只有一次机会。他们做出的决定一般是不可逆的。所以,科学家靠实验或推算了解真理;战略家至少部分地靠过去类似的情形来推理首先需要确定哪些历史事件与目前情形可比,哪些过去的结论如今仍有意义。这样做的时候,战略家必须仔细选择可类比的事件,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经历过去。对过去的事只能如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说,好似“在记忆的月光下”想象。 有意义的政治选择很少只考虑一个变量。明智决策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地理、技术和心理各个方面。这一切还要辅以借鉴历史的本能。20世纪末,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著述中谈到,不可能将科学思维运用到科学范围之外。他也谈到了战略家因此面临的持久挑战。他认为,领导人就像小说家或风景画家,必须吸收生活中所有眩目的复杂内容: 在有别于知识渊博、学问有成、见多识广的层面上,一个人是愚蠢还是明智,是明白事理还是蒙昧无知,要看他是否辨得出每一个形势独有的特点——也就是该形势具有的不同于所有其他形势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得该形势无法用科学的办法来处理。6 六位领导人和他们的背景 性格与环境相结合创造了历史。本书介绍的6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李光耀(L Kuan Yew)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所塑造的。然后,他们又成为战后本国社会和国际秩序演变的建筑师。我有幸在他们6位处于影响力巅峰时期与他们相识,并有机会与理查德·尼克松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些领导人继承了一个因战争而失去了所有确定性的世界。他们为国家重新确定了目的,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为变化中的世界创造了新的结构。 6位领导人中每一位都经历了“第二个三十年战争”的洪炉,那是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毁灭性冲突。如同第一个“三十年战争”,“第二个三十年战争”同样从欧洲开始,但外溢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第一个“三十年战争”改变了欧洲,使其从一个合法性来自宗教信仰和王朝继承的地区转变为一个以世俗国家的主权平等为基础、决心将自己的理念传遍全球的秩序。3个世纪后,“第二个三十年战争”对整个国际体系提出挑战,要它采用新的秩序原则来克服欧洲的失望幻灭,消除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 进入20世纪时,欧洲正处于它全球影响力的巅峰,充满自信地认为它几个世纪以来的进步会永远持续下去,甚至认为此乃天命注定。欧洲大陆的人口和经济都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工业化和日益放开的自由贸易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民主机制几乎存在于每个欧洲国家:在英国和法国处于主导地位;在仍是帝国的德国和奥地利尚不成气候,但重要性在增加;在革命前的俄国则是刚刚起步。20世纪早期的欧洲知识阶层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魔山》(The Magic Mountain)里的自由人文主义者洛多维科·塞滕布里尼(Lodovico Settembrini)一样,坚信“事态在向着对文明有利的方向发展”。7 这种乌托邦式的思想在英国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1910年写的畅销书《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达到顶点。该书认为,欧洲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增加使得战争的代价昂贵到无法承受。安吉尔宣称,“人类正不可抗拒地从冲突转向合作”。8此言和许多其他类似的预言很快就灰飞烟灭。破灭的预言中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安吉尔说的,“任何政府都不再可能采取圣经中的古老做法,下令消灭整个人口,连妇孺都不放过。”9 第一次世界大战掏空了国库,终结了王朝,毁掉了人们的生活。欧洲从未真正从那场大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到1918年11月11日签署停战协议时,已有近1,000万士兵和700万平民命丧黄泉。10应召参军的士兵中,7个人里就有一人再也没有回来。11欧洲两代青年被耗尽——年轻男子战死沙场,年轻女子成为寡妇或孤身独处,无数孩子成为孤儿。 法国和英国是战胜国,但两国都精疲力竭,政治脆弱。战败国德国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债台高筑,对战胜国心怀怨恨,国内各个政党还互斗不止。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俄国则在经历了史上最激进的一场革命后,处身于所有国际体系之外。 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民主政体步履维艰,极权主义阔步向前,欧洲大陆陷入贫穷匮乏。1914年的崇武热情早已退去。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态度是忧心忡忡夹杂着听天由命的无奈。这次整个世界和欧洲一样遭了难。住在纽约的英裔美国诗人W.H.奥登(W.H.Auden)写道: 愤怒与恐惧的电波 盘旋在光明 与昏暗的大地之上, 侵扰着我们的私人生活; 那难以启齿的死亡气息 侵犯着九月的夜晚。 奥登这几句诗堪称未卜先知。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少于6,000万,主要在苏联、中国、德国和波兰。13到1945年8月,从科隆和考文垂到南京和长崎,多少城市因炮轰、空袭、大火和内战被夷为废墟。大战过后,处处是破碎的经济、普遍的饥馑和疲惫的人民。此刻国家重建的昂贵任务令人望而生畏。德国的国家地位,几乎可以说它的合法性,都被阿道夫·希特勒毁坏殆尽。在法国,1940年第三共和国在纳粹进攻下土崩瓦解,到1944年才刚刚开始从道德虚空中恢复过来。欧洲大国中,只有英国保持了战前的政治制度,但它实际上处于破产境地,很快又要面对帝国的逐渐解体和持久的经济困难。 以上动乱给本书介绍的6位领导人中的每一个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康拉德·阿登纳(生于1876年)从1917年到1933年任科隆市长,政治生涯涵盖两次大战之间因莱茵兰问题与法国发生的冲突和希特勒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两次遭纳粹监禁。从1949年起,阿登纳放弃了德国数十年来对统治欧洲的追求,使德国牢固地扎根在大西洋联盟之中,并在反映他自己信奉的基督教价值观和民主信念的道德基础上重建了国家,带领德国度过了它历史上的最低潮。 夏尔·戴高乐(生于189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威廉二世的德国当了两年半的战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起初担任一个坦克团的指挥官。法国沦陷后,他两次重建了法国的政治结构——第一次在1944年,为的是恢复法国的本质。第二次在1958年,为的是重振法国的国魂,防止内战。戴高乐引领了法国的历史过渡,从一个输掉战争、四分五裂、不堪重负的帝国转变为一个有合理的宪法作依靠的稳定、繁荣的民族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戴高乐使法国在国际关系中重新发挥了重要的、可持续的作用。 理查德·尼克松(生于1913年)从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中学到,他的国家必须在新生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尼克松是唯一被迫辞职的美国总统,但他在1969年到1974年间缓和了超级大国之间在冷战高峰期的紧张关系,并带领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出来。其间他与中国建立了关系,开启了给中东带来巨变的和平进程,并强调基于平衡之上的世界秩序观,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在全球各地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本书讨论的领导人中有两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殖民地臣民。安瓦尔·萨达特(生于1918年)作为一名埃及军官,在1942年因企图与德国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合作将英国人赶出埃及而被捕入狱两年,然后在亲英的前财政大臣阿明·奥斯曼(Amin Osman)遇刺后又被判刑3年,其间多数时间是单独监禁。萨达特长期受革命思想和泛阿拉伯理念的激励。1970年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突然离世后,他被推上埃及总统大位。此时的埃及正沉浸在1967年战争中败于以色列的震惊沮丧之中。萨达特精明地将军事战略与外交相结合,努力收复失地,重建埃及的自信,同时本着超越当下的理念实现了与以色列长期以来渺不可及的和平。 李光耀(生于1923年)在1942年差一点被日本占领者处决。他主导了太平洋岸边强邻环伺的一个贫穷的多族裔港口城市的演变。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安全、良治、繁荣的城市国家。它的文化多种多样,但它有共同的国家身份来确保国民的团结。 你绝对想不到的趣味历史!一年365天串起来的历史,365个跟孩子亲子沟通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