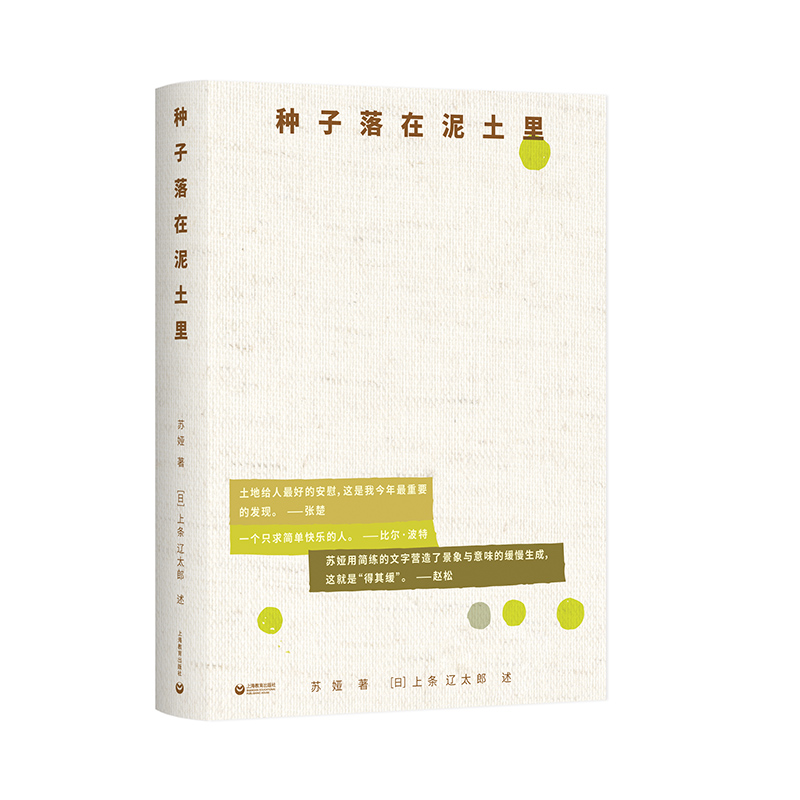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教育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33.80
折扣购买: 种子落在泥土里
ISBN: 9787572020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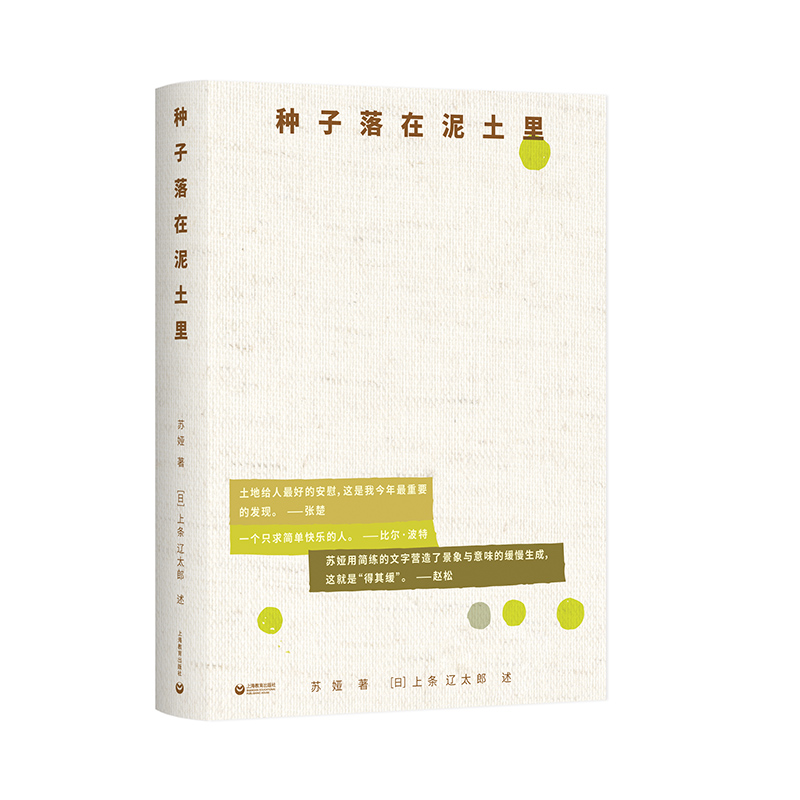
苏娅 生于云南,钟爱阳光和风土的写作者,关注自然和文学。 [日]上条辽太郎 日本千叶人。旅居大理七年,现居浙江,昵称“六”。
彩虹 七月,一个暴雨初歇的日子,我开车去银桥镇上银村,六一家就住在那里。也是从这里,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对话。 这里夏季多雨又干燥,风和太阳都大,路边干活的人唱歌的声音让太阳显得更大。老天爷会毫无征兆地下一场豪雨,你只能加快步子,待走进家门时,雨又停了,这时候,更厚的积雨云又悄悄堆积在天边,蓄谋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一天之中,暴雨和烈日轮番催化着这里的山川田野,雨带走一些什么,太阳又让它长出来。 我在这里见过最多形状的彩虹。双彩虹、拱形的完整彩虹、彩虹尾巴。从一个村庄伸向另一个村庄,甚至能看清彩虹一截截显现的过程,上升或坠落的头绪。彩虹的尾巴最漂亮,有时是一小段,有时被裁成几段,孤立的。往往这时候,天空已经黯淡了,暮色四合而来,只剩这一点凝固的颜色悬在天幕上,发出液态金属般的暖光,有留恋的意味。 我非常喜欢多雨又干燥的地方。我们的谈话,从夏天持续到冬天。 夏天,在六家的正屋或偏房的工作间里聊天,午后,六和阿雅的孩子和空、结麻在院子里玩耍,隐约传来孩子们嫩声嫩气、自带音效的日本语——咦、呢 …… 各式各样的语气词浮动游移。雨后的天空蓬松、水灵。 我们用中文、手写的汉语和日语词汇交谈。六熟练地在日 、英、中三种语言之间自由切换,偶尔接个电话,说的话也是同时切换着这三种语言,听得人暗暗称奇,忍不住对电话那头的人也好奇起来。 六说起做发酵的食物,酿酒、做味噌和豆腐乳 …… 看不见的微生物在一段时间里相互作用,形成发酵食物特有的风味,这有点儿像人和人在彼此的气息中交往,我们说了什么没说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做发酵的食物,也是和看不见的事打交道:制作时的温度和湿度 、制作者的感觉 、此时此刻的氛围 …… 如果你的工作对象是看不见 的东西,就要祈祷神灵的帮助。 六在说发酵食物时,把“发酵”带到了语言里。他的语言才能,能够把对话引向深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物,仿佛已经竭尽全力展示了所有,语言却能在最幽微的地方,又延伸进去,更深入一点。 冬天,我们在装了“火箭炉子”的阁楼上聊天。十一月中,苍山上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六说:下星期你来的时候,我们把楼上的炉子生上火,可以到楼上工作。“火箭炉子 ”是六亲手垒的,他收集了废汽油桶和珍珠岩,砂石、砖头和沙子——这些乡下容易找到的材料,运用炉体的空间比例和珍珠岩的散热性能,最大限度让柴火燃烧,再缓慢地释放热能,很节约柴禾。在日本和欧美的农村,“火箭炉子”仍被一些家庭采用。 很多个太阳偏西的午后,当我敲响六的家门时,院子里传来劈柴的声音。楼上的炉膛里,已经生起了火,隐约的柴火香笼罩着这所用石头 、泥和木头建造的房子。和空和结麻从镇上的幼儿园放学了,趴在正屋小桌上的一团橘色的光里,吃着阿雅备好的晌饭看动画片。阿雅刚给第三个孩子天梦喂完奶,她单手举起襁褓里的婴儿,站在门口,露出笑容:看——,我的猫。 结束谈话已是入夜时分。开车返回的路上,在细长的乡道上与人错车通过,互道感谢。很温暖的冬夜印象。 冬天的晚上,冷是世间唯一发出声音的事物。远远近近的犬吠、逡巡的风声、飞鸟的振翅,霜在草尖凝聚也带着很轻的音调。而此时,温暖的事物都是静默的。黑黢黢的田野里冒着灰白色热气的堆肥,村舍窗棂上的灯光、秃树梢上的鸟窝 …… 温暖的一切,停留在没有意味的寂静里。 整个冬天,苍山上的山林和雪地持续地争夺着领地。每当山下的气温升高几度,夜晚就会刮 起大风。风,轰鸣一整夜,从山顶直接地滚落下来,劈岩穿石,又在不远处的空地上盘旋一阵,向着东方的村落呼啸而去。第二天早上,湛蓝天空下树林的顶端,便薄薄地覆盖了一层雪。 月色不歇地雕刻着夜晚乡村的轮廓,瓦蓝色的山脊线在天际尽头延伸,田野反射着银亮的月色,世界映照在一层比白日更鲜明柔和的光亮中,枯草摇晃着一条灰白色小路。从海拔突降的村路上看山下的平地,树木杀气腾腾的,小巷转角昏黄的路灯下,几个晚归的老人默不作声地坐着,浮木一般松散。 我们的对话,大部分时候是顺畅的,有很多信息,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皱褶里:一阵无人描述的风,一道皱纹,一句笑话 …… 带来无尽的谈话乐趣。 但有时,又像有什么阻力存在,有可能是累了,有可能是那一天心情低落,话题和谈兴都显得艰涩无力。我意识到这一天将付诸东流,但回来听录音,在一段很长的沉默里,是雨季淅淅沥沥雨幕的背景音,沙沙沙的无垠与人声消隐的录音中,偶尔听见一个浑圆的水滴落下,如坠落深潭般明净无惑。 这本书像一串喻示了古怪讯息的鸟叫声,一度让我不安。简单说,初版(《六》)出版之后,六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二○一九年的春天,他们一家就离开了大理,开启新的生活。想到那段告别在即的日子,最让人尴尬的事情莫过于,一些平时根本不联系的人会忽然跑来问一句:你知道吗,六要离开大理了。我心想:这不是在这本书写之前就已经注定了的吗?更何况,作者最终都会是自己作品的局外人,这也是早就注定的。 六曾有个愿望,在地球不同的地方实践农业,他最想种的当然是水稻。水稻和杂草的习性很像,只能生长在潮热的季风带。很有可能,六的这个愿望是徒劳的,所以他自己也说“只是一个轻轻的愿望”。但徒劳的事情,是一个神秘世界的锁孔,常常赠予人一份纯粹的快乐,超脱的快乐。所以我更在意的是,六又去了哪里?水稻种得好不好?更关心这条线索中人和事的变化,时间兀自溜走时留下的痕迹。 二○一二年,六刚到大理时,一个人骑着单车背了个背包就来了,晚上就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等二○一九年离开时,他和阿雅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家当塞了满满一卡车。他们离开之后,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有和无是对等的。有些终将告别,有些还在继续。 二○二○年的四月底,我从大理去浙江六和阿雅的新家玩,正赶上六准备撒稻种、育秧。播种那天,天光刚刚泛白六就动身去田里平整田地。春天温暖的阳光缓缓爬过山上的林木,降临山谷,自然的声息渐渐洪大起来,鸟的叫声、土地和植物发散着温热的香气,还有更远处未知空间中传来的嗡嗡声,每一次田间的劳动,都在放大人的感觉,一种身心直接地与自然、宇宙接触的获得感、满足感。如果从最多的合于目的性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农业是最好的劳动。 我想起,在六一家离开大理后的第三年,陪朋友去过一次上银村。当时,朋友想在那里找一个可以租住的房子。我们后来顺道去看了看六一家曾经住过的小院。以前通向正门的石径,已被半人高的茂密的杂草湮灭了,我们又绕到后院,一座敞亮的白族农舍取代了原本几近荒弃的石墙小院,后院土墙上的仙人掌长得更壮硕了,凝神奇幻地伸向天空,穿过它,更远的蓝奔流。 写下六的故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说话的方式吸引我。他说的事,让人很容易感觉到,那些与自然离得近的人、在自然中劳动的人,语言中峻洁天真的气息。苍山上的护林员张口就跟你说:这座山上有多少多少泉眼在深茂的草丛中流淌;村舍中做甲马的手艺人,顺手从胸口前的衣服口袋中摸出张小咒符,就直指垂悬高处的神明之力—他们的叙说方式与古老的神话叙事一脉相承,元气丰沛,只有直觉很少为经验与积习所束缚的人才能说出。他们在持久的孤默中生活,在发声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倾听,而倾听是人不能主动终止的事情。当他们发声,语言只是倾听之后,意义的最终出口。 1. 现代人的田园牧歌。苏娅用简练的文字营造了景象与意味的缓慢生成,读来令人身临其境。 2. 六的农耕实践有打动现代人的力量。六以种地为生活的立足点,以自然农法耕作、酿造,把自己的音乐梦想融入泥土,是生活在大理的“当代梭罗”。 “人和自己做的东西有对话”“现在很多人活得太干净,他们也许是逃跑的人”“吃自然里长出来的好东西,是给你机会去改变和解决心的问题”……六朴实的话语就像从地里生长出来一样,富有禅机。 3. 畅销书《空谷幽兰》作者、向世界介绍中国禅的比尔?波特,作家赵松,歌手张楚联袂倾力推荐! 4.32开文库本,平装锁线,封面采用高级麻布,给人一种亲近土地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