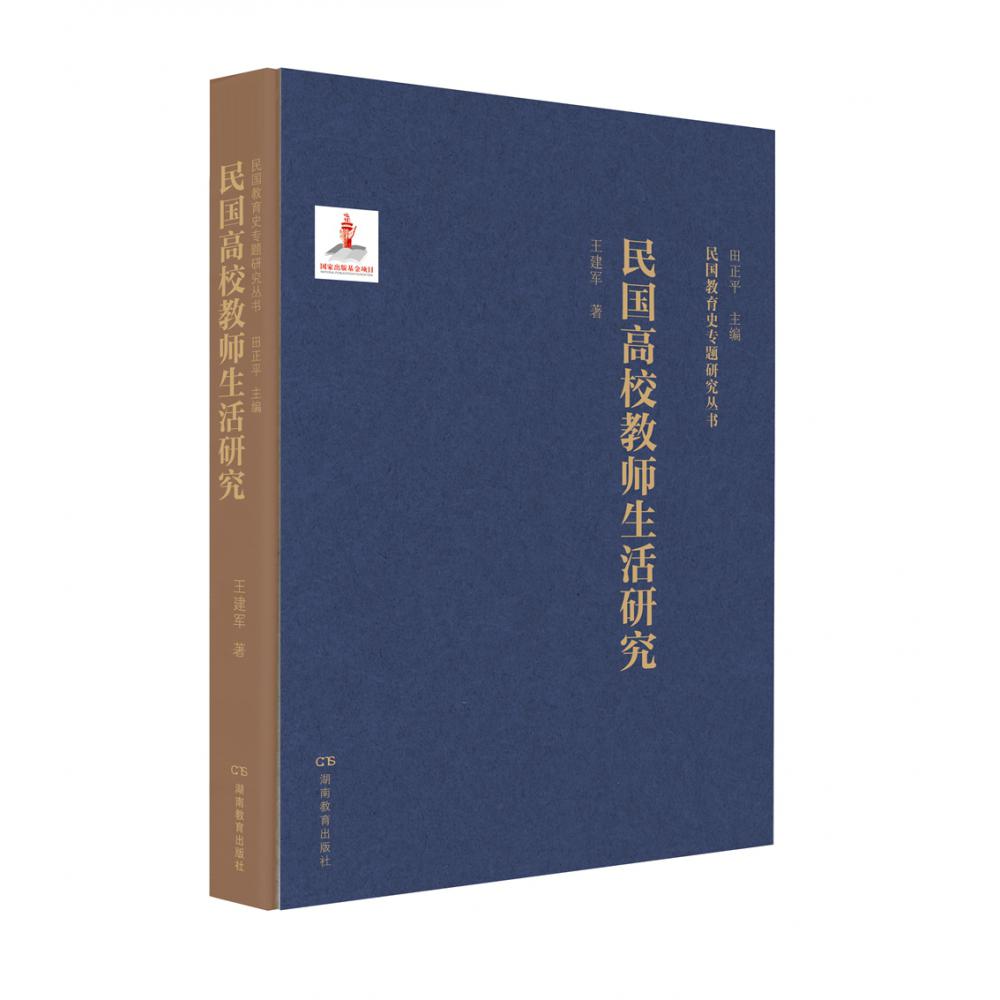
出版社: 湖南教育
原售价: 195.00
折扣价: 132.60
折扣购买: 民国高校教师生活研究/民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553965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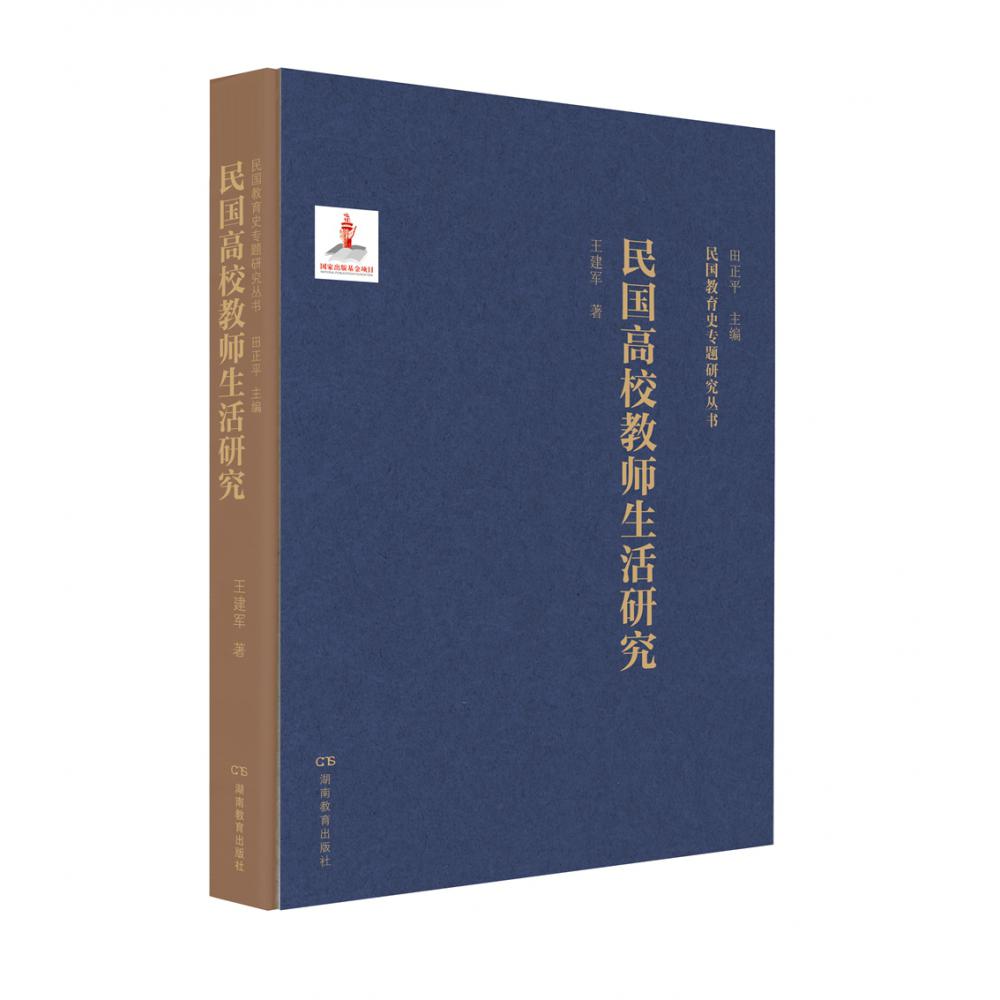
王建军,男,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常务理事、广东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管理史和成人教育。主持、参与国务院古籍整理项目“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丛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项目“中国教育史研究”等多项国家、地方课题。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中国教育管理史教程》(广东高教出版社1998年6月)、《中国教育史新编》(广东高教出版社2003年12月)等。发表论文有“盲目趋新与教学改革--舒新城对道尔顿制教学实验的忧虑”(课程-教材-教法2005年第5期)、“论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模式的演变”(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高等教育》转载)等。
第五章:民国高校教师的日常生活情趣 日常生活情趣,讲的是工作之余的生活享受。任何社会群体的生活享受都受制约于他们的经济条件,也都摆脱不开他们社会身份的特性。民国高校教师的生活享受当然也不例外。一般情况下,他们的经济条件能够使他们过上无忧且体面的生活,然而又不足以让他们享受奢华。当然,他们的专业身份也不允许他们沉溺于奢华。可以这么说,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情趣不主要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林语堂说过:“享受悠闲的生活当然比享受奢华生活便宜多了。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闲暇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 这种悠闲更在意的是生活的品味,是特立独行的个性,是艺术家的性情。 自古文人雅士在生活中都着力追求着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悠闲心境。孔门弟子曾点曾阐述他的生活之向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这一番话引来了孔子的喟然长叹:“吾与点也!”这一声长叹,触动了多少文人墨客的情思,引领了千百年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趣,铸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美感追求。进入民国,这一长叹的余韵依然绕梁不绝。加之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民国高校教师群体又为这一长叹增添了新的韵味。 一、衣食住行,自得其乐 讲到生活情趣,它当然是建筑在衣食住行的基础之上。连马克思都说过,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的活动。这对于民国高校教师来说又何尝不是真理。经历过清末民初动乱的吴虞曾说过一句话:“政界波澜起伏,余有田可耕,有屋可居,有书可读,虽非充裕然尚可以自给,有以自娱。若王茗聪之徒家无恒产,终岁遑遑于衣食住三要件,受此影响不知胸中如何冰碳。呜呼!人生可哀,不其然乎!” 吴虞在这里提出生活享受的基本条件,即有田可耕,有屋可居,有书可读。这三项条件“虽非充裕然尚可以自给”,方可“有以自娱”,方可谈生活情趣的问题。 但衣食住行并非就与生活情趣绝缘。生活以衣食住行为基础,生活也因衣食住行而展开。作为知识群体的民国高校教师,在具备了基本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即使是衣食住行也要活出个精彩。所谓精彩,并非奢华,而是格局,是品相。衣食住行讲究的是柴米油盐的事,但又绝对不止柴米油盐。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身份群体,因着柴米油盐水平的不同,也因着生活情趣的不同,由此活出了不同的格局和品相。民国高校教师在衣食住行中所倾注的热情和爱好,表现出一种对生命之乐的感知,一种审美感觉上的自足,一种与职业身份相表里的生活精神。 (一)衣着 衣着是最能体现人们生活态度的外在标志。当然,这个标志首先是烙上了时代色彩。进入民国,民众的服装渐趋多元,那种“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的传统观念也渐渐失去了市场。清末传入的西装逐渐普及于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当年满族的长袍马褂也逐渐为汉族所流行。一阵子的洋服热,又一阵子的长袍马褂流行,在民国社会此消彼长。但民国高校教师的衣着却不关风潮。他们我行我素,该穿西装便着西装,想穿长袍马褂便套长袍马褂,民国高校教师特立独行的品味在这方面可谓是极尽风采。 先看看辜鸿铭。辜鸿铭在民国是个很独特的人,在衣着上也极具个性。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了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 辜鸿铭在西方国家待的时间可不短。当时有种说法,说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据说他刚回国在清末政府当幕僚时,当初也是断发西装革履,一派新潮的打扮,进入民国后却截然更换了一副装束。何也? 有人依据其留辫子而认定其期望清朝复辟。辜鸿铭有次也自嘲地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但民国初期的两次复辟,跟辜鸿铭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说明他的留辫子跟政治不沾边。也有人从性格角度评介辜鸿铭:“引人注目地炫耀他的辫子,是他整个为人的特征。他脾气倔强,他以对立为生。大众接受的,他拒绝。大众喜欢的,他厌恶。大众崇拜的,他鄙视。与众不同是他的乐趣和骄傲。因为剪掉辫子成了时尚,所以他偏要保留。” 这个判断也不够准确,因为支配辜鸿铭这么做的后面是他的文化信仰,正如他所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服,就对我们稍加尊重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欧式假洋人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正是凭着这样的文化精神,于是在西风东渐、社会转型之时,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颇为奇特的景观:“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无独有偶,当时具有这一景观的不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有一景。据当年学生回忆说:“一个不很高大的身材,面孔也瘦小,牙齿有点獠在外面。常穿着当时通行的及法布袍子,罗缎短袖马褂。后面拖了一条短辫子。冬天他戴上一个瓜皮帽子,或者穿上羊皮袍子。但他没有比羊皮更高贵的皮衣。他的衣式不很时式,也不很古板,但很整洁。他的近视眼镜是新式的。他也会抽香烟。总之他的物质生活,很随随便便,决没有一点遗老或者名流的气味。看去有点像旧式商店里的伙计。” 这人就是王国维。在衣着上,王国维也是长袍马褂,也是瓜皮帽子,也是拖着一条辫子。 对王国维的这身装束,人们似乎没有提出更多的非议。王国维是从溥仪身边进入高校的,其衣着的传统应是当然的。据其女儿回忆说:“父亲对仪表向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杉。平时只穿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父亲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 虽然王国维这时戴上了新式的眼镜,还抽着香烟,但其衣着的主体还是长袍马褂式的传统样式。 陈寅恪是留学归国者,但西式服饰在他身上没有体现。清华的学生回忆说:“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他的侄子则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寅恪叔到清华时,我已10岁。我没见他穿过西装,简直看不出他是留过洋的。他总是一身长衫布履。冬天是棉袍加马褂,三九天就在脖间缠上一条五尺多长的毛围巾,头戴厚绒帽,棉裤还扎着布带子,一副土老儿模样,陌生人绝对猜不透他是个精通古今中外的学者。” 胡适的着装至少在学生眼里是好奇的。这位留学美国的博士,且学术思想上追求新潮的老师,其衣着却是传统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入读北京大学的张中行说:胡适“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 当然,毕业于本国高校的教师也有不少以长袍马褂为时尚。著名词曲学家顾随,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成为词曲大家吴梅的入室弟子,在词曲研究方面很有造诣。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都担任过教授,讲授诗、词、曲,前后达二十多年。顾随的穿着纯粹是东方式的风格,不要说不穿西装,就连西式大衣也不穿。冬天内穿春绸衬绒袍子,外面套丝棉或灰鼠袍子,灰鼠袍子外面再套大毛的狐肷袍子,狐肷袍子外面围五六尺长,可以在脖子上围两圈的黑绒线围巾。单只这套着穿三件袍子的穿法,在其他老先生当中,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妙的是他还要穿到教室中去,先除围巾,上台讲一会之后脱皮袍子,再过一会儿,教室越来越热,先生讲的也越来越高兴,微微出汗,再脱一件,快要下课时,停止讲授,再一件件穿上出去。 只有中学学历的钱穆后在北京大任教,因汤用彤而认识了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对陈寅恪的学问十分佩服,并爱屋及乌,在衣着上也仿效陈寅恪。“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 当然,民国高校教师着西装者也是这样的特立独行。例如清华大学的赵元任夫妇的衣着便倾向于西式。赵元任妻子杨步伟爽朗,大方,豪放不羁。她常穿洋装,由于身体略胖,所穿丝袜必须要外国买来才穿得下。赵元任对衣着也很讲究,他常穿西装,或在长袍下穿西装裤。一副金丝眼镜,更显得温文儒雅。 一个社会群体的形成须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民国才短短38年时间,高校教师共同体的营建当然是显得仓促了。但就是这仓促的历程,也充满着新与旧、中与西、前进与倒退的交叠与碰撞。这些交叠与碰撞,却促成了民国高校教师共同体中一种精神的成长,那是一种历史担当的精神,一种本真的生活情怀。 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看,对民国高校教师生活状况的展示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对民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研究中。如马嘶的《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许纪霖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罗志田的《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倾向》,杨小辉的《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转型》,蔡登山的《民国的身影》,刘克敌的《困窘的潇洒: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等。也有从经济角度揭示民国文人的生活,如陈明远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人与钱》,等等。 对民国高校教师的专门研究,主要有校史研究和校史资料整理,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南大百年实录》、《北京大学史料》等等。这些资料较系统地收集了当时高校教师的生活资料。还有对某校教师生活、工作的研究,如苏云峰所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11—1929》、黄延复所著《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谢泳所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等。对民国高校教师作较全面研究的则有汪修荣撰著的《民国教授往事》,内容涉及19位教授,材料丰富,剪裁得当,较形象地反映了当年高校教师的生活容貌。陈平原所著《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则是对特定时期高校教师的群体研究,个案研究则有民国高校教师的人物传记。另外,最近整理出版了许多民国高校教师的日记、回忆录,以及他人的追忆文集,这些资料较真实地回放了民国高校教师的生活图景。 近年对民国高校教师生活状况的研究论文开始增多,其内容比较多地集中在民国高校教师待遇问题上。比如高校教师的聘任问题、流动问题、薪酬及生活状况问题、教师结构问题等,以及与教师待遇相关的“教授治校”、教授权力制度、教师身份、教师的社会角色等问题。其研究视角或按民国历史阶段集中讨论某一问题的演变,或按区域探讨某一地区教师的薪酬状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浙江大学吴民祥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已出版),华东师范大学胡悦晗的博士论文《日常生活与阶层的形成——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为例(1927 — 1937)》,浙江大学葛福强的博士论文《民国高校教师薪酬研究》,以及数篇相关主题的硕士论文,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民国高校教师的生活状况。 这些研究成果注意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公共层面考察民国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从校史角度介绍了高校教师的工作状况,有的是从启蒙思想的内在复杂性考察近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自我冲突,有的是从地缘与学派的角度考察近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脉络和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有的则将晚清士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相比较,考察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剧变时代的思想与社会关怀,有的则从民国高校教师的聘任、待遇、流动等方面来考察民国的教师管理制度。这些成果包含有较丰富的民国高校教师的往事,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民国高校教师的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但将民国高校教师视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全方位探讨其生活的研究成果还是很少。特别是从民国高校教师共同体营建角度来探讨民国高校教师生活的成果则基本空缺。 既然民国高校教师共同体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那么,这个新兴的知识群体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个群体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从生活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就十分必要。如果我们能从民国高校教师共同体营建的角度,通过对这个群体成员的构成,他们的物质待遇,以及他们的教学生活、学术生活和日常生活作深入探讨,我们就有可能抓住民国高校教师生活的时代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