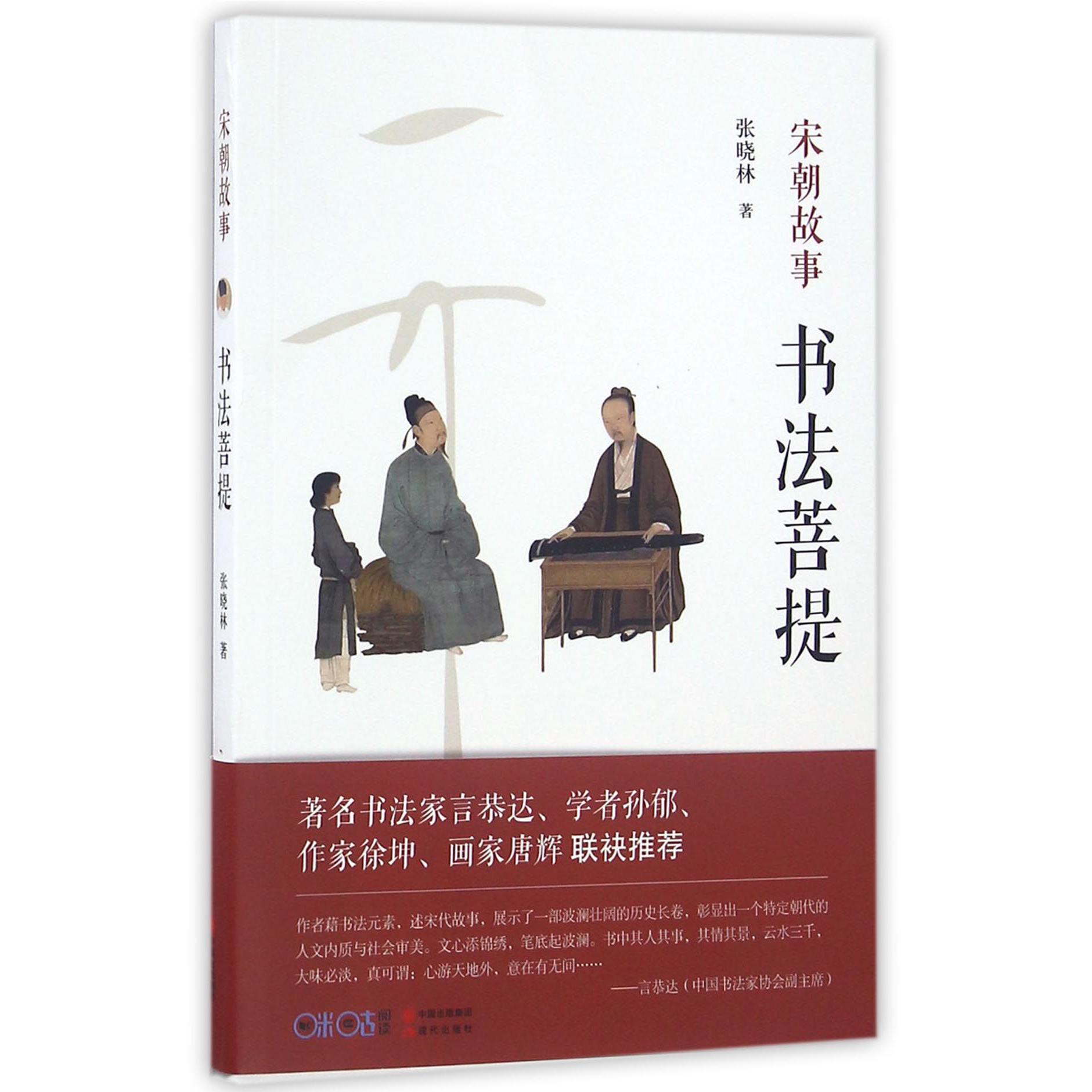
出版社: 现代
原售价: 29.8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书法菩提(宋朝故事)
ISBN: 9787514348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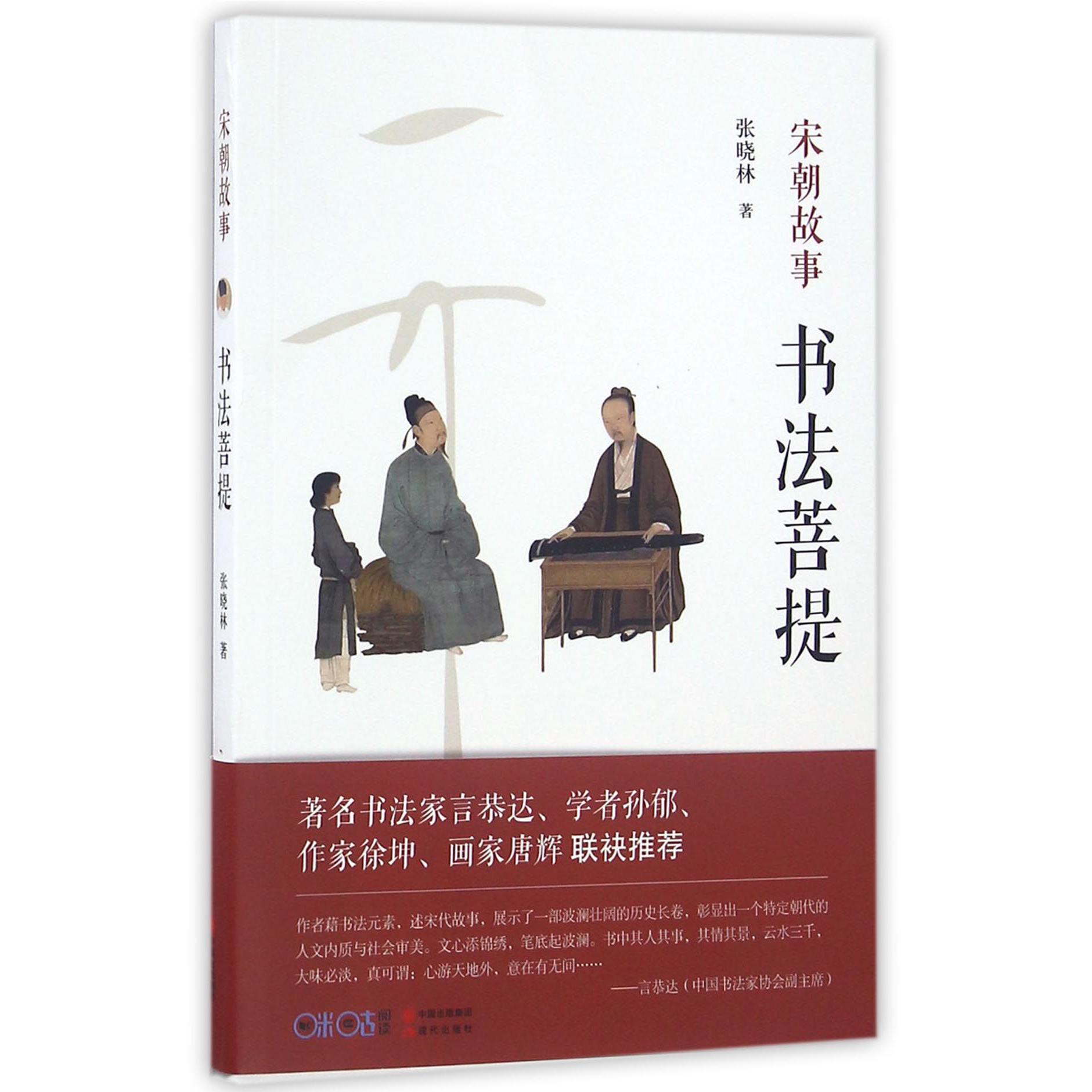
张晓林,河南杞县圉镇人。《大观》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青海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开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开封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先后获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优秀论文二等奖、河南省第二届“杜甫文学奖”、全国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榜首等。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选刊》《作家文摘》《读者》等名刊选载,入选《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等各种选本100余种。
苏轼的敌人 苏轼是个豪放的人。他的豪放,是从骨子里面透 出来的。是一种天生的豪放。作《赤壁赋》,作“大 江东去”,都是他内在豪放的外化。 豪放的人,大都豁达、大度、不计小节,体现在 苏轼身上,则是悯天忧人的仁厚。苏轼从来记不住别 人的过错,照豫东乡里人的说法,就是不记仇。即使 当时气得不行,甚至都怒发冲冠了,但过不了两天, 他准会把这些都忘到脑后边去。这样的人,一般都会 有很多的朋友。 苏轼就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中,有王公卿 相、文人雅士、世外高人,还有一些江湖中的奇人。 大臣欧阳修、张方平、范镇、司马光,书画家黄庭坚 、米芾、文与可,高僧佛印,隐士陈季常,剃头匠阿 杜等,都是苏轼的朋友。 苏轼也有敌人。谁又会没有敌人呢?有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的敌人就已经产生了,防 也防不住。不说李定、吕惠卿、王珪等人了,像朱光 庭、贾易这号人,与苏轼素无交往,甚至连认识都不 认识,心底就把苏轼当成了仇敌,百般辱骂,尽露小 人嘴脸。 抛却朝政上的原因,朱光庭之流怎么也会把苏轼 当作敌人呢?开始我咋着也弄不清其中的玄机,后来 读《全宋笔记》,才慢慢看出门道。苏轼的这类敌人 ,都是读苏轼的诗文读出来的。有的读苏轼的诗文, 读着读着,脸白了,黄了,黑了,这句话是在骂我呀 !还有的,读苏轼的诗文,读过,沉默了。写得太经 典了!我咋就写不出来呢?于是,苏轼就凭空多出了 这么些敌人。 还有一类敌人。起初是朋友,携手走天下,煮酒 论诗文,关系铁得很,后来却成了敌人。像章惇、沈 括辈。 朋友与敌人,这只是我们替苏轼划分的,苏轼并 不一定认可这种划分。认可与否,已无法亲向苏轼考 究,只能去与之有关的故事中寻找答案了。 寻找答案之前,有一个话题得向读者交代明白。 那就是苏轼是如何不肯记人过错的。且听分解。 嘉祐六年,一道圣旨,苏轼来到凤翔府,做了“ 签判”。刚上任的时候,凤翔府知府是宋选,宋知府 雅爱诗歌,而苏轼恰是个中高手,所以,刚步入政界 的苏轼小日子过得就顺溜一些,舒坦一些,有诗意一 些。一句话,活得有尊严。一年后,宋知府被朝廷罢 免了,又来了一个陈知府。 陈知府叫陈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与苏轼 同乡,不仅如此,两家还是世交,若论起辈分来,陈 知府比苏洵的辈分还高,也就是说,他是苏轼的长辈 。按说,有了这层关系,陈知府对苏轼应多一些关照 才对,但陈希亮这个人有些古怪,面很冷,做起事来 得他说了算,容不得商量。这样的一个人,行事往往 会超出常规。 上任后的第三天,苏轼去谒见他。名帖投进去, 仆人把苏轼领到偏房等候。等了许久,也不见陈希亮 出来招呼,苏轼几次想离去,又觉得不合礼仪,心里 很不是滋味。从此,在苏轼面前,陈知府摆出了两个 面孔。一个是长辈的面孔,一个是长官的面孔。 这一年的中元节到了,苏轼因为其他事,没有去 给陈希亮贺节。这本来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可陈 知府却记到心里去了。 到了黄昏,他问家仆:“苏轼来过吗?” 家仆说:“没见苏轼来。” 陈知府的脸很难看。“目无尊长!”他骂了一句 ,连夜写道折子,第二天就让人送到汴京去了。不久 ,苏轼就受到了处罚,罚铜八斤,几乎罚去了苏轼大 半年的俸禄。 有一段时间,陈知府似乎专意和苏轼过不去。苏 轼为府衙写了几篇斋醮、祈祷之类的小文章,文章的 草稿呈上去,陈希亮总要这儿涂涂,那儿改改,甚至 大段删减,然后扔给苏轼重写,一篇短小的文章常须 往返数次。苏轼深感耻辱。 终于有一天,苏轼爆发了。苏轼曾应“贤良方正 能直言极谏”科的制举并得中高第,同僚都喜欢称呼 他为“苏贤良”。那一天,有一个小吏在府内喊苏轼 “苏贤良”的时候,恰被陈知府听见了。陈知府大怒 ,呵斥那个小吏道:“什么苏贤良,一个签书判官罢 了!”还不解气,喊来衙役,当着苏轼的面将那个小 吏狠狠地打了一顿。 苏轼当场和陈希亮闹翻,恶骂了一架,几乎动粗 ,被同僚们拉开了。 若干年后,当陈季常请苏轼为其父陈希亮作传的 时候,苏轼没有推托,或许他把当年不愉快的事早给 忘掉了。苏轼写了一篇《陈公弼传》,把陈希亮塑造 成了一个有勇有谋,敢给老百姓办事,刚直不阿的廉 吏形象。 多少年来,豫东民间一直把陈希亮视为白脸包公 ,很大程度上是从苏轼《陈公弼传》里演绎得来的。 对于自己的敌人呢?继续看来,答案已露冰山一 角了。 章惇贬谪苏轼于儋州后的第七个年头,也即元符 三年,宋哲宗驾崩。赵佶继位。不久,章惇罢相,被 远谪雷州,踏上了当年苏轼所走过的道路。而这个时 候,苏轼却遇赦行走在北归汴京的路途中了。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苏轼北归行至润州,由于路 途的鞍马劳顿,苏轼生起病来,不得不在润州小停几 日。连日来,朝野上下纷纷传言,说苏轼一到汴京, 就是当朝的宰相了。对于这一传说,苏轼早些时候就 有所耳闻了,他并不怎么当回事,岭南七年,已使他 对人生有了更为通彻的感悟。 忽然有一天,章援前来求见。章援来到苏轼的病 榻前,“扑通”跪倒在地上,口里喊着“恩师”,已 泪流满面。章援是章惇的小儿子,他中进士的时候, 苏轼是这一榜进士的座主,这也是章援以师生之礼拜 见苏轼的缘由。 就是这个学生,在苏轼南谪的数年间,未曾给老 师写过只字片纸,而这次来,却给苏轼呈上了一封长 信。信中说,章惇年事已高,贬谪雷州,恐身心难以 承受,恳求苏轼还朝以后,念在多年的交情上,对章 惇援之以手,云云。 苏轼被章援的孝心所感动,他强撑病体,走下病 榻,给章援写回信。拈起笔来,往事涌上心头,客栈 长谈,山中游历,“乌台诗案”的出手相救……苏轼 念及的,都是章惇的种种好处。苏轼在信中仍称章惇 为丞相,写得也很动情:“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 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接着介绍了 雷州的风土、注意的事项等,还一再叮嘱章援多备些 药物。 信写好,苏轼想了想,又在信的背面抄录了一道 “白术方”。苏轼说:“这个方子最适合岭南用,服 了可延年益寿,请交与丞相。” 章援拿着方子见到章惇的时候,章惇正借酒消愁 ,已喝得醉眼蒙眬了,他见章援手里拿着东西走了进 来,不禁问道:“拿的什么东西?” 章援说:“苏轼为你开的药方。” 章惇嘴角抽搐几下,指定章援,含混不清地说: “扔掉它,我不要苏轼的东西!” P8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