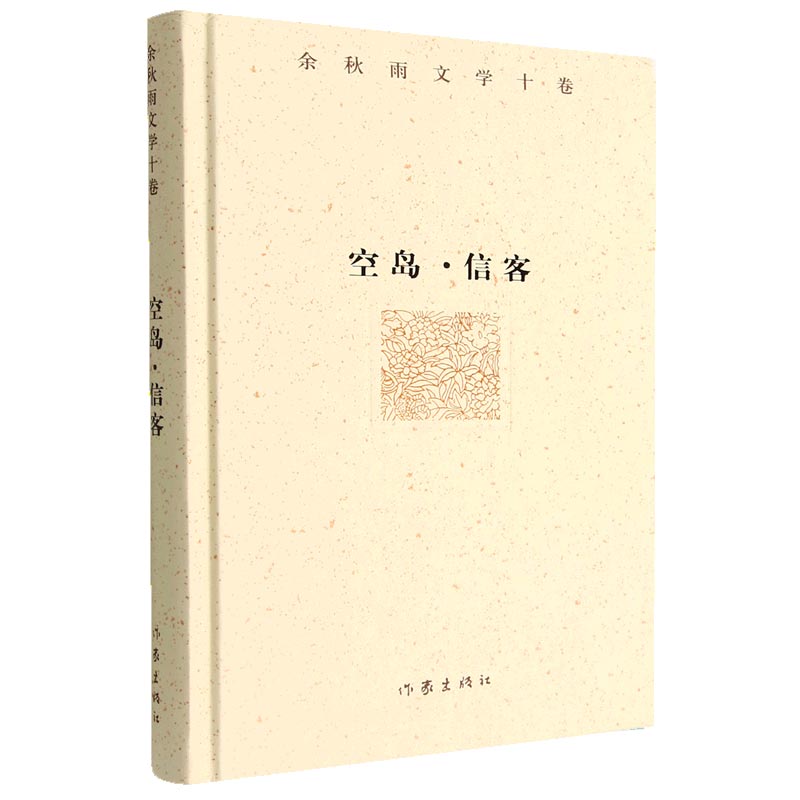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7.80
折扣购买: 空岛·信客(精)
ISBN: 9787506392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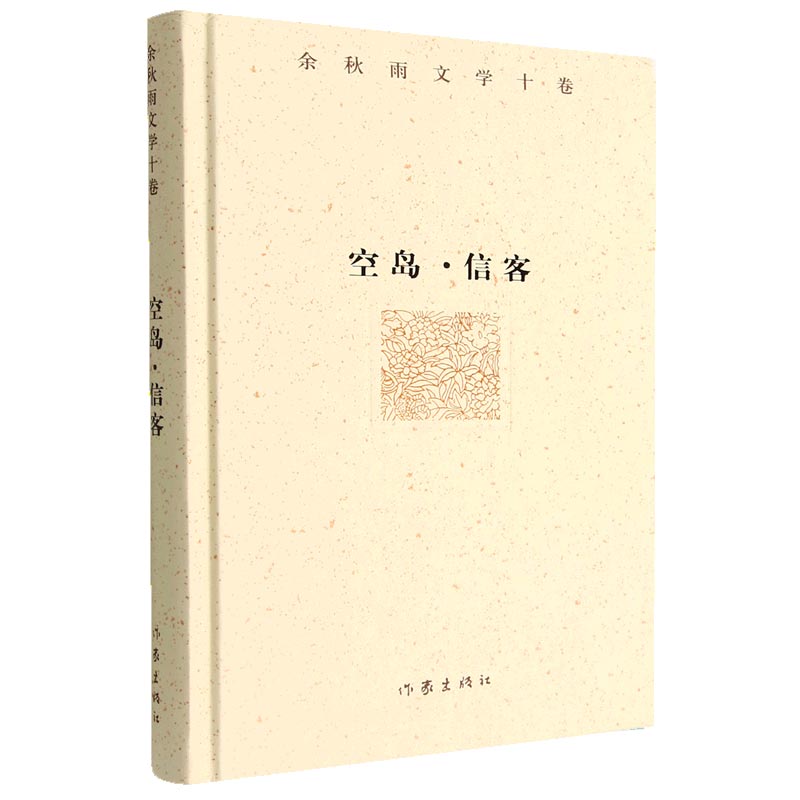
余秋雨,中国当代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探险家。他的《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等历史文化散文凭借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深刻的思考、诗意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深厚的内涵,更以独创性“文化大散文”文体为中国当代散文开辟了新路,以卓尔不群的品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第一章 一 前面所说的落水事件,发生在清代嘉庆五年,按照国际公历,也就是一八〇〇年,十九世纪的第一年。 说准确一点,是十九世纪第一年的夏天。 世上很多偶然小事,一探根脉却让人震惊。这个落水事件,就牵连到中国最大的文典《四库全书》、中国最大的贪官和珅、中国最大的海盗王直,跨时好几百年。这实在太让人好奇了,那就请允许我费点事,从远处说起,再慢慢绕回来。有的段落比较复杂,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明白。 先从《四库全书》说起。乾隆皇帝在晚年为了彰显“盛世修典”的气派,下令召集全国各地学者,在他眼皮底下把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全部重要文献汇编在一起。这事,最难的不是学识,而是张罗。 那么多学者,名气不小,脾气很大,方言各异,举止古怪,谁能把他们拉扯在一起?那只能靠“全朝实权第一人”和珅了。 和珅对各地学者照顾得热情周到,又派出一批年轻的书吏殷勤侍候。那些书吏其实也是他的“情报人员”,帮助他更精准地掌握了汉族文人,特别是南方汉族文人的思想动态。 这天,一个书吏向他报告,徽州籍的王进士与余姚籍的徐进士一见面就争吵起来了。 “一见面就争吵?为什么?”和珅问。 书吏就把争吵的过程仔细描述了一番。 两位进士一见面,余姚的徐进士就对徽州的王进士说:“从名帖上看,贵府在歙县,是出砚台的好地方,我家几代都用歙砚。” 但是,这位徐进士把“歙”念成了“西”。这是不奇怪的,这个字本来就有两种读法,“西”的读法更通行。但在歙县的地名上,却是另一种读法。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说,别人读错自己家乡的地名是不可容忍的,他们总是高看家乡的知名度。 “我要纠正一下,我家乡歙县的歙,不读‘西’,读‘麝’,‘麝’香的‘麝’。顺便,请告诉一下你家长辈,那砚台的正确读名是什么。”王进士的语言十分犀利,除了保卫家乡的名号,还因为,自己在进士榜上的排名远远高于徐进士。 受到王进士的抢白,徐进士一下来气了。只要是中国人,最忌讳人家要教训自己家的长辈。他才思敏捷,冷笑了一下就说:“我家长辈不会忘记贵乡的地名,因为二百四十多年前贵乡有一位强人,在我们家乡留下了几笔重债。很巧,他也姓王。从此,我们那里的人怕提贵乡,把砚台的名字也另读了。” “留下几笔重债?”王进士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说重债是客气了,是血债,而且是灭村屠城的血债,在明代嘉靖年间。”徐进士提醒王进士。 王进士立即明白过来了,说:“我知道,你在说五峰先生的事。五峰先生确实是我的本家,我们整个王家都不讳避,整个歙县都不讳避。” “五峰先生?那是他的号,还是直呼其名,叫王直吧。整个明代,倭寇成为第一大患,而倭寇的第一首领,非贵家的这位先祖莫属了!”徐进士提高了声调。 王进士似乎早有准备,平静地说:“这事说来话长,我现在不想与你辩。只问一件事,倭寇,是日本海盗,王直,是中国徽州歙县人氏,他怎么会成为第一首领?如果他是第一首领,为什么不叫徽寇、歙寇?” “这……”徐进士语塞了。 王进士用鼻子“哼”了一下,转身就走。 …… 书吏描述完这段争吵,就不再作声,但两眼直直地看着和珅,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 和珅也直直地看着他,说:“就吵这个?明朝的事,倭寇王直,二百多年了,还有什么意思?” 书吏说:“开始我也觉得没有意思,但我后来侍候徐进士回寓所,他还在给我说王直的事。有一句话,我觉得需要向您禀报。” “什么话?”和珅问。 “徐进士说,直到今天很多南方长者还在疑问,王直的财产富可敌国,却一直没有找到。” 这一下和珅果然来了精神,问:“你是说,王直被杀后,财产不知去向?” 书吏点头:“不知去向。” 和珅不再讲话。这话题,触动了他的神经。 他十分清楚,乾隆朝经济繁荣,但由于奢靡过度,又由于自己一直在营建一个庞大的私家财富大城堡,朝廷的库帑已出了问题。乾隆皇帝并不知道财政的艰难,谁也不敢对他实言。万一乾隆皇帝察觉了什么,下令盘查,自己就会很不安全。因此,如果能用朝廷的力量追寻到王直的遗存,至少可以补充 库帑。 如果追寻不到,那大笔财富就有可能落入当代强人之手。此刻,天地会秘密团体正蔓延南方,福建又兴起了由蔡牵领头的渔民、船工暴动。他们当然很需要钱,如果能够得到、或者将要得到王直遗存,那必定是一场大灾难。和珅想,既然民间有那么多传言,即使那些强人还没有得到,也不会不听到,因此,也一定在寻找。 这是一场世代相传的地下暗战,这是一场决定荣衰的秘密争夺。而且,与平日自己的贪污、侵吞不同,参与这场暗战和争夺,还能获得一个有利朝廷的好名声…… 想到这里,和珅的眼睛亮了。 二 此后,和珅与各位学者聊天,总会频频地拐到明代的倭寇事件上。这是前朝的事,说起来不犯忌,大家都说得很直率。毕竟是学者,言之有据,思路清晰。 和珅很快就明白了,把大明王朝搅得惶惶不安的倭寇之患,最高首领确实不是日本人,而是王直。日本的海盗、浪人、流氓固然是主体,但都接受王直和其他几个徽州人如徐海、徐惟学的摆布。 王直通过贸易从葡萄牙船队那里取得了大量新式火枪,又把这些火枪卖给正处于战国时代的日本人。这使日本的军事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他本人,也成了让日本人不得不争相追随的人物。 他是一个海盗王,更是一个国际贸易的天才。两种身份叠加在一起,当然更强悍了。他会有多少财产,人们无法估量。 和珅还知道了,王直在嘉靖三十七年中计被捕,但处置王直案件的最高官员吴宗宪也受到朝廷的弹劾和调查,因为吴宗宪牵涉到严嵩的案件。吴宗宪几年后在狱中自杀,政治角力波诡云谲,谁还想得到王直和他的财产呢? 和珅搞清了事情的基本轮廓之后,认真想了好久。他觉得追寻虽然没有把握,甚至毫无线索,但数额之大让他难以抵挡,而在毫无线索中发现一丝依稀线头,又挑拨起了他心底的好奇。 和珅决定,追寻王直遗存的事,必须交由自己掌控的军机处来秘密进行。他已经与军机处的两个专任官员“军机章京”商谈很久,布置了追寻计划。由于他反复说明了这事关及朝廷库帑、天地会和蔡牵暴动,因此全部追寻任务确实也名正言顺,成了军机处的头等大事。那两个“军机章京”,深知 轻重。 和珅特别关照,这件事能否查出结果,完全不得而知,因此,暂不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一向好大喜功,又被和珅历来的办事效率宠坏了,如果他知道了,就会不断查问,容不得久查无着。这一来,麻烦就大了。而且,皇帝的不断查问,又会引起朝廷各部关注,万一那笔财富与哪个系脉有涉,事情就会变得很混乱。 于是,和珅开始安排一件平生难事:给予追查的权力,却又必须无声无息,无痕无迹。 他平日再忙,也经常会把历书和舆图翻出来,让目光在那些年号和线条间扫动。 三 不久,一些黑衣人开始从京城出行。 最早出行的两个黑衣人,现身在南下的大船上。大船是《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送几位南方学者回家的。反正大书编完了,学者们在船上心情放松,就与那两个黑衣人天天神聊,以解旅途之闷。那两个黑衣人,一个中年人,姓何,自报名字为“何求”,学者们一听,直夸名字起得好,有人生哲思;另一个是年轻人,姓李,自报的名字大家都没有听清楚,也就没有追问。 两个黑衣人自称此行是陪送学者,却又说顺带办点别的事。何求说是到扬州查核一笔漕运税银,姓李的说是老父有病,顺道省亲,但他们却又都客气地说,陪送是“此行主旨”。 神聊到第四天,明朝倭寇,成了主要话题。 两个黑衣人慢慢听出来了,王直的事,在徽州、浙江流传很广,但最重要的内容却最含糊。例如,像王直这么聪明的人,对家产一定早就有隐秘的安排。安排的核心,必然是照顾宗族血缘,代代相传。那就是说,追查遗产,应该寻找一份可靠的家谱,然后顺藤摸瓜。但是,这份家谱在哪里? 黑衣人何求问:“王直既然都已经在日本九州立国了,任命高官不分国籍,哪里还在乎家谱?” 一位年长的学者说:“那他为什么还会回国而被擒?照他的狡诈阅历,不会不懂得朝廷的诱降之计,但他还是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回来了,为什么?最终丢不下桑梓血亲。因此我敢断言,家谱还是修了。” 黑衣人何求诚恳地点头,却又小声追问:“家族已经分崩离析,秘藏一份家谱在哪个后代手里,极可能毁损,现在大概早就不在了。” 那位年长的学者说:“如果遗产还在,按惯例,那就一定还会有一个家谱抄本,在一家藏书楼收藏着。这样,可以避免谱系流失,为后代分配遗产留下了依据。浙江的天一阁、嘉业堂都收了很多家谱,但那太容易被旁人发现了。王直的后代懂事,不会藏在这么有名的藏书楼。应该是在二流小藏书楼,而且是在不会倒闭的藏书楼。” “不会倒闭的藏书楼?”黑衣人何求带着巨大的好奇追问。 年长的学者含蓄地一笑,说:“是啊,只有不倒闭,家谱才存得下去。但是,一家小藏书楼为什么能历代而不倒闭?如果没有特殊理由,那只能是因为有一笔常可观的预先赞助。王直如果要在哪家藏书楼暗藏家谱,那么,一定会提供这种预先资助的。” 黑衣人何求睁大双眼看着这位学者,然后闭住了眼睛。想了一会儿,他又把眼睛睁开了,说:“对这件事,我可以归纳几点了。第一,王直如果真有大笔遗产,应该还留有一本家谱;第二,这本家谱应该藏在一家不大却又不会倒闭的藏书楼里;第三,这家藏书楼财源神秘,无人知道。” 他的归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一位年纪稍轻的学者说:“我们不想丝毫沾染王直遗产,但对那种说不清财源的小藏书楼却充满了好奇。真有吗?会是哪一家?” 黑衣人何求说:“有疑点,就有线索。不怕麻烦追寻下去,说不定巧上加巧,万中遇一,撞上了。” 以后几天,几个人在船上无聊,就爬梳着江淮流域各种藏书楼的一个个屋顶,一堵堵高墙。爬梳不到的,就想象着。 终于,扬州到了。黑衣人何求离船上岸了,说是要急着去查核漕运税银。姓李的黑衣人还要坐原船去池州,然后走陆路到徽州。几位学者,也分别到扬州和徽州。于是,大家就在扬州码头分手了。毕竟同船相处了那么久,互相频频作揖,依依惜别。 一个娓娓道来的传奇故事, 几个凝聚着时代烙印的身影, 纪实与悬疑的完美融合,呈现给我们对大善大美的全新领悟。 我们都走在《信客》之路上,可又有几人可以寻到《空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