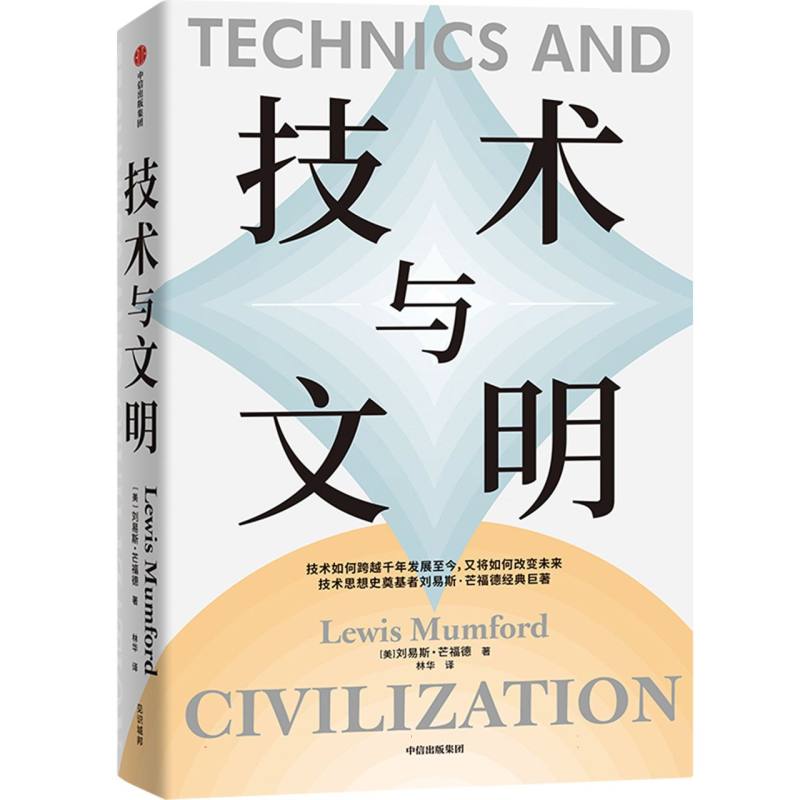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64.49
折扣购买: 技术与文明
ISBN: 9787521767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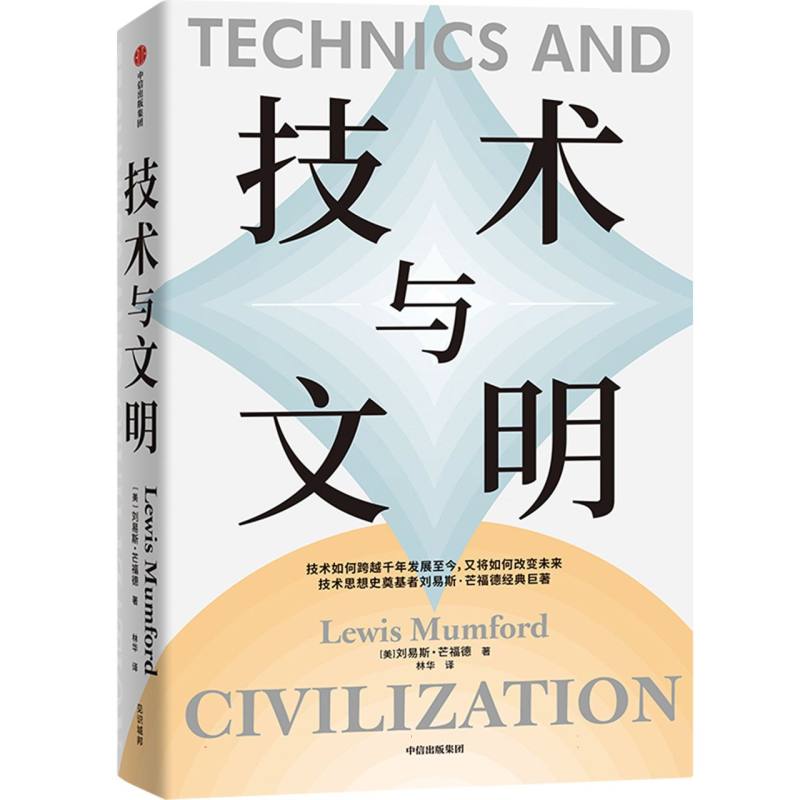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 芒福德是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技术思想家。要研究技术变化中人的维度,终究避不开刘易斯·芒福德。他就此题目撰写的富有远见的开拓性著作《技术与文明》是巨大的知识宝库,对20世纪早期的普遍学术观点公开提出质疑,帮我们思索构成现代物质文化核心的基本义务和伦理难题。后来数十年间,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芒福德围绕着我们以技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前景展开了诸多生动活泼的辩论。 促使芒福德关注这个议题的直觉植根于他的成长经历。他12岁时做出了自己的第一架收音机,进入纽约顶级高中斯代文森接受了扎实的技术与科学基础教育,后来在美国标准局水泥测试实验室做助手时,得以沉浸在典型的古技术环境中。20世纪30年代早期,芒福德已经是纽约学界的新星,发表的著作涵盖世界乌托邦思想、19世纪先验哲学和美国建筑学的演变。 芒福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关于“机器时代”的进修课时积累了诸多资料,并产生了撰写《技术与文明》的念头。1932年,作为研究的收官之举,他前往欧洲参观了大大小小的技术博物馆和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技术与文明》的参考文献和自10世纪以来各项发明的清单内容,这是当时能够获得的最详细的资料。 芒福德毕生著述范围涵盖文学批评、建筑学、历史、城市社会学和哲学。他曾任《日晷》杂志副主编、《社会学评论》(伦敦)主编和《美国大篷车》联席主编。他不仅是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还担任《纽约客》杂志的建筑评论家长达30多年。他共发表过30多本著作,包括《城市文化》《城市发展史》《生活的准则》《人类的状况》和《机器的神话》,还有数百篇期刊文章,并最终荣获美国自由勋章和大英帝国爵士称号。
引言 要研究技术变化中人的维度,终究避不开刘易斯·芒福德。他就此题目撰写的富有远见的开拓性著作是巨大的知识宝库,帮我们思索构成现代物质文化核心的基本义务和伦理难题。芒福德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部著作《技术与文明》对20世纪早期的普遍学术观点公开提出质疑。后来数十年间,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围绕着我们以技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前景展开了生动活泼的辩论。 20世纪30年代早期,芒福德开始把研究方向转向技术。当时他已经是纽约文学界的新星,发表的著作涵盖世界乌托邦思想、19世纪先验哲学和美国建筑学的演变,还出版了一本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9世纪美国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译者注)的重要传记。为了弄懂工具、器械和生产工艺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中发挥的影响力,芒福德如饥似渴地遍览论述工业社会兴起的标准著作,却发现那些书籍实质内容出奇贫乏、知识涉猎非常肤浅。当时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的此类学者,满足于狭隘叙事,只强调18世纪以来“机器”的发展及其在塑造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芒福德注意到,尽管技术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系统性概述技术史的英文著作仍付阙如,也没有哪部作品充分探讨过人与“技术”丰富而复杂的关系。他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除了强大的新式发动机和它们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外,技术史难道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内容吗?世界各地的社会难道不是在工业革命到来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技术了吗? 芒福德怀着活跃的好奇心,在解释现代科技领域的奠基性重大发展时大大延长了他研究的历史时期,也扩大了他的叙事所包括的创造性活动的范围。所以,本书以10世纪的发明创造为起点稳步向前,记叙了艺术、工艺、科学、工程学、哲学、金融、商业等各个领域的千年技术进步史,也讲述了相关社会惯例的演变。芒福德论称,假若不是长久的文化准备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强韧的基础,工业革命中那些广为称颂的突破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此书强调了人类探索在各方面的发展,有一些初看之下似乎与技术装置和技术系统风马牛不相及。 芒福德的叙述中,修道院与时钟的故事可能最令人难忘。在中世纪欧洲的本笃会修道院,敬神和劳作分割为精确的时间单位,称为祈祷时刻(canonical hours),用以增强修道士的宗教信仰力量。有了这个制度,就需要能够衡量时间的装置,第一批简单可靠的时钟于是应运而生。芒福德认为,修道院“帮助给人的活动设定了有规律的集体节拍和机器的节奏,因为时钟不仅是计时的手段,而且可以用来实现人的行动的同步。” 在探讨这类事情时,芒福德并不长篇大论地解释重大的突破是如何形成的。他根据能够找到的最佳学术资料(主要是欧洲的),先是简短描述历史演变的标志性时刻,随即对其历史意义展开天马行空,甚至是幽默顽皮的猜想。例如,芒福德描述了玻璃制作工艺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改善如何极大地推动了在今天的知识生活和经济活动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重大发展:“玻璃帮助把世界套进了一个框子,它让人更清楚地看到现实的某些因素,并把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明确划定的领域,也就是框内的领域。”芒福德提出,没有玻璃工艺的改进,就不会有现代的“自我”来投入发现和发明。 芒福德的根本意思非常清楚。与普遍观点相反,现代生产的奇迹并非始于工业化时代叮当作响、喷吐白气的蒸汽机,也绝非源自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8世纪英国发明家、企业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译者注)、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18世纪英国工业家,发明了新型水力纺纱机——译者注)和工业革命的其他偶像级人物做出的发明。芒福德坚称,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有实际的工具和机器,还有反映人的各种动机的活动,那些动机包括宗教信仰,也包括在科学、工程学以及无数日常活动中对美的追求。芒福德的建议清晰明确:当今时代,利用这些资源仍然会给我们带来裨益。 本书另一个中心内容是探索后来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特征的制度的起源,如军方对各种技术选择始终具有的影响力。事实上,书中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是芒福德对矿山作为一切工业思想和工业方案的塑型器的描述。在他看来,15世纪和16世纪德意志地区采矿业的兴旺确立了后来数百年对于自然、工作、机器、生活品质乃至科学理论重心的基本态度。在芒福德的描写中,矿井张开大口,将它们黑暗而危险的执念喷遍整个社会。“采矿的典型方法并不止于矿井井口,而是或多或少地流行于一切附属行业。” 读者被芒福德引导着读过一个个堪称典范,让人欲罢不能的章节的时候,可以看到他喜欢花大量篇幅开展“宏大叙事”。但在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他这种叙事方法不大牢靠。毕竟,谁敢说能讲清楚如此庞杂的现代技术文化呢?芒福德对这类担心毫不在意,夷然挺身而出,对专家和普通读者许诺说会给他们做出可靠、冷静的讲述。 芒福德理论的中心是关于三个历史“阶段”的系统性论点。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论点来看待植根于我们周围的技术和制度中一层层的知识、信念和技能。芒福德认为,这三个阶段并非界限分明,而是相互重叠,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渗透。最早的“始技术阶段”包括从公元1000年到进入18世纪相当长时间的各种发明和思想。下一个是“古技术阶段”,以工业时代的材料和能源为突出特点。芒福德认为这个时期鲁莽轻率到了野蛮的地步。“对古技术社会状况最恰当的描述是战争状态。它的典型组成部分,从矿井到战场,都是为死亡服务的。”【这句话的原文是“它的典型组成部分,从矿井到工厂,从鼓风炉到贫民窟,从贫民窟到战场,都是为死亡服务的”前言的作者把内容压缩了,却不知为何没有用省略号——译者提醒】然而,在前面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阶段”更加成熟,给人带来了希望。这个阶段在20世纪头几个十年强势亮相,其间出现了新型合金、电力和更好的通信手段,也出现了在新的社会和技术项目中强调“有机性”这一高度必要的意愿。 《技术与文明》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的开创性方法和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也因为它阐述了一个新颖的理论。芒福德论称,技术表现了人类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在实际物质活动中最伟大的成功经常是深切的精神需求与最大的理性及非理性激情的投射。与此同时,生活在由物质组成的世界中刺激人的意识产生创造性反应,发展出了语言、符号、礼仪和丰富的灼见。芒福德后来这样总结自己的观点:“人将外部世界内化,将内心世界外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芒福德这部著作不仅试图准确全面地讲述技术史,而且意在阐释一切人类经验的一种根本性格式,这样的阐释比“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种普遍却笨拙的认知准确得多,充满了可能性。 当然,美国人一直称颂技术变化,但角度与芒福德建议的大不相同。正统观念着重的几个关键理念是:征服与控制自然是现代社会的伟大使命;效率是社会普遍适用的选择标准;现代历史表明,科学进步的积累直接增加了人类福祉;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的使命是永远保持竞争力,在技术前沿奋勇争先。在今天的语汇中,描述这类决心和努力的时髦词是“创新”。大公司和科技园都热情宣称,创新是人类的伟大使命。 《技术与文明》赞扬技术发展,不仅因为它减轻了生活的实际负担,也不仅因为它促进了生产,而且因为它能够出色地展示人类的灵性和感性,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深层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芒福德和任何其他现代思想家一样,对技术寄予广泛而巨大的希望。然而,他对20世纪30年代早期情形的审视显示机器时代陷入了一场严峻的危机——大萧条。普遍认为技术代表着“进步”,可现在似乎事情不再必然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生产方法显然满足不了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基本需求。说是要给所有人带来富足,事实却是遍及全球的失业、贫困、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 芒福德注意到了这段惨淡时期中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崩坏,但他并未过多纠缠这些问题,而是试图找出更深层的格式。即使在消费者经济早已重焕活力,生产力攀至新高之后,这些格式仍然痼疾难解,包括对工作的严格管理,社会组织的军事化,对宝贵资源的浪费,对自然系统的粗暴破坏,对空气、土地和水的大面积污染,以及把愚蠢的消费主义鼓吹为生活的终极满足。芒福德认为,真正的问题超越经济萧条,触及了现代技术文明的性质和我们想象这种文明带给人类的可能性时采用的思考方法。 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技术专业人士一直对芒福德这部著作深感兴趣,但更广大的读者群也能对书中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产生共鸣。他的案例研究和思考成果预示了后来科幻小说和电影的重大主题,如技术力量过于强大;创造出人工生命世界;看似非常理性的政治结构突然爆发暴力;部分与整体、生物实体与合成替代物之间的持续紧张。仅举一例,2009年出品的热门科幻惊悚片《阿凡达》就反映了芒福德的担忧,表现了一个渴求资源的高技术文明与一个更加和平、全面的植根深厚的有机文化之间的冲突。在詹姆斯·卡梅伦(James Cameron)导演的这部电影中,潘多拉星球上那些和平、理性的可爱生物最终取得了胜利。同样,芒福德希望在现代技术领域开展全面改革,这个思想预示了当今时代发展“可持续”技术的努力和实现“绿色经济”的希望。对环境退化、石油储量减少和全球变暖的担忧促使我们直面本书最后一章“今后方向”中提出的问题。“对生命体和有机体的兴趣在各个领域都开始重新觉醒,撼动了纯机械体的权威。过去一直受摆布的生命现在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芒福德在审视20世纪30年代早期现代社会的困境时表现出惊人的乐观态度。他相信,古技术时期的过分和不公最终完全有可能通过成熟化过程得到克服,被一个彻底的新技术时代所取代。届时,社会组织的形式将更加符合人性、更加规划周密、更加有利生态。思维缜密并怀有爱心的人将努力解决原始机械化社会的弊病,磨平这种社会的粗砺棱角,从内部实现社会的人性化。在那之后,芒福德目击了冷战、核军备竞赛、生态环境污染、城市和郊区生活的错乱方式、大众媒体对公共舆论的神秘化和他所谓的“权力复合体”的制度化统治地位。因此,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原有的信心不复存在,代之以日益强烈的怀疑。也许正是为此,我们才应该重温芒福德以前的思想。那时,光芒尚未被阴影遮蔽,最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让我们把事情不可能如愿的所有理由暂且放在一边,和年轻的刘易斯·芒福德一起发问:我们希望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兰顿·温纳 1963年版的导言 《技术与文明》初版于1934年。那时,学者常把当今时代称为“机器时代”,却到18世纪去寻找这个时代的起源。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位亲戚A.J.汤因比(A.J. Toynbee)在19世纪80年代用“工业革命”一词来描述当时发生的技术创新。虽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原始人的技术装备给予了应有的注意,有时还夸大工具的重要作用,但他们鲜少触及技术对人类文化更广泛的影响。有用的、实在的东西依然不属于真善美的范畴。 《技术与文明》脱离了忽视技术的传统。它不仅首次总结了西方文明的千年技术史,而且揭示了由修道院生活、资本主义、科学、玩乐、奢侈品和战争构成的社会环境与发明家、工业家和工程师的具体成就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卡尔·马克思认为技术力量(生产体系)自动演进并决定所有其他机构制度的特点;这个观点并不正确。本书的分析显示,技术力量与其他机构制度的关系是相互的、多方面的:一件儿童玩具可能导致一项新发明,如电影;关于即时远程通信的古老梦想可能促使莫尔斯(Morse,19世纪发明家、艺术家,发明了莫尔斯电码——译者注)发明了电报。 本书的主题初次反映在1930年8月载于《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的一篇文章里,那篇文章题为“机器的大戏”(The Drama of the Machines)。我在文章中写道: “如果想清楚地知道机器是什么,就必须不仅了解它的物理起源,还要考虑它的心理起源,也必须评价机器产生的审美和伦理结果。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只看机器的技术成功,不及其余;我们对发明家和科学家的工作顶礼膜拜;我们有时因这些新器械的实际成功而对其称赞有加,有时又因它们成就的狭隘而对其嗤之以鼻。 然而,对此题目重新审视之下,会发现许多原来的想法站不住脚。我们发现,机器体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人类价值观。我们还发现了普通经济学家绝口不提的浪费、损失和能量的误用。长远来说,机器给我们的物理环境造成的巨大物质变化也许不如它对我们的文化做出的精神贡献那么重要。” 促使我重新审视这个题目的直觉植根于我的亲身经历。我12岁时做出了我的第一架收音机。不久后,我开始为通俗技术杂志写短文,描述我对收音机的各种改进。因为我这方面的兴趣,我进入了斯代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纽约市的顶级高中——译者注),在那里接受了扎实的技术与科学基础教育,特别是熟悉了家具制造、锻造、木材及金属切削、铸造等行业使用的基本工具和机械工艺。几年后,我进入当时设在匹兹堡的美国标准局水泥测试实验室,成为一名助手,沉浸入那个典型的古技术环境。 R.M.麦基弗教授(R.M. MacIver)看了我题为“机器的大戏”的文章后,邀请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一门关于“机器时代”的进修课。这门课不仅研究技术的经济与实际方面,而且审视技术的文化方面。据我所知,此前任何地方都从未开设过这种课程。在备课的过程中,我不仅获得了必要的资料,而且产生了撰写本书的念头。1932年,作为研究的收官之举,我前往欧洲参观那里大大小小的技术博物馆和图书馆,尤其是在维也纳、慕尼黑、巴黎和伦敦。那次欧洲之行大大丰富了《技术与文明》的参考文献和自10世纪以来各项发明的清单内容,是当时能够获得的最详细内容,至今依然有用。 《技术与文明》的基本理念与方法有意挑战许多流行的学术常规,尤其是束缚着研究者的僵化程序。那种程序将研究者局限于题目的一小部分,使之无法评价技术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副产品。我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态背景下讨论技术发展,因而避免了目前流行的将技术作为最重要的支配性因素的偏见。即使今天,人们依然在这种偏见的影响下幼稚地把我们的时代称为“喷气机时代”“核时代”“火箭时代”或“空间时代”。我对旧思维方式的挑战尚未得到广泛接受,也许这就是本书一字不改重新出版的最好理由。 至于我没有讨论过去30年的技术发展,我不打算为此做任何辩解。这项任务太艰巨了,就连拥有专业知识的历史学家也望而却步。由于另一个不同的原因,我也没有改动本书的原稿以反映后来的知识发展和我自己认识的加深。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文章,对我早先的论点做了修正和补充。有些文章发表在《科技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期刊上,有些载于《美国哲学学会会议纪要》(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还有些纳入了我的著作《艺术与技术》(Art and Technics, 1952)《以理智的名义》(In the Name of Sanity, 1954)和《人的变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 1956)。如果幸运眷顾于我,我准备再写一本《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来进一步阐述我这些新观点。我将在新书里审视在古老文化中已经显示出来的当今技术的负面影响,并将进一步拓展本书“今后方向”一章的内容,纳入上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的巨大技术成就及其造成的同样巨大的社会危险。 《技术与文明》预示了学者们态度的改变,主要是对于作为人类文化要素之一的技术史的态度,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在评价技术造成的社会与文化结果时的态度。可能本书帮助引起了这方面的兴趣,或至少帮助建立了这类书籍的读者群。除了乌尔里希·温特(Ulrich Wendt)的《作为文化力量的技术》(Die Technik als Kulturmacht, 1906)和斯图尔特·切斯(Stuart Chase)的《人与机器》(Men and Machines, 1929)之外,所有泛论技术的著作,如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的《机械化的决定作用》(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和R.J.福布斯(R.J. Forbes)的《作为创造者的人》(Man the Maker)都出版于本书之后。由于同样的原因,本书的参考文献中没有A.伍尔夫(A. Wulf)的《16和17世纪科学技术史》(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我撰写本书时,找不到全面的技术史。所幸现在这个空白填补上了。50年代出版了五卷本的《技术史》(History of Technology,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及T.K.德里(T.K. Derry)和T.I.威廉姆斯(T.I. Williams)在其基础上写出的短小精悍的一卷本技术史(牛津,1961)。 由于没有改动正文,也就没有在参考文献中添加这个领域中许多新人的贡献,特别是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ndmann)、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罗歇·凯卢瓦(Roger Caillois)、皮埃尔·弗朗卡斯泰尔(Pierre Francastel)、贝特朗·吉勒(Bertrand Gille)和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等法国学者的大作。他们的著作沿袭了之前德国学者的传统,包括卡尔·毕歇尔(Karl Bücher)、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甚至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若还需要更多证据证明对于技术与我们整个文化的关系的兴趣在日益增加,只需提及1959年创刊的《科技与文化》期刊、美国“技术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的成立和出色的意大利期刊《机器文明》(Civilità delle Macchine)。 几年前,《代达罗斯》(Daedalus)杂志的主编杰拉德·霍尔顿教授(Gerald Holton)要我在《技术与文明》出版25年后从当今的角度对本书写篇书评。那次我发表在《代达罗斯》(No.3, 1959)上对我自己著作的评论相当严厉(讽刺的是有些过于严厉)。因此,在此不必多谈本书的弱点和缺点,而对本书优点的重新评价又必须由他人来做。为了确信通过出版平装本来延长本书的寿命和影响力是明智之举,我又将本书重读了一遍。虽然如此说有自负之嫌,但坦白地说,读完后我对书中直觉的领悟和新颖的洞见印象深刻。靠着这些领悟和洞见,我常常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达成了经得起推敲的结论,并揭示出之前一直泾渭分明的各个领域之间重要的相互关系。 当时的评论者恰当地把《技术与文明》称为一部充满希望的作品,但现在令我感到庆幸的是,即使在那时,在世界尚未因人类掌握核能后出现的野蛮的道德沦丧和疯狂计划而陷入危险的时候,我就指出,许多最给人以希望的进步可能反而会造成倒退。我预见到了我后来所说的“自动机”和“本我”之间的不祥联系。上一代的读者若是看懂了本书的后半部分,就不会对后来惊人的科技进步以及各种变态和偏执的欲望感到意外。所以,虽然本书未曾提及此前30年的技术史,但解读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及其后果所必需的基本洞察力却始终贯穿其中。因此,我愿意准许本书不加修改再版:无异议! 刘易斯·芒福德 纽约州阿米尼亚 1963年春 核心卖点: 现代最重要的社会哲学家、技术思想家、城市理论家 刘易斯·芒福德的史诗巨著 纵览1000年技术与文明发展史 理性批判与浪漫构想的完美结合 无数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启蒙读物 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可或缺的一本书 为全球数以万计的大众读者获得认清技术时代真相的机会 编辑推荐: 人类如何发明技术,技术又如何改造人类? 技术发展是幸福还是苦难, 在人类历史中早有答案。 现代科技究竟带来的是幸福与进步还是苦难与堕落?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从工业革命开始便从未停止。如今新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经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智能终端几乎成了我们的新“器官”,同时,信息安全问题、核扩散问题、科学研究尤其是生物科学研究领域的伦理问题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至今日,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十分必要且迫切。 ☆千年技术史巨著,亦是波澜壮阔的记录片,技术思想史奠基者刘易斯·芒福德最重要的代表作 在学者满足于狭隘叙事的年代,芒福德大胆挑战学术常规,首次总结了西方文明的千年技术史,不仅阐述技术的物理起源,更聚焦技术的心理起源,以及经济学家鲜有提及的浪费、损失和能量的误用和与人类文化、精神不可忽视的互动关系。 ☆密集的思考+幽默的文笔让人大呼过瘾,要了解技术与社会文化不可思议的相互塑造,必须阅读本书 芒福德对于史实材料的切割、拼接、抽象、融合出神入化,揭示了由修道院生活、资本主义、科学、玩乐、奢侈品和战争构成的社会环境与发明家、工程师的技术成就之间不可忽视的相互作用:一件儿童玩具可能导致电影的出现;即时远程通信的古老梦想可能促使电报的发明……他天马行空甚至幽默顽皮的猜想让这部充满洞见的著作成为经典。 ☆惊人地预见人类新型生活的贫乏、健康的丧失、个性的抹杀以及对体量的崇拜,冷静犀利,醍醐灌顶 不同于一般技术史,芒福德不会讲一只机械表是如何被发明的,而是讲表这种技术出现之前,人为什么对“计时”有了需求,以及表出现之后,它对人们的时间观念、社会组织方式以及生存状态等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造。 技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要素,是利是弊全看使用它的社会群体的意愿是好是坏。西欧人曾把自然科学发展到了其他文化未曾达到的高度,并调整了整个生活方式去适应技术的节奏。本书将探索这是如何发生的,技术到底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愿望、习惯和思想,如何把控社会,直到社会心甘情愿臣服于它。 ☆看过本书的警告,就不会对今天的技术侵蚀再感意外 在世界尚未因人类掌握核能后出现的野蛮道德沦丧和疯狂计划而陷入危险的时候,芒福德就指出,许多最给人以希望的进步可能反而会造成倒退。看过本书,我们也就不会对如今惊人的科技进步及各种偏执的欲望感到意外。 ☆弄懂技术,不仅是驾驭技术的第一步,也是懂得社会,进而懂得我们自己的方法 当“进步”表现为健康的丧失和生活的贫乏,我们需要思考是什么限制了技术的裨益?技术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让我们收获更大的成就?本书便是向着驾驭技术迈出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