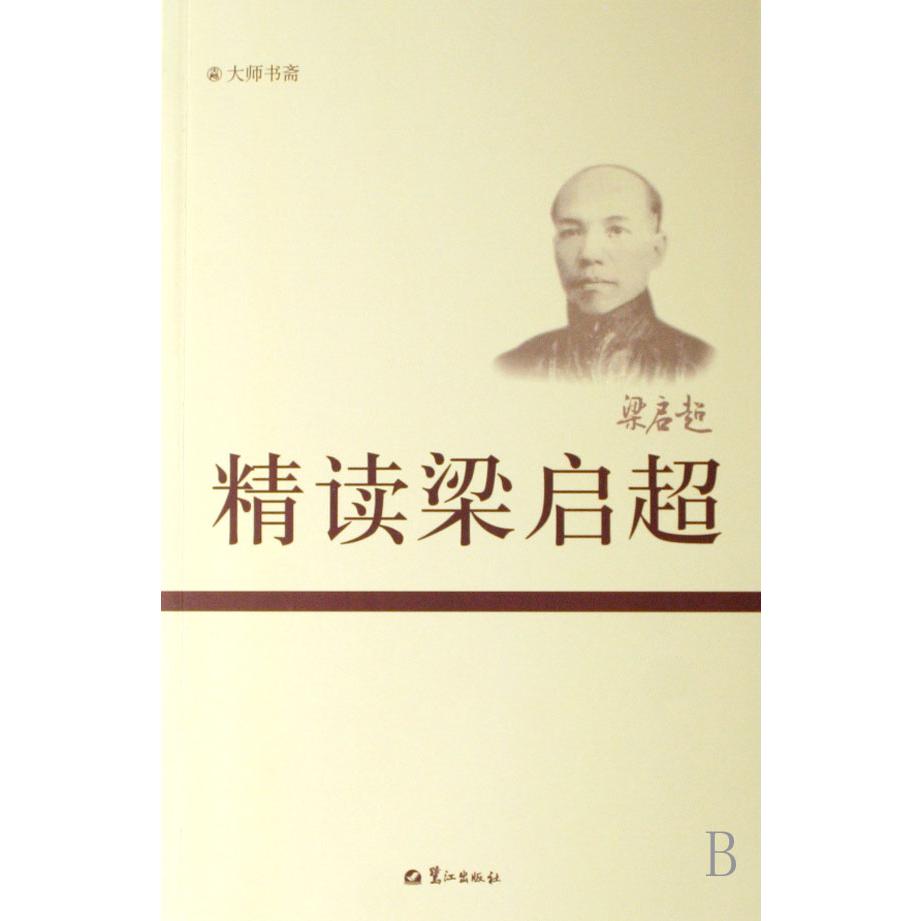
出版社: 鹭江
原售价: 30.00
折扣价: 21.30
折扣购买: 精读梁启超/大师书斋
ISBN: 97878067146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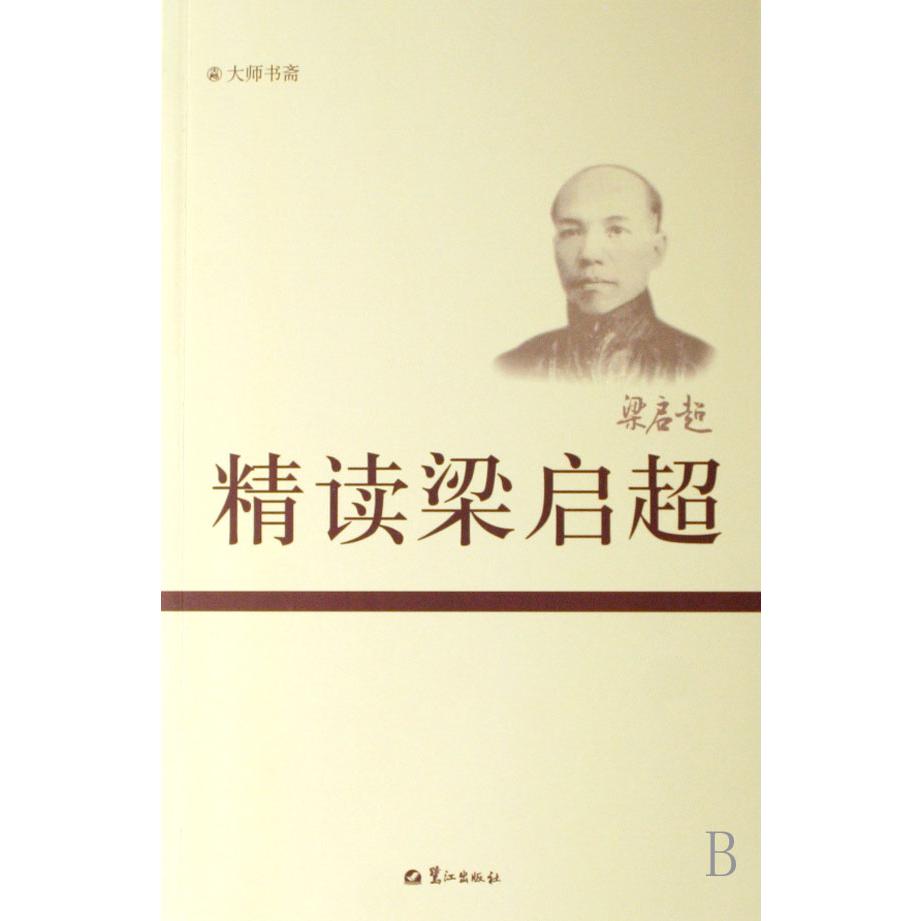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伟大的社会活动家,被时人称为舆论界的骄子。他还是一位重量级的学者,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他的文章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纵笔所至不拘束,而笔端又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代表作《少年中国说》影响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 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 国民之资鉴者,则日中国史。 今宜将此定义分析说明: 一 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活动休止, 则人道或几乎息矣。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史也者 ,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 叙述者也,是故非活动的事项——例如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现象者,皆 非史的范围;反之凡活动的事项——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 之相,即皆史的范围也。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日活动之产品, 二日活动之情态。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 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产品者,譬犹海中生物,经无数个 体一期间协合之嬗化而产出一珊瑚岛,此珊瑚岛实经种种活动情态而始成 。而今则既僵矣,情态不复可得见,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 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 现在相,再现于今曰也。 二 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 动者,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 然未必皆为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 ,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 —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 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复次 ;言活动而必申之以“赓续”者: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 ,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隐然若悬一目的以为指归;此目的地辽远 无垠,一时代之人之所进行,譬犹涉涂万里者之仅颐一步耳。于是前代之 人,恒以其未完之业遗诸后代,后代袭其遗产而继长增高焉,如是递遗递 袭,积数千年数万年;虽到达尚邈无其期,要之与目的地之距离,必日近 一日;含生之所以进化,循斯轨也。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 情状者也。率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 性者,皆非史的范围,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 也。 三 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 。然成绩云者,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 计其总和。质言之,即算总账也。是故成绩有彰显而易见者,譬犹澍雨降 而麦苗茁,烈风过而林木摧;历史上大圣哲大英雄之出现,大战争大革命 之经过,是其类也。亦有微细而难见者,譬犹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宿茶 浸陶壶而留陈渍;虽聪察者,犹不之觉,然其所演生之迹,乃不可磨灭。 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 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 类之总和也。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之因;而今 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 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然因果关系,至复赜而难理; 一果或出数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别证始明; 故史家以为难焉。 四 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 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 效果。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 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 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 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 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 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 而已。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 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 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 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 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夫如此,则史之目的,乃为 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 今人韦尔思有言:“距今二百年前,世界未有一著述足称为史者。”( 注一)夫中外古今书籍之以史名者亦多矣,何以谓竟无一史?则今世之史的 观念,有以异于古所云也。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虽然,彼 其体例,多属千余年前学者之所创;彼时所需要之史,与今不同。彼时学 问未分科,凡百智识皆恃史以为之记载;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 久,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吾侪居今日而读旧史, 正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离沙无金,固也。然数斗之沙,得金一颗 ,为事既已甚劳。况拣金之术,非尽人而能;苟误其涂,则取沙弃金,在 所不免。不幸而中国现在历史的教育,乃正类是。吾昔在友家见一八岁学 童,其父面试以元明两代帝王世次及在位年数,童对客偻数,一无漏讹; 倘此童而以他朝同一之事项质客(我)者,客惟有忸怩结舌而已。吾既叹异 此童之慧敏,转念以如此慧敏之脑,而役以此等一无价值之劳动,其冤酷 乃真无极也。不宁惟是,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 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试举其 例:如巴蜀滇黔诸地,自古本为中华民族文化所未被,其次第同化之迹, 治史者所亟欲闻也。而古代史上有两大役,实兹事之关键。其在巴蜀方面 ,为战国时秦司马错之定蜀;其在滇黔方面,为三国时蜀诸葛亮之平蛮。 然而《史记》之叙述前事,仅得十一字;《三国志》之叙述后事,仅得六 十三字。(注二)其简略不太甚耶?又如隋唐间佛教发达,其结果令全国思 想界及社会情状生一大变化,此共见之事实也;然而遍读《隋书》、《新 、旧唐书》,此种印象,竟丝毫不能印入吾脑也。如元明间杂剧小说,为 我文学界辟一新纪元,亦共见之事实也;然而遍读《元史》、《明史》, 此间消息,乃竟未透漏一二也。又如汉之攘匈奴,唐之征突厥,皆间接予 西方史迹以莫大之影响,明时欧人之“航海觅地热”,其影响之及于我者 亦至巨;此参稽彼我年代事实而可见者。然而遍读汉唐明诸史,其能导吾 以入于此种智识之涂径者,乃甚稀也。由此观之,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 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 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 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P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