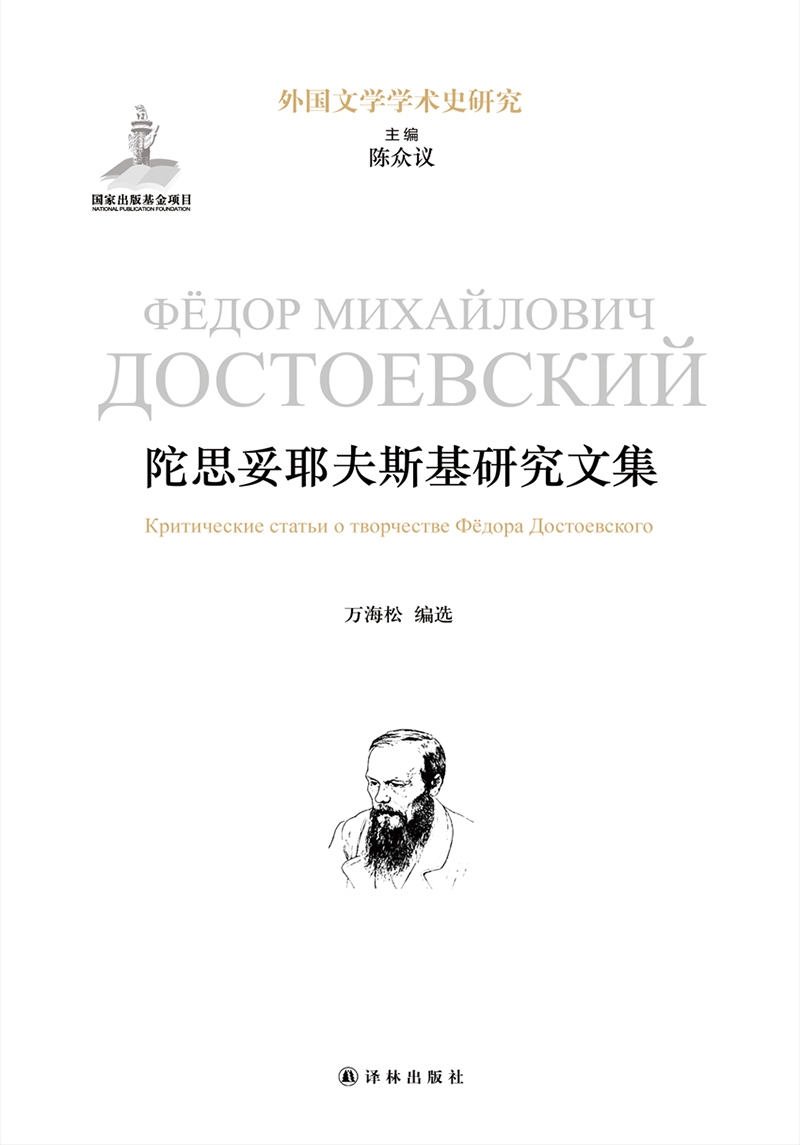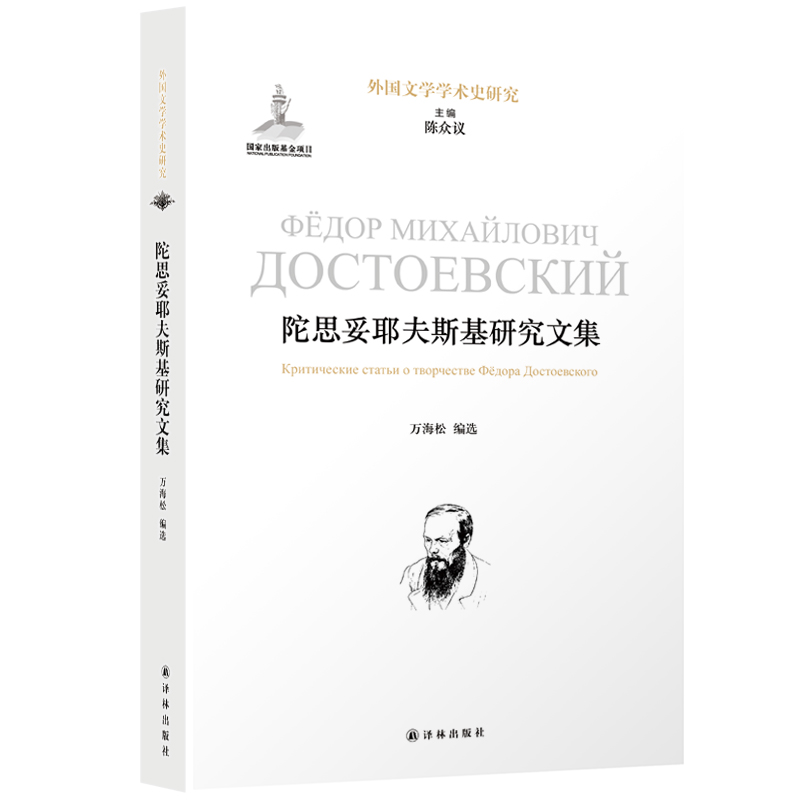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文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ISBN: 9787544780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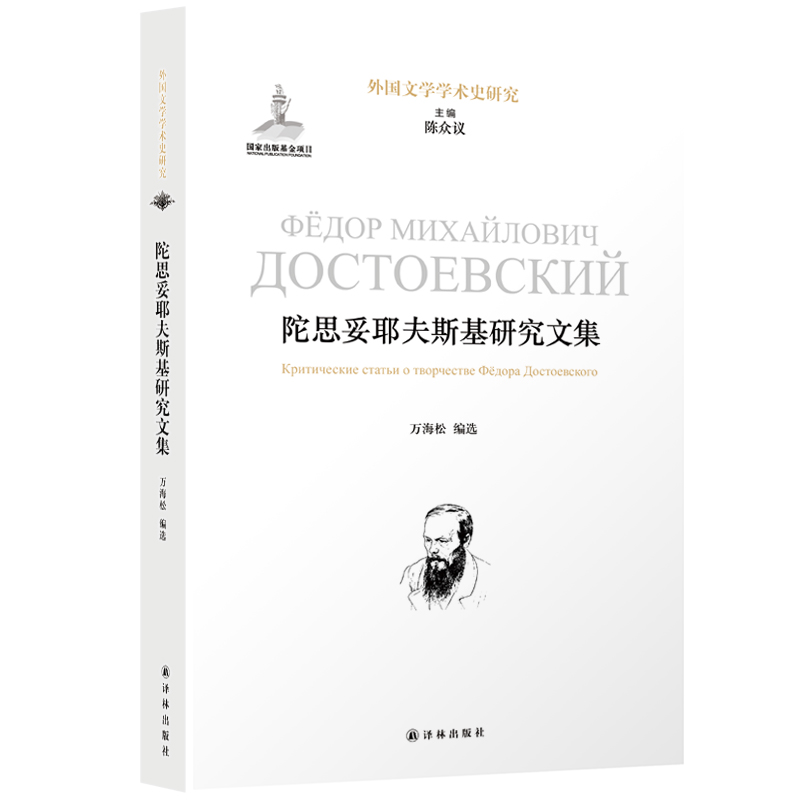
万海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重点为巴赫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重大项目子项目各一项。著有《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俄国根基派刍议》《〈死屋手记〉中“不幸的人”与东正教认同感》《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萌芽期与发展期的原创性》等论文,译著有《斯科奇诗集》、《巴赫金传》(合译)、《巴赫金全集》(第7卷)(合译)等。
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 作者 [俄罗斯] 康斯坦丁·巴尔什特 译者 许金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实质上是一种“宗教—文化”模式,视耶稣基督为人类道德的理想和精神追求的终极目标。这同时也是在新基督教的基础上使俄罗斯和全世界实现宗教复兴的一种理想。19 世纪下半叶俄国很多作家和哲学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认真思考。费 · 米 ·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米 · 米 · 陀思妥耶夫斯基,尼 · 尼 · 斯特拉霍夫和阿 · 亚 · 格里戈里耶夫在《时代》(1861—1863)和《时世》(1864—1865)杂志上刊发的文章阐述了这一思想的核心原则。一方面,它能将分裂成各个等级的俄罗斯社会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与追求经济发展不同的另一种社会进步选择,变追求技术进步为追求道德完善。从“宗教—哲学”层面来看,这种思想是哲学的人格主义,其思想基础是每个人要为所有人,要为“作为有机体的世界”全面负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的支点是明确把耶稣基督的肉身看成是上帝在地球物质中的化身,恰恰是“根基”引发了符合自己本性的理想:“基督是上帝,大地帮助上帝道成肉身。”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走向其“根基主义”有三条路径:第一条源于“俄罗斯民族乐于自我牺牲的特殊性”,第二条源于他倡导的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作用的美学思想,第三条源于他为自己的宗教信仰选择的特殊信仰象征(“基督的圣像”),与之相关的是在这种革新后的基督教中“长老制度”发挥特殊作用。受篇幅所限,很难完整地阐述这一系统的思想,而且,过去对此已有颇多著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赢得过赞誉,也遭到过批判,人们批评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乌托邦主义、 “玫瑰色的基督教”(розов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是无稽之谈,批评他夸大俄罗斯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甚至批评他的唯物主义。康 · 列昂季耶夫、瓦 · 罗扎诺夫、尼 · 别尔嘉耶夫、谢 · 布尔加科夫等很多人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学说持否定态度。因此,本文仅限于阐述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以及在作家看来俄罗斯宗教复兴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从流放之时起(1850—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打算撰写有关俄罗斯民族宗教改革的著作,后来他在著名的《普希金纪念碑前的演说》中提到了这个计划的一些想法(1880)。他在 1856 年 4 月 13 日给亚 · 叶 · 弗兰格尔的信中谈及《论俄罗斯》一文的构思,把这篇文章描述为“纯粹政治性的抨击文章”。五年后,他回到圣彼得堡,把这些想法写进论艺术的文章,其中的“某些章节直接取自那篇抨击文章。这其实是讲基督教在艺术中的使命的” 。这些有关基督教和艺术使命的文章形成《俄国文学论丛》,发表在 1861 年的《时代》杂志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沿着神指定的道路前进的主要手段是艺术,首先是文艺作品。他认为,艺术是通向真理的捷径,艺术是使垂死的灵魂重生并遵守基督教戒律的最有效方法。他所有作品情节的原型都是他未完成的小说《一个伟大的离经叛道者的生活》中所体现的思想,这部小说的内蕴实际上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小说中的思想早在其写作计划之前就已经形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计划创作的作品应当是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因其去世没有完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为谈论艺术的文章(19 世纪 60 年代初)而预备材料的笔记本中写有一则短文,阐述了他和对手有关基督的争论的意义:“基督在布道之时只是把自己的学说当成一种理想,他自己预测,到世界的尽头将会有斗争和发展(有关利剑的道),这是自然的规律,因为地球上生命是发展的,而在那里 — 生活,永远是喜悦的,是充实的……” 在他看来,世界的发展将沿着这样的道路进行:“所有的历史,无论是全人类的历史,还是每一个人的历史,有的只是发展,斗争,追求和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基督教是实现人类道德完善的一种途径,这样的道德完善不仅仅建立在基督教的“教义”上,而且建立在“基督的圣像”上。同时,基督是一种理想,是人类发展的终极。在他看来,俄罗斯应该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因为俄罗斯人民在心灵中特别珍视基督的形象。应该指出,阿 · 亚 · 格里戈里耶夫对这种想法有着更为明确的表述,他在 1859 年 8 月 26 日给 М.П. 波戈金的信中写道:“对我而言,东正教意味着著名的自然历史原则,它还应该存在,给予生活和艺术以新的形式……应该以斯拉夫世系的土壤,特别是以拥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大俄罗斯斯拉夫世系的土壤为根基复兴世界。” 这一思想逻辑的发展符合兼容并存的价值观,也符合必须把宗教“土壤”与“民族—地理”土壤结合起来的理念。实现道德完善的人们将是什么样的存在,取决于目标选择的正确性;他们走向这个目标的意愿强烈的程度,还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空间位置。“根基主义”的根源是这样的:“它是什么样的,它在哪里,在什么样的星球上,在什么样的中心,是否在终极的中心……亦即上帝的怀抱? — 我们不知道。这种未来的存在是否还会被称之为人(对于我们将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们还没有概念),我们只知道未来的存在之未来的本性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为基督 —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全人类发展的伟大和终极的理想 — 所预测出来,根据我们的历史规律,在于肉身。”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基督教的命运取决于为基督献身的道路, “为他献身的功勋。这就是我要强调的”;作家是如此醉心于这个思想,以至于把这个在所有的基督教教派中流传相当广泛的思想归功于自己:“这是我的思想,没有人指出这一点,但这是事实,这是真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种走向真理的进步运动的机制,建立在记忆传承的效应之上(类似于当前的记忆遗传假说):“在生理上孕育了儿子的人,把自己个体的一部分传给了儿子,而在道德上把自己的记忆留给了人们(追悼会上有关永恒的记忆的愿望是意味深长的),也就是说,自己以前的,在大地上生活过的个体的一部分,进入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我们清楚地看到,伟大的启蒙者的记忆活在人们中间,甚至对于人们来说,成为与他们相似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意味着,这些人物的一部分,在肉体和心灵上都进入了其他人之中,基督整体上进入了人类,人类的理想是追求把自己改造成为基督似的‘我’。他清楚地认识到,达成这一点之后,在大地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所有人,进入他理想的最终人物的队伍,即基督的队伍。”“在《福音书》中基督讲到了人类发展的最后话语。” 显而易见,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道德的(对亲人的爱和为了亲人牺牲自己)即意味着“基督教的”, “道德情操的问题,就是基督教的问题”。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基督教壮举完成的道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等价的,因此,在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时,不需要过多强调宗教信仰,他所看重的首先是道德理想,在其他宗教,例如佛教之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道德理想。与确立对基督的理想追求的人相对立的,是一种昆虫似的生活,所有试图否定这种追求的做法,都会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的蔑视,在他看来, “希望把一切都归结为哲学”的黑格尔就变成了这种试图绕过基督的昆虫 — “德国的臭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主要的主人公 — 哲学家的行为之中体现出来的一些理念,以及他的一些文论著作的论述,都由此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消灭自己对手的宗教活动家可称为“忠诚的人”,但不认为他们是基督徒:“我心中有道德的模范和理想,是基督赐予我的。我问:他会烧死异教徒吗? — 不会。这意味着烧死异教徒是不道德的行为。”由此得出结论,在一些情况下,遵循自己的信念将会导致完全违背道德的行为。 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完全符合这种范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遵循道德理想,甚至以犯下许多错误为代价;另一类是放弃这条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寻找一个圣徒 — 类似基督的人,这类主人公位于他所有作品的中心,从其第一部……《穷人》到其最后一 部……《卡拉马佐夫兄弟》。小说《白痴》的主人公在这部作品的草稿中并非随意地被命名为“基督公爵”。作家在有关这部小说的构思中指出,主人公的主要特征在于:“他原谅一切,认为一切皆因果,认为没有罪过是不可以原谅的,要宽恕一切。”他试图归纳在其作品主人公道德品质中体现的自己学说的主导思想,在笔记本上写道:“慈悲 —基督教的全部。”他在小说的定稿中丰富了这样的想法:“慈悲是全人类生活最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法则。”流放西伯利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二月党人娜 · 德 · 冯维津娜送给他的《福音书》上的下列 话语之上做出了如下的标注:“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需要指出, 《约翰福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约》中最喜欢的章节。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理想的基督徒 — 并不只是那些尽心完成他所信仰的宗教规定的整套仪式的人而是积极帮助拯救和恢复自己周围处于绝望或者是困境中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介绍维克多 · 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俄译本的文章中指出:“他的思想,是 19 世纪全部艺术的基本思想,而维克多 · 雨果作为一个艺术家,几乎是第一个宣示了这种思想。这是基督教的思想,是崇高的道德思想;它的核心原则是:帮助那些因受环境、数世纪的停滞和社会偏见等不公正的重压而处于衰亡之中的人们获得新生。这种想法是为社会上那些受屈辱者、被所有人遗弃而毫无权利者伸张正义。” 基于这些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以“点燃绝望者希望之光”为己任者都称为真正的基督徒,而不看他们的宗教归属,根据人在实际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对基督教信仰的程度来衡量其人格尊严。在他晚年的笔记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组名字, “巴尔扎克、莫里哀、基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可以被称为真正基督徒的,有狄更斯和坚持自然神论哲学的乔治 · 桑,实际上,乔治 · 桑“她并不信奉基督”;作家认为, “她也不喜欢在自己的小说中描写蒙垢忍辱的人物,不喜欢描写公正的但却是畏缩的、痴呆的和逆来顺受的人物,正如伟大的基督徒狄更斯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所做的那样;相反,她把自己的女主人公塑造得很高傲,简直写成女皇”。 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高兴地读到《新时代》上评论乔治 · 桑的文章,其中写道:“桑对无神论者,与对那些把恪守宗教教规视为拯救灵魂的必要条件的伪君子一样持厌恶的态度……她相信神明,认为信仰的最好证明是行善。”她令人难以置信的个性在于,她作为一位并不信仰基督的基督徒,却精确地传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观念的根本含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读到,乔治 · 桑不履行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仪式,不遵守宗教礼仪。他还从这份报纸中及时知悉乔治 · 桑去世的消息以及她那“非宗教性质的”没有牧师参加的葬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十二岁离开监狱时给娜 · 德 · 冯维津娜的信中写道:“我是时代的产儿,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乔治 · 桑的名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纲领性的《普希金纪念碑前的演说》中多次出现,她的人道主义学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展“根基主义”之时,对她的思想的汲取并不少于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所学到的圣西门、卡贝、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认为的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 — 全世界“兄弟友爱”的阶段 — 与当前的社会状态相对立,他把当前建立在人们之间激烈竞争基础上的社会状态称为“文明”,认为这是一种“过渡状态”,是一种病态, “人们对上帝的信仰衰退”:“人们划分成为各个个体,丧失了对于基督的真正思想。人们在这种状态下情绪忧郁,丧失积极生活的动力,不知道直接的感觉,一切都要凭意识去认知。”这种病态的症状之一,是无神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受到了感染。在他看来,甚至是真正的信徒也处于钟摆似的状态,处于信仰和不信仰两点之间的某个位置。他在创作《白痴》时写道:“一个基督徒,同时却没有信仰。这深刻体现了人性的双重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无神论理解成为一种信仰,或者是某种教派,认为它也可能会带领人们走向上帝的正确道路,在他看来,比无神论更为危险的状态是冷漠, “冷淡主义”会使社会“没落和腐化”。作家认为这种漠不关心“几乎成了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即便是与欧洲其他民族相比也是如此”。谢 · 季 · 韦尔霍文斯基(《群魔》)欣赏从《福音书》中摘录的一段 饱含这种想法的话语的深度:“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他认为,每一个精神生活丰富的人都会在信仰和不信仰神之间痛苦地徘徊,感受它们之间焦灼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 — 哲学家们 — 可能会同在“信仰与不信仰神灵的深渊”进行探索。《群魔》中 认为“最高的思想莫过于没有上帝”的基里洛夫点燃了圣像前的长明灯。作家同时代的人,例如,列夫 · 托尔斯泰认为,这种思想反映了作家灵魂深处的斗争。 基督 — 是上帝理想的肉体化身,同时,是人类的道德本体论状态的理想体现;有关“神人”的理念占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他的作品,尤其是在 1870 年代 — 《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他所构建的“基督的天堂”的结构的脆弱性,在这个天堂,所有人在道德状态方面都与基督非常接近。《黄金时代,唾手可得》和《一个荒唐人的梦》 — 是两个乌托邦,同时,也是反乌托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表明,类似基督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但只要有一个不类似于基督的人,就足以破坏和谐。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和研究,在白银时代简直如雨后蘑菇般急剧涌现。这其中,较为集中呈现也最值得重视的,也许就是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宗教哲学解读。列昂季耶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罗扎诺夫、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沃伦斯基、卡尔萨文、舍斯托夫、阿斯科利多夫等人的著名的陀学论述,大多发表在这一时期。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故事既有来自于现实的生动案例的,又不乏想象甚至臆测的成分,他所提出的问题和他的引发争论的思想,既源于对历史与传统的解读和对发生在身边的活生生的现实的持续关注,亦有高于、超前于历史和现实的虚构因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进行文艺学方面的考察,是苏联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大亮点。这种研究卓有成效,成就斐然,其中名家迭出,涌现出以恩格尔哈特、巴赫金、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艾亨鲍姆、多利宁、什克洛夫斯基、维诺格拉多夫、莫丘利斯基、尤里?曼、弗里德连杰尔、图尼曼诺夫等一大批文艺学家及其陀学论著。因此,本文集的第二辑主要收录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论述,诗学在俄语中不仅仅是研究诗歌的学问,它扩展到了文学史发展、形象分析、创作理念、话语表述诸多方面,具体则有历史诗学、结构主义诗学、空间诗学等分类。同一时期,从心理学、病症学角度切入的陀学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形象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大量地散见于在这些文艺学论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