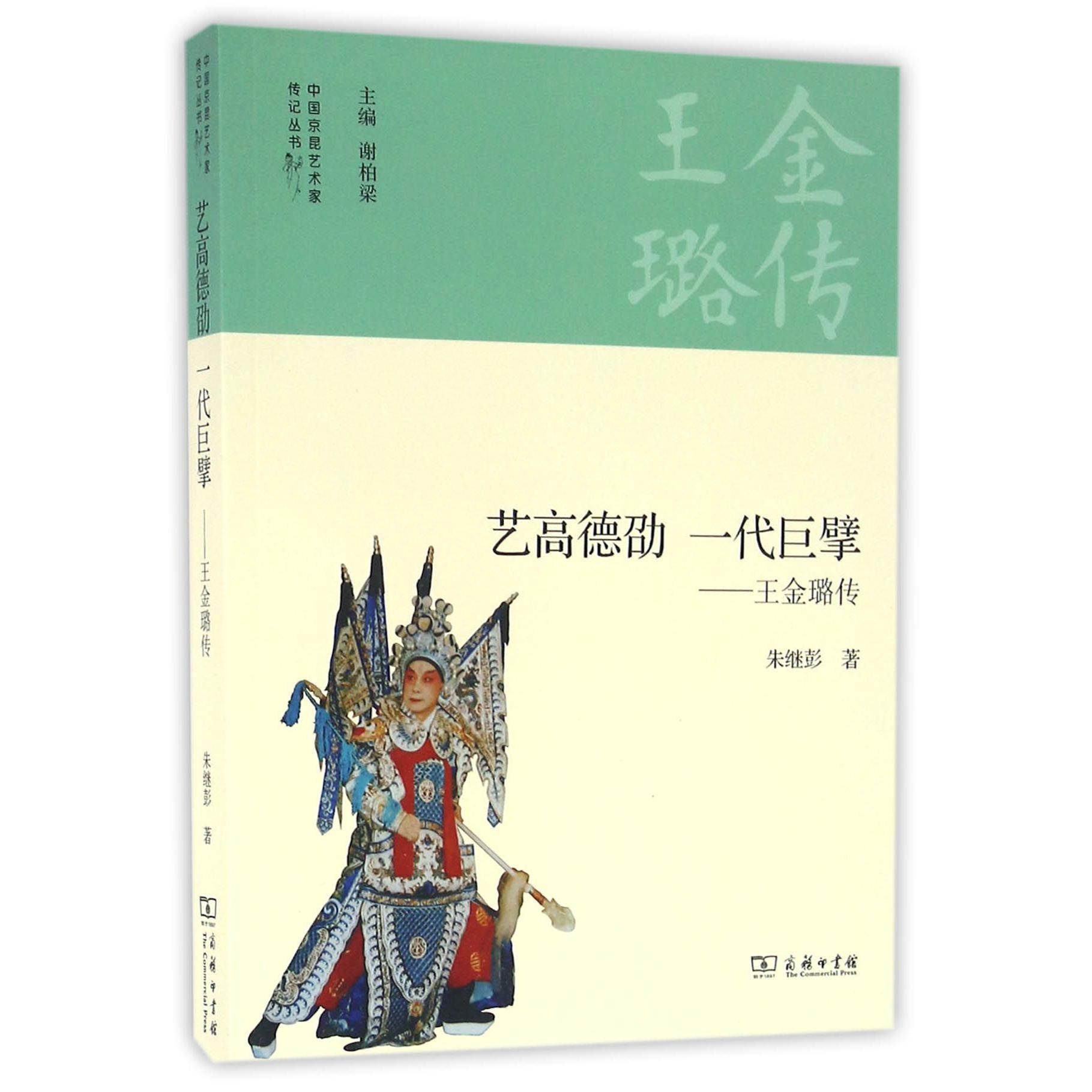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66.00
折扣价: 45.60
折扣购买: 艺高德劭一代巨擘--王金璐传/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
ISBN: 97871001226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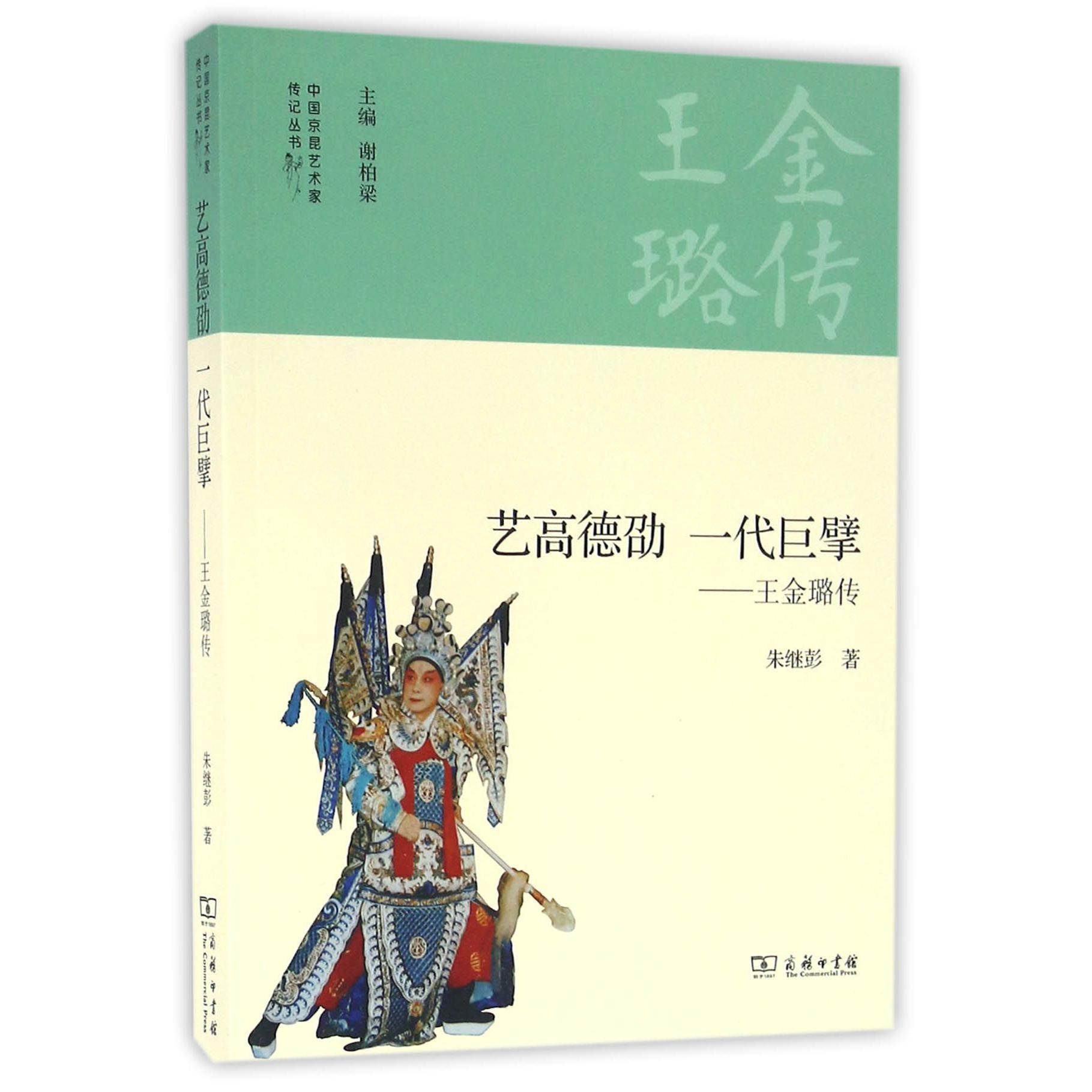
朱继彭,1938年出生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后从事石油化工研究,1981年起任教于华东理工大学。自幼酷爱京剧,七岁起频频出人戏院,对京剧的迷恋几近痴迷,在六十多年的戏迷生涯中,常以自研为乐,几无中断。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著有《童芷苓传》和《武生泰斗王金璐传》两本名家传记,并发表评论文章十余篇。 谢柏梁,文学博士 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戏文系主任 北京市特聘教授、市教学名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戏曲艺术当代发展路径研究》首席专家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 国际剧评协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
第一章求学篇 第一节 少小已识愁滋味 1919年11月22日,一条活跃着艺术细胞的小生命 呱呱坠地,降临在北平东珠市口三里河的一个家徒四 壁的贫寒厨行人家。他五官端正,哭声响堂,模样儿 十分喜人,这个取名王庆禄的新生儿就是二十年后声 名四播的著名京剧武生王金璐。 王金璐并非出生在一个盛开艺术花朵的家庭。祖 父是地道的北京人,父亲曾在前门外同兴堂当学徒, 出师后主要为四邻街坊的红白喜事做一些普通的饭菜 ,也为某些体面人家当下厨,但是专为府里下人做饭 ,收入菲薄。母亲操持家务,且替人缝缝补补以维持 一女二男三个孩子的艰难生计。大姐长他十来岁,兄 长比他大两岁,他排行老三。两年后兄弟出世,家境 就变得益发的困苦不堪了。 他们一家六口合住在靠山胡同的一间小破屋里。 靠山胡同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只能走一辆自行车。巷 子倒是挺深,胡同尽头便是他们的家,说是屋子,实 际上是普通住家户的一个外院而已。穷人的邻居也穷 ,但好心肠的人却不少。王家有户近邻是“打鼓儿的 ”,即过去北京收购旧货的,这营生实同捡破烂的无 异,就是这么一家穷户经常在周济着他们。大姐拜了 “打鼓儿的”作干爹,庆福、金璐、庆寿三弟兄也随 同认了干亲,家里总算多了一个生活依傍,才不至于 去乞讨要饭。 王金璐的童年,北洋军阀连年混战,时局动荡。 但政局是政局,百姓是百姓,穷人哪有心思去理会政 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依然是在日继一日地挣扎着求 生存。比他家再穷的恐怕不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是“穷得叮当响,两袖清风,连两裤腿也是清风”。 他落生以后最早记住的一件事便是自家屋小睡不开, 夜里常被带去邻居家借宿。家里的煤球炉是一家子心 目中最宝贵的家产,一天晚间忘了从过道搬回屋内, 第二天发现被人偷走,大姐还心疼得大哭一场,全家 竟是一片愁云。他多么希望能同别人家孩子一样,过 着不饥不寒、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生活的阴影过 早地压在了他稚嫩的心头。 王金璐吃不饱还闲不住,因此终日腹中饥肠辘辘 的躁得难受。家里几乎全年不见白面,能吃上棒子面 和山芋已算不错。金璐食量大,见饭桌上有山芋就抢 ,家人全都让着他,尽管如此,顶多也只能吃个半饱 。他饿急了,便不择手段找饭吃。旧时北平豪门富户 讲排场,红白喜事必铺张一番以炫富贵,娶亲讲究花 红彩车或大红彩轿,死了人要用名贵棺材,棺材不是 用金丝楠木就是阴沉木、杉木做的,十分考究。迎亲 送殡,还要雇上一伙小执事,在前边分成两行沿街而 行,浩浩荡荡,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气派。要是娶亲, 执事一律穿红色号衣;若是出殡,一律穿白孝袍,手 里举一根短白纸条粘成的“雪柳”。为求一饭,小孩 哪顾得拿雪柳的晦气,金璐常是不雇自来的编外执事 ,跟在棺材后面,把死人送进墓地,别人领赏钱,混 在执事队伍里手举白幡的他为的仅是领一碗赏饭。 一家人有了上顿没下顿,心力交瘁的母亲终被生 活重负压垮,从此病势日益加重。在金璐眼中,几乎 从不见母亲有过笑容,笼罩在母亲那张凄苦的脸上的 ,除了愁,还是愁,这个“愁”字,不可能不在少小 的王金璐的心头刻下烙印。毕竟是孩子,童心所使, 他比谁都淘气,凡有他参与的游戏全能让他玩出水平 来。胡同里穷孩子中他是公认的首领,小孩们爱玩的 “拍屁股队”“蹦高”等游戏的冠军非他莫属。实在 闲得没事,他就在胡同里疯跑,常挡了拉洋车的道而 遭骂,于是他便生出捣乱的主意,把破洋铁缸、土簸 箕之类的破烂儿偷着挂在车后的横杆上,一路上哗啦 哗啦乱响一气,存心惹人发火,不等拉车人回头,以 他为首的一帮顽童早已一溜烟地哄笑而散。他另有一 手抓蛐蛐的能耐,手法灵捷异常,出手必有斩获,这 也是童年时代属于他仅有的一点乐趣,可能就在此时 ,冥冥然已注定了他将一辈子与舞拳弄脚的武戏为伴 。 王金璐的戏缘始于干爹家。干哥是前门外广德楼 戏院的茶房,平时常带他去看“蹭戏”,从天桥到前 门,大小戏院都光顾过。父亲也爱看戏,只看比较下 层的“天桥”,相比之下,他比父亲阔多了。王金璐 生性好动,他对武戏最感兴趣,干哥便在家里窗台上 搭了竹竿,让他在竿上攀越翻滚,一来二去的,还真 有几分样儿,这也许就是他接受的最早的京剧基本功 训练了。苦水没有淹没他的聪慧,王金璐学戏似乎有 一种灵性伴随,他的戏缘纯属一种偶然。 干哥见王金璐小有灵气,便建议王母不如让儿子 吃口戏饭。昔时国人向视优伶为贱业,以唱戏为下品 。在清代,娼、优、隶、卒最为人不齿,一戏子的社 会地位连妓女都不如。民国后二十年,唱戏一行比之 晚清虽有改观,可“开口饭”总为人不屑,不少人家 家谱并不显赫,却也看重名望,子弟们听戏消遣纯是 一种雅兴,真的吃这口饭就有辱门庭了,稍有身价者 更鲜入此道。唱戏几乎是穷人家一统天下的“低三品 ”,多为穷人不得已而为之。母亲怎忍心让孩子去挨 打受苦、低三下四,对于哥的建议自然一口拒绝。常 言道“家有三斗粮,不进梨园行”,母亲抵制得十分 坚决,此事便暂时搁起一边。后来,眼看母亲病势沉 重将不久人世,邻居大嫂已在帮着赶缝丧服,姐弟四 人属他最淘气,最让临危的母亲牵肠挂肚割合不下的 就是他。一位大娘不明内情,上前劝慰:“是惦记小 三吧?赶明儿让他学戏去,让你放心。”谁知旧话一 重提,母亲顿时激动起来,胸部剧烈起伏,睁圆了一 对无神的眼睛,苍白的嘴唇哆嗦不止,似有话说却吐 不出一句。突然,她挣扎着抬起一条无力的手臂,在 炕头摸到一只茶碗,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呆立在床前的 王金璐,拼着全身的气力掷了过去。她无力倾述此时 的心情,只能凭此发泄一下心中的凄楚,这是一位母 亲最后的抗拒,痛彻而激烈,然而又显得多么的无力 和无奈,穷人家选择的余地本来就很小很小。明知坐 班学戏如同蹲大狱,破板子打肉,里外是伤,钻进去 就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如今家里生路似乎已到了尽头 ,母亲所有努力就同那只茶碗一样,被摔得粉碎。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