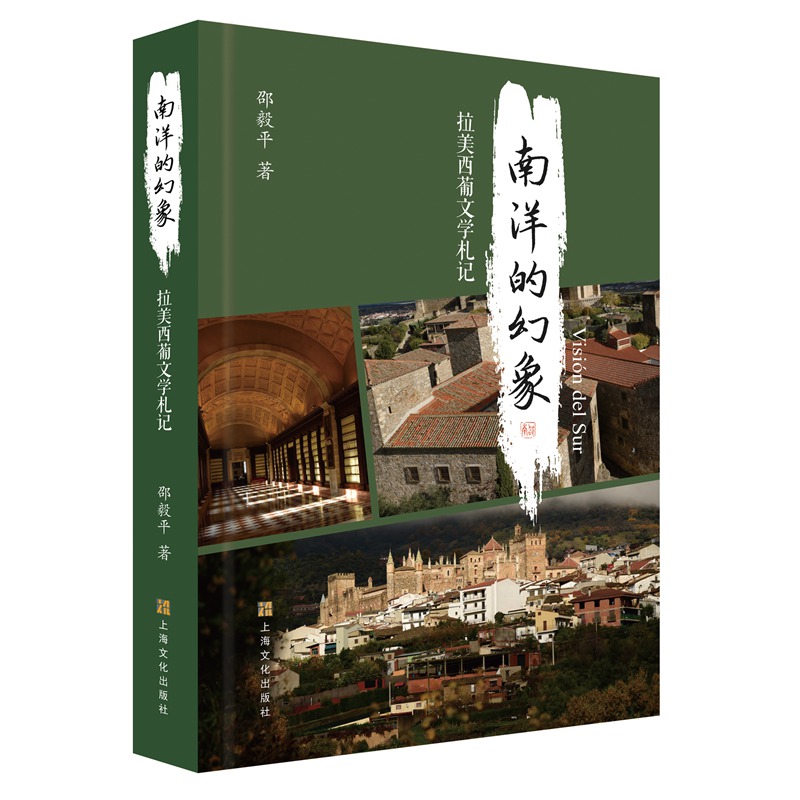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化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1.20
折扣购买: 南洋的幻象:拉美西葡文学札记
ISBN: 978755353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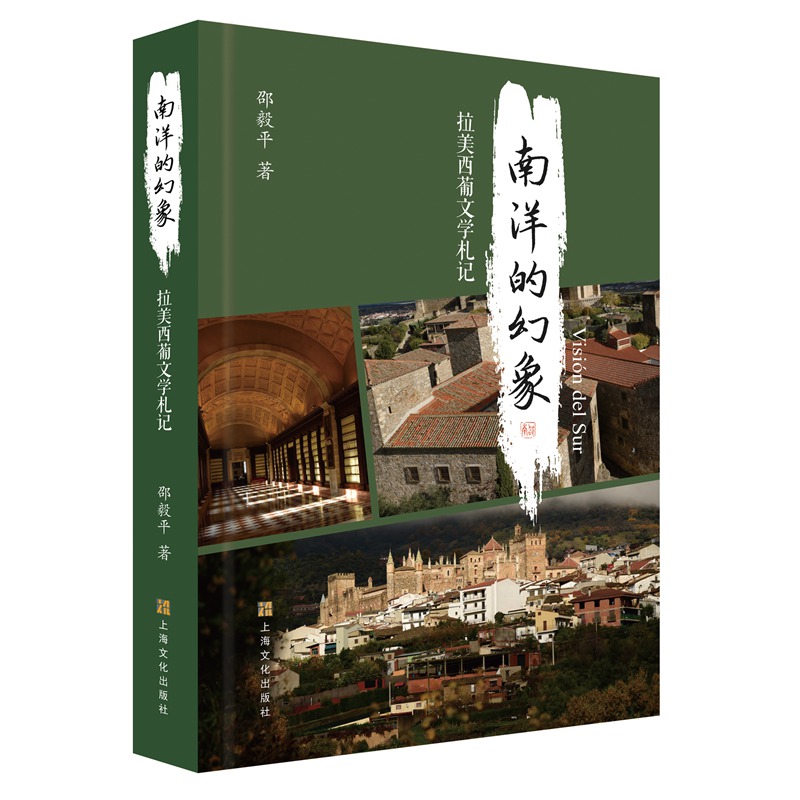
邵毅平,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古典学。著有《论衡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东洋的幻象》《今月集》《远西草》《西洋的幻象》《中西草》《中国文学特别讲义》等廿二种。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活着为了虚构 一 1955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马尔克斯作为《观察家报》特派记者被派往欧洲的前夜,诗人杜兰来到他在波哥大的房间里,为《神话》杂志向他索稿。马尔克斯正好刚把自己的稿子看了一遍,把他认为值得保存的收了起来,把那些没用的都一撕了之。于是杜兰开始在废纸篓里翻找起来,忽然,有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东西太值得拿去发表了!”那是从已出版的《枯枝败叶》(1955)里删下来的一个完整章节,马尔克斯解释说,它最好的去处当然只能是废纸篓了。杜兰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它在《枯枝败叶》里确实显得有点多余,但它独立成篇反而具有了特别的价值。马尔克斯为了让他高兴,同意他把撕碎的稿子用透明胶粘贴起来,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单独发表。“我们给它安个什么题目好呢?”杜兰问。“不知道,因为这只是一篇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马尔克斯回答。于是杜兰在稿子上写下“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这成了它的标题。 “我最受评论界,特别是最受读者们赞誉的短篇小说,就是这样被从废纸篓里挽救出来的。”马尔克斯这样完成了富有戏剧性的叙述。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写作的励志故事,里面有作者对于写作的敬业态度,有好编辑慧眼识货的动人情节,也有一不留神便成功的名作传奇。然后他回到“如何写小说”的主题,告诫年轻作者要严肃认真地写,哪怕一本也卖不出去,哪怕得不到任何奖励;要舍得把不满意的统统撕掉,就像自己以身作则的那样——不,还得吸取自己的教训,把稿子撕得更彻底一些,不让别人把它粘起来:“不过,这一次的经历并没能阻止我继续把自己认为不值得出版的稿子撕掉,反而教会我要撕得彻底一点儿,让人永远不能再把它们粘贴起来。”(《如何写小说》,1984) 过了十八年,在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2002)中,关于《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1955),马尔克斯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诗人杜兰来向我告别时,我正在撕没用的纸。他很好奇地翻垃圾桶,想翻出点儿东西来,登在他的杂志上。他找到三四张拦腰撕开的稿纸,在桌上拼起来读了读,问我是哪儿的文章。我说是从《枯枝败叶》初稿中删掉的《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提醒他已经用过了。这个短篇曾在《纪事》周刊和《观察家报》周日增刊上发表,用的是一模一样的题目。我记得是在电梯里匆忙答应下来的。杜兰并不在意,把它登在了他的下一期《神话》杂志上。”——原来早就有了题目,原来早已发表过了,原来还是一稿多投……美丽神话瞬间破灭。 大约他撰写《如何写小说》的初衷,是要劝年轻作者舍得割爱,以致让他对记忆作了修改,顺便还添加了点文学色彩——正要撕稿的年轻作者们,且慢着下手呵! 其实,真要撕稿,真要撕得彻底一点儿,让人永远不能再把它们粘贴起来,还不如学萨瓦托干脆把稿子直接烧掉,这样更彻底:“我经常会在下午就把上午写的东西烧掉。我就这样看着一篇篇短篇小说、文论作品、戏剧作品被火焰吞噬,这曾经也注定是《英雄与坟墓》的命运——我总是喜欢犹疑。就焚烧手稿的习惯来说,有时我也会感到后悔;我至今仍会怀念某些被烧掉的作品,例如《鸟人》,还有本我在超现实主义时期写的长篇小说,叫《不语泉》……那本书现在幸存的只有几个章节和一些想法了。”(《终了之前》,1998) 关于在《枯枝败叶》初稿中删掉《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那段一事,据《活着为了讲述》说,其实是他在遭遇出版社退稿的打击后新一轮修改的结果:“于是,我以朋友们的意见为基础进行新一轮的修改,删去了女主人公在秋海棠长廊观看下了三日的暴雨那一段——后来被我改写成短篇《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我还删去了香蕉种植园大屠杀前外公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之间一段多余的对话——差不多有三十页,从内容到形式都破坏了小说的整体结构。”由此也再次证明了《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是作者主动改写的产物,而绝非杜兰从废纸篓里翻找抢救出来的;外公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之间一段多余的对话则无此幸运。 但同样是在《如何写小说》中,为了教诲年轻作者要严肃认真地写,马尔克斯还讲了另一件以身作则之事:“那几个短篇已经不成问题:它们都进了垃圾桶。我在不多不少一年之后把它们重读了一遍,从这种有益的距离看去,我敢发誓——也许事实真是如此呢——它们根本就不是我写的东西。它们是过去一个写作计划的组成部分,我本来计划要写六十篇或者更多的短篇小说,来描写居住在欧洲的拉丁美洲人的生活,可它们的主要缺点是根本性的,所以还是撕了为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那里面写的鬼话。”马尔克斯这次说的却完全是实话。 关于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即以六十来个短篇来写居住在欧洲的拉美人的生活,马尔克斯确实有过,也确实没能全部完成。但至少完成了一部分,大约五分之一,那就是《十二个异乡故事》(1992)。在该书的序中,马尔克斯回顾了该书长达十八年的艰难形成史,以及它背后的写作故事。从1974年开始,他在一个学生用的作业本上陆续积累了六十四个素材,以及相关的各种细节,都是发生在旅居欧洲的拉美人身上的奇闻异事。1976年,他完成并发表了其中的两个故事,即《雪地上你的血迹》和《福尔贝斯太太的快乐夏日》。大概因为另两个故事难产了,以致他把这个笔记本遗失了。1978年,他重建了其中三十个素材的笔记,过程之艰辛不亚于把它们写出来。接着,他又狠心剔除了那些他感觉难以处理的素材,最后仅剩下十八个素材,其中的六个写到中途又被他扔进了废纸篓——《如何写小说》中说撕掉的,应该就是这六个故事,幸存的则成了《十二个异乡故事》。“一个好作家被欣赏,更多的是由于他撕毁的东西而非他发表的。”(《十二个异乡故事》序)《十二个异乡故事》十八年的艰难形成史及其背后的写作故事,的确证实了马尔克斯对待写作严肃认真的敬业态度,与他关于《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的传奇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十二个异乡故事》的形成史其实还远不止十八年,在1971年6月3日的一次访谈中马尔克斯就已经提及:“我有一个笔记本,我把想到的故事草草记在里面,为它们做笔记。我已经有了六十个左右的故事,我的设想是要达到一百个。”(《马尔克斯访谈录》,2006)他还介绍了其中的七号故事“淹死在灯光中的孩子们”是怎么来的,二十一年后,它以“光恰似水”为题收入了《十二个异乡故事》中。由此可见,《十二个异乡故事》的形成史至少还得提早三年。 有关马尔克斯的毁稿传奇,甚至从他文学生涯的开端一直延续到了他的身后。最近刚出版的他的遗作《我们八月见》(2024),据其儿子罗德里戈和贡萨洛说:“当年,我们只知道加博做出的最终判决:‘这书不行,得把它毁了。’”但他们没有遵从父亲的判决,最终还是同意把它出版了:“我们没有把书稿毁掉,而是将它放到一边,希望时间能帮助我们决定最终如何处理它。在父亲去世近十年之后,我们再次阅读了这份手稿,发现它其实有许多令人愉悦的优点……我们认为这本书比记忆中的样子好得多,因此突然想到另一种可能性:当年加博失去了完成此书的能力,那么他是否也失去了察觉此书之美的能力?于是我们决定违背他的意愿,优先考虑读者的愉悦。如果读者喜欢这本书,也许加博会原谅我们。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我们八月见》前言)我们终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还是得到了父亲的一脉真传?也许是他们父子齐心协力,制造了一个新的毁稿传奇? (节选自《活着为了虚构》) 《南洋的幻象:拉美西葡文学札记》是邵毅平教授集中研读拉美西葡文学后写的读书笔记。经历了上世纪拉美的“文学爆炸”以后,世界文学的版图早已被改写,马尔克斯、略萨、博尔赫斯等作家成为文学形式的革新者,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学爱好者。作者以个人独特的视角、思考、文笔,展现这个令人震撼的文学时代与极具个性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