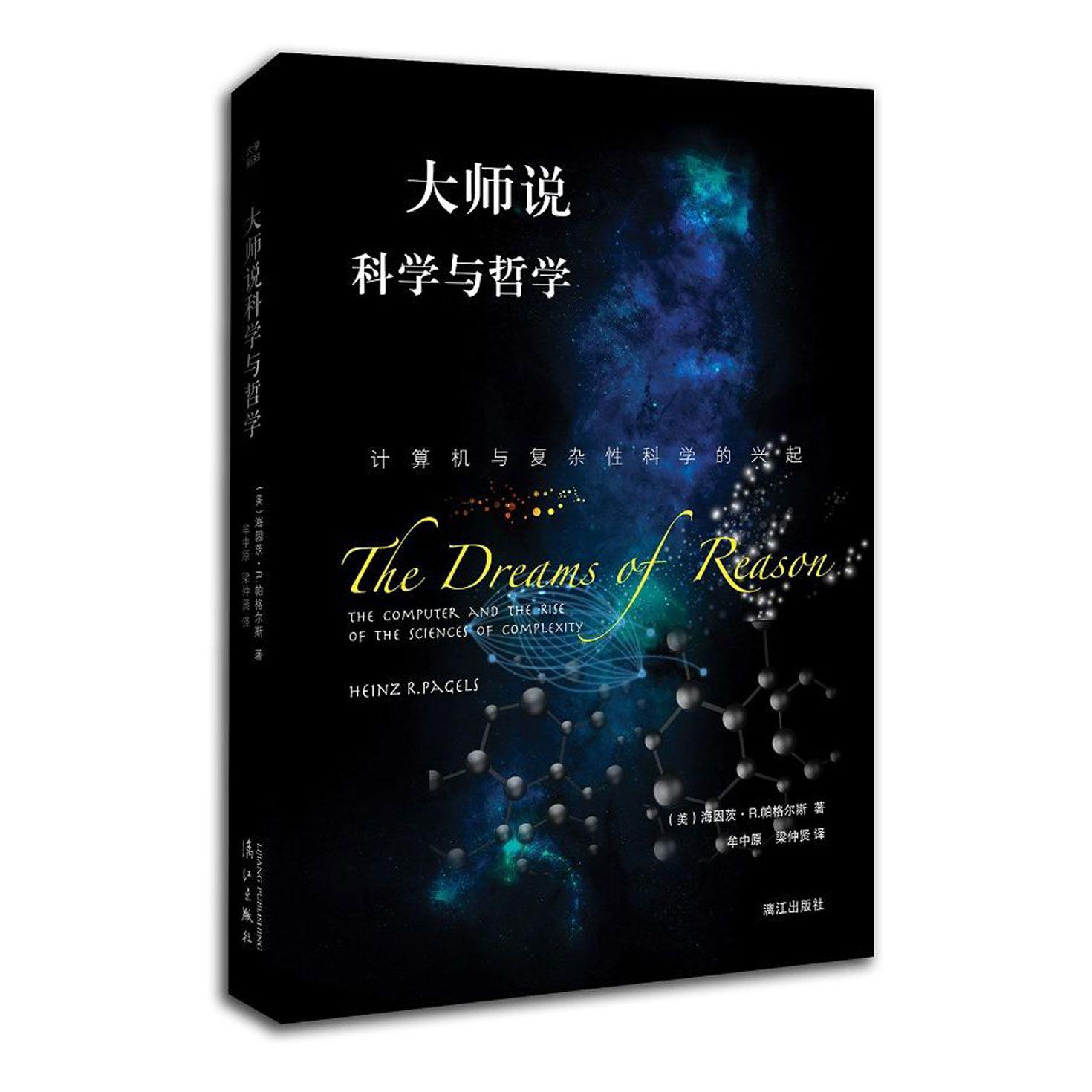
出版社: 漓江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7.00
折扣购买: 大师说科学与哲学(计算机与复杂性科学的兴起)
ISBN: 9787540779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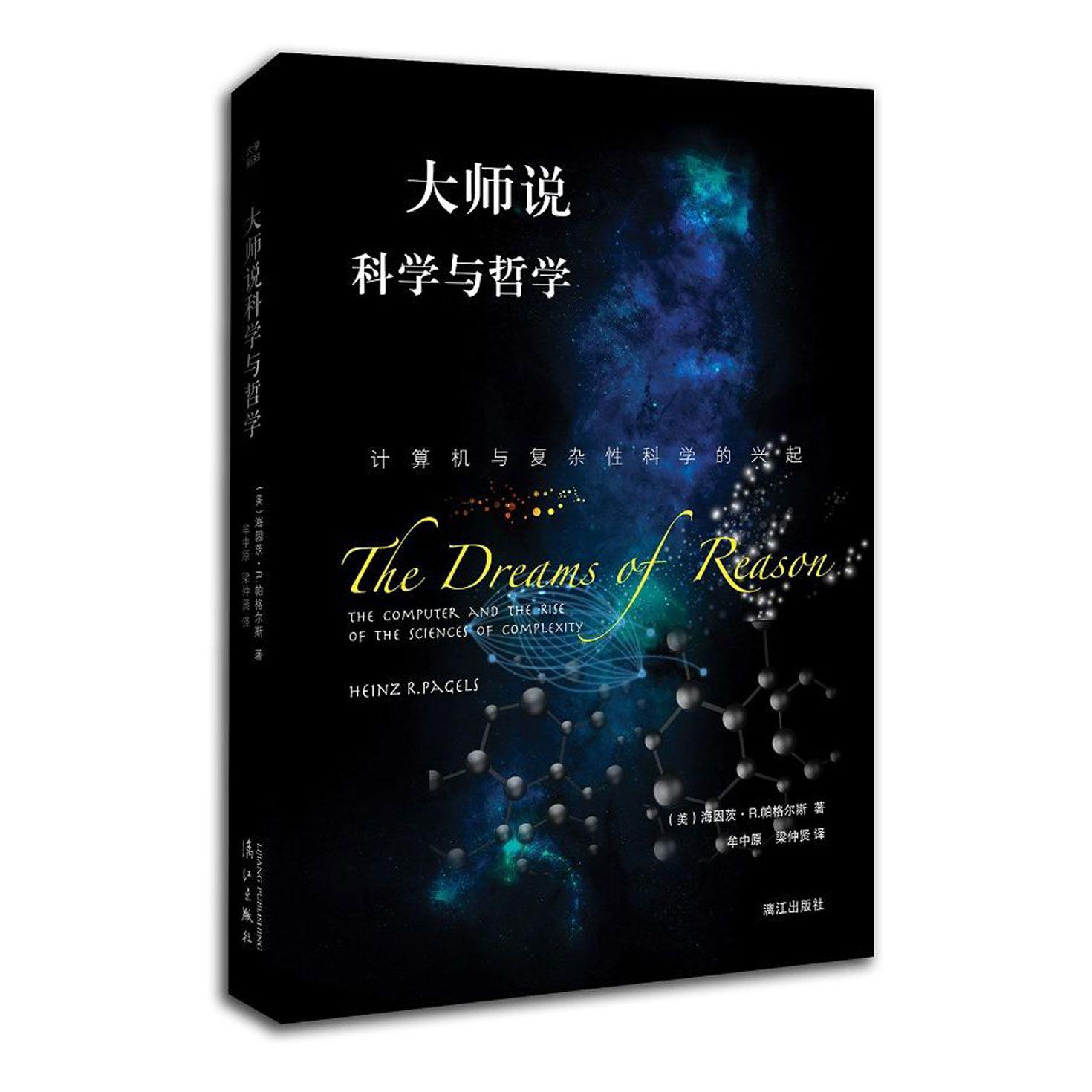
梁忠贤,出生于台湾新竹,台湾成功大学化学系毕业,台湾清华大学化学硕士、台湾大学化学博士。 牟中原,出生于台湾基隆,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化学博士,台湾大学教授。曾获世界科学院“化学奖”。研究领域包括:纳米材料、界面化学、催化等。 著有学术研究论文约四百篇、专著《原住民教育》《物理化学实验》;译有《大师说科学与哲学》《氢弹之父:沙卡洛夫回忆录1921~1967》《人权斗士:沙卡洛夫回忆录1968~1989》《周期表》。 海因茨·R.帕格尔斯(Heinz R.Pagels),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兼科学作家。曾任洛克菲勒大学副教授、纽约科学院执行董事兼执行长。除了科学家的身份,海因茨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关心人权议题;曾任纽约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评议委员,试图使科学与人文不再有隔阂。海因茨的天赋在于能用简单的表达解释艰涩概念。 著作包括《宇宙密码》(The Cosmic Code)、《完美对称》(Perfect Symmetry),皆获科学界一致赞赏。《大师说科学与哲学》则将科学讨论带往更高层次,除了预言复杂性科学对人类的影响,也讨论了分道扬镳的科学与哲学如何才能重新融合。 海因茨于1998年夏天,在前往阿斯本物理中心的路上遭遇山难,英年早逝,而其留世的《大师说科学与哲学》,仍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成为不朽之作。
第1章 美丽的大苏尔、塞尚的苹果 阴茎勃起时,理性便从窗口溜走。 ——摘自哈钦斯(Robert M.Hutchins)的幽默 剧《笨瓜》(Zuckerkandl) 美国加州坐落在两大地壳板块之间,地质变动剧 烈,虽然目前地壳相当稳定,却只是暂时的。事实上 ,太平洋板块正沿着圣安德烈亚斯断层、紧挨着北美 大陆板块往北滑,最后在阿留申群岛附近深入地球熔 岩之中。 加州地层的活跃,使得陆地与海洋间出现剧烈的 冲突.是我生平仅见,尤其在莫罗贝之北、卡梅尔市 之南的大苏尔(Big Sur)一带最为明显。这儿,圣卢 西亚岭直逼海洋,千尺悬崖对着大海的惊涛骇浪。 大苏尔是个原始而美丽的地方,迷人之处在于它 的阳光——在冬天和有雾的清晨阳光幽幽散射,夏日 午后则澄澈明亮。山坡干燥的草皮在艳阳下呈金黄色 ,阴凉的森林满布杉柏、松树、橡树、红杉以及野生 动物,海岸外是绵延的海藻床,沉浮在海浪中。岩岸 间,偶尔夹着沙滩,其间充满各种海洋生物:寄居蟹 、海星、海胆和鲍鱼。海鸥和鹈鹕安详地翱翔着,似 乎没有进化这回事,鸬鹚则在岸边等着浮游生物吸引 过来的鱼儿。 那里唯一的人造物是一号海岸公路,它是由一群 囚犯在1930年代建造的。原本只有牧人的地方,因为 这条公路而出现了人潮,其中多数是艺术家和流浪者 。有一些旅馆和餐馆坐落其间,但大苏尔的孤立,以 及冷寂的冬天和欠缺的工作机会,使那儿迟迟没有得 到开发。 在东部长大的我,于1960年代来斯坦福大学读物 理研究所以前,从没听说过大苏尔。那时我年方二十 一,像我那样年纪的研究生常在学生活动中心门口的 喷泉边流连,希望交到朋友。在那儿,我遇见了哈尔 ,他自陆军情报局退役以后,就成了老学生。哈尔是 第二代的加州人,祖先是爱尔兰人,他黑发、碧眼, 皮肤晒得很黑,跟许多爱尔兰诗人一样,是个叛逆的 冒险者。 他对大苏尔区很熟,有次他邀我一起去那儿度个 长周末。他有几辆自己改装的大众甲壳虫轿车,其中 一辆把车顶切了,在切口处加上木条,然后为车装上 强力的保时捷引擎,看来活像装了轮子的澡缸——好 快的澡缸!我们就坐着这辆澡缸上路去。 我们走的是一条小道(哈尔似乎知道所有的路), 穿过向日葵田,海水的咸味飘浮在空气中。在蒙特雷 湾,我们花了整个早上探看那些老制罐厂,它们生产 的鱼罐头曾喂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人!功 成身退之后,就被废弃在那儿任海浪侵蚀。这儿是小 说家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家乡,一个人吃人 、聚集失败者的地方(拜斯坦贝克小说之赐,现在有 些制罐厂被整修后成了观光中心)。 哈尔认识一些意大利渔夫,他们还记得湾里充满 鱼虾的光景。在那些日子里,当地餐厅的海鲜都是由 他们供货的。 我在哪里? 经过蒙特雷湾之后,我们从一号公路经过卡梅尔 、洛沃斯角.通过苏尔岬的灯塔,直入圣卢西亚岭, 海浪在悬崖下不断拍打着。四周出奇地安静,我们好 像跨过了门槛,回到了原始时代。但是。我在哪里? 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曾 说:“生命的无奈,在于走过方知来时路。”回想起 来,在我生命中的那段时光,走访大苏尔是很有意义 的——自然的力量激发我思考自己的存在。 我那时是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口若悬河,对人 类充满希望。而在研究所,我攻读最具挑战性的高能 物理和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除了研 究物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可做。像其他在战后 富裕中成长的一代一样,金钱对我来说似乎没什么必 要,也没有多大意思,我要追寻的是:智识理念、解 决问题和名声。 那时候,西岸的大学从东岸争聘了许多名教授。 斯坦福大学正计划建造巨型线性加速器(linear accelerator),将电子加速撞向约3.2千米外的靶子 。在那儿,物理学家将要发现核子的组成粒子——夸 克(quark);另一方面,生物学家专注于解出遗传密 码.进行着生命问题的基本研究;心理学家则正拓展 认知的新领域: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也诞生了 ;而电机工程师正深入电子控制与信息系统的理论。 1950年代末期,活力四射的校长特曼(Fred Terman)争取到修改法令,使大学也能租地皮设立工 业区,那就是硅谷的前身。他使得技术界和财经界的 关系日益密切,促成了斯坦福附近的高科技发展。在 圣克拉拉,他们砍掉杏树来建房子和办公室。一场将 改变都市人口、经济力量、战争方式、就业形态的计 算机革命即将爆发。 除了理论物理,我也被其他智识,例如哲学和艺 术所吸引。我开始学画,尝试弄清楚画家都在做些什 么,也想改变我的视觉感受和习惯。在所有的画家之 中,塞尚(Paul Cezanne)最早让我了解了用不同的方 法去看这个世界,而人类的视觉经验往往是文化的产 物。 一位叫凯彻姆的朋友,经常在家里举行艺术和哲 学讨论会。在那儿,我开始读康德和胡塞尔(Edmund Hussel)。从室友和同学那儿,我学到计量经济学、 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在学校里,我旁听一些课程 (为兴趣,而不是为学分)。记得有一门课,分析哲学 家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对一群大学生解释塔斯 基(Alffed Tarski)有关真理的语法观念。我们分析 的是这样的句子:“雪是白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真理的语法观念,也没搞懂 语言哲学的多层次真实意义。不过,这并不是哲学老 师的错。 我猜我是学了太多物理,以至毁了我的哲学灵气 。物理太讲实际了,物理学家常很快区分出物理和数 学。数学是研究物理的语言形式,那些着迷于数学之 美而不见事物之理的理论物理学家,总使我想到那些 忽略了语言到底在描述什么事物的语言哲学家。每当 我问起到底语言哲学家在做些什么时。我得到的回答 使我相信他们和语言学家做一样的事——了解怎么用 字。 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