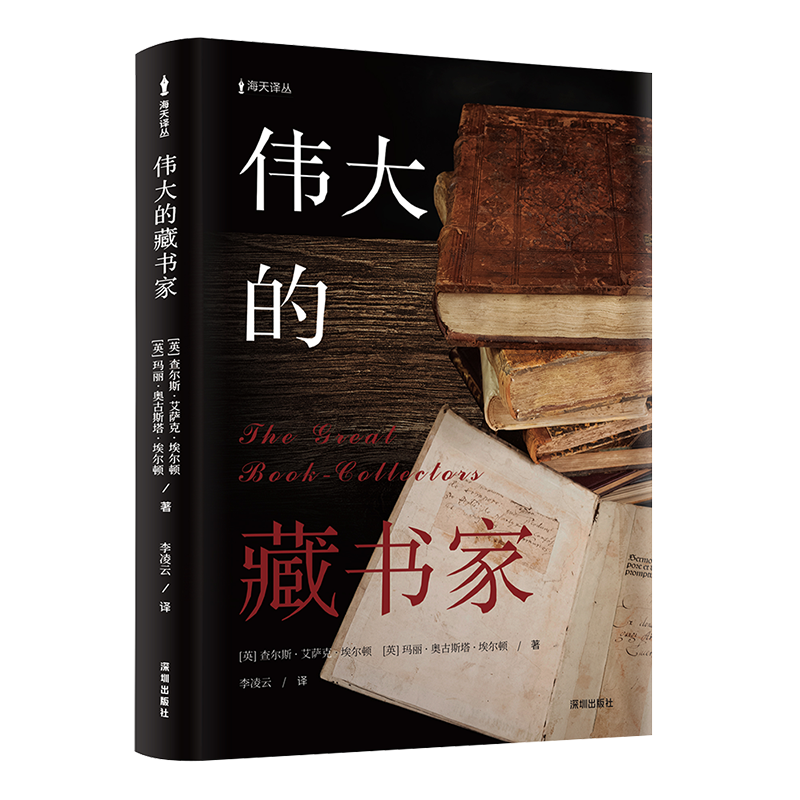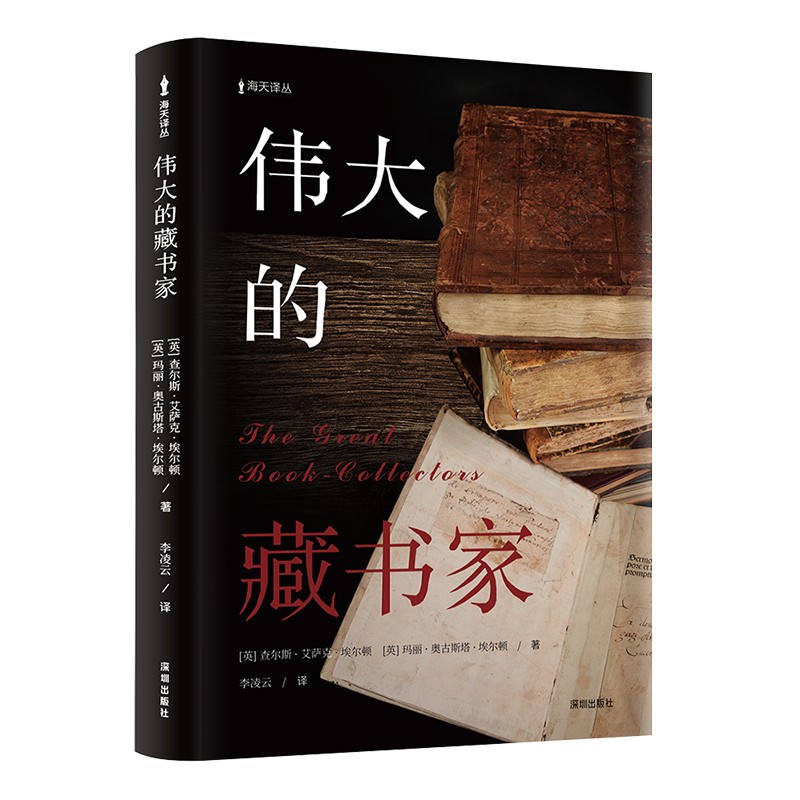
出版社: 深圳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2.90
折扣购买: 伟大的藏书家
ISBN: 9787550739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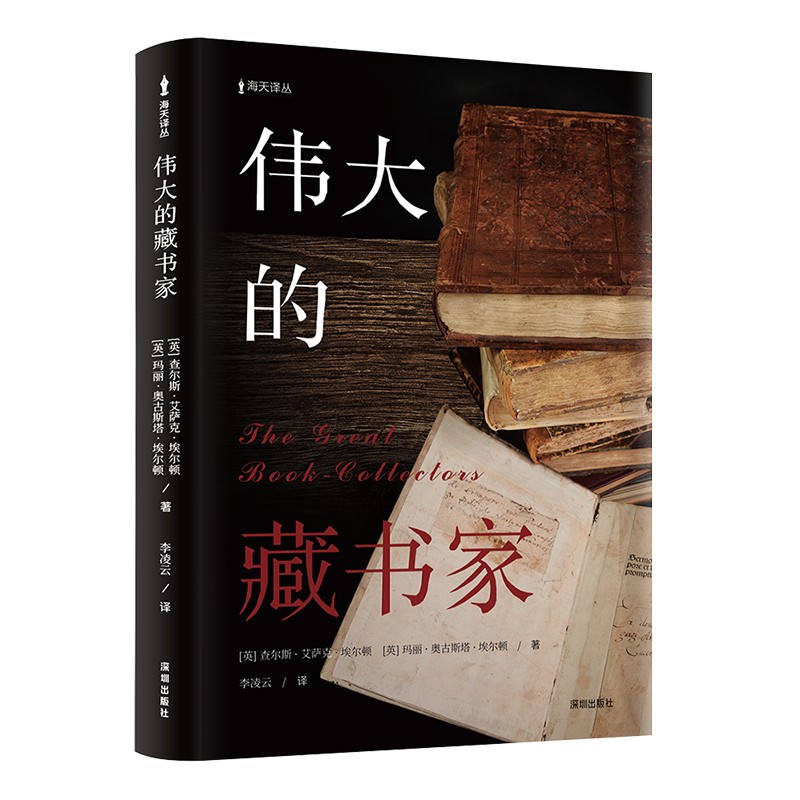
查尔斯,艾萨克·埃尔顿 (CharlesIsaac Elton,1839一1900),英国律师、古董商、政治家和作家。平生著述颇丰,著有《伟大的藏书家》《肯特时期》《公地与荒地论》《副本土地所有权法》《英国历史起源》《习惯法和承租人权利》《威廉·莎士比亚、他的家人和朋友》等。 玛丽·奥古斯塔·埃尔顿(MaryAugusta Elton,1838一1914),出身于英国贵族斯特拉奇家族,著名的女性藏书家,与丈夫查尔斯 ·艾萨克·埃尔顿共同撰写了畅销一时的《伟大的藏书家》。 译者: 李凌云,文字工作者,译有《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艺术中的灰姑娘》等。
愚昧年代的启蒙非个人之力所能为之。公正地说,中世纪的黑暗渐渐消退时,有一人恰好伫立前方,正是被誉为“时代先驱”(the harbinger of day) 的彼特拉克。他的名声,除了来自他创作的那些抒情诗,更源自他在启蒙教化同胞方面的不懈努力。彼特拉克自幼酷爱书籍,青年时代在阿维尼翁附近“多风的罗讷河(Rh?ne)”畔度过,先是接受语法和修辞教育,后至蒙彼利埃(Montpellier)学习四年,再前往博洛尼亚(Bologna)研习法律。他在回忆这段生涯时说:“余研习民法课已有数学期,颇有收益,然终自作主张放弃这一学科,并非厌学,实因这一饱含古罗马智慧精华之思想学说,常被心怀叵测之人恶意曲解。”有段时间,他在好友、法学家和诗人皮斯托亚的奇诺(Cino of Pistoia)手下做事,还旁听过法学家安德烈(Andrea)的课。相传安德烈的女儿诺薇拉(Novella)偶尔在父亲缺席时代课,“以面纱遮住美丽的面庞”。还在博洛尼亚读书时,彼特拉克就开始藏书,老父亲某次来探望,见此情景,盛怒之下,将那些羊皮书一股脑地扔到火堆里。年轻人又是哀求,又是发誓,才使其余书籍免于劫难。他虽努力遵从父命,结果却总是徒劳,天性引导他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而与天性作对往往劳而无功。 彼特拉克后来返回阿维尼翁,得到红衣主教斯蒂凡诺·科隆那(Stefano Colonna)的赏识。正是在阿维尼翁,他初次目睹劳拉(Laura)芳容,“一袭绿色长裙,上面绣着紫罗兰”。劳拉的倩影深深镌刻于他的脑海,令他心潮难平。或许正因对劳拉的长久迷恋,彼特拉克才跻身抒情诗人之列,并在罗马受封“桂冠诗人”。自此,他便全身心投入文学事业。彼特拉克自称患上了写作病,此病在那年头倒也广为流行:“人人皆热衷写作,而写作本应是少数人之行为。罹病者越来越多,病情亦日渐恶化。”身为躁狂症患者,彼特拉克曾自嘲不如当个苦力或者织布机上的织工,“抑郁症有几种,有的疯子会写书,有人则不停地将手里的石子扔出去”。至于写作带来的文学声名,则如稀薄的空气,水手在海上遇此情景,也只能静候来风(watch a breeze)或吹哨唤风(whistel for a wind)方可行船。 彼特拉克曾到欧洲许多地方淘书。1329 年,他正好二十五岁,经瑞士到佛兰德斯游历。这一带的大学历史悠久,但自从巴黎大学兴起后,就只能屈居其下。好书依旧保存在修道院中,劳贝斯修道院(Abbey of Laubes)里有关《圣经》注解的书尤为丰富,但不幸毁于大火,仅一本8世纪的拉丁文通用《圣经》,恰因被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借用而幸免于难。彼特拉克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他在列日(Liège)的经历:“此间藏书甚多,余游说众人延宕时日,直待与同僚将发现的一本西塞罗演讲稿抄写完毕。此地甚美,却被野蛮人盘踞,墨水极难得,故所抄字迹皆为藏红花那样的橘黄色。” 几年后,他从阿维尼翁来到巴黎,为学生宿舍区密如蛛网、肮脏不堪的小巷所震惊。这位旅行者宣称,除了阿维尼翁“这个世界的水槽”,他还未见过比巴黎更脏之地。但这里却是书的天堂,所有的书都依照学校规定平价出售。回到罗马后,他目睹众多书籍珍宝沦为外国人的猎物,那些曾因哥特人、汪达尔人(Vandals)网开一面而躲过浩劫的书,却被英国和法国的商人成批运出意大利,“诸君竟不以为耻乎”?他对着罗马的朋友大声疾呼:“皆因尔等贪婪,竟致吾国古老庄严的历史文物落入外人之手。” 说实话,彼特拉克这位看守实在粗心,他随时准备将书借给旁人,某次慷慨之举竟导致学术史上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他有一本西塞罗的著作,乃海内孤本,本待被人誊抄,却阴差阳错地借给一位老学究,不知何时被此人抵押出去,竟至下落不明,踪影皆无。 节选二 约翰·斯通是历史学家和文物学家,他在极度贫困中死去,实际上有很多年,他都过着拥有执照的乞丐生活。他年轻时曾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的保护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图书馆之外另起一座精美藏书楼。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宗教迫害中,他因藏有罗马天主教的出版物残片几乎被处以叛国罪,而且他发现很难让冷冰冰的审讯官相信自己只是个与世无争的收藏家。议员西蒙兹·迪维斯从政之余,还是文物学家,他效仿德图,立下遗嘱,将平生所藏珍贵书籍留给儿子,遗嘱写得情真意切:“留给阿德里安·迪维斯(Adrian D’ Ewes),我年幼的儿子,他至今还在摇篮中。”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努力保护这些藏书以使其完整无失,尽管有各种约定和罚金,他终究未偿所愿。牛津伯爵罗伯特·哈利曾建议安妮女王(Queen Anne)购买一批有很多珍贵文件和记录的收藏,被女王拒绝。女王声言,当人民的生命和荣誉在战争中受到威胁的时候,身为国王,在未能保证人民享有崇高的和平之前,她不能将国民的财富花费在这些无生命的信件上。于是,我们后来都知道,伯爵只得自掏腰包,花六千英镑将这批收藏买下来。彼得·勒尼夫毕生都在收集有关盾形纹章和家谱的文件典籍,他本打算供其同僚即那些纹章官员所用,但他后来与纹章院产生过节,遂把这些纹章从书上剪下来,余者皆送至拍卖行,“牛津伯爵在那里大肆扫荡”,欧戴斯写道。而对于约翰·白福德这位书籍克星,我们实在找不到太多理由为他辩护,他因编纂一本关于印刷术历史的书,竟对25000 本书痛下狠手,将书上的标题页和版权页撕去,将书边裁掉,即使如《古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和红衣主教希梅内兹(Ximénes)的《多语种圣经》(Polyglot Bible)这样价值连城的书籍珍品,都难逃其魔掌。后人指控他为学术魔鬼,同时代的人却视其为学术奇才。白福德对书籍的蹂躏并未使他致富,他不得不远到荷兰和德国寻找买主,并在那里寻得若干珍贵民谣。有些人为白福德的行为辩护,认为此一时彼一时,今时的消遣地,或成他日的屠宰场,小吉丁(Little Gidding)的费拉尔(Ferrar)家族即是一例。这个擅长书籍装帧的家族曾被视为“裱糊印刷”(pasting -printing)的发明者,他们以此称呼自己那野蛮的装帧:把一本书中的插图剪下插入另一本书中,或者用其他书上的插图和书页把一本书的篇幅拉长。这种装帧做法曾受到查理一世的褒扬,称费拉尔家献给他的那本以碎片装帧的书籍为“书中之王”,“乃人们目之所见盖世无双之杰作”。后代大藏书家迪布丁也认为这种装帧“实用且令人愉悦”。而到了今日,这种对书籍的破坏自然受到许多爱书人的口诛笔伐。 1. 一部图文并茂的传记体通俗藏书史:百余幅手抄本插图和名人画像,呈现不同时代的藏书狂热和文化现象。 2. 一部藏书家轶事集:公元前1世纪到18世纪的著名藏书家,均有露面,比如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彼得拉克,蒙田,博德利…… 3. 一部书籍兴衰史:借由藏书和藏书家这一特殊群体,展示西方书籍的制作、印刷、流转以及学术演变。 4. 《伟大的藏书家》在19世纪畅销一时,被译为多种语言,中文版首次面世,带来一场惊喜重重的跨文化时空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