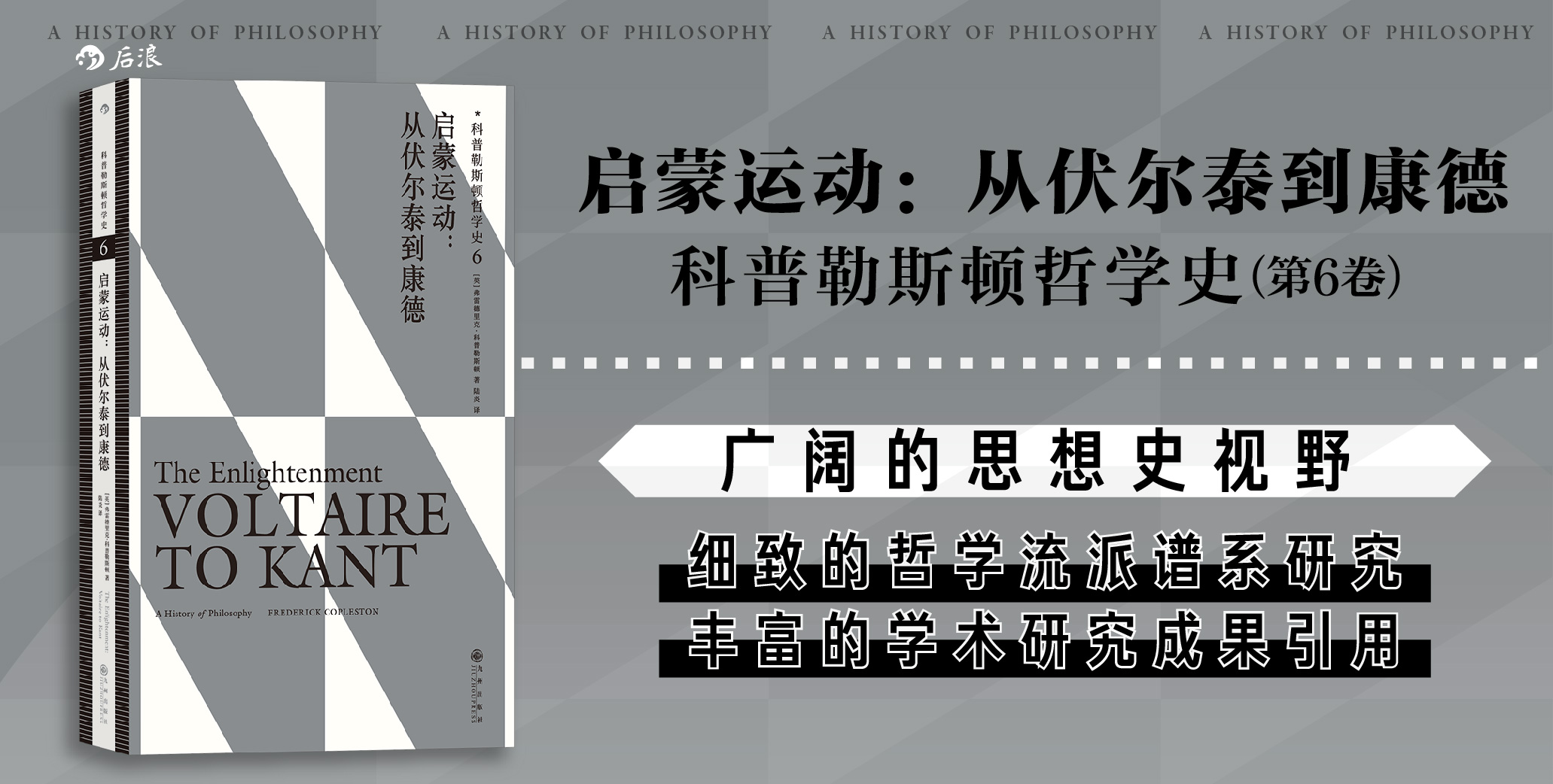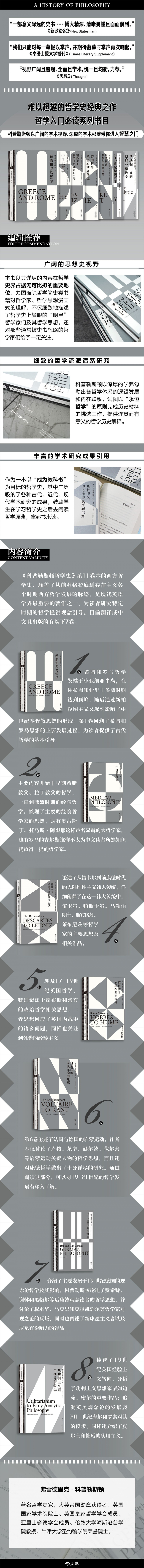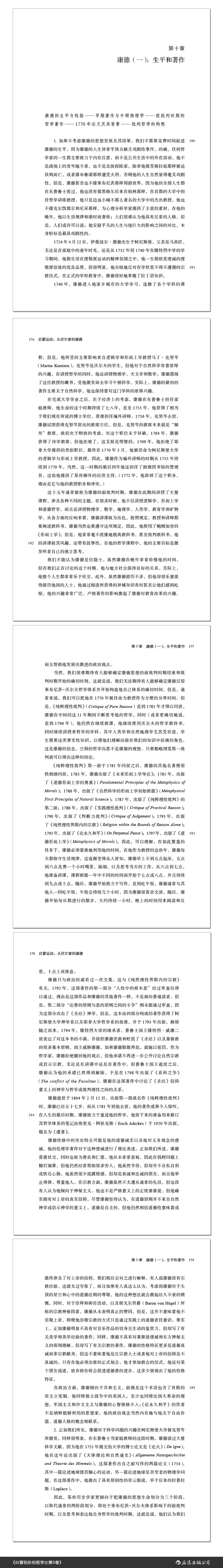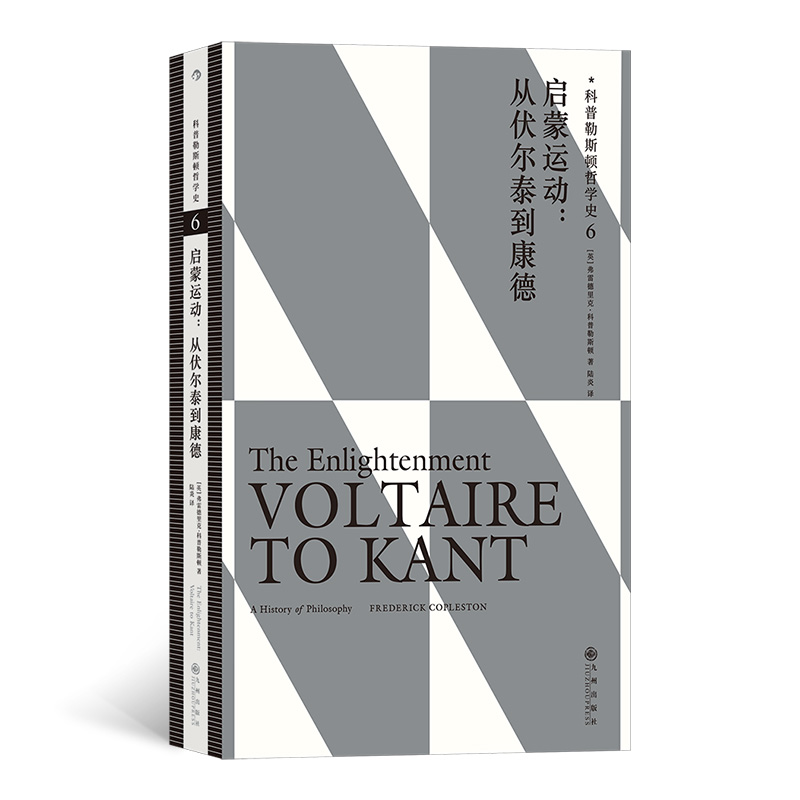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82.00
折扣价: 52.50
折扣购买: 科普勒斯顿哲学史.6,启蒙运动:从伏尔泰到康德
ISBN: 9787522516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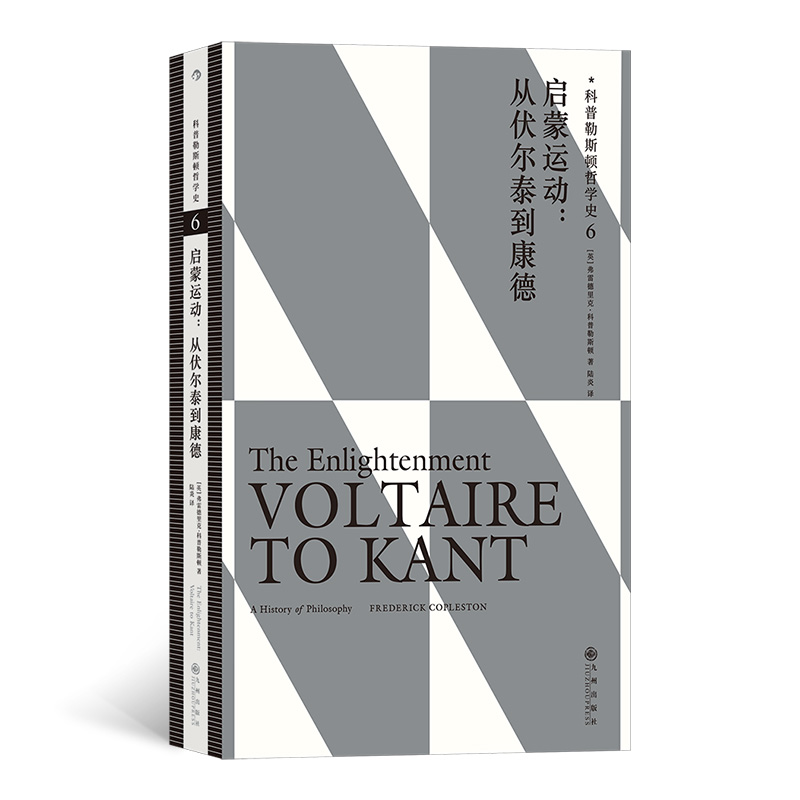
★著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科普勒斯顿,著名哲学史家,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国皇家哲学学会成员、亚里士多德学会成员、伦敦大学海斯洛普学院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院士。 ★译者简介 陆炎,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及其古代注疏传统和18世纪哲学,关注问题主要涉及形而上学、哲学心理学和道德哲学。发表译著和论文若干。
第十章 康德(一):生平和著作 康德的生平与性格——早期著作与牛顿物理学——前批判时期的 哲学著作——1770 年论文及其背景——批判哲学的构想 1.如果不考虑康德的思想发展及其结果,我们不需要花费时间叙述康德的生平。因为康德的人生异常平淡且缺乏戏剧性事件。的确,任何哲学家的一生都主要致力于内在反思,而不是公共生活中的外在活动。他不是战场上的发号施令者,也不是北极探险家。除非他像苏格拉底那样被迫饮鸩而亡,或者像布鲁诺那样遭受火刑,否则他的人生自然显得毫无戏剧 性。但是,康德甚至也不像莱布尼茨那样周游世界。因为他的全部人生都在东普鲁士度过。他也没有像黑格尔后来在柏林那样,在首都的大学中担任哲学讲席教授。他只是边远小城不那么著名的大学中的杰出教授。他也不像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样,为心理分析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他的晚年,他以生活规律和准时而著称;人们很难认为他具有反常的人格。但 是,人们或许可以说:他安稳平凡的人生与他巨大的影响之间的对比,本身恰好是最具戏剧性的。如果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艺复兴与后文艺复兴哲学家的观点在它们表面的价值上被普遍地接受,那么这种情况部分地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在中世纪确实没有什么东西能称得上哲学。事实上,曾经在古希腊熊熊燃烧的带着独立性与创造性的哲学反思之火焰一度熄灭了,直到文艺复兴时才再次燃起,并在17世纪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1724年4月22日,伊曼纽尔·康德出生于柯尼斯堡,父亲是马具匠。无论是在家庭中的童年时光,还是从1732年到1740年在腓特烈中学的学习期间,他都生活在虔敬派运动的精神氛围之中。他一生都欣赏虔诚的虔敬派信徒的优良品质,但很明显,他尖锐地反对在学校里不得不遵循的宗教仪式。在正式的学校教育中,康德很好地掌握了拉丁语知识。 1740年,康德进入他家乡城市的大学学习,选修了各个学科的课程。但是,他所受的主要影响来自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马丁·克努岑(Martin Knutzen)。克努岑是沃尔夫的学生,但他对于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讲授哲学的同时,他还讲授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康德借阅了这位教授的藏书,受他激发而去学习牛顿科学。实际上,康德的最初的著作主要关于自然科学,他也保持着对这门学科的浓厚兴趣。 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康德在东普鲁士担任家庭教师,他生命的这个时期持续了七八年,直至1755年,他获得了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博士学位,获准担任编外讲师。1756年,克努岑去世,康德试图获得克努岑留出的教席空位。但是,克努岑的教席本来就是“额外”教席,政府出于财政的考虑,对这个职位未予补缺。1764年,康德获得了诗学教席,但他拒绝了,这无疑是明智的。1769年,他拒绝了耶拿大学提供的类似职位。最终在1770年3月,他被任命为柯尼斯堡大学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因此,康德作为编外讲师的时期从1755年持续到1770年,当然,这一时期的最后四年他还担任了助理图书馆的管理员,这给他提供了某些额外的经济支持。(1772年,他辞掉了这个职务,理由是它与他的教授职务相冲突。) 这十五年通常被称为康德的前批判时期。康德在此期间讲授了大量课程,涉及各种不同的主题。在很多时候,他不仅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而且还讲授物理学、数学、地理学、人类学、教育学和矿物学。从各方面的反响来看,康德讲课极为出色。按照规定,教授和讲师都要阐述教科书,康德当然也要遵守这项规定。因此,他使用了鲍姆加登的《形而上学》。但是,他常常毫不犹豫地脱离教科书,甚至批判教科书,他的讲课极其风趣,还带有故事性。在他的哲学课程中,他的主要目标是激发听者自己的独立思考。 我们不能认为康德是位隐士。虽然康德在晚年非常珍惜他的时间,但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时期,他与地方社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实际上,他整个人生都非常乐于社交。此外,虽然康德游历不多,但他却很乐意接待游历他国的人士,他通过阅读所获得的异域知识有时甚至让他们感到吃惊。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卢梭著作的影响激起了康德对教育改革的兴趣,而且帮助他发展出激进的政治观点。 当然,我们很难期待有人能够确定康德思想的前批判时期结束和批判时期开始的确切时刻。这就是说,我们无法期待有人能够确定康德反驳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并开始构造他自己体系的确切时间。但是,通常来说,我们可以把他在1770年被任命为教授作为方便的分界时间。但是,《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直到1781年才得以问世。康德在中间的这11年期间不断思考他的哲学。同时(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到1796年),他仍然在继续教课。他继续使用沃尔夫的哲学教科书,同时继续讲授非哲学的学科,其中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尤其受欢迎。学生需要这类事实性知识,以便他们理解经验在我们的知识中扮演的角色,这是康德的信念。空洞的哲学沉思不是康德的理想,只要粗略浏览第一批判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于1781年问世之后,康德的其他名著便很快相继问世。1783 年,康德出版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5年,出版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1786年,出版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Metaphysical First Principles of Natural Science);1787年,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1788年,出版了《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1790年,出版了《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1793年,出版了《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 Alone);1795年,出版了《论永久和平》(On Perpetual Peace);1797年,出版了《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Morals)。因此,可以理解,在如此繁重的任务下,康德必须紧凑地利用他的时间。在他作为教授的这些年,康德每天都恪守生活规律,这逐渐变得众人皆知。康德早上不到五点起床,五点到六点花费一个小时喝茶、抽烟,以及思考当天的工作。从六点到七点,他准备讲课,课程根据一年中不同的时间而开始于七点或八点,并且持续到九点或十点。随后,康德开始致力于写作,直到吃午饭。康德通常与其他人一同吃午饭,午饭会持续几个小时,因为康德很喜欢交谈。随后,康德开始每日都进行的散步,大约持续一小时。晚上的时间用来阅读和反思,十点上床休息。 康德只与政治权威有过一次交集,这与《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有关。1792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人性中的根本恶”经过审查后得以通过,理由是这部作品和康德的其他著作一样,不是面向普通读者。但是,第二部分“论善的原则与恶的原则之间的斗争”则未能通过审查,因为这部分攻击了《圣经》神学。但是,这本由四部分构成的著作获得了柯尼斯堡大学神学系以及耶拿大学哲学系的批准,并于1793年出版。麻烦随之而来。1794年,腓特烈大帝的继承者,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表达了对这本书的不满,并指控康德歪曲和贬低了《圣经》以及基督教的很多基本原则。国王威胁康德,如果康德胆敢再犯,就施以惩罚。作为哲学家,康德拒绝撤回他的观点,但他承诺不再进一步公开讨论自然宗教或启示宗教,无论是在讲课中还是在著作中。但普鲁士国王逝世之后,康德认为他的承诺已然得到解除,于是在1798年出版了《系科之争》(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康德在这部著作中讨论了《圣经》信仰意义上的神学与哲学或批判理性之间的关系。 康德逝世于1804年2月12日。出版第一部成名作《纯粹理性批判》时,康德已经五十七岁,而从1781年到他去世,他的著作成果令人惊叹。在人生的最后时期,康德致力于重述他的哲学,他留下来的准备用来修订其哲学体系的笔记由埃里克·阿狄克斯(Erich Adickes)于1920年出版,题名为《遗著》。 康德性格中的突出特点可能是他的道德诚实以及他对义务观念的虔诚,他的伦理学著作对于这种虔诚进行了理论表述。正如我们所述,康德喜爱社交,同时也极为善良和仁慈。他从未非常富裕,因此在钱财问题上精打细算,但他仍然经常帮助很多穷人。他虽然节俭,但却并不自私自利或铁石心肠。他虽然很少流露情感,但却是真诚和忠诚的朋友,而且他举止得体,尊重他人。在宗教方面,康德虽然不太遵从通常的礼仪,但也没有人认为他倾向于神秘主义。他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统基督徒。但他确实拥有对上帝的真实信仰。尽管康德坚持认为,在道德原则并不来自自然神学或启示神学的意义上,道德是自主的,但他仍然相信道德性意味着或最终涉及了对上帝的信仰,我们稍后会对之进行解释。有人说康德没有宗教经验,这就太过夸张了。而且如果有人真这么认为,考虑到康德对于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的尊敬,他的这种想法就会激起经久不衰的愤慨。同时,对于崇拜和祷告活动,以及胡戈尔男爵(Baron von Hügel)所称的宗教神秘因素,康德从未表明真正的赞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崇敬上帝,即便他崇敬宗教的方式只是通过实践上的道德责任意识。事实上,正如康德明显不具有对音乐作品的切身且生动的鉴赏力,但却写了有关美学和美学经验的著作,同样,康德不具有对基督徒虔诚和东方神秘主义的深刻理解,但却写了有关宗教的著作。康德的性格特征更多是道德真诚而非宗教献身,但这不意味着他是反宗教人士或者他对上帝的信仰是不真诚的。只有在他必须出席的正式场合,他才参加教会的仪式。他还对某个朋友说道,放弃祷告将会促进道德善的进步。这多少展现出了他的性格特征。 在政治方面,康德倾向于共和主义,前提是这个术语包含了有限的君主立宪制。他同情独立战争中的美国人,至少也同情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与康德的心智格格不入:《论永久和平》的作者不是纳粹能够利用的思想家。他的政治观念当然内在地与他关于自由价值、道德人格的概念相联系。 2. 正如我们所见,康德对于科学问题的兴趣在柯尼斯堡大学被克努岑所激发。同样很明显,在东普鲁士当家庭教师的这段时期,康德读过大量科学文献。因为他在1755年提交给大学的博士论文是《论火》(De igne),他在这年还出版了《天体理论和自然通史》(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这部著作出自之前写作的两篇论文(1754),其中一篇论述地球绕其轴心的运动,另一篇论述地球是否变老的物理学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星云假说,早于后来的拉普拉斯(Laplace) 因此,某些历史学家更倾向于把康德的思想生命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取代通常的两阶段划分,即处于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影响下的前批判时期,以及思考和表达他自身哲学的批判时期。这就是说,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承认原初阶段的存在,在这个阶段,康德主要考虑的是有关科学本性的问题。这个时期持续到了 1755年或者1756年,而前批判时期则集中在18世纪60年代。 当然,某些证据支持三分说。因为三分说可以让人注意到康德早期著作中占主导的科学特征。但就通常的目的而言,传统两分说在我看来已经足够。毕竟,康德没有放弃牛顿物理学转而寻求其他物理学。但他却放弃了沃尔夫的哲学传统,开创了新的哲学。这在他的心灵发展中是重要的事件。此外,三分说可能也有误导性。一方面,康德的早期著作虽然以科学为主导,但却并非完全如此。例如,在1755年,他在《论火》之后还发表了另一篇拉丁文论文,《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e nova dilucidatio),这篇论文使他获准在大学中作为编外讲师授课。另一方面,康德在批判时期仍然发表了几篇科学论文。在1785年,他发表了《论月球上的火山》(Ueber die Vulkane in Monde) 但是,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是浪费时间。重点在于,康德虽然从来不是专业的物理学家或天文学家,但却掌握了牛顿科学的知识;对他而言,关于世界的科学概念具有有效性是严格的事实。科学知识的本性当然仍然需要探讨;科学范畴和概念的应用范围也是个问题。但是,康德从未质疑过牛顿物理学在其自身领域内的普遍有效性;他后来的问题是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世界是受规律统治的系统(每个事件在其中都具有其决定和决定过程)这种科学概念,与包含了自由的道德经验的世界,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二者之间进行调和?而且,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似乎否定了对关于世界的科学概念的所有理性的、理论性的辩护,面对这种经验主义,我们能为科学陈述的普遍性和科学命题的有效性找到什么样的理论辩护呢?我并不是想说这类问题已经出现在了康德最初的思考之中,我也不想在此预先讨论他后期的批判哲学中出现的问题。但是,要想了解他的问题特征,就必须从一开始就理解他接受且一直接受牛顿科学的有效性。鉴于这种接受,鉴于休谟的经验主义,康德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不得不提出有关科学知识的本性的问题。而且,鉴于他接受关于世界的科学概念,同时鉴于他接受道德经验的有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康德发现自己不得不讨论必然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的相容性。最后,鉴于科学的进步以及经典物理学获得了普遍接受,康德发现自己不得不去追问形而上学是否缺乏相应的进步,是否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体系都没有获得普遍的接受,而这难道不需要彻底修正我们关于自然以及形而上学功能的观念?康德将来会处理这些问题,但这预设了他对牛顿科学的接受,这种接受显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 3. 当我们说到康德思想发展中的前批判时期,所指的当然是他构想和撰写自己的原创哲学之前的时期。换言之,这个术语必须在严格意义上被理解,而不是“不加批判地”被理解。在这个时期,他多少仍然坚持沃尔夫哲学的观点,但他绝不是以盲从和不加批判的方式接受这种哲学。早至1755年,在其拉丁文著作《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中, 他已经批判过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某些哲学,例如他们对充足理由律的使用。但在这个时期,他对莱布尼茨哲学的了解与沃尔夫及其追随者对它所做的经院哲学阐述不同,是有限的和不充分的。但是在 18世纪 60年代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批判态度越来越强烈,虽然直到60年代末期,严格意义上的批判观点才首次出现。 1762年,康德发表了《四种三段论格的烦琐错误》(Die falsche Spitzfindigkeit der vier syllogistischen Figuren)。在这篇论文中康德认为,将三段论逻辑划分为四种形式是过于烦琐和不必要的。同年年末,康德发表了《证明上帝实存的唯一可能根据》(Der einzig m?gliche Beweisgrund zu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这篇论文颇为有趣,我们在此可以进行简要讨论。 在论文的结尾,康德说道,虽然“设想上帝实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证明它却不是十分必要”。[ 参见 3,5;W.,II,第 163 页。字母 W. 表示普鲁士科学院版的康德全集,引用为全集、卷次、页码。参见本书文献部分。译者注:普鲁士科学院版的康德全集于1902年启动编纂,1942 年完成二十二卷版,二战后继续编纂。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康德著作的英文译本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版康德著作集”(Cambridge Editions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因为神意不希望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是形而上学上的烦琐论辩。如果事实如此,我们就会处于令人遗憾的困境之中。因为还没有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明,能够提供类似于数学的确定性。但是,专业哲学家自然应该想要探究上帝实存的严格证明是否可能。康德想要对这种探究有所贡献。 所有有关上帝实存的证明,必须或者依赖于可能性的概念,或者依赖于关于实存的经验观念。此外,这两类各自还可以划分为两个子类。首先,我们可以尝试从下述两种进路展开讨论:一种是以上帝实存作为结果,而可能性是这种结果的基础;另一种是以可能性作为结果,以上帝实存作为这一结果的基础。其次,如果我们从实存的事物出发,同样有两种进路可供选择。我们或者可以尝试证明这些事物的第一个、独立的原因之实存,随后表明,这种第一因必须拥有某些属性,这些属性可以使第一因恰当地被称为上帝。或者我们可以尝试同时证明上帝的实存和属性。康德认为,任何上帝实存的证明只能是上述四种形式之一。[ 3,1;W.,II,第 154—155 页。] 第一种论证,即以可能性作为基础,以上帝实存作为结果,对应于所谓的本体论论证,从关于上帝的观念到上帝的实存。安瑟伦(Anselm)和笛卡尔提出了这种证明的不同形式,莱布尼茨接受并对之进行了重述。康德在《证明上帝实存的唯一可能根据》中对之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这种证明假设了实存是个谓词,这是错误的假设。第三种证明对应于康德后来所称的宇宙论论证,在康德看来这种证明方式更多地被沃尔夫学派的哲学家所采纳,但由于我们不能证明第一因必定是我们所说的上帝,所以这种证明也被康德排除在外。第四种证明对应于目的论证明或者设计论证明,康德对这种论证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尊重(正如他之后持续表现出的那样),前提是这种论证的重点是被放在有机体内在的目的论上。即便如此, 它不能且不可能等同于对上帝实存的证明。因为它至多将我们引向产生出世界的系统、秩序和目的的神圣心灵或者神圣理智,而不是将我们引向创造者。换言之,它给我们带来了二元论,一方面是超越世界的心灵,另一方面是等待形塑的物质。就这一论证而言,这种物质是独立于还是依赖于上帝,我们仍有疑义。 最后还剩第二种论证,从作为结果的可能性推出作为基础的上帝实存。康德提出,第二种论证是证明上帝实存的唯一可能。他告诉我们,否认所有实存,这本身并没有内在的逻辑矛盾。但是,我们不能合理地做出在肯定可能性的同时否认可能性有实存基础。我们必须承认可能性。因为我们不能不经过思维就将可能性否定,而去思维就是含蓄地肯定了可能性的领域。康德继续论证道,这种存在者必须是唯一的、简单的、不变的、永恒的、精神的,以及具有形而上学中“上帝”一词所包含的所有其他意涵。 从中世纪哲学来看,第二种论证让我们想起了邓·司各脱而非托马斯·阿奎那,司各脱试图从可能性论证上帝的实存及其属性。阿奎那的确在其第三条道路中把他的论证建立在“可能性”概念的基础之上,但他的可能性概念来自经验事实,即某些事物能够产生和消失,因而是“可能的”(经院哲学家通常称之为“偶然”)。康德论证道,上帝实存包含在所有思维之中,而非偶然事物的实存显示出了上帝的实存。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康德所要求的是,莱布尼茨从永恒真理出发的论证应当转变为严格的证明。无论如何,非常有趣的是,他的论证道路虽然不同于本体论证明,但与设计论证明相比却具有先天特征,而且预设了莱布尼茨式的观点,即把形而上学视为非经验科学。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没有看到数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具有内在区别。这种区别在我们即将提到的著作中得到了清楚的肯定。 在《证明上帝实存的唯一可能根据》中,康德认为形而上学是“无底的深渊”和“没有彼岸没有灯塔的黑暗海洋”。[ 《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前言;W.,II,第 66 页。]在《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Untersuchung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 1764)中,我们看到康德更为清楚地阐明形而上学的本性。在此前那年,柏林科学院发布了有奖征文,讨论形而上学真理是否具有普遍性,或者更具体地说,自然神学和道德的第一原则是否能够与几何真理具有相同程度的论证确定性。如果不是,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本性和确定性程度?这种确定性程度是否足以为我们的形而上学信念做辩护?康德的论文未能获奖,获奖的是门德尔松的论文,但康德的论文非常有趣。 康德坚持认为,数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具有根本区别。[ 在《将负数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1763)这篇论文中,康德已经明确反对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哲学观念,虽然他仍然坚持认为,数学真理在哲学上可以是相关和有效的(W., II,第 167—168 页)。]数学是构造性的科学,因为数学可以任意“综合地”构造它的定义。几何图形的定义不对之前拥有的概念或观念进行分析所带来的结果,而是概念通过定义而产生。但是,在哲学[康德称之为“世界智慧”(Weltweisheit)]中,定义是通过分析而获得的。这就是说,我们首先会对某个事物具有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是模糊或不充分的。通过对这种观念的应用实例进行比较,以及通过实施抽象活动,我们试图努力澄清它。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分析性的而非综合性的。康德以时间为例说明这之间的差异。在我们对时间进行哲学探究之前,我们已经具有某些关于时间的观念和知识。这种探究采取的形式是比较和分析时间经验的各种例子,从而形成充分的、抽象的时间概念。“但是,如果我想要在这里试图以综合的方式得出时间的定义,如果这个概念恰好就充分表达了先前给定的观念,那么这该会是怎样的幸运巧合啊。”[ 《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1, 1;W.,II,第 277 页。]这就是说,如果我随意构造时间的定义,像几何学家构造其定义那样,那么,如果我碰巧对我(和其他人一样)已经拥有的具体时间观念给出了明晰的、抽象的表达,这只能是出于运气。 据说,哲学家的确“综合地”构造定义。例如,莱布尼茨自己就构想出了只拥有模糊或混乱表象的简单实体,他称之为沉睡的单子。这的确是真的。但是,重点在于,当哲学家任意地构造定义,这些定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定义。“对于语词意义的这类规定从来都不是哲学定义;但如果它们被称作解释,那也只不过是语法上的解释而已。”[《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1, 1。]如果我想,我 就可以解释我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术语“沉睡的单子”,但这样我只是作为语法学家而非哲学家而行动。莱布尼茨“没有解释这种单子,而只是设想了它,因为单子的概念并不是被给予的,而是由他创造的”。[ 同上。]与此类似,数学家常常处理某些能够进行哲学分析而不仅仅是任意构造的概念。空间概念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但是,这类概念是被给予的;严格来说,它们不是像多边形这种意义上的数学概念。 我们可以认为,在数学中,我完全没有关于对象的概念,直到定义提供了概念;但在形而上学中[ 康德把形而上学描述为“关于我们知识的最终原则的哲学”(《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2;W.,II,第 283 页。)],我有已经被给予的概念,虽然这种概念仍然是混乱的,我将尝试使之清楚、分明和确定。[ 《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2;W.,II,第 283 页。]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只要没有人向我追问时间的定义,我就清楚地知道时间是什么。在形而上学中,即便我们不能定义思想对象,我也能够很好地知道有关思想对象的 真理,而且能够从这些真理中推出有效结论。康德给出了关于欲求的例子。即便我不能定义欲求,我也能谈论有关欲求之本性的真理。总之,数学以定义作为起点,形而上学所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康德总结道,如果要在形而上学中获得确定性,那么需要注意的原则性规则是,要确定人们对于当下主题能够直接和确定地知道的内容,以此决定这种知识所能够引出的判断。 因此,形而上学不同于数学。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哲学理论多数就像陨石,它们的明亮程度不会保证其持续时间。“形而上学无疑是人类所有知识中最困难的,但还没有任何写出来的形而上学。”[ 《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1,4;同上。]我们必须转变方法。“形而上学的真正方法与牛顿引入自然科学并在那里获得有益结果的方法,从根本上是相同的。”[ 同上,2;同上,第 286 页。]形而上学家应当以“内在经验”现象作为起点,精确地描述它们,确定它们能够给出且我们可以确定的直接判断。形而上学家随后追问,各种现象是否能够像引力的普遍规律那样,在单一的概念或定义之下联合起来。正如我们所见,康德在哲学课程中使用了沃尔夫的教科书,而在形而上学课程中使用了鲍姆加登的教科书。鲍姆加登的方法以普遍定义为出发点,进而引出更为特殊的内容。这种方法是康 德明确反对的。康德主要关注的不是纯粹逻辑意义上和形式意义上的前件与后件之间的关系。他关注的是“真正的基础”;他必须以被给予的作为起点。 至于柏林科学院所提出的有关自然神学和道德的特殊问题,康德在《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中坚持认为,自然神学的原则是或能够是确定的。他简要引用了他的上帝实存证明作为可能性的实际基础。但在道德领域,情况稍有不同。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情感在道德生活中起到了部分作用。康德引用了“哈奇森(Hutcheson)和其他人”,他论述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首先开始认识到,虽然表象真理的能力是认识,但感受善的能力却是情感,这两者必须不能相互混淆”。[ 《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4,2;同上,II, 第 299—300 页。][英国道德学家和作家对于康德美学的影响也明显体现在康德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nen und Erhabenen,1764)中]。但是,不同于情感在道德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道德的第一原则仍未得到充分阐明。康德区分了“或然的必然性”(达到目的 X,必须以 Y 作为手段)与“法则必然性”(你有责任做某件事,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目的),这预示了他后期的伦理理论。同时,康德告诉我们,他在深入思考后得出结论,义务的第一形式原则是“做对你而言最完美的事情”。[ 同上;同上,第299页。]但我们不能从这个原则推导出具体的责任,除非“质 料”的第一原则也同时被给予。所有这些主题都需要仔细考察和思考,在此之后,我们才能够给道德第一原则提供最高程度的确定性。 在《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中,康德澄清了我们的时间观念。这或许使当代英语读者认为,他把哲学还原为“语言分析”,还原为对词项的使用所做的分析。但是,康德并没有想要否认形而上学的实存意义。例如,这很清楚地表现在他对自然神学的论述中。他在这部著作中的主要观点是,真正使用了数学方法的形而上学将会局限于展示形式蕴含关系。如果形而上学家想要增加我们的实在知识,他就必须停止仿效数学家,并且转向类似于牛顿在自然科学中成功使用的方法。实际上,他应当从澄清经验上的模糊概念开始,为这些概念提供充分的、抽象的表达;随后他可能会继续推论、建立形而上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相信形而上学可以把我们的理论知识扩展到科学领域之外。当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后期思想的发展,我们自然会想到这本书中的某些观察已经预示了他后期的观点。这些观察指形而上学关注于我们知识的第一原理。但是,我们在此并不试图证明康德在这个阶段已经具有批判哲学的观点。我们能够说明的是,他建议在形而上学中用牛顿的方法代替数学方法,我们不应该因此就不去注意他对于思辨形而上学日益增长的怀疑主义。实际上,这种建议部分表达了这种怀疑主义,或至少包含了疑义。这与对自然科学的信念相反,自然科学增加了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而形而上学则没有。对于形而上学应当做什么,康德提出了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投身于思辨形而上学的要求之中。事实上,康德很快清楚地表明情况远非如此。 1766年,康德匿名(虽然作者的身份绝非秘密)出版了半严肃半幽默的著作,《以形而上学的梦来阐释一位视灵者之梦》(Tr?ume eines Geistersehers, erl?utert durch Tr?ume der Metaphysik)。因为康德有段时间对伊曼纽尔·斯韦登堡(Immanuel Swedenborg)的幻觉经验非常好奇,而且研究了他的“属天的奥秘”(Arcana coelestia),康德的反思的结果形成了《视灵者之梦》。对于幻觉经验,康德没有明确接受或反驳它们可能起源于灵神世界的影响。一方面,康德给我们描述了他所称的“秘密哲学的片段”[ 《以形而上学的梦来阐释一位视灵者之梦》(以下简称《视灵者之梦》),1,2;W.,II,第 329 页。],考虑到其中假设了(未经证明的)灵神世界,他提出灵神对人类灵魂的影响可能被投射在想象的幻觉中。另一方面,他还描述了“普通哲学的片段”[ 同上,1,3;W., II, 第 342 页。],他在其中提出对斯韦登堡所说的那些经验的解释,使得这些经验可以成为医学诊断和治疗的对象。读者可以自己选择采纳哪种解释。但重点不在于康德对幻觉经验的讨论,而在于他提出:思辨形而上学的理论就其自称是超越经验的而言,是否比斯韦登堡的观点具有更强的立场。康德清楚地表明,这些形而上学理论只具有更弱的立场。斯韦登堡的经验似乎通过与灵神世界接触而引起,即便这得不到证明。但是,形而上学理论本应该是在理性上可以证明的,而这就是有关灵神存在者的形而上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我们甚至不可能具有有关灵神的积极构想。的确,我们能够尝试借助否定来描述它们。但康德认为,这个过程的可能性既不依赖于经验也不依赖于理性推理,而是依赖于我们的无知,依赖于我们知识的限度。结论就是,灵神学说必须从形而上学中清除出去,如果形而上学想要具有科学性,它就必须划定“人类理性的本性所设定的知识界限”。[ 同上,2,3;W.,II,第 369 页。] 康德对形而上学采取的这种态度被休谟的批判所影响。这极其清楚地体现在《视灵者之梦》对因果关系的论述中。因果关系不能与逻辑蕴含关系相混淆。肯定原因而否定结果,这不涉及逻辑矛盾。原因和结果只能通过经验获得。因此,我们不能超出经验(感官经验)地使用因果观念,获得关于超可感实在的知识。康德否认的不是超可感实在的实存,而是否认形而上学能够像以往形而上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开启通往它们的大门。 传统形而上学对于道德而言是必要的,因为道德原则依赖于比如灵魂不死、上帝在来世的奖惩等形而上学真理 —康德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恰切。道德原则不是从思辨形而上学中得出的结论。同时,道德信仰(der moralische Glaube)可能指涉经验世界之外的领域。“将对于未来世界的期待建立在德性灵魂的经验之上,比(与之相反地)将人的道德态度建立在对彼岸世界的希望之上,看起来更合乎人性和道德的纯粹性。”[ 《视灵者之梦》,2,3;同上;W.,II,第 373 页。] 因此,在《视灵者之梦》中,我们发现了对康德后期观点的预示。传统思辨形而上学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可证的知识的来源。道德是自主的,不依赖于形而上学或神学。这就是说,道德原则不是从形而上学或神学前提得出的结论。同时,道德可以超出自身之外,也就是说,道德经验可以产生对某些真理的(合理的)道德信仰,这些信仰不可能由形而上学家证明。但是,除了认为形而上学应当采取人类知识界限的科学形式,康德还没有构想出他的独特哲学概念。他思想的否定方面,即对思辨形而上学的怀疑主义批评仍然非常突出。 康德还没有形成批判观点,这清楚地体现在他 1768年发表的论空间的论文中。在这篇论文中,康德发展了他非常尊敬的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的某些观点,他认为,“绝对空间不依赖于所有物质而实存,具有自身的实在性”。[ W.,II,第 378 页。]同时,他表明自己意识到了空间具有独立的、客观的实在性这个理论所具有的困难。他认为,绝对空间不是外在知觉的对象,而是使外在知觉成为可能的基本概念。[ W.,II,第 383 页。]这个观点在他的就职论文中得到发展。 ◎广阔的思想史视野 本书以其详尽的内容在哲学史界占据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力图破除哲学简史类书籍对哲学家、哲学思想漫画式的理解,不仅细致地描述了哲学史上耀眼的“明星”哲学家们及其哲学思想,还对那些通常被史书忽略的哲学家们给予一定关注。 ◎细致的哲学流派谱系研究 科普勒斯顿以深厚的学养勾勒出各哲学体系的逻辑发展和内在联系,试图以“永恒哲学”的原则完成历史材料的挑选工作,提供连贯而有意义的哲学历史解释。 ◎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引用 作为一本以“成为教科书”为目标的哲学史,其中广泛吸纳了各种古代、近代、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鼓励学生在学习哲学史之后去阅读哲学原典,拿起书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