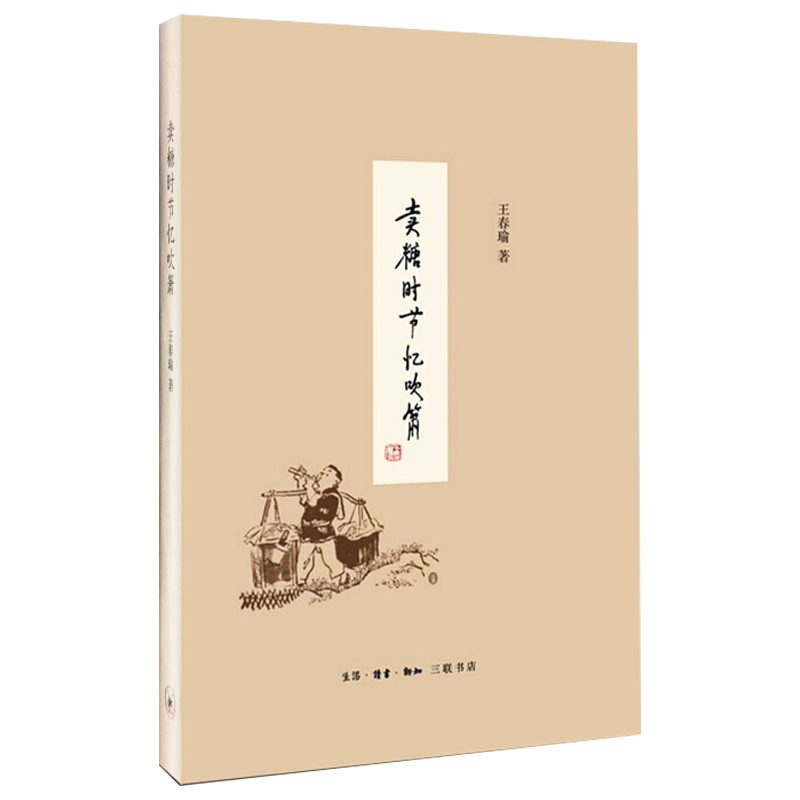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25.80
折扣购买: 卖糖时节忆吹箫(精)
ISBN: 9787108047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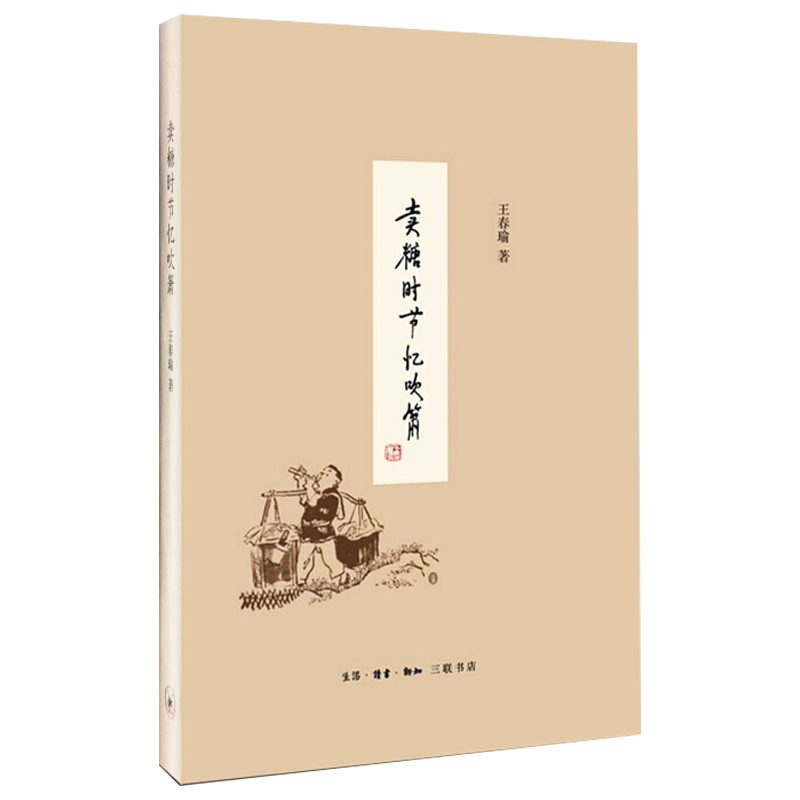
王春瑜,江苏省建湖县人。1937年生于苏州。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63年毕业于该校研究生班元日明清史专业,获得副博士学位。在上海师范大学任讲师。1979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工作。 1988年晋升研究员。担任《明史论丛》主编,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多年来主要研究明代政治史、社会生活史,并研究清初及其他王朝商业经营史、政治史、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历史学概论》、《明代宦官》(以上合著)、《“土地庙”随笔》、《明朝酒文化》、《明清史散论》、《古今集》、《牛屋杂俎》、《喘息的年轮》、《交谊志》、《续封神》、《铁线草》、《今古一线》、《漂泊古今天地间》《老牛堂三记》、《老牛堂札记》、《庙门灯火时》、《新世说》等;主编《中国反贪史》上下册90万字、《中国反腐败史话》10册、《中国小通史》10册,其中《中国反贪史》获得第13届中国图书奖。
我是研究历史的,又是写杂文、随笔的,说得雅 一 点,是文史两栖,说得俗一点,是觅食于文史两界。 曾 有读者、报刊记者问我是如何走上史学道路,并从事 文 学创作的?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做了回答。回首往事, 我 深深感到,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散发着浓烈盐阜 平 原乡土气息的淮剧,是我的文化启蒙老师。从草台戏 到 县城简陋戏台、到地级市正规剧场演出的一幕又一幕 的 淮剧,像长长的流水,滋润着我的心田。 我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一直留意江苏 地区的方志、文集、笔记,都没有淮剧起源的相关记 载。 淮剧老艺人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能够追溯的最早年 代, 也不过是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我1937年生于苏州,因 避 日寇战火,随母亲、长兄春友(参加革命后改名王荫) 逃亡至水乡建湖县,在那里度过童年、少年艰苦的岁 月。 我三岁记事,那时我家住在蒋王庄。在炎热的夏天的 晚 上,人们在打谷场上乘凉时,俗称唱晚场者,撑着小 船, 在庄后小河上停下,然后走到打谷场上。庄上热心人 士, 搬来一条长凳,请他们坐下。其实就是两个人,一个 拉 胡琴,一个中年男人只是把头部装饰一下,脸上涂了 些 脂粉,扮成女人模样,一身旧布衣,用现在的话说, 真 是寒碜。三岁的我,根本不懂他唱的什么。我问母亲 : “他唱的什么呀?”母亲告诉我:“他唱江淮戏昵! ”这 是淮剧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过了几年,我长大一些 了, 才知道唱晚场的人,并不是职业淮剧演员,是会唱一 些 淮剧的民间艺人,白天务农,晚上出来唱戏文,唱完 后, 庄农凑几斤稻谷给他们,作为报酬。他们根本买不起 戏 装。不过,近七十年过去了,这位民间艺人的面影, 还 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淮剧第一次给我留下完整的美好印象的,是1945 年 深秋,看阜宁县一个戏班子演出的古装戏。这一年, 邻 庄吕老舍一位吕姓地主,稻子丰收,而且收割后,过 了 两个月,稻茬上又长出二季稻,收割后,居然还打出 好 几担谷子,吕家高兴不已,以为是神灵保佑,便按乡 俗, 唱戏谢神,俗称香火戏。庄民在庄前打谷场上搭起戏 台, 坐南朝北。消息不胫而走,乡农平时难得看戏,都焦 急 地等待着,包括我在内的小孩子们,更急切地等着看 热闹。 此时我已八岁,读小学三年级,能看懂《盐阜大众报 》, 还看了《隋唐演义》之类几本历史连环画,可谓茅塞 初 开。演出那天,锣鼓震天,乡民纷纷赶往戏台下。这 个 戏班的演出非常正规。演出前,一位武生爬上一根很 高 的木头上做各种杂技动作,身上不系保护绳,观众不 时 发出惊叹声。最惊险的是,他表演“乌鸦攘翅”。肚 皮贴 着木头顶端,身体连续做360度旋转,观众惊呆了, 发 出一片欢呼。这项表演结束,便是“跳加官”,在锣 鼓声 中,跳了很久,直到观众挤满了打谷场,才结束,开 始 了正式演出。第一出戏,当时就没看懂,只记得一位 白 发苍苍的土地爷,托梦给一位书生,不知道干什么, 我 看了觉得乏味。但第二出戏,是王宝钏抛彩球,击中 一 个讨饭花子,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几乎家喻户晓的王宝 钏 与薛平贵故事中的一段,现在京剧、地方戏舞台上仍 在 演出抛彩球、投军别窑、探寒窑、大登殿,可谓久演 不 衰。这出戏很热闹,我觉得太有趣了,势利的王丞相 、 坚贞的王宝钏、有志气的薛平贵,从此作为历史人物 , 深深在我脑海里打下烙印。但是,接下来的《活捉张 三 郎》,更给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美好享受。其中扮 演张 文远的演员,表情丰富,动作灵活,最后被阎婆惜追 命, 用白素练勒死,伸出长舌头,欢众一阵欢呼,觉得大 快 人心。更使我心灵震撼的是,扮演阎婆惜的女演员, 也 不过二十岁左右,身材苗条,扮相俊美,唱腔悦耳。 在 我的童心里,颇为惊诧世界上还有这样美丽的姐姐, 真 正是貌若天仙。这次演出结束后,听大人们说,他们 还 要再来唱戏的。但是,我和小伙伴们,从秋盼到舂, 从 春盼到夏……望穿秋水,再也没有看到他们来演出。 我 急切地想看到他们的演出,很大程度上,是想再见到 那 位阎婆惜的扮演者。岁月悠悠,这位姐姐如健在,至 少 也有85岁了。她的美丽形象,是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 记 忆之一。P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