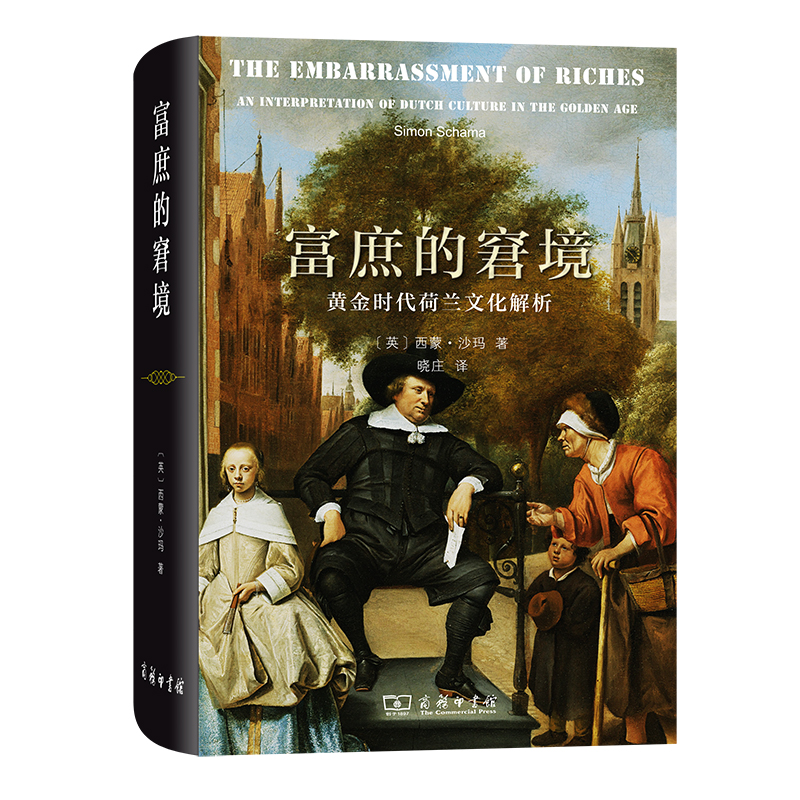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58.00
折扣价: 110.60
折扣购买: 富庶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精)
ISBN: 97871002100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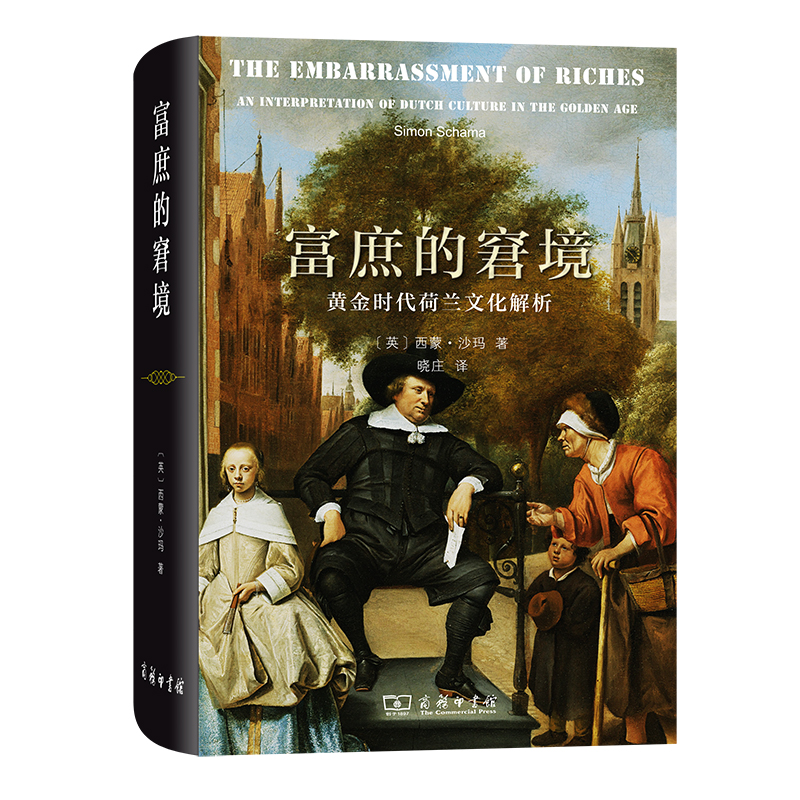
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的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专长于艺术史、荷兰史、犹太人史和法国史。同时,他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撰稿人和解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曾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教,1995年被遴选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荣誉成员,2015年成为英国学术院通信会员,2017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2018年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代表作有《爱国者和解放者》《富庶的窘境》《公民们:法国大革命编年史》《风景与记忆》《英国史》《艺术的力量》《犹太人的历史》等。
历史学家与淘金者并无二致。经年的艰苦劳作之后,终于发现了宝贵金矿,他们愿意将之秘而不宣,在竖起成果分享的标志以阻拦不法入侵者之时,偶尔可以给人们惊鸿一瞥。他们非常重视其好运道的独特价值。我也未能免俗。在努力举荐荷兰世界的特色时,我也许夸大了它与众不同的一面。无疑,我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心得远远多于对17世纪其他文化社会史的研究,这使我很容易辨识出在荷兰环境之下表现出的特征和态度。显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反应库——特别是对新教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可以从中寻到应对良方的绝不止一个社会群体。荷兰世界真正的特殊性不在于单个人的态度或行为,而是集体意识中使他们彼此相连的方式。荷兰画家与同时代的意大利、佛兰德斯画家使用同样的颜料,最终效果却截然不同。我的兴趣所在就是探究这个最终效果是如何产生的。 荷兰处境的特殊性——它的幸运及其困境——使它与巴洛克时代欧洲其他国家和民族迥然不同。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的早熟。仅仅经历了两代人它就变成了世界帝国。从范迪门之地到新地岛,最令人敬畏的经济实力在全球延伸。不过周游世界的荷兰人有幽闭恐惧症。最终,斯凯尔特河与埃姆斯河之间的狭小地带吸食了全部权力和巨大财富:那里密布着将近两百万个蜂箱(bijenkorf)。规模惊人的成就让他们既飘飘然,也感到一些心神不宁。就连他们表达自鸣得意的最豪放的文献中也萦绕着对丰饶(overvloed)的忧心忡忡,丰饶如在洪峰之巅的过剩——这个词充满了警示和狂喜。尼德兰文化的奠基元老之一,人文主义者迪尔克·沃尔克茨祖恩·库恩赫特(Dirk Volkertszoon Coornhert)创作了《富人的喜剧》(The Comedy of Rich Man),剧中人奥费尔弗路德(Overvloed,意为丰饶)扮装成一个得到大量赠予的带眼罩的女佣,和康慎思先生(Conscience,意为良知)以及(“德高望重的牧师”)斯科里普彻尔·威兹德姆先生(Scriptural Wisdom,意为圣典智慧)争夺一个富人的灵魂。戏一开场,奥费尔弗路德抱怨说,虽然她吃起来津津有味,虽然她的“舌头品尝着”最甜美的红酒,虽然她衣装华美,却还是闷闷不乐,惴惴不安。也许并不奇怪,在尼德兰可以发现托克维尔在另一片早熟的丰饶之地——19世纪的美国——也注意到了的现象,即“民主国家生活富足的居民总是被奇怪的忧郁所萦绕,在平静与舒适的环境中,他们常有厌世之感”。 就17世纪荷兰市民的心绪而言,“忧郁”“厌世”这样的字眼也许言之过重,虽然他们的艺术也浸润在对于死亡联想——他们本人以及尘世的商品均如是——的暗示之中。不过,至少,对于沾沾自喜持续不断地感到良心刺痛并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困窘的自觉意识。 节选自《导言:巴达维人的性格》 为何富足的民族,却因幸福而忧惧? 沙玛为我们解锁荷兰黄金时代的文化密码, 唤起我们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反思。西蒙?沙玛是一位机敏睿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一个极具艺术眼光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他笔下的荷兰黄金时代既是一部民族建构的英雄史诗,又是一部风俗习惯的百科全书,更是一部荷兰文明心灵成长和情感养成的精神史。 通过揭示“富庶的窘境”这一荷兰文化中隐含的神秘矛盾,沙玛也唤起我们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