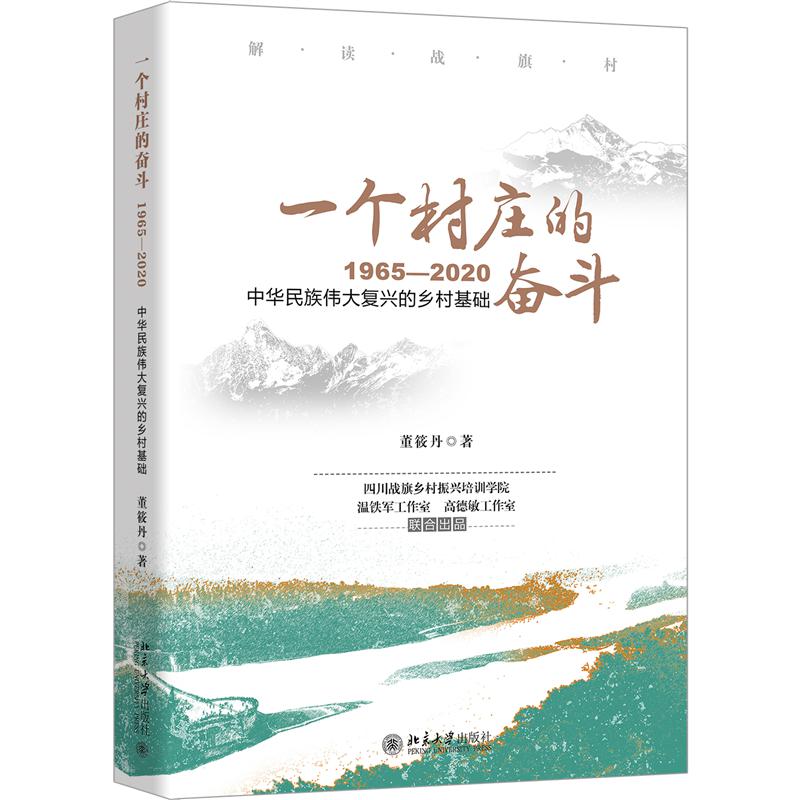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3.70
折扣购买: 一个村庄的奋斗 : 1965—2020
ISBN: 9787301320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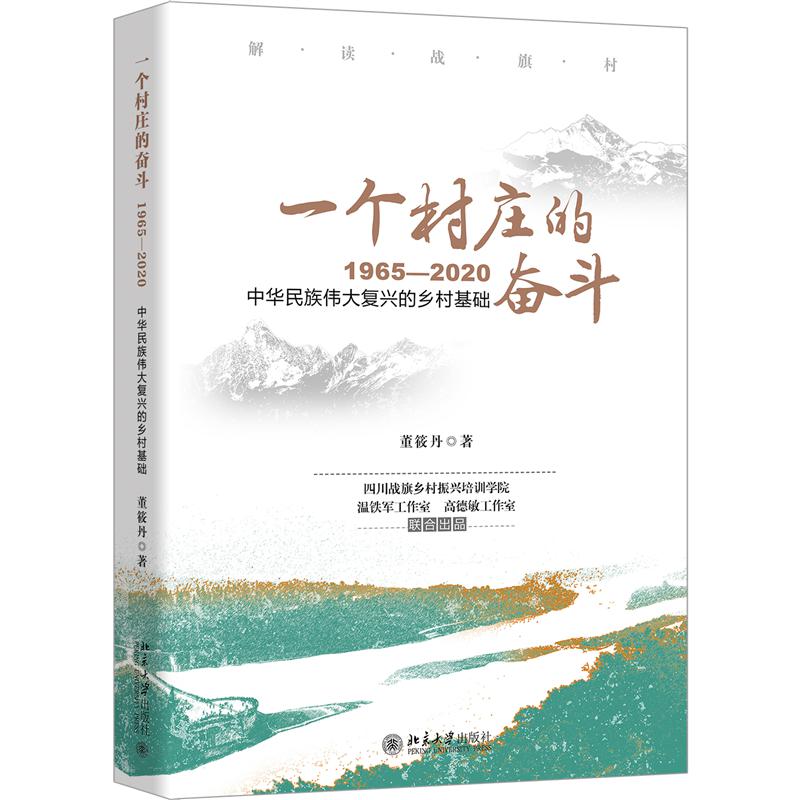
董筱丹,女,1978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省,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区域发展、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等。主要著作:《再读苏南》《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参与写作:《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解读苏南》《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等。以第一和主要获奖人身份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0项。
20 世纪 50—70 年代,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间,一般被认为是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若依据经典理论,则为国家工业化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该阶段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任何发达国家。如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外向的、殖民的、血腥的,而中国是内向的、本土的、艰辛的。 因此,中国迈向工业化的前 30 年创业史可谓“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又“宏大辉煌”,同时危机“此起彼伏”,危机之下各种运动“纷至沓来”。 这 30 年不仅有新中国成立之初新政权面对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危机时关乎生死存亡的艰难一跃,有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为发展工业化而过度提取三农剩余导致小农交易成本过高的困境,也有“二五”计划初期苏联撤资造成中国工业化中断并跌入“发展陷阱”的危机,还有三次城市经济危机后不得不发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以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在这30 年中,我国面临着外部全面封锁和周边地缘环境高度紧张等严峻的国际环境,如朝鲜战争、苏联撤资、美国飞机不断侵扰中国领海等,中国与苏联及西方国家事实上已经处于冷战时期的“热战”边缘。 正因如此,我国国内宏观政策被迫不断调整,逐渐形成与群众结合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方针。而这样的经济方针,不得不寻找最有效的方法来动员广大劳动群众。各地方政府延续土地革命时期的国民政治动员机制,以政治化动员和竞争激励为主,促进劳动力几乎不计成本地高强度投入,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克服了资本短缺等一系列危机。 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通过自力更生迅速工业化,其实现是以组织化为载体的。中国共产党将如一盘散沙般的农民组织动员了起来,使人民群众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伟大动力。集体化时期以村社为组织载体,使古典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劳动力、资金、土地被村社集体内部化占有。可以被村社组织内部支配的要素,依照初期农田水利建设、中期种养结合培肥地力、后期工副业发展等不同需求,形成不同的生产力要素,在集体内部被合理配置,且几乎没有组织成本,形成集体经济的高积累,从而低成本地完成了工业化必需的资 本原始积累。 同时,农村组织化的过程与国家政权建设深入基层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是同步的。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建设虽然不断深入基层,却始终遭遇着不同程度的抵抗。当时的老百姓没有国家的概念,国家根本没有力量完成需要巨大投入的工业化转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更加垂直地深入到基层社会,在国家权力深入生产队的同时,在横向上,国家权力也扩张到了征税之外,掌握了农业生产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当然,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运行也时刻遭遇着传统社会的抵抗,尤其是基层干部与社员以个人或家庭利益为核心的反抗。国家政权、地主士绅与农民的关系演变为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关系后,在国家理性、集体理性与小农机会主义的不断博弈下,中国农村曲折向前发展。 相比过去学术界关于集体化时期的劳动监督成本太高或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等观点,我们强调将集体化时期的历史过程放置于工业化初期导致的内外部条件的约束中,考察其具体的发展过程。通过具体的案例,我们发现该时期对农民的动员是螺旋上升的,其目标是追求单产,而非追求劳动生产率。 广大基层干部与群众意气风发,参与国家建设,使得能够移山填海、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出现在这个伟大而古老的国度。将乡村社会发展的真实历史呈现出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该阶段各类如今看上去匪夷所思的国家行为与个人行为。 也正因如此,我们或许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前 30 年农村的集体化时期,在深入分析该时期的内外部环境后,只有厘清其制度机制,才能渐窥其全貌。四川西部小小的战旗大队的经验历程恰好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样本,让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在这一时期发展的缩影。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任何一个生产大队,在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都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壮大,就必须寻找自己的竞争优势。 集体化时期反复强调“政治挂帅”,在该阶段(1965—1978 年),战旗大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实现了“革命生产双飞跃”,举起了西部地区的一面战旗,写下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完成了村庄内部的资本原始积累,逐步走上了农村工业化的道路。这便是中国能在这 30 年内创造出宏伟业绩的微观视角,是战旗里的中国。 战旗大队被分出来前,该地区作为新解放区,历经了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运动,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从农村提取尽可能多的剩余资源,促进国家工业化初期发展。也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对基层干部和社员进行“公与私”“集体与个人”的思想教育,培养其集体意识。 在资本极度缺乏的 1965—1973 年,战旗大队通过动员妇女、民兵建设等手段,动员了大量内部劳动力参与农副业生产,使农业总产量、养猪数量等迅速增加,在高积累、少分配,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的情况下,通过“种养”结合内部调配劳动力,实现了农副业综合收益最大化,完成了大队的资本原始积累,其增产经验、民兵制度先后被县委作为宣传材料发送给全县各大队学习。战旗大队成为此过程中的佼佼者。 1974—1979 年,战旗大队开始从农业村向农工副业综合发展转型。其利用 1973 年前后积累的各种社会资本,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机会优势和制度收益,较其他大队更快速地获得了设备、资金等。加上集体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极强动员能力,战旗大队迅速开办了曲线窑,在工业化发展的起步阶段抢占了先机,为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旗大队的经验绝非偶然,仔细考察可以发现,集体经济名村都有相似的发展过程。如华北的柳庄、江苏的华西村、湖北的洪林村等,就与战旗村的发展历程相似,也是通过大量投入劳动力发展大队的集体经济而被关注。 阅读战旗村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伟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看到中国共产党在短短几年内就在新解放区依靠少数的“南下干部”树立起权威,从而真正实现了政权的交替;看到战旗大队面对这些外部的政治力量快速调整自身的制度,成立后的短短几年内就一跃成为粮食、养猪、民兵等工作中的佼佼者。这是中国的战旗,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激昂前进的组成部分之一。 战旗飘飘 名副其实 走在前列 起好示范 通过“一二三四”解读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探索中国乡村建设的全新方法论: 一个核心——乡村作为中国“去依附”的微观基础; 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相结合; 三个阶段——政治化竞争阶段的红色战旗、产业化竞争阶段的金色战旗、生态化竞争阶段的绿色战旗; 四个启示——成本内化、村社理性、资源权益、空间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