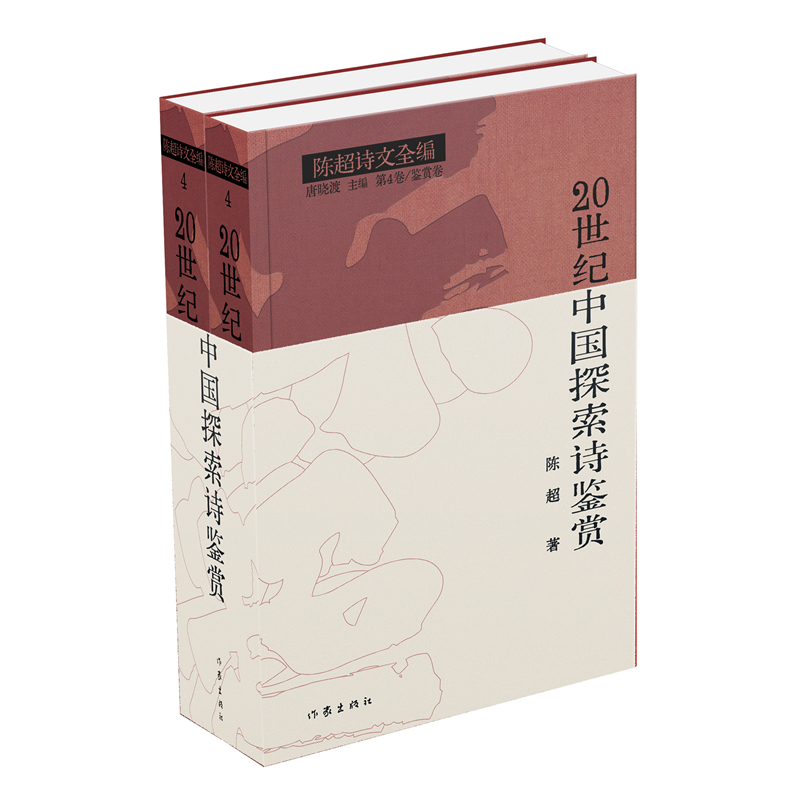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198.00
折扣价: 147.36
折扣购买: 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
ISBN: 9787521230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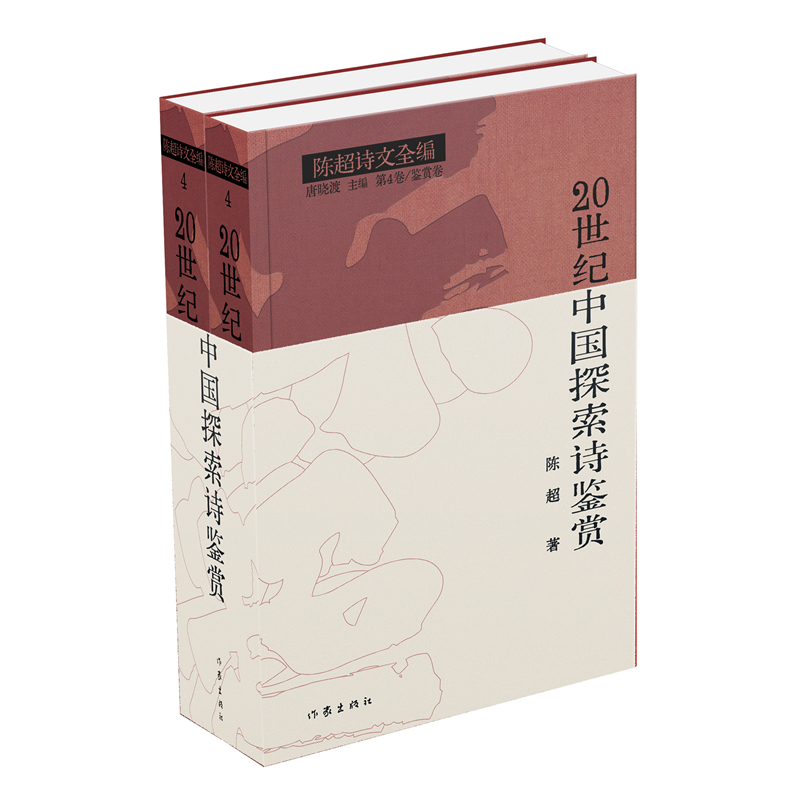
陈超(1958一2014),当代诗歌评论家、诗人。生于山西太原,辞世前系河北师 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的诗学和批评论著包括《中国先锋诗歌论》《生 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游荡者说》《精神重力与 个人词源》《诗与真新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 (两卷本)《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两卷本)等;著有诗集《热爱,是的》《陈 超短诗选》(英汉对照)等。 唐晓渡,诗歌批评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4年1月生于江苏仪征, 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和作家出 版社。现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当代国际 诗坛》主编。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的研究、评论和 编纂工作,兼及诗歌创作和翻译。著有诗论、诗歌随笔集《唐晓渡诗学论集》、 《今天是每一天》、《与沉默对刺》、《先行到失败中去》、《镜内镜外》、《所谓伊人》 等十余种;译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主编或编选 各种诗选数十种。先后参与创办民间诗刊《幸存者》、《现代汉诗》,中坤帕米尔 文化艺术研究院等。评论和诗歌作品被收入国内外多种选(译)本。多篇论文先 后获国内重要奖项。2012年获首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2013年 获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2016年获第14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 度批评家奖”。1995年起多次应邀往欧美多所大学访学或朗诵。2001年应邀出席 在法国里尔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2008年9月应邀出席第八届柏林国际 文学节。2006年起多次组织并主持中外诗人高端交流项目。
第一辑 象征派诗群 李金发 弃 妇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 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 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 越此短墙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 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游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徜徉在丘墓之侧, 永无热泪, 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李金发是中国诗歌中象征派的执牛耳者。他的诗幽邃、抑郁、神秘、精微。他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借鉴,不只是技巧上的,更是骨子里的。这表现在他的诗与波特莱尔们的诗,有着同构的关系:以社会和人生的“恶”为对象;强调“不幸”的忧郁美;追求万物与主体神秘的交感契合,认为自然是主观世界的“象征森林”;关心生与死等抽象的问题;在语言效果上,追求象征、隐喻、通感、暗示、视角转换;追求光、色的奇幻组合及音乐般的效果等。李金发曾被文学史判为“新诗发展中的逆流”,今天再回过头去看,就会发现这种评判是惟社会功利的,它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进入艺术的范畴。正如历史是无数个“当代”不断重写的,对李金发的诗,我们也不妨重新考察评定一番,本着缪斯独异的原则! 《弃妇》这首诗有着双重含义。一是本来意义上的被生活蹂躏的妇女;更主要的是其深层意义,以弃妇象征人的悲慨命运、生存的基本现实。第一层含义不必重视,让我们来看此诗的深层意义。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这是一幅可怕的图画,它让我想起蒙克的《呼号》。这是一种“世纪末”的情态,颓丧、仇恨、残酷、猜忌都被赤裸裸地象征出来了。诗人说用长发“隔断”这些,即视而不见,返回内心求得安宁。但这只能是妄想。你遁入内心后,仍然有“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越过你灵魂的“短墙”,发出尖厉痛楚的呼叫声!你陷入了更可怕的境地,像在旷野上遇到飓风的“游牧”一样,恐惧、孤单、无助、战栗!要是我们能联系诗人写作此诗的年代,这种深切的忧惧是不难理解的。你说它颓废也好,但这是时代的善良的弱者别无选择的基本心态!一种广义的被弃感! 第二节,诗人写惟有艺术能暂时安抚他饱经忧患的灵魂。象征主义诗人认为,自然万物都是人内在生命的象征符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故有“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一句。诗人深切的隐痛“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野蜂无家可归且无时不发出凄凄的嘤嗡声,使诗人找到了他“哀戚”的对应物;诗人的“哀戚”,又像“长泻在悬崖”的山泉,无尽无休,随着败落的秋叶一道流走。这一节虽然还是痛苦的,但我们发现这痛苦中隐隐有一种安慰感,意象(草、蜂、山泉、红叶)也较上一节显得吉祥、美好,这是艺术的力量使诗人感到生的意义。正如象征主义大师波特莱尔所言:“我几乎不能想象……任何一种美会没有‘不幸’在其中”(《随笔》)。 “弃妇”——“我”的忧郁是无尽无终的,它不可避免,难以抛掉。太阳有升有落,而“我”的隐忧却永远弥散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游鸦也不能载走“我”的痛苦,让它落在海边听一听幸福的歌唱!这是多么微薄的乞求,但却是如此之难!诗人,你的忧郁征服了我们,我们的心在颤抖,它充满了咸涩的泪水!——而你,却说:“徜徉在丘墓之侧,/永无热泪,/点滴在草地/为世界之装饰”。你知道人被弃置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有“热泪”与“永无热泪”,对这一事实并无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着这一命运,勇敢地揭示它的本质,永不转过头去…… 这首诗的象征分整体象征和局部象征。前者如“弃妇”象征人的生存、命运;后者指诗中每个主要意象的内涵。有许多人责怪李金发的诗晦涩、“文字游戏”,其实这种隔膜主要还不是审美习尚上的,而是精神深度上的。如果没有达到李金发对生命体验的深度,怎么可能理解和接受他的诗歌?这首诗备受指责,读者朋友,你怎么看?这是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吗?它的晦涩难道不是由“命运”本身的不可把握、充满神秘决定的吗?优秀的诗是生存的证据,是生命体验和生命情调的瞬间展开,《弃妇》就达到了这种境界。 希望与怜悯 希望成为朝雾,来往在我心头的小窗里。 长林后不可信之黑影, 与野花长伴着, 疾笑在狂风里,如穷途之墨客。 怜悯穿着紫色之长裙, 摇曳地向我微笑——越显其多疑之黑发。 伊伸手放在我灰白的额上, 我心琴遂起奏了。 我抚慰我的心灵安坐在油腻之草地上, 静听黑夜之哀吟,与战栗之微星, 张其淡白之倦眼, 细数人类之疲乏,与牢不可破之傲气。 我灵魂之羽,满湿着花心之露, 惟时间之火焰,能使其温暖而活泼。 音乐之震动, 将重披靡其筋力,与紫红之血管么? 我愿生活在海沫构成之荒岛上, 用微尘饰我的两臂如野人之金镯; 白鸥来时将细问其破裂了的心之消息, 并酌之以世界之血,我们将如兄妹般睡在怀里。 平庸之忧戚,猜不中你的秘密。 残忍之上帝, 仅爱那红干之长松,绿野, 灵儿往来之足迹。 深紫之灯光,不愿意似的, 站立在道旁,以殊异之视线 数行人之倦步。 我委实疲乏了,愿长睡于 你行廊之后, 如一切危险之守护者, 我之期望, 沸腾在心头, 你总该吻我的前额。 呵,多情之黑夜! 希望和怜悯,是人类两大基本感情。它们既是人内心良知的神异之声,又是人类从洪荒世界跋涉到今天的动力和意义。这是两个很抽象的名词,同时它们之间还存有难以理清的微妙关系,在正常的语义难以表述的时候,诗人进入了象征的原野。 先写希望。这里的希望存在于有和无之间,像“朝雾”,给人欣悦和行动的渴望,却又难以捕捉。尽管如此,诗人还是肯定了它,穿过苦难的“长林”,就有可能找到它的“黑影”!即使找不到,又有何妨?!“疾笑在狂风里”的艰难的人,虽然“穷途”之感日盛,但这奔走本身不就是“希望”的形象么?! 再写怜悯。诗人说怜悯是“紫色”的,这种色彩意味着沉郁、哀恸、平和与理解。它不是黑,那太冷硬了,也不是红,那太浮泛了,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色调。怜悯别人是一种幸福,被人怜悯也是一种幸福,在这个多灾多创的世界上,正是有了“怜悯”这种人类圣洁的情感,才“起奏了”多少渐将沉沦的人的“心琴”啊!那温和的紫色,伤口般的紫色的心琴! 第三、四节,诗人写希望和怜悯的关系。他坐在草地上凝思着,领悟着人世的艰难,“静听黑夜之哀吟,与战栗之微星”。“细数人类之疲乏”是怜悯体恤同类生存之苦,“牢不可破之傲气”是歌颂人类为希望殒身不惜的精神。这里,怜悯与希望成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犹如黑白木刻,互为因果和表里。人终归是要失望的,但重要的是不能没有希望,生命的时间还有,希望就会永远“温暖而活泼”。那由怜悯的“心琴”奏出的“音乐之震动”,会抚慰由失望带来的创伤!“将重披靡其筋力,与紫红之血管”?不!最高的希望就是拥有怜悯人类之心。 但人世间的苦难毕竟太多了,在“文明”社会,希望和怜悯居然成了一种奢想!在诗人的经验中,挺身反抗这种处境的办法是遁入内心世界的“荒岛”。让宽厚的自然来怜悯自己,让“白鸥来时将细问其破裂了的心之消息”。在这种宁静的、与世隔绝的气氛中,那些充满怜悯和感伤的“荒岛”避难者,“将如兄妹般睡在”自然的怀里。这是一个转折,整首诗在这里被加入了新的意义。对异化现实的批判使得它不同于那些廉价的博爱主义者,而具有相对和怀疑主义的深意。这种相对和怀疑是深刻的,不仅对现实生存,而且指向了上帝!“残忍之上帝”,只钟爱自然,却不去拯救人类的苦难。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诗人,你还在等着什么样的奇迹出现?! ——“深紫之灯光,不愿意似的,/站立在道旁,以殊异之视线/数行人之倦步。”哦,是怜悯,是深紫色的像创伤一样的怜悯!它站在每一条坎坷的路上,像忠实的路灯,照亮惨淡的人生之路。这与第三节的“我”“细数人类之疲乏,与牢不可破之傲气”是一种呼应;与第二节的“怜悯穿着紫色之长裙”是一种复现语象的关系(紫长裙与紫灯光)。到这里,前面的希望和怜悯的全部情感又一次被搅动、被唤起,“我”虽然疲乏之至,但“我”知道,希望还栖止在“我”心头,总有一天它会“吻我的前额”。黑夜是无情的,但正是在这样的夜里,我们感到了希望和怜悯的亮光。它一次次塑造和挽留了我们的爱欲,“呵,多情之黑夜”。绝望和希望、残酷和怜悯在较量,这是生命意志新的引力场,也是生存中的一个最深刻最有意义的悖论。李金发就这样用远距离设象的手法,为我们揭示了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虚无。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象征主义与现代人灵魂的同构关系。不是现代人选择了它,而是它和现代人的相互选择和发现! 里昂车中 细弱的灯光凄清地照遍一切, 使其粉红的小臂,变成灰白。 软帽的影儿,遮住她们的脸孔, 如同月在云里消失! 朦胧的世界之影, 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 远离了我们, 毫不思索。 山谷的疲乏惟有月的余光, 和长条之摇曳, 使其深睡。 草地的浅绿,照耀在杜鹃的羽上; 车轮的闹声,撕碎一切沉寂; 远市的灯光闪耀在小窗之口, 惟无力显露倦睡人的小颊, 和深沉在心之底的烦闷。 呵,无情之夜气, 卷伏了我的羽翼。 细流之鸣声, 与行云之飘泊, 长使我的金发退色么? 在不认识的远处, 月儿似钩心斗角的遍照, 万人欢笑, 万人悲哭, 同躲在一具儿——模糊的黑影, 辨不出是鲜血, 是流萤! 李金发的诗总给人以雕塑般的坚实简洁和现代油画般的光、色的新奇组合。他写诗时,不只是用单纯的情感,而是充分调动各种官能,使之交错起来,构成一枝有声有色有情有味的苦难的玫瑰。诗人在法国留学学习的是雕塑和绘画,印象派绘画大师马奈、雷诺阿,以及现代雕塑大师希尔德尔、贝纳尔等,都是诗人一往情深的崇拜对象。在诗人的诗中,随处可见绘画和雕塑审美效果的渗透,这首著名的《里昂车中》则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首诗表现的是诗人在列车上捕捉的一系列“印象”。车厢里微弱的灯光照在姑娘们的身上,使她们健康而红润的裸臂呈一种灰白的色调,正暗合了诗人凄清颓丧的心情。但诗人认为,这正是一种美,美在朦胧和暧昧之间。正是灰白的灯光照在她们身上,照在她们遮住脸孔的软帽上,才使人感觉到仿佛是月光被薄云罩住一般。月亮不见了,只留下月的印象,多么诱人联想,多么教人渴待!这是诗人对光所产生的变化的细微捕捉,没有“细弱的灯光”,这一切都无从解释。下面两节是诗人对窗外景物的印象。先是从大处写。“朦胧的世界之影,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远离了我们,/毫不思索”。车窗外一片迷离模糊,景物迅速滑过,仿佛它们是有意识地“远离了我们”,“不可勾留”,也“毫不思索”。这是拟人化的描写,却具有了人的特点,暗示了诗人那种被世界抛弃的孤独心境。接着是从细微处写。“山谷的疲乏惟有月的余光,/和长条之摇曳,/使其深睡。/草地的浅绿,照耀在杜鹃的羽上”;远方的山谷仿佛睡熟了,月光在深情地安慰着它的疲乏。而草地在月光的抚摸下,发出凄清的惨淡的绿光,像是一群群啼血的杜鹃的羽毛。这个意象美丽而凄艳,我们看到了那种由光的微妙变化改变了的物体形态,也听到了那凄厉孤单的杜鹃鸣叫声。这一切,再加上车轮声撕碎的世界之寂静,远方城市有灯光的小窗前痛苦疲乏的倦睡人……是多么教人黯伤心怀、苦泪盈盈!这就是诗人在列车上幻化出的整个人生的缩影,是诗人精神的象征“对应物”。 列车奔驰着,“无情之夜气”终于覆盖了一切。诗人灵感的“羽翼”,从外物的印象中收回,转入了内在生命的感悟。列车不息的前进声,在诗人的耳中幻化成了生命的流逝声、生命的飘泊感(细流与行云);正是在这种无家可归的灵魂浪迹中,“我的金发退色”了,希望一次次捉弄了“我”!这是悲慨的感悟,但它的意象却又是多么美。透明的羽翼,清澈的细流,洁白的行云,蓬松的金发,这一切美好的东西与“流逝”放在一起,给人以美被毁灭的感伤。 月儿挂在远天,但在诗人看来,它是人世间“钩心斗角”的象征,它的光那么普遍,那么人世间的欺诈、利诱、背叛也是一样的普遍;它使“万人欢笑”和“万人悲哭”都缠在一起难辨真伪。在它的明灭下,分不清那是“鲜血”还是“流萤”!诗歌最后出现的月的意象,与第一节姑娘脸孔——月光的意象,发生了呼应,暗示在残酷的人生中,惟有幻觉的美是有价值的;而生存中即使是美的幻觉也是那般转瞬即逝!那般难见!这表现了李金发悲郁、颓废的人生观,也表现了他对丑恶现实的否定。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首诗意象奇幻,整体象征深刻而富于魅力。在对异化现实的否定中,诗人借助了艺术之美的力量。这种“恶之花”式的抒情方式,正是李金发对中国新诗的贡献。 陈超既是大批评家也是大诗人。他真的拥有大能力。我一直期待再遇到一个陈超,但是没有。 ——西川 陈超先生的诗与文,皆高笔悬言、修远寻赜之作,于我而言,可持续一生读之诵之,惜之念之。 ——欧阳江河 陈超在批评理论和诗歌写作两个领域均展现出富有时代感的卓越创造力,他的诗文集是智识、直觉和灵感的完美融合。 ——耿占春 陈超,一个诗歌道途上永远的攀登者。这形象从未稍有形。他一点点吸收了那大地上倾斜的巨冰,那从天空垂直洞彻的阳光,那冰凌中火焰的卷宗,直到和它们混而不分…… ——唐晓渡 陈超以人格的高标、独卓的知识分子精神以及先锋意识构建了以生命诗学、文本细读、现象学剖析为原点的批评谱系。 ——霍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