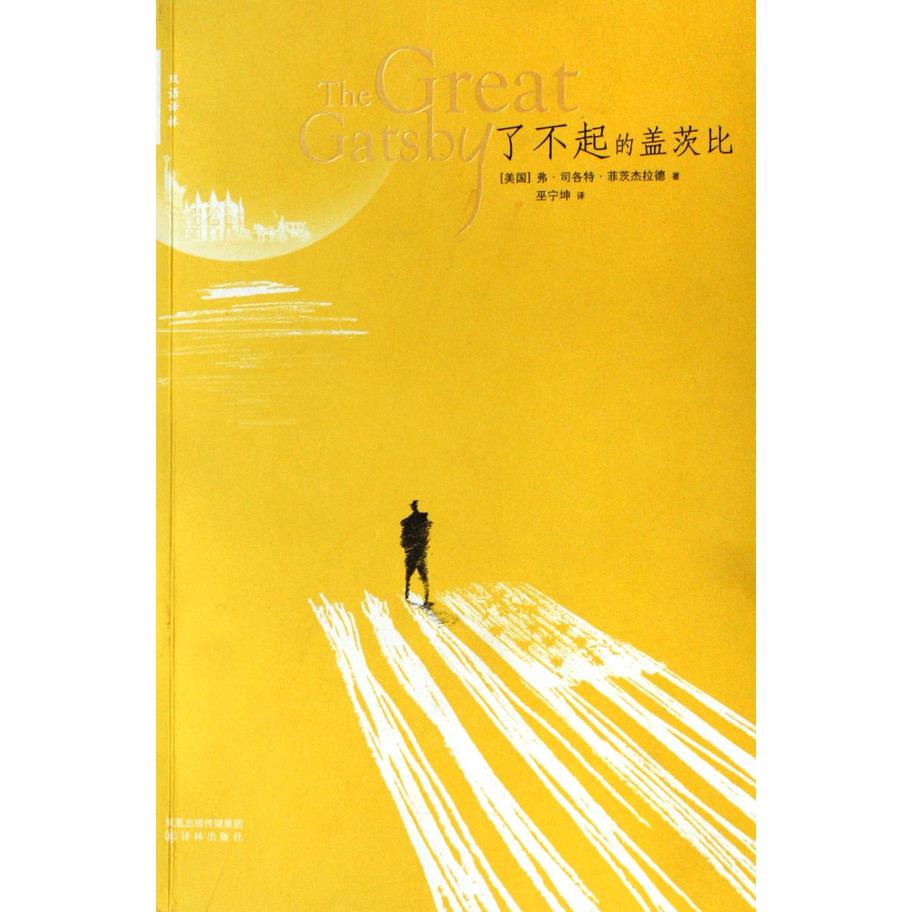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25.00
折扣价: 17.50
折扣购买: 了不起的盖茨比/双语译林
ISBN: 97875447017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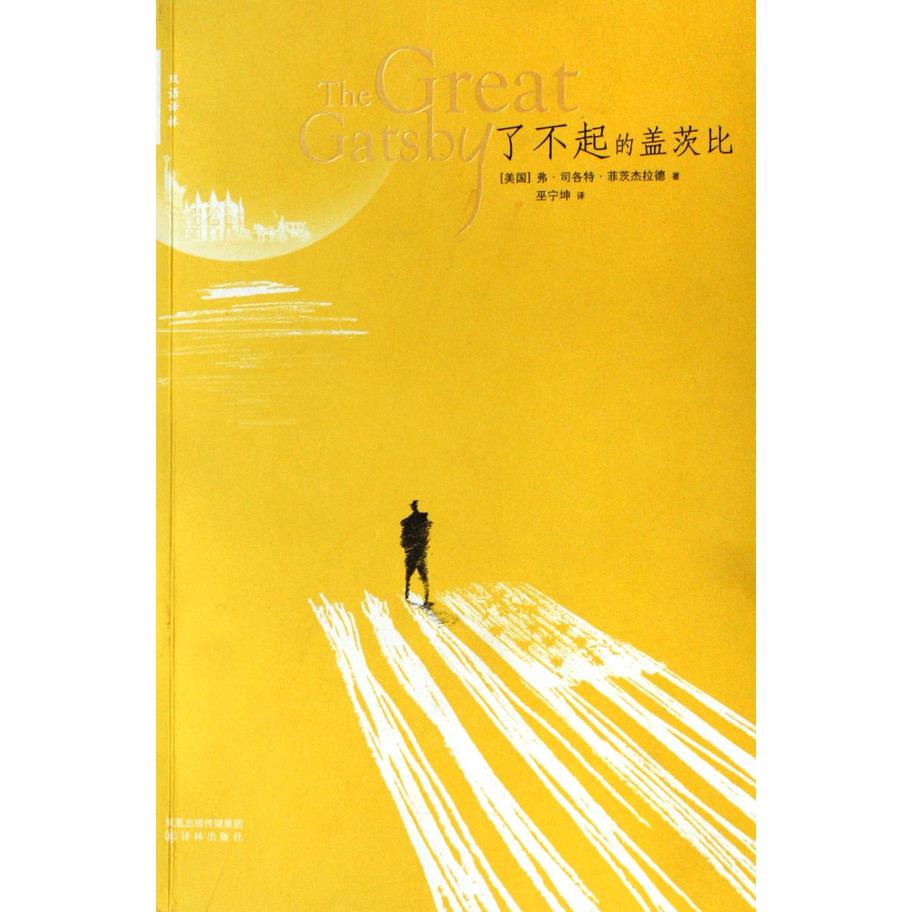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 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 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话虽不多,却一向是非常通气的 ,因此我明白他的话大有弦外之音。久而久之,我就惯于对所有的人都保 留判断,这个习惯既使得许多有怪僻的人肯跟我讲心里话,也使我成为不 少爱唠叨的惹人厌烦的人的受害者。这个特点在正常的人身上出现的时候 ,心理不正常的人很快就会察觉并区抓住不放。由于这个缘故,我上大学 的时候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小政客,因为我与闻一些放荡的、不知名的人 的秘密的伤心事。绝大多数的隐私都不是我打听来的——每逢我根据某种 明白无误的迹象看出又有一次倾诉衷情在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的时候,我往 往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或者装出不怀好意的轻佻态度。因为青年人 倾诉的衷情,或者至少他们表达这些衷情所用的语言,往往是剽窃性的, 而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判断是表示怀有无限的希望。我现在仍然唯恐 错过什么东西,如果我忘记(如同我父亲带着优越感所暗示过的,我现在 又带着优越感重复的)基本的道德观念是在人出世的时候就分配不均的。 在这样夸耀我的宽容之后,我得承认宽容也有个限度。人的行为可能 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面,也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之中,但是一过某种程 度,我就不管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姿 势。我不再要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也不再要偶尔窥见人内心深处的荣幸 了。唯有盖茨比——就是把名字赋予本书的那个人——除外,不属于我这 种反应的范围——盖茨比,他代表我所真心鄙夷的一切。假如人的品格是 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姿态,那么这个人身上就有一种瑰丽的异彩,他 对于人生的希望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类似一台能够记录万里以外的地震 的错综复杂的仪器。这种敏感和通常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那种软绵 绵的感受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水葆希望的天赋,一种富于 浪漫色彩的敏捷,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来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大可能 会再发现的。不——盖茨比本人到头来倒是无可厚非的、使我对人们短暂 的悲哀和片刻的欢欣暂时丧失兴趣的,却是那些吞噬盖茨比心灵的东西, 是在他的幻梦消逝后跟踪而来的恶浊的灰尘。 我家三代以来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家道殷实的头面人物。姓卡罗威的 也可算是个世家,据家平传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的后裔,但是我们家系 的实际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哥哥。他在一八五一年来到这里,买了个替身 去参加南北战争,开始做起五金批发生意,也就是我父东今天还在经营的 买卖。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是据说我长得像他,特别有挂在父亲办公 室里的那幅铁板面孔的画像为证。我在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毕业,刚好比 我父亲晚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久以后我就参加了那个称之为世界大战的延 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我在反攻中感到其乐无穷,回来以后就觉得百无聊 赖了。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的边缘——于 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债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是做债券生意的,因 此我认为它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总不成问题。我的叔伯姑姨们商量了一番, 他们怦然是在为我挑选一家预备学校,最后才说:“呃……那就……这样 吧。”面容都很严肃而犹疑。父亲答应为我提供一年的费用,然后又几经 耽搁我才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到东部去,自以为是一去不返的了。 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在城里找一套房寄宿,但那时已是温暖的季节,而 我又是刚刚离开了一个有宽阔的草坪和宜人的树木的地方,因此办公室里 一个年轻人提议我们俩到近郊合租一所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个很妙的 主意。他找到了房子,那是一座风雨剥蚀的木板平房,月租八十美元,可 是在最后一分钟公司把他调到华盛顿去了,我也就只好一个人搬到郊外去 住。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跑掉以前我养了它几天——一辆旧道吉汽车 和一个芬兰女佣人,她替我收拾床铺,烧早饭,在电炉上一面做饭,一面 嘴里咕哝着芬兰的格言。 头几天我感到孤单,直到一天早上有个人,比我更是新来乍到的,在 路上拦住了我。 “到西卵村去怎么走啊?”他无可奈何地问我。 我告诉了他。我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成了领 路人、开拓者、一个原始的移民。他无意之中授予了我这一带地方的荣誉 市民权。 眼看阳光明媚,树木忽然间长满了叶子,就像电影里的东西长得那么 快,我就又产生了那个熟悉的信念,觉得生命随着夏天的来临又重新开始 了。 有那么多书要读,这是一点,同时从清新宜人的空气中也有那么多营 养要汲取。我买了十来本有关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籍,一本本红 色烫金封皮的书立在书架上,好像造币厂新铸的钱币一样,准备揭示迈达 斯、摩根和米赛纳斯的秘诀。除此之外,我还有雄心要读许多别的书。我 在大学的时候是喜欢舞文弄墨的——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连串 一本正经而又平淡无奇的社论——现在我准备把诸如此类的东西重新纳入 我的生活,重新成为“通才”,也就是那种最浅薄的专家。这并不只是一 个俏皮的警句——光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究竟要成功得多。 纯粹出于偶然,我租的这所房子在北美最离奇的一个村镇。这个村镇 位于纽约市正东那个细长的奇形怪状的小岛上——那里除了其他大然奇观 以外,还有两个地方形状异乎寻常。离城二十英里路,有一对其大无比的 鸡蛋般的半岛,外形一模一样,中间隔着一条小湾,一直伸进西半球那片 最恬静的咸水,长岛海峡那个巨大的潮湿的场院。它们并不是正椭圆形— —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一样,在碰过的那头都是压碎了的——但是 它们外貌的相似一定是使从头上飞过的海鸥惊异不已的源泉。对于没有翅 膀的人类来说,一个更加饶有趣味的现象,却是这两个地方除了形状大小 之外,在每一个方面都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卵,这是两个地方中比较不那么时髦的一个,不过这是一个 非常肤浅的标签,不足以表示二者之间那种离奇古怪而又很不吉祥的对比 。我的房子紧靠在鸡蛋的顶端,离海湾只有五十码,挤在两座每季租金要 一万二到一万五的大别墅中间。我右边的那一幢,不管按什么标准来说, 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诺曼底某市政厅的翻版,一边有一座簇新的塔 楼,上面疏疏落落地覆盖着一层常春藤,还有一座大理石游泳池,以及四 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位姓 盖茨比的阔人所住的公馆,因为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光生。我自己的房子实 在难看,幸而很小,没有被人注意,因此我才有缘欣赏一片海景,欣赏我 邻居草坪的一部分,并且能以与百万富翁为邻而引以自慰——所有这一切 每月只需出八十美元。 小湾对岸,东卵豪华住宅区的洁白的宫殿式的大厦沿着水边光彩夺目 ,那个夏天的故事是从我开车去那边到汤姆·布坎农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 上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远房表妹,汤姆是我在大学里就认识的。大战 刚结束之后,我在芝加哥还在他们家住过两天。 她的丈夫,除了擅长其他各种运动之外,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伟 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也可说是个全国闻名的人物,这种人二十一岁 就在有限范围内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免有走下坡路的 味道了。他家里非常有钱——还在大学时他那样任意花钱已经遭人非议, 但现在他离开了芝加哥搬到东部来,搬家的那个排场可真要使人惊讶不已 。比方说,他从森林湖运来整整一群打马球用的马匹。在我这一辈人中竞 然还有人阔到能够干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为什么到东部来,我并不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在 法国待了一年,后来又不安定地东飘西荡,所去的地方都有人打马球,而 且大家都有钱。这次是定居了,黛西在电话里说。可是我并不相信——我 看不透黛西的心思,不过我觉得汤姆会为追寻某场无法重演的球赛的戏剧 性的激奋,就这样略有点怅惘地永远飘荡下去。 于是,在一个温暖有风的晚上,我开车到东卵去看望两个我几乎完全 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料想的还要豪华,一座鲜明悦目,红白 二色的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厦,面临着海湾。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 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甲,一路跨过日文、砖径和火红的花园——最后跑 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爽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 往上爬。房子正面有一溜法国式的落地长窗,此刻在夕照中金光闪闪,迎 着午后的暖风敞开着。汤姆·布坎农身穿骑装,两腿叉开,站在前门阳台 上。 从纽黑文时代以来,他样子已经变了。现在他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时 体健壮,头发稻草色,嘴边略带狠相,举止高傲。两只炯炯有神的傲慢的 眼睛已经在他脸上占了支配地位,给人一种永远盛气凌人的印象。即使他 那会像女人穿的优雅的骑装也掩藏不住那个身躯的巨大的体力——他仿佛 填满了那双雪亮的皮靴,把上面的带子绷得紧紧的。他的肩膀转动时,你 可以看到一大块肌肉在他薄薄的上衣下面移动。这是一个力大无比的身躯 ,一个残忍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又粗又大的男高音,增添了他给人的性情暴戾的印象 。他说起话来还带着一种长辈教训人的口吻,即使对他喜欢的人也样、因 此在纽黑文的时候时他恨之入骨的大有人在。 “我说,你可别认为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是说了算的,”他仿佛在 说,“仅仅因为我力气比你大,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们俩属于同一 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然而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总觉得他很看重我, 而且带着他那特有的粗野、蛮横的怅惘神气,希望我也喜欢他。 我们在阳光和煦的阳台上谈了几分钟。 “我这地方很不错。”他说,他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 他抓住我的一只胳臂把我转过身来,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指点眼前的 景色,在一挥手之中包括了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型花园,半英亩地深色的、 浓郁的玫瑰花,以及一艘在岸边随着浪潮起伏的狮子鼻的汽艇。 P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