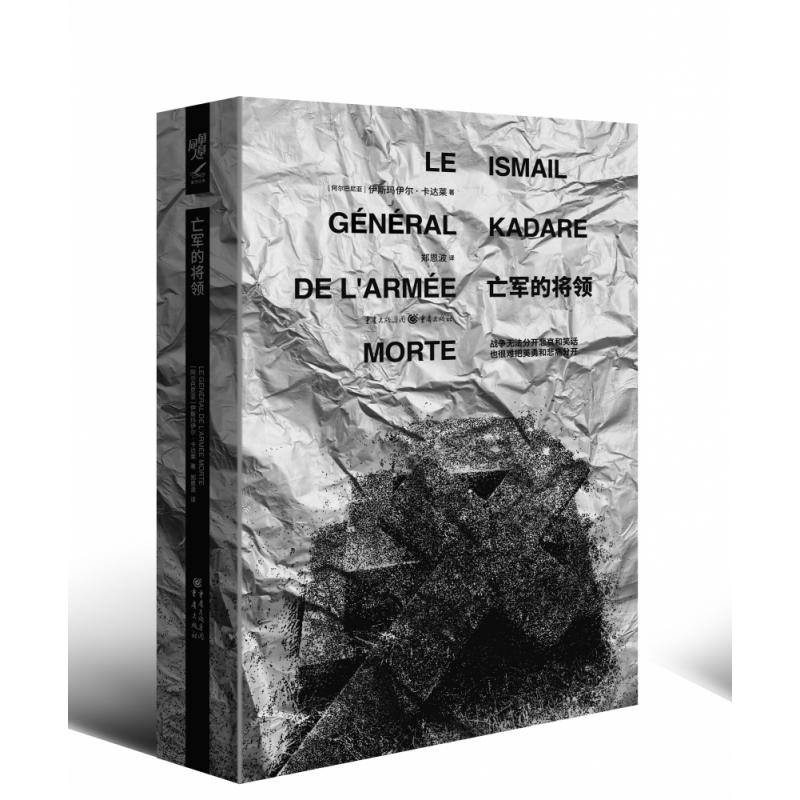
出版社: 重庆
原售价: 59.80
折扣价: 37.10
折扣购买: 亡军的将领(精)
ISBN: 9787229150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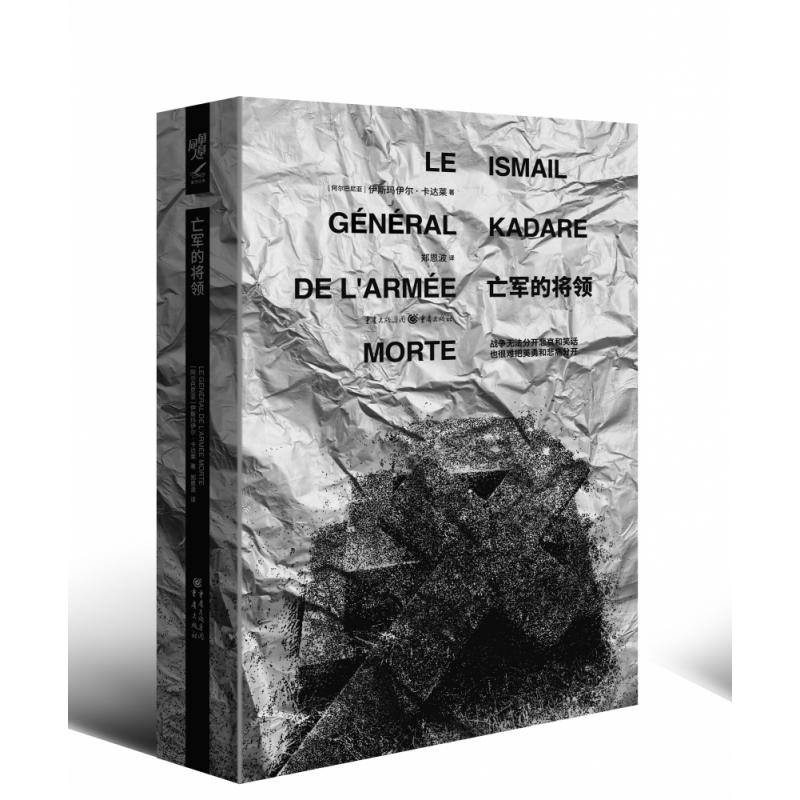
作者伊斯玛伊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作家、诗人。1936年卡达莱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城市吉诺卡斯特。1954年他以诗集《青春的热忱》初登文坛,此后创作了《群山为何沉思》《山鹰高高飞翔》《六十年代》等,在诗坛独领风骚。1963年,他的首部小说《亡军的将领》问世,在法国名声大振。之后创作了《雨鼓》《石头城纪事》《破碎的四月》《梦幻宫殿》《阿伽门农的女儿》《金字塔》等代表作。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共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著名文学奖,包括2005年的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2009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2015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奖、2019年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等,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 译者郑恩波,作家、翻译家、记者,辽宁盖州市人,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留学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精通阿尔巴尼亚语,并多次为中、阿两国高级领*人任翻译。代表作有《亡军的将领》《阿果里诗选》《破碎的四月》等译著,《阿尔巴尼亚文学史》等学术专著。2019年,郑恩波被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授予 “纳伊姆·弗拉舍里”勋章,以表彰其在发展中阿友谊与文化交流事业中做出的特殊贡献。
第一部 第一章 雨夹雪洒落在异国的土地上,打湿了用混凝土铺就的飞机场跑道、建筑物和人群。它浇灌平原和山丘,在公路黑黝黝的柏油路面上闪烁出白光。如果不是秋初,除了刚刚到达这里的将军之外,任何人都会觉得这场单调的雨是一种痛苦的巧合。为了将在最近一次战争 中阵亡、散葬在阿尔巴尼亚全国四面八方的军人的遗骨运回国内,这位将军从一个国家来到了阿尔巴尼亚。 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春天就开了头。但是,最后的协议直到八月末才签字,恰好碰上雨季开始了。时逢秋天,这雨可是有个下头呢。这一点将军是晓得的。出发之前,他了解了有关阿尔巴尼亚的许多知识,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气候也掌握了一点常识。将军知道,阿尔巴尼亚秋天阴霾多雨。然而,假如他读过的书上真写着阿尔巴尼亚秋天阳光充足,气候干燥,面对这场雨他也不会觉得突然。事情恰恰相反,原因在于他总是觉得,只有在雨中他的使命才能完成。也许这是受书籍或电影的影响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乘机旅行和阴愁多雨的时日,都给他增加了思乡恋故的心绪。 他从机窗向外望去,长时间地俯瞰群山万壑威严可怕的景色。锋利的山尖,仿佛随时都要划破机腹。处处都是陡峭的土地,将军自言自语地说。在这片土地上,似乎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在群峰众谷当中,他将在这儿召集起来的士兵,时而穿破云雾,时而又被云雾淹没,向雨中涌去。霎时间,他觉得完成这一使命是不可能的。可是,后来他又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怀着自己肩负这一使命的豪情,竭力同群山那种可怕而充满敌意的景观展开搏斗。在他的国家,成千上万的母亲在等待着她们儿子遗骨的到来。他将把遗骨运回去还给她们,完成他那伟大而神圣的任务。他将不惜任何代价。任何一个阵亡者都不应当被忘记,他们的身躯绝不能留在异国。啊!这可是一项崇高的使命!旅途中,他几次重复出发之前一位伟大而可敬的夫人对他讲的话:“您将像一只高傲而孤独的鹰,在那可诅咒的悲剧性的山峦上空飞翔,您将把我们那些苦难的小伙子,从它们的咽喉里和爪子下拯救出来。” 而现在,旅行即将结束,当把群山甩在后头,先在峡谷里而后又在平原上空飞行的时候,将军觉得轻松自在极了。 飞机在湿漉漉的跑道上降落了,跑道两侧亮起了许多盏时而红时而绿的灯。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士兵出现了,接着又出现一个。在机场建筑物前面,几个穿风雨衣的人向正在停下来的飞机走来。 将军第一个下飞机。他的后边是陪同他的神父。湿润的秋风强有力地扑打在脸上,于是他将衣领竖了起来。 一刻钟以后,他的汽车飞快地向地拉那驰去。 将军把头朝神父那边转过去,神父正默默无声地朝车窗外面张望。他的脸是冷淡的,毫无表情。将军懂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他说,于是便点着了一支香烟。然后,他又向外边望去。玻璃上满是雨水,因此在他看来,异国土地的外貌便打了卷儿,歪歪扭扭地变了形。 远处传来了火车头呜呜的鸣叫声,将军竭力想弄明白火车是从什么方向通过,从他这边还是从神父那边。火车是从他这边通过的。他的目光随着火车而去,直到它消失在雾气中。然后,他朝神父那边转过头去,可是,神父的脸是冷淡的,毫无表情。将军再次感觉到,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他说。他甚至还想到,再也没有什么可想的了。旅行途中,他把一切事情都考虑过了。现在,他累了,最好别再去打任何新的主意。足够了,最好还是照照小镜子,看看自己的军容是否整齐吧,这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呢。 他们抵达地拉那的时候,天色已晚,雾气笼罩在楼房、街灯和公园里光秃秃的树木上空。将军活跃起来了。他从车窗向外望去,看见许许多多的行人正在雨中急急忙忙地朝前赶路。这里伞可真多呀,他想。他想对神父说点什么,因为默默不语使他感到寂寞,不过,他并不晓得跟神父说什么才好。从他坐的那侧,他看到了一个教堂,再远一点,还看到了一个清真寺。在神父那边,耸立着尚未竣工的楼房,四周围着施工用的脚手架。安装着红眼睛一般的灯盏的起重机,如同妖魔在雾气里活动。将军把教堂和清真寺指给神父看,但是,神父对此毫无兴趣。这说明让另外的事情使他产生兴趣是困难的,将军在思考。现在,即使他有点兴趣,也没有交谈的对象。阿尔巴尼亚的陪同者坐在神父前面。在机场迎接他们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议员和部里的代表乘另一部车跟在后边。 在“达依迪宾馆 ”,将军自我感觉不错。他走进他的房间,刮了脸,换下了军装,然后下楼来到前厅,要了国际长途,同家里通了话。 将军、神父和三个阿尔巴尼亚人在一张桌子旁坐好,谈论起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来。他们回避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话题。将军异常严肃、殷勤,神父说话不多。将军摆出一种架势,让人明白他才是主角儿,尽管神父说话较少。他讲述了人类所建立的与埋葬士兵有关的美好传统,提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说起他们在战斗的空闲时间里,举行极为隆重的葬祭仪式。将军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感到欢欣鼓舞,心想他将非常出色地完成这一重要而神圣的使命。成千上万的母亲在等待着她们的儿子,她们已经等了二十多年。确实如此,这种等待同她们期盼自己的儿子活着归来是不一样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死者也能被人期盼,受到迎接。他要把许许多多儿子的尸骨送到母亲手里。当年,那些愚蠢的将领不会率领他们作战。将军对自己担负这一使命感到很自豪,要竭尽全力去完成。 “将军先生,有您的电话……” 将军神气十足地站了起来。 “先生们,请原谅!”他步履威严、大步流星地向宾馆门口的服务台走去。 他又迈着同样威严的步子走回来,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神父、将军和三个阿尔巴尼亚人坐在桌旁喝着白兰地酒和咖啡。谈话变得更加热烈,将军再一次摆出一种架势,让别人懂得他才是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角儿,这是因为,神父虽然有上校军衔,但在这种场合,他只是一个魂灵的代表。将军是主角儿,想谈什么,就把话题在哪个领域里展开。各类品种的白兰地、世界各国的首都、各式各样的香烟全谈到了。在宾馆这间挂着沉重窗帘的大厅里,听着异国甚至比异国音乐还有情趣的音乐,将军自我感觉真是妙极了。他总是迷恋文明,贪图舒适享乐,到其他国家旅行已成为一种嗜好。旅行使他想念起家里十分美好的安逸生活。在这种国际性的宾馆里,在遥远的航线上,在飘扬着各种国旗的港口,在外国的语言当中,每一点都很吸引人。 将军感到兴奋,特别的兴奋。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喜悦的波浪,为什么能卷到他的身边。这是一个在糟糕的天气里完成了一次危险的旅行,并且找到一个安身之地的旅行者的喜悦。那小小的黄黄的白兰地杯,将群山那淡绿色的撩拨人心的容颜,越来越快地从他的面前驱散了。现在,这酒杯正在桌子上一次又一次地骚扰着他。“简直就像一只骄傲而孤独的鹰一样……”突然,他觉得自己变得孔武有力。成千上万的士兵的遗体埋在地下,那么多年来一直在等待他的到来。现在,他来了,要把他们从泥土中取出来,送给他们的父母和亲属。他用地图、名单和准确无误的记录把自己装备起来,好似一个年轻的基督。其他的将领,曾率领一望无尽的队伍走向失败,走向毁灭。而他来到此处,却是要拯救他们当中存留下来的一点点东西,使它们摆脱被忘却和溃亡的境地。他要在墓地辗转逗留,仔细巡视每座坟墓。他要在当年的战场上到处转悠,以便找到所有的失踪者和遗失者。在与泥巴的搏斗中,他不承认会有失败,因为他是用精确的统计学的魔力武装起来的。 他代表一个文明的大国,因此他的事业应该是宏伟的。他的事业,有着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伟大之处,有着荷马史诗中的安葬意味。啊!你们这些手里擎着伞的阿尔巴尼亚人,将会怎样的目瞪口呆啊! 将军又回敬了一杯。从这天夜里以后,每一天,每个晚上,在他遥远的祖国,所有期盼亲人尸骨归来的人,都将这样谈论他:他现在正在寻找呢。这会儿我们到电影院看电影,到饭店美餐,去散步,可他却在异国他乡四处奔波,任何一个小地方都不放过,寻找我们惨遭厄运的儿子们。噢,这工作太繁重了,不过,他知道怎么干。人家不会瞎派他去的。 愿上帝帮他的忙吧! 第二章 镐头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神父画着十字,将军以军礼回敬,公用局的老工人高高地抡起镐头,反复朝地上刨下去。 也就是说,寻找士兵遗骨的工程开始了。将军心神惶遽,两眼望着在他们脚下叽里咕噜滚动着的第一批湿漉漉的土块。这是他们挖掘的第一座坟,大家像冻僵了的冰人似的团团围在那里。他在自己的本子里写道:阿尔巴尼亚专家是一位黄头发、瘦脸盘的俊小伙。公用局的两位工人吸着香烟,第三位工人叼着烟斗,而最年轻的那一位,倚着镐把,以一种若有所思的眼神观望着。他们需要学习挖掘遗骨应遵循的程序,所以都站着观看第一座墓的挖掘过程。 将军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工人脚下逐渐增高的一堆土块。黑黢黢、软乎乎的土块散发着雾气。 瞧,就是它,异国的土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土地跟任何土地都一样,那黑黑的泥巴与任何地方的泥巴也相似;土壤中那些小石头,那草根,还有那雾气,也都毫无二致。然而,尽管如此,它们毕竟是异国的。 在他们身旁的公路上,不时地响起飞驰的汽车的鸣叫声。一般说来,士兵的墓都修在公路旁。他们挖掘的墓也是这样。在离公路稍远一点的地方,牛群正在吃草,它们那零星的哞哞叫声在沟谷里安然地回响。 将军稍微受到一点震动。一堆土块在逐渐加高,一刻钟以后,挖掘工的膝盖就给挡上了。其中一个挖掘工用锹清除堆积起来的黏泥巴,休息了几分钟,然后又跳进坑里。 一群野鹅在天空高高地飞翔着。 一个孤单单的农夫拉着缰绳牵着马,正从公路上走过。 “祝你们工作顺利!”农夫说道,看来他并不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活计。围在坟墓周围的那些人谁也没搭讪,于是农夫便向前走去了。 将军时而望望挖出的泥土,时而瞧瞧阿尔巴尼亚掘土工的脸色。他们脸上的表情安详而严肃。 他们在想什么呢?将军暗暗对自己说。这五个人要把整个军队从坟里挖出来,他们爱干这个活儿吗? 可他从掘土工的脸上什么也弄不明白。其中的两个人各自点起一支烟,第三个人抽烟斗。另外一个最年轻,继续倚着镐把站着,看得出来,他的心思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这会儿,年长的那位工人跳进齐腰深的坑里,专家在向他讲解一点什么。他们谈了一阵子,工人重新挖了起来。 “说了些什么?”将军问道。 “我没听清楚。”神父说。 所有的人都默默无声地站着,好像在参加什么人的葬礼似的。 “幸运的是雨季还未开始,这真是太好了!”神父说。 将军举目向前望去。地平线湮没在云雾中。在遥远的地方,弄不清楚是山峰高高地耸入天际,还是团团云雾悬在空中。 挖土的那位工人把土挖得更深了。将军望着他那银灰色的头发;那头发随着镐头凿地的节奏摆动着。将军觉得他很像哥白尼,真是莫名其妙。 显而易见,他是一位蛮有经验的工人。将军心里琢磨着。他们决定让他当挖掘队负责人,这可不是盲目行事。将军满心希望工人挖得再快些,尽早打开坟墓,尽快地找到那些阵亡者。工人刚刚开始挖,他就无法忍耐了。他多么想一掏出名单,上面就满是红十字,而每个红十字就是一名找到的士兵啊! 现在,镐头凿地发出的响声已经来自很深的地方了,这声音好像是从大地的最深处传出来的。将军突然觉得有一个警报传遍了他的全身。 假如阵亡的士兵不在这儿呢?将军在想心事。如果图纸不准确,为了寻找一个士兵,我们被迫要在两处、三处、十处去挖掘,那可如何是好? “如果我们挖不出什么呢?”将军对神父说道。 “那我们就重新挖,付出双倍的代价。” “这事不在乎钱,重要的是我们得挖到。” “应当挖到。”神父说,“我们不可能挖不到。” 将军心神不安地望了望他的表情。 “这里给人的印象是,从来就没发生过战斗。”将军说,“只有那些咖啡色的母牛在这儿放牧过。” “这是后来经常给人留下的印象。”神父说,“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这倒是真的,过去很长时间了,所以我才担心。” “您为什么要担心?”神父说,“这里的土质很稳定,里边埋了什么东西,可以保存许多许多年不坏。” “对,是这样。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相信他们就埋在这附近,在我们脚下只有两米深的地方。” “您不相信?那是因为战争期间您从未来过阿尔巴尼亚。”神父说。 “可怕吗?” “可怕。” 现在,年长的那位工人几乎全身都埋进了土坑里,围着他的其他人距离更近了。阿尔巴尼亚专家俯到坑边,一边用手对他指着什么东西,一边不停地说话。 土里净是一些小石头,碰到铁锹,发出一种混浊不清的响声。将军回忆起在他出发之前那些老战士对他讲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故事。为了表达对阵亡在阿尔巴尼亚的同伴的坟墓的关心,他们曾多次去过将军家里。 我的短剑撞击在小石头上,同它们摩擦,发出一种令人战栗的声音。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朝土块劈去,可是面对这种泥土,我的剑是无能为力的。费了好大劲儿它才劈下拳头大那么一块泥巴,我自言自语道:我若是在工程兵队伍里服役,随身携带一把铁锹,很快很快地挖土该有多好。因为我最亲密的伙伴就死在这附近,他的腿长拖拖地甩在一个水沟里,脑袋朝下呛着水。我把他的短剑也从他的腰上拔下来,开始用两只手同时挖土。我想给他挖一个深坑,因为这是他生前的愿望。他常跟我说:“假如我死了,可要把我深深地埋好,因为我害怕,可别让狗和胡狼把我扒出来,就像在戴佩莱那 发生的可怕的事情那样。你还记得在戴佩莱那狗干了些什么吗?”“我记得。”我吸着烟对他说。而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一边挖土,一边对自己说:“你别担心,我要把坑挖得深深的,很深很深。”挖完坑把他埋了之后,我又竭尽所能地把上面弄得平平的,不留任何一点痕迹,连一块石头也没有。因为任何痕迹都会使他害怕,他怕人们痕迹把他找到,将他从土下面再拽出来。夜色中我朝着与机*相反的方向朝前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望着黑暗中我埋好的伙伴,心里想:别害怕,人们是没法找到你的。 “从迹象看,我们什么也找不到了。”将军说时,竭力掩饰心中的火气。 “难说。”神父说,“希望还是有的。” “战争中埋葬死者的坑挖得都挺浅的。” “也许是埋了第二次。”神父说,“埋葬第二次是常有的事,甚至还有埋葬第三次的。” “也许是这样。不过,如果葬得深的话,我们就永远也结束不了这项工作了。” “我们还可以再雇另外一些临时工。”神父说,“在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再要二十个工人。” “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将军说。 “是的,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不知哪一天没准还可能要一百个呢。” “难说呀。” “不过,这五个我们是长期需要的。” “对。协议上是这么写的。” “可他们干了些什么呢?”将军说,“还是什么也找不到?” “现在挖的深度已到了极限。”神父说,“如果有,现在应该挖到了。” “我觉得这个头儿开得不顺利。” “也许是泥土移动了。”神父说。 阿尔巴尼亚专家弯下腰来,更加靠近土坑,别的人全都凑到他跟前来了。 “找到了。”年长的老工人说道。因为他低头在坑底下说话,所以声音听起来显得又远又不清楚。 “挖到了。”神父说。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公用局的工人一起动了起来,倚着镐把站着、若有所思的那个最年轻的工人,跟同志要了一支香烟,点火抽了起来。 年长的老工人开始用铁锹往外捡骨头。人们的脸上毫无害怕的表情。骨头与湿土粘在一起,看上去好像是一块块干木头混在了泥土里。刚刚掘开的泥土在四周散发着清香。 “消毒剂!”专家喊道,“把消毒剂拿来。” 两个工人朝停在路边的卡车跑去。那卡车就在小轿车后面。 专家在遗骨中间找到了一件小东西。 “瞧瞧这个挂在脖颈上的身份牌。”专家说道,手握一把钳子,把身份牌指给将军看,“请您不要动它。” 将军把脸靠近,去看这件小东西,好不容易认出了圣母玛利亚的头部。 “这是我们军人的身份牌。”将军慢条斯理地说道。 “你知道我们的脖子上为什么挂这么个身份牌吗?”一天他对我说,“有朝一日我们死了,好让人们找到我们的尸体。”他带着讥讽的意味说,“你以为人们真的会寻找我们的遗骨?好吧,就算他们会寻找,你以为这事就能安慰我?没有比战后寻找遗骨这种事更虚伪的了。我可不想让自己得到这种好处。别让他们到我将要倒下去的地方胡折腾了。说不定哪天我就把这个身份牌给扔了。”有一天他真的把身份牌扔掉了,成了身上没有身份牌的人。 经过消毒处理之后,专家将几块骨头逐一地量了一下,然后把铅笔夹在又细又长的手指中间,在本子里计算了一会儿。 “身长是一米七三。”专家说道。 “很准确。”将军查了一下名单,然后说道。 “把骨头包好。”专家对工人们说。 将军向一个工人望了一眼,走过去坐到道旁的一块石头上。他掏出烟盒,疲惫地点着一支烟。 “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看我?”将军自言自语道。 几分钟以后,地面上有五处同时被挖了起来。 每一部关于战争的小说,都有一个悲伤的主题。阿尔巴尼亚,始终和战争抵抗,与死亡同行,是惨烈的,也是悲剧性的,这个民族对战争、死亡、悲伤,有着深切而透彻的体悟。 《亡军的将领》讲述了一位意大利将军赴阿尔巴尼亚搜寻阵亡将士遗骨的故事,通过将军挖掘阵亡将士坟墓、寻找遗骨的过程串连起战争期间的各种故事,反映战争的惨烈与由此造成的悲剧,以及所有战争参与者的心态变化,再现了战争中复杂的人性,展示了阿尔巴尼亚的历史画卷和民族心灵史。 此外,故事套故事、链条接链条、环环相扣的叙事技巧,富于戏剧性、冷峻又不失幽默的笔法,赋予了《亡军的将领》很强的可读性,使其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杰作,从墓穴中目击战争也为人们认识战争带来了新的视角。 作者卡达莱是享誉世界的阿尔巴尼亚作家,2005年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米兰·昆德拉、 纳吉布·马哈福兹、大江健三郎等享有崇高声誉的国际作家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卡夫卡式的洞察力、昆德拉式的反讽、奥威尔式的犀利以及马尔克斯式的魔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