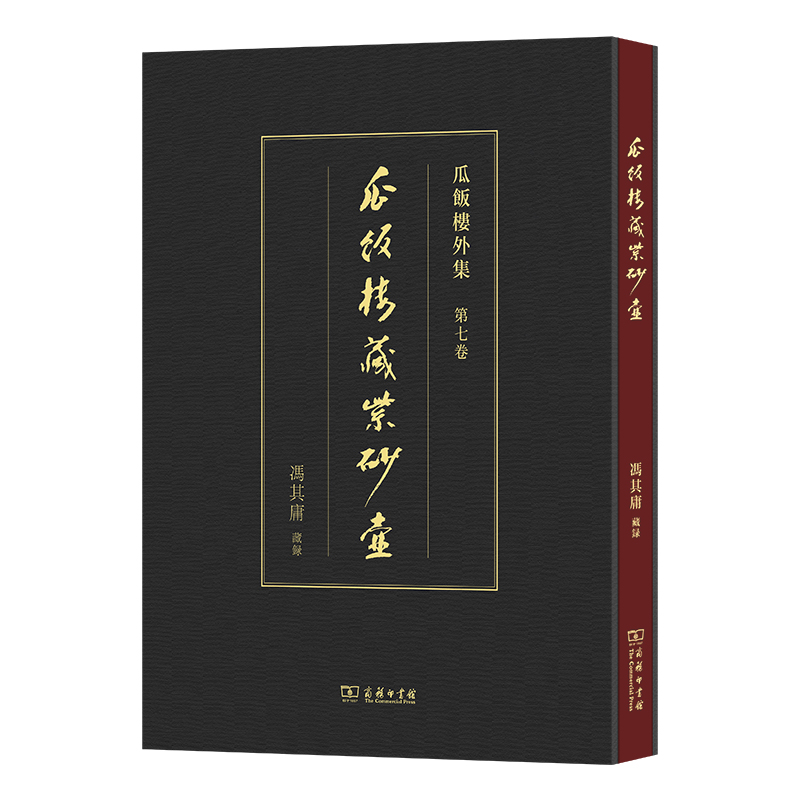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660.00
折扣价: 462.00
折扣购买: 瓜饭楼藏紫砂壶
ISBN: 97871002307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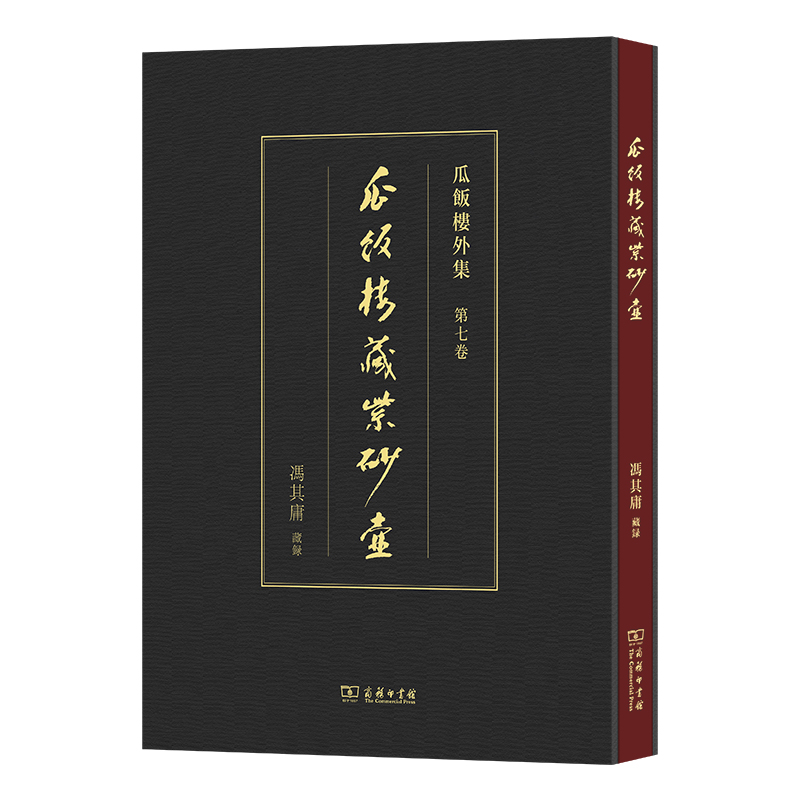
" 冯其庸(1924—2017),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人。著名红学家、史学家、书画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首任馆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 "
"一、 自序 我與紫砂大師顧景洲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認識了,顧景洲早期用的印章,是我的好友高石農刻的,由於高石農的關係,我們很早就認識了,那時顧景洲大約四十歲,我還不到三十歲。 一九五四年八月我調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我與顧景洲的交往暫時間斷了,但不久,宜興紫砂廠在北京有紫砂展銷等商業活動,顧景洲也經常來京,同來的還有紫砂廠廠長高海庚。有一次,顧景洲同高海庚一起來看我,我住張自忠路,這次,顧景洲鄭重對我説,他的徒弟中只有高海庚能傳他的絶藝。這時顧景洲的壺藝已是紫砂第一人了。這次,海庚還送我一把 他做的壺。海庚爲人樸誠信厚,我們一見如故。之後,海庚又送我一把他夫人周桂珍做的小方壺,我纔知道他夫人也是製壺高手。 後來,我又認識了紫砂雕塑藝術大家徐秀棠。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經常有機會到南方去,每去,我總要到宜興丁山去看顧老和海庚。不幸海庚突然患心臟病去世了,這是紫砂藝術的一大損失,幸而他的紫砂藝術,也是顧老的紫砂藝術,由他的夫人周桂珍繼承并發揚了。 那時,我每次去丁蜀鎮,都爲他們題紫砂壺,我是直接寫在壺上的,左手拿壺,右手執筆書寫,開始是爲周桂珍題壺,後來被大家看見了,就都來要我題壺,幾乎一寫就是半天或一整天。因此我也得到了他們不少饋贈,桂珍還特意爲我做了不少把壺。周桂珍現在已是紫砂藝術的『雙大師』,是顧景洲以後的第一人。 紫砂刻字最好的是徐秀棠,我寫的不少壺都是他刻的。他刻的壺燒好填墨後,稍遠一點看,就同我剛寫在紫砂壺上的墨迹一樣。當然,他的更高成就是他的紫砂人物雕塑,那是開拓了紫砂雕塑的新天地,他是這一領域的創始人。在這之前,雖也有紫砂雕塑,都還是游戲之作,遣興而已,從未被當作專項來從事創作。從徐秀棠開始,有了紫砂雕塑的專項藝術。秀棠也榮獲了『大師』的稱號。 紫砂上刻字的還有譚泉海,也是一流的功力,我寫的壺有一部分是他刻的。 宜興紫砂中的『花貨』,即摹寫果蔬之類實物形象的作品。當時年齡最大的作者是蔣蓉,與周桂珍同輩的是汪寅仙,蔣蓉已去世,汪寅仙後來也獲得了『大師』的稱號。 顧景洲先生後來改名『景舟』,他創作極嚴,一年只做幾把壺,每把壺做完後要反復看幾個月,纔拿去燒製。所以,直到他去世時,缸裏還有幾把已做好、未看够、未曾燒製的壺。 顧景舟大師以他的成就,成爲紫砂史上劃時代的人物。在此之前的紫砂壺,其藝術水準和製作的工細,從來未達到這樣的高度。其内在原因是他更具有文化素質。他在早期常與吴湖帆交往,現在還有一把吴湖帆爲他題的壺。但這把壺,現在看來,比他晚年的創作又有些差距了。 喜歡紫砂的人都推崇陳曼生的壺,其實陳曼生并不會製壺,他只是題字。他題字的壺大都是楊彭年做的,而楊彭年的壺藝并不是絶頂的。我有一把曼生壺,顧老晚年來京時鑒定過,他説這把曼生壺藝術極高,絶不是楊彭年做的。 現在,顧老的繼承人,自然就落到了周桂珍。這是純客觀的自然選擇,不是炒作出來的。舉個事實,前些年,桂珍爲我做了一把壺,我用來泡茶,無意之間,拿起壺蓋,把一壺茶都提起來了,我萬萬没有想到這把壺的精密程度會達到如此高境界,因爲這是古人傳下來鑒證紫砂壺精良程度的最高標準。上面所説的我藏的那把曼生壺,也能做到以蓋提壺。這可證周桂珍的壺藝早已達到古人最高的標準。我把這個情况告訴周桂珍,她説她做好了壺,自己覺得滿意了,燒好後就給人了,自己没用過,也就不知道有這個效果了。 我的藏品中,有幾把是高振宇做的,特别是那把大匏瓜壺,靈動而書卷氣,儒雅大方,真正表現了紫砂本身的文化素質。這是我藏的紫砂三大件之一。 我的紫砂藏品中,最奪人眼目的是秀棠大師給我做的紫砂大畫筒,口徑約三十多厘米,形如竹筒,在紫砂藝術中,這恐怕是空前的杰作,我把它視同拱璧。 還有周桂珍給我做的那把特大曼生提梁,那是壺件中的極品,即使是曼生來看了,也絶想不到有這樣的大器。 我平生的紫砂交游,都印刻在這些藝術品上,這都是傳世之作,因此我的紫砂情誼也會隨着這些名器傳之久遠。 本書的砂壺攝影都是汪大剛兄的精心杰作,若無此高妙攝影,則讀者無從鑒賞這些名壺的神韵,所以本書的砂壺原器與攝影可以妙合無間,故特爲奉告讀者。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寬堂九十又一於瓜飯樓 二、宜興的紫砂藝術 宜興紫砂,是中國傳統的茶文化和陶文化相結合的産物,是製陶工藝史上的一枝奇葩。 據現代考古所得,宜興鼎蜀鎮周圍有豐富的新石器時代以至於各代的陶器遺存,羊角山的發掘,更證實了從北宋中期一直到明初,已經開始用當地的紫砂製陶。 宜興歷來又是著名的産茶區,唐代詩人盧仝的名作《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説:『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陽羨就是宜興的古稱,此詩下半部分描寫喝茶的豪興: 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 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 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這一段文字,已成爲描寫飲茶的千古名句,殊不知它恰好是描寫飲陽羨茶的,由此可見陽羨茶聲名之高。 宋代大詩人蘇東坡有寫煎茶的名詩《汲江煎茶》云: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 大瓢貯月歸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忽作瀉時聲。 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 此詩短短八句,把汲水煎茶到茶熟而飲,一直到茶後不眠,坐聽夜更種種情事,寫得生動逼真。東坡晚歲曾買田陽羨歸隱,至今宜興東坡書院還有東坡買田碑的石刻,昔年我去書院曾親見。現在宜興紫砂中流行的東坡提梁,雖并非東坡實迹,但也足見詩人見愛於茶鄉兼陶都的人們了。 以上種種,都説明宜興於陶、茶二事,是得天獨厚、淵源極深的。 我家鄉無錫與宜興緊鄰,近年宜興與無錫又合爲一市,多年來我常去宜興鼎山、庚桑、善卷、慕蠡諸洞,東氿、西氿水區,國山碑,周孝侯墓,蛟橋諸名迹,都曾尋訪。我十分欣賞陽羨山水,尤其是從宜興到鼎蜀鎮的一段,真是風景絡繹,如行山陰道上,據説南山深處茶區,風景更爲清絶,無怪乎宜興會成爲人文之鄉了。 宜興紫砂自明供春、時大彬以來,盛名不衰,供春壺我只看過顧景舟老先生的臨本,大彬壺則看過幾件,書載大彬壺初期題刻係用竹簽畫刻,我在故宫看到過這樣一件用竹簽題名的大彬壺,現在此壺還陳列在珍品展覽室,實爲罕見的珍品,但是否爲真品,也待確證。大彬以下各家,我雖未能盡閲,但大都是親眼見過的。紫砂之得享盛名,一是因爲宜興鼎蜀鎮的紫泥優質獨絶,冠甲天下,無與倫比;二是歷代以來,工藝相傳,青出於藍;三是與文人結合,一握紫泥,詩畫題刻,琳瑯滿目,雖黄金美玉,無以過也。因此數端,宜興紫砂至今見重於世,珍貴勝於翠玉。當代的紫砂大師顧景舟先生,我與他論交已四十餘年,他的藝術,實在已臻紫砂的至高境界。論歷史,大彬、曼生等功不 可没,論工藝,則今天已是後來居上,顧老先生早已度越前輩了。我曾有詩贈顧老云: 彈指論交四十年。紫泥一握玉生烟。 幾回夜雨烹春茗,話到滄桑欲曙天。 然而,并不僅僅顧老先生孤峰獨秀,與顧老同輩的蔣蓉,以花器馳名天下,其所作瓜果草蟲,傳神文筆,妙絶一時。而顧老的傳人高海庚、周桂珍、徐秀棠也都是一時俊才,還有汪寅仙、徐漢棠、李昌鴻、顧紹培等,如群星燦爛,輝耀陶都。 其中尤以周桂珍的《曼生提梁》《井欄六方》《仿古如意》《僧帽》《追月》等壺,綫條端莊流暢,風格樸實凝重,呈現出大家風範,我也有詩贈云: 長空萬里一輪圓。憶得荆溪寒碧仙。 我欲乘風歸去也,庚桑洞外即藍田。 紫砂雕塑中,徐秀棠天南獨秀,一時無雙。他的作品傳神寫意,别具風韵。他的羅漢、八怪諸塑,早已是馳名宇内、洛陽紙貴了。秀棠還能書能畫,他的刻尤爲精妙,我近年在宜興所寫茶壺,大部分是秀棠所刻,能與我的字妙合無間。我在壺上的書法也大抵借重他的刻,纔得傳神,所以我也有詩贈他: 秀出天南筆一支。千形百相有神思。 曹衣吴帶今何在?又見江東徐惠之。 今以顧老的聲望功力,秀棠、昌鴻諸君的才思,編此一部大書,自然聚百代壺珍於一集,晴窗展玩,衆美畢備,如對古賢,如接今秀,其樂爲何如也!因樂爲之序云爾。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八日於京華雨窗,時蘇、錫、宜、常正在洪水包圍中也,遥望南天,不勝神馳 三、記陶壺名家顧景舟 去年我到美國講學,參觀舊金山博物館時,看到展品中有兩件中國江蘇宜興的陶壺,其中一件標明是清代名手時大彬製的。我拍了照片回來,經宜興紫砂壺的老工藝師、著名的製壺名手、紫砂壺的鑒定專家顧景舟同志看後,指出它是贋品,他説時大彬很少做這種菊花形的壺。一件贋品尚且被陳列在舊金山的博物館裏,可見紫砂壺是如何地被人珍視了。 這種馳名中外、享有盛譽的藝術珍品紫砂陶歷史悠久。根據對古窑址的發掘,可追溯到北宋中葉,距今已有千年。製壺的能手,自明清以來,名家輩出,代不乏人。明代最著名的有供春、時大彬、李仲芳、徐友泉等;到了清代,又有陳鳴遠、項聖思、楊彭年、陳曼生、邵大亨等名手。他們製作的茗壺,在今日已經成爲稀世之珍,爲收藏家所寶藏。 我與顧景舟同志相識已經十多年了,他在紫砂工藝上的成就是卓越的,在國内和國際上早已享有盛名。一件蓋有他的圖章的紫砂壺,在國際市場上就會成爲巨富們争奪的對象。景舟同志的作品所以能獲得這樣高的國際國内的聲譽,絶不是偶然的。他今年已經六十八歲,自幼就從事紫砂工藝,對紫砂工藝的全過程有十分精辟透徹的瞭解,精於鑒别古器,又工於造型設計。他分析品評傳品,往往片言中的,發人之所未發。我有兩件藏器,一直很珍視,也經幾位行家鑒定過,都是贊揚一通,稱兩壺不分高下,我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高下之分,但經過景舟同志的法眼,他一下就指出了兩個壺時代的先後,特别指出其中一壺在造型上的不足之處,而另一壺則骨肉亭匀、穩重沉静雅致,弧綫正反的結合十分諧和清秀,壺把和壺嘴自然渾成而又藏巧於拙,不見刻鑿痕迹。景舟同志對一件舊壺的分析評論,實際上反映了他對紫砂壺的全面而深厚的美學修養,這是與他具有很高的書、畫、金石、文物覽賞的修養分不開的。他與海内許多著名書畫家都有很深的交往。前面提到的明代的製壺名家時大彬,他的原作目前國内只有一件,而這一件珍品,是一九七五年在江蘇江都縣丁溝公社的一個明代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的墓葬中出土的,當時認爲是一把普通壺。顧景舟同志聞訊後騎了四十里路的自行車趕到丁溝,對這件茗壺做了十分精確的鑒定,指出它確是大彬壺無疑。不久前,我國著名的陶瓷專家馮先銘也明確地指出,國内真正可信的大彬壺,就只這一件,可見景舟同志鑒别之精。 五十多年來,景舟同志創作了數十種壺型,他善製素面光身,不事堆雕。實際上製壺藝術中,素面最難,因爲它全身綫條畢露,既無假借,亦無藏躲,完全靠造型美、綫條美、色調美來抓住觀衆。所以一件素面壺,一入鑒賞家的眼睛,就好壞立見。其精者,就如二王的書法,耐人尋味;其俗者,往往搔首弄姿,反而不成姿態。當然,我絶没有輕視『花貨』(以堆雕捏塑手法摹擬自然形態的器形)和『筋囊貨』(壺身處理成有規則的曲直綫條紋,如花瓣樣筋囊器形)的意思,這兩種壺形及其製作手法,也自有它們的獨到之處,所謂各有所長,不能相輕也。 一件佳壺,往往要形神兼備。所謂『形』,當然就是指造型、綫條;所謂『神』,就是通過結構匀稱、綫條流暢簡潔、製作精巧、色澤沉静幽秀等各個方面綜合形成的一種藝術氣質、藝術風格,它往往能引人入勝,叫人入眼難忘。景舟同志的作品,就能够做到形神兼備,令人看後不能忘懷。 景舟同志幾十年間帶了二十多個徒弟,其中水平較高的有十多人,現任紫砂陶廠的副廠長高海庚就是景舟同志最得意的傳人,他繼承了景舟同志的技法,設計和製作也能一絲不茍,而且亦能自出新意,創製佳作。景舟同志説,二十七年來,像小高這樣特别拔尖的人只有一兩個,可見人才之難。然而,我們畢竟已經有了一批紫砂特種工藝的優秀傳人了,這是值得慶賀的事。 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於北京 四、後記 我與紫砂藝術家的交往,從我還在家鄉無錫時算起,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我現今還藏有一把紫砂廠合作社時期的作品,那時『左』的風氣説來難以令人置信,那時紫砂壺上不准署個人的名字或印章,哪怕你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也不准留名。做完後,壺底只准蓋『中國宜興』一個公章,其他位置,都不准有個人的印記。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到宜興去,買了一把綫圓壺,就是這樣的作品,我一直用它泡茶,有一次,周桂珍來看到了這把壺,她説這是五十年代名家的作品,那時不准署名,哪怕是最有名的高手,也不准用私章。那是提倡無名氏的時代,有了個人名字,就是個人突出,就是個人主義。所以這把壺儘管是名家作品,但也只准蓋『中國宜興』一枚公章。這把壺總算被我保存了七十年,可以作爲時代的見證。 這本書裏收的一些紫砂名作,還有一些要向讀者説明的,我那把曼生壺,壺蓋上的款爲『維松』。顧景舟曾説過,這把壺不是楊彭年做的,比楊彭年的好得多。當時他未説下去,後來知道,當時爲陳曼生製壺的,并非只有楊彭年一人,故顧老的意思是説這是另一位比楊彭年水平更高的人爲陳曼生做的。但『維松』是何人,我一直未能考查出來。 我另有一把綫圓壺,是汪寶根的杰作。據説汪寶根製壺,自守極嚴,凡做得不滿意的,寧可把它毁了,也不讓傳世。我藏的這把壺,曾經名家品評,均推爲典範之作。還有一把馮桂林的菱花壺,其花瓣上下綫條準確,無絲毫差錯。最近,有友人用相機拍攝放大,其上下綫條凹凸交錯,儘管一小半在壺蓋上,一大半在壺身上,而壺蓋圓轉自如,停下來依然上下綫條只是一根綫,分不出上下截。這種手工的絶藝,允稱絶活,所以我一直珍藏着它。 從當代的紫砂大師中,我極賞周桂珍,前面序言裏提到她給我做特大曼生提梁,當時共做了三把,一把爲南京博物院收藏,一把爲我收藏。當時正值我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末,奉國務院外交部、文化部之特派,去蘇聯列寧格勒(今稱聖彼得堡)鑒定《石頭記》抄本,擔任專家組組長和中方發言人,蘇聯的《石頭記》抄本經過我們鑒定後,由我代表鑒定組做了結論性的發言,肯定了這個抄本,因此與蘇方達成了聯合出書協議。李一氓先生是全面策成此事者,蘇、我兩方聯合出書協議的簽訂,實際上是重開了中蘇政治對話的新局面。李一氓先生爲此大喜,寫詩贈我和李侃、周汝昌(後二位是小組成 員)三人,詩云:『泪墨淋漓假亦真。紅樓夢覺過來人。瓦燈殘醉傳雙玉,鼓擔新鈔叫九城。價重一時傾域外,冰封萬里識家門。老夫無意評脂硯,先告西山黄葉村。』我收到李老給我親筆手書的詩稿後,立即次其原韵,敬賀一首。詩云:『世事從來假复真。大千俱是夢中人。一鐙如豆拋紅泪,百口飄零繫紫城。寶玉通靈歸故國,奇書不脛出都門。小生也是多情者,白酒三杯吊舊村。』此詩隨即抄奉李一氓先生。這時,恰好周桂珍製成此特大曼生提梁,而且兩把已定出,我正在此時到宜興,幸運地得了最後一把。我立即把我奉和李一氓老的上述七律,寫在了壺上,由秀棠爲我刻寫。此事一時傳爲紫砂佳話。實際上這壺上還銘刻着一段當時中蘇復交的友好史話。 這把壺在京展出過,凡見到的人,無不高度稱贊周桂珍的壺藝和徐秀棠的刻工。以上一段特殊内情,我從未公布過。今已事過三十年,李一氓老及其他兩位俱已作古,就連當時蘇方主要參加談判的李福清、孟列夫也已作古。我趁此書之出,特將這一段紫砂佳話公之於衆,藉以懷念故去的諸友和李一氓老。 本書除叙跋及所附詩、文爲我所作外,有關紫砂壺的作者、刻者、壺件的評析等文字均爲我的助手高海英廣集前人資料所作。所以,特此説明并致謝。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夜於瓜飯樓,時年九十又一 " "一部紫砂壶文化的简史 镌刻陶艺大师与文化名家的百年情谊 。冯其庸先生的紫砂壶收藏,与一般的收藏不同,是深入参与紫砂壶制作,并与紫砂壶制作者关系匪浅。有的是自己题字,邀请名家为自己制壶;有的则是为制壶名家题字增辉。冯先生对紫砂壶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阐述。本书有助读者了解宜兴紫砂壶世家及其制作风格,还见证了冯先生与紫砂壶世家数代的交谊,犹如一部紫砂壶文化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