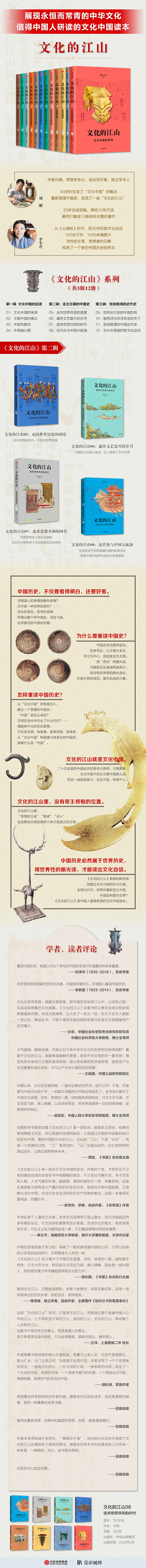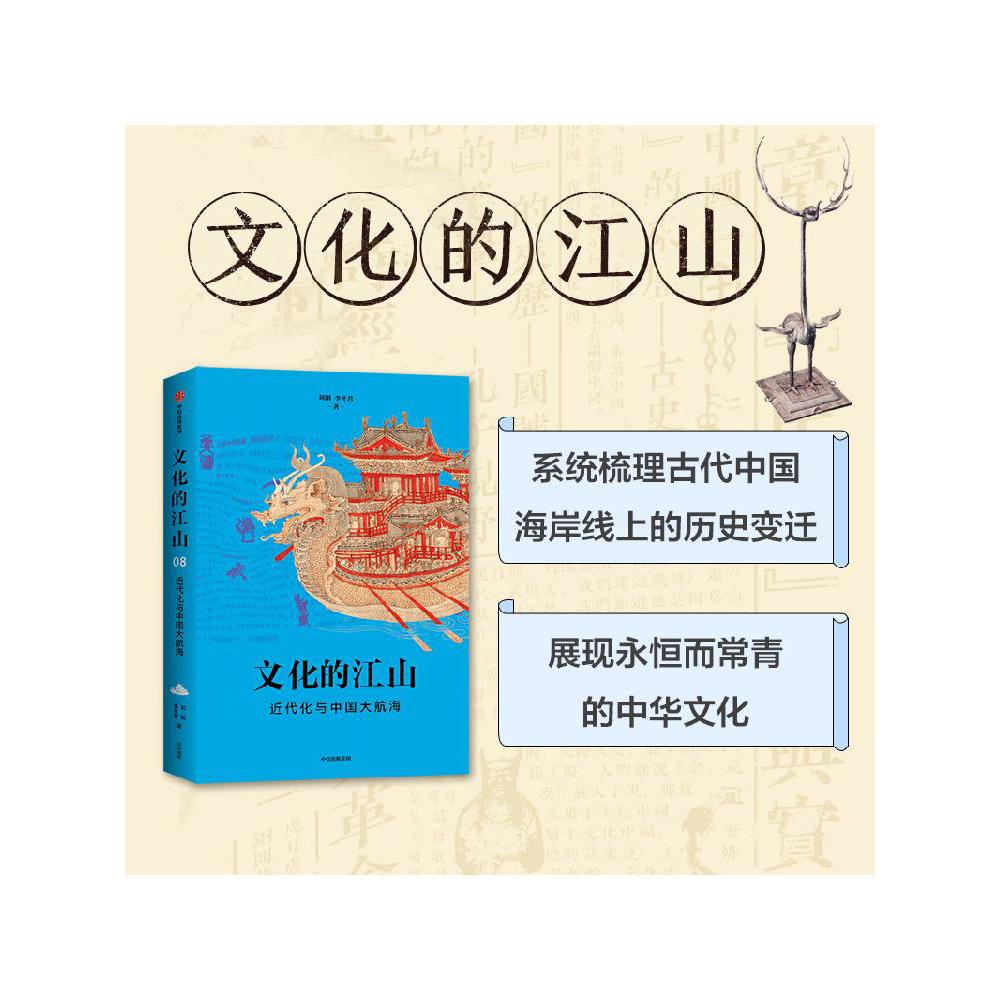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50.70
折扣购买: 文化的江山08:近代化与中国大航海
ISBN: 97875217497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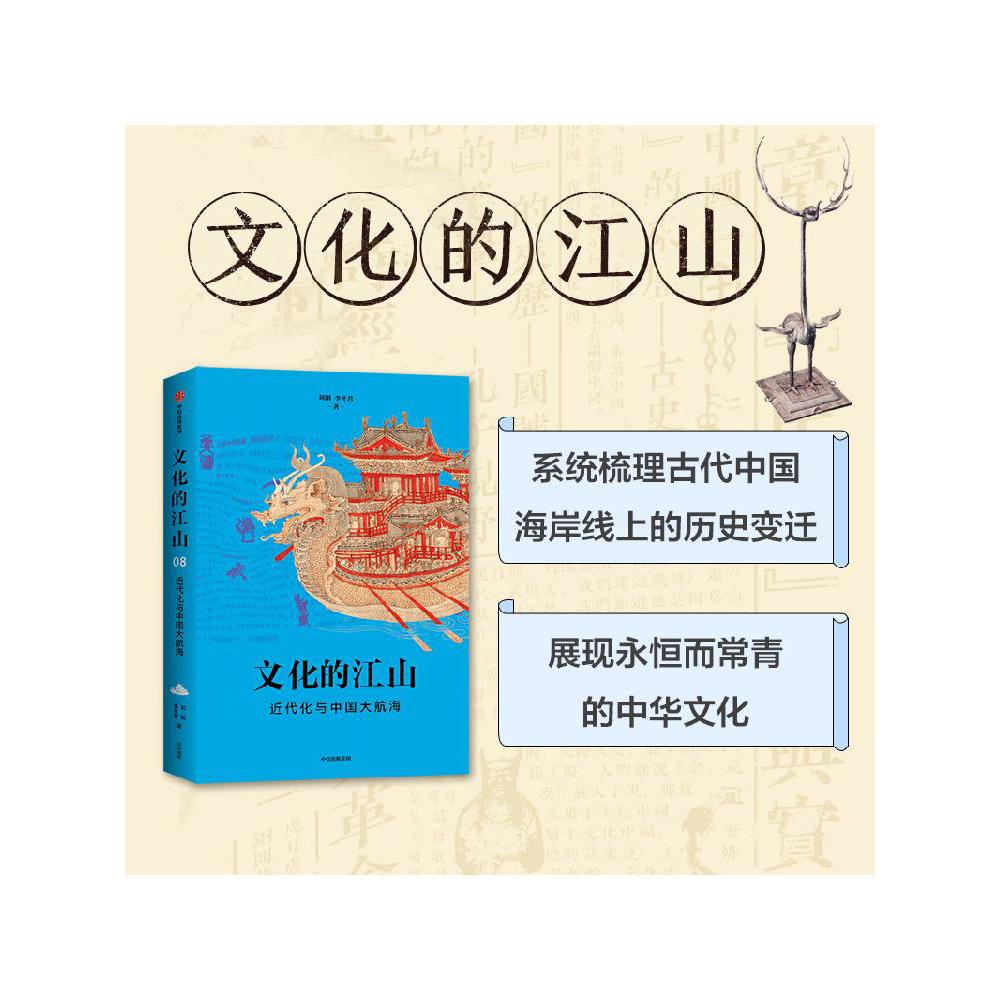
刘刚 自由写作者,独立学术人,以市场经济安身,在文化江山立命。主要著作:《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自由的款式》《中国近代的财与兵》《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回到古典世界》(以上均与李冬君合著),《中国史诗》。 李冬君 历史学博士,独立学者,主要著作:《走进宋画》《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乡愁的天际线》《思想者的产业》(合著)《载舟覆舟:中国古代治乱的经济史考察》(合著),译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叶隐闻书》。《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国家人文历史》《新京报》等媒体专栏作家。
一位大唐战俘的西海游历——重读杜环《经行记》 大唐航海DI一人,应该就是杜环吧。他不仅到过南海,还到过西海——地中海,他的书,就是那本《经行记》,其中所记录的国家,有许多就在地中海沿岸。 可《通典》引《经行记》仅有1511字,杜佑何以未将全书收入?他只节选了这千余字,致使近人岑仲勉阅之喟然而叹曰:杜君卿与环既同族,不将《经行记》全纳入《西戎典》,而使人莫窥全豹,是亦天壤间一恨事! 那杜君卿,也就是杜佑。杜佑介绍杜环是这样说的: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到西海。宝应初,因商贾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寥寥数语,才三十余字,对杜环参与“西征”后发生的事情,杜佑全不提,仅以“zhi西海”三字统言之,致使其本人记事亦如其书《经行记》之“原书已佚”,亦可谓“本末皆失”。 杜环失落大食国十余年,这十余年,杜佑只字未提,怎么说呢?一个战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还为大食所用,做了叛徒,那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ZHI于他为什么回来,回来以后又去哪儿了,何以销声匿迹,且不知所终,这些问题,应该问一问的。 荣新江在《记唐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一文中,提到了“杨良瑶之选择广州作为出发地,也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了解杜环在阿拉伯地区的见闻和他回程所经的海路情况”。怎么了解?是面谈吗?跟谁面谈?是跟杜环谈,还是跟杜佑谈? 杜环回到广州是在公元762年,杨良瑶出使大食是在785年,其间已过二十多年,如果杜环还在,那就证明他已定居广州了,可杜佑明明说杜环“自广州而回”,那个“回”字表明,杜环回原籍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时杜佑正在广州,任广州刺史和岭南节度使,如果两人见面,这种可能性很大,不见反而意外。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断定,杨良瑶出使有可能随身带着《经行记》,作为他下西洋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的指南。 大唐开疆拓土,有两本游记起了重要作用:一本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大唐定西域提供指南;另一本就是杜环的《经行记》,为大唐向西海做了参考。前者进取陆疆,为大唐盛世开光,后者开拓海洋,把东亚和西亚用政治和贸易联系起来。连汉唐盛世也没做到的,却被逆势的唐中期做到了,千军万马没做到的,被一本游记做到了。 杜环归来是个意外。怛逻斯之战后,他是死是活,已无人晓。也许杜佑会去高仙芝那里追问,高亦定是无可奉告。过了十来年,某一天,他突然回来了,除了给家人一个惊喜,也要给国家一个交代,将十来年的行迹说个明白,也许这就是《经行记》一书的由来。由于原书已佚,我们无法从杜佑引用的资料里确认其行迹,好在宋岘有一篇《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用阿拉伯文献做参照,将《经行记》的行迹考述出来。 宋岘追寻杜环在大食国的历程,可他的目光却转向一位大食人。那人就是大食国东道使艾布·穆斯林。此人在推翻倭马亚王朝过程中立有殊功,阿拔斯王朝创立之初,他手握重兵,也就是那支打败高仙芝军团的呼罗珊大军。 战俘的命运跟着财宝的线索走,先是跟着艾布·穆斯林走,于是,艾布·穆斯林所在的位置就成了确认杜环行迹的坐标;然后跟着阿拔斯王朝走,从呼罗珊走向亚俱罗,走到巴格达去。在王朝的动向里,杜环的行迹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宋岘对杜环在大食国的历程所提供的线索吧。他一上来就提到末禄国,为什么?张一纯笺注曰:此地为呼罗珊首府,黑衣大食之发祥地,艾布·穆斯林的故里。对艾布·穆斯林来说,还有比这里更重要的地方吗?他本应将这批中国财宝和中国人才送到亚俱罗去,献给阿拔斯王,为王所用,可他没这么做,他觉得自己作为阿拔斯王朝的开创者,有权享用这些来自中国的人、财、物。于是,他把那些人、财、物,全带到自己老家,留为己用。他的军队沿着阿姆河向西行,先从撒马尔罕即康居到达亚梅国,再从亚梅国到达末禄国。 杜环在末禄待了多久?据宋岘推算,大约待了六年。这六年中,阿拔斯王朝换了四任东道使,加强了对呼罗珊军队的控制。杜环被俘以后,加入呼罗珊军,适逢西边摩邻国动乱,阿拔斯王朝征调呼罗珊军前往讨伐,杜环就成了一名随军记者。 《经行记》就是对漫漫征途所做的记录。宋岘认为,“《经行记》所言之地,皆应是杜环游历过的”。这样一说,就出了问题。拂菻国呢?他去过吗?应该没去过。因为拂菻国亦即拜占庭,“胜兵约有百WAN,常与大食相御”,为此,拂菻曾多次遣使大唐,从贞观到天宝的一百多年间,前后凡七次,其欲与大唐结盟,令大食两面受敌。 拂菻与大食“相御”,说明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杜环随军游历,不可能进入拂菻,故其关于拂菻的记载,除了“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一句,是无须进入其国界内,仅从外部就可以确认的地理位置,其余就是“鬼市”与“女国”之类的传闻。 此外杜环所言各国均在大食势力范围内,应该是他亲历过的。杜环随呼罗珊大军从末禄往摩邻国去,他发现“从此zhi西海以来”,波斯人和大食人“参杂居止”。因为大军走的是呼罗珊大道,它不光是一条连接和平城——巴格达到呼罗珊的有邮传驿站的官道,还是一条连接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历史通道。 这一路行来,杜环涉猎了文明古国的两个源头:一个是亚俱罗所在地的西亚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源此;还有一个就是北非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源此。 在古巴比伦文明的遗址上,一个新的帝国正在冉冉升起,那就是大食国。在《经行记》“大食国”里,杜环如是说,“大食一名亚俱罗”。但“大食”又是什么?张一纯笺注,诸说之中有这样一说:“阿拉伯”的意思为“明哲”,而波斯语则将“明哲”称为“大食”,中国人因波斯而知有“阿拉伯”,故因袭波斯人的称谓。当然,这是从文明上来说的,把大食说成了一个“明哲”的国度,这样的国度要建立在做学问上、求知上,一如其国之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只此一句,便道出大食对中国的向往。 1. “文化中国”史观: “文化中国”史观是一个创新的提法,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带来新鲜的视角和很多可能。历来写史,多以王朝为本位,以宫廷政治和帝王权谋为主线,被王朝史观牵引进王朝中国的历史。王朝中国不过历史表象,文化中国才是历史本体。摆脱二十五史里的王朝中国,深入文化江山的本体,重读中国历史,发现一座丰富的文化的江山。 2.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本书述评文章,一套建立文化自信的文化中国读本: 《文化的江山》系统又鲜活地挖掘出文化中国的巨大价值,这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在重新定义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时,每个中国人应该研读的文化中国读本。 3. 有故事,有灵感,有思想,有体系,呈现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航海景象: 不仅有人们熟知的郑和下西洋、王安石变法,还包含了不常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汪大渊的世界环游、宋代海外贸易、朱棣的海权思想和秦汉海上活动,生动讲述沿海文化与内陆文化的相互影响,以及阿拉伯人、欧洲人与古代中国互动的大航海。 4. 中西对比研究: 作者把通常割裂开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将罗马帝国地中海沿岸的庞贝古城与中国南海边上南越国番禺城对比,寻找其内在相通相连的一脉。 5. 满含对国史的温情与敬意。 哲思深长,底蕴丰盈,感情浓烈,文气飞扬,典故文献信手拈来,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满含对国史的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