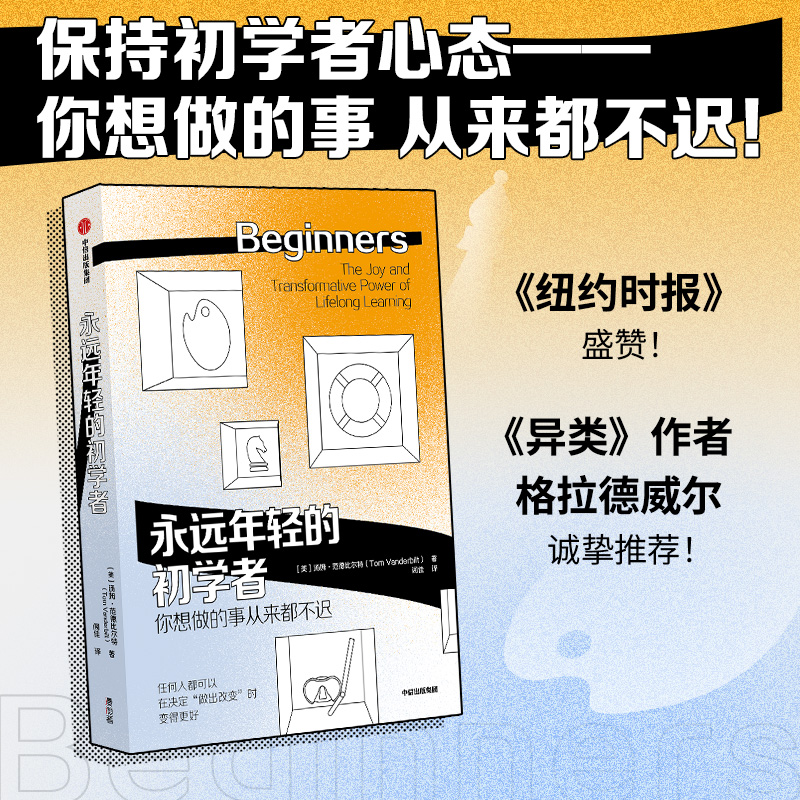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永远年轻的初学者
ISBN: 9787521748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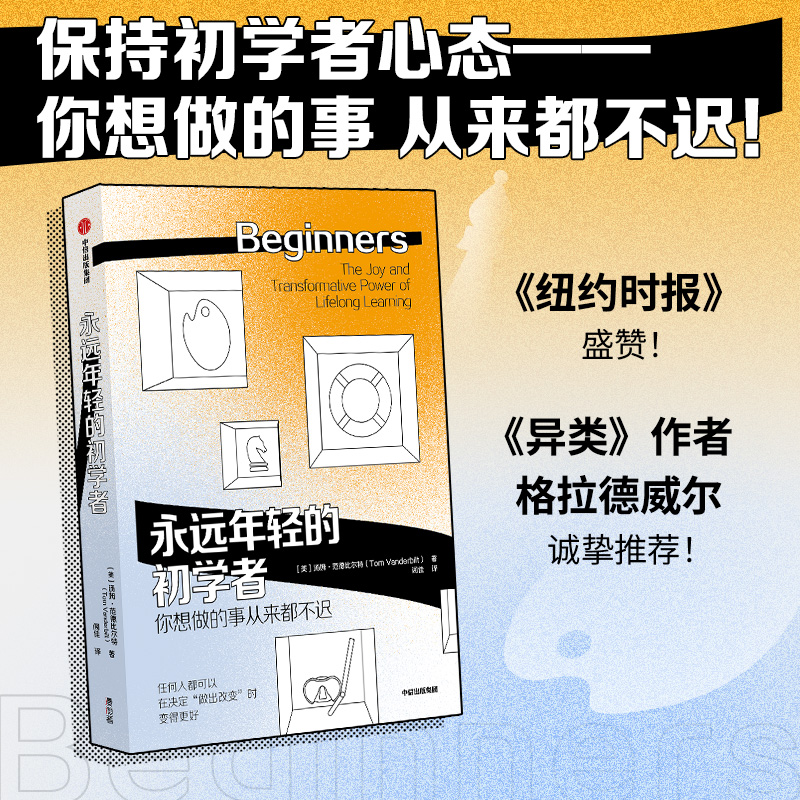
自由作家,擅长以新锐的眼光看待周边事物。曾长期为许多媒体和出版物撰稿,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大众科学》《金融时报》《史密森尼》《伦敦书评》等。他还是《连线》英国版、《户外》和《艺术论坛》的特约编辑。著有畅销书《开车心理学》《生还的城市》等。
序幕:开场白(节选) 几年前的一天,在一个海滨小镇的小图书馆里,我和当时快4岁的女儿玩起了节日跳棋。她的目光移到了旁边一张桌子上,那里有一张黑白格棋盘,上面摆满了有趣得多的棋子。(好些国际象棋大师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马和王吸引的。)“那是什么?”她问。“国际象棋。”我回答。“我们能玩吗?”她恳求。我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但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下。我依稀记得小时候学过基本走法,但没能坚持下来。这个事隐隐地困扰着我,每当在酒店大堂里看到一张闲置的棋盘,或是在周末报纸增刊上看到残局游戏,我就会感到一阵心痛。 我对国际象棋有个大致的认识,知道菲舍尔和卡斯帕罗夫的名字,知道国际象棋曾吸引马塞尔·杜尚、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历史名人,知道国际象棋大师甚至能提前预见几十步棋。我知道,和古典音乐一样,国际象棋在电影中是天才(通常是邪恶的一方)的代名词。但说我“知道”国际象棋,就跟说我“知道”日语差不多:我知道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听起来像什么,但我对它并不精通。 我决定学下国际象棋,哪怕只是为了能教女儿。基本下法学起来很容易,在孩子们的生日聚会上,或是在超市排队时,我在智能手机上花几个小时就掌握了一些基本下法。很快,我下起棋来,有时甚至能打败最弱的计算机对手(就是编程中故意设计了有毁灭性失误的对手)。但我很快发现,我对更深层次的策略几乎毫无概念。 我不想教女儿那些我粗浅掌握的东西,但我要怎么学呢?国际象棋入门书多得惊人,当然,有《傻瓜国际象棋入门》。除此之外,国际象棋文献也浩如烟海,它充满了像代数一般错综复杂的符号,这些符号本身就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准语言。 有些图书的内容异常具体,例如《用三马开局破法兰西防御完全指南》。没错,一整本书都在讲区区一着棋的种种变化(我应该补充一句,这着棋人们用了100 多年了)。然而,人们仍在琢磨它,经过了100 多年外加出了许多书以后,有一本书用了整整288 面讲述关于它的新内容。 一开始接触国际象棋,人们可能就会听到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在仅仅走了3 步之后,棋局中可能的变化就比宇宙中原子的数量还多。实际上,对于该怎样把这指数级复杂的游戏解释给一个平常最爱看《好奇的乔治》的小孩听,我感到无解。 于是,我做了有自尊心的现代父母都会做的事——聘请一位教练,我希望有人能同时教我和我女儿。 我做了一些网络调查,找到了西蒙·鲁多夫斯基,他是一位住在布鲁克林的波兰裔移民。西蒙有一股来自旧世界的严肃态度,严厉里带着爱,对这项任务有几分在我看来恰到好处的庄重感。下棋时,他用热情得近乎夸张的动作移动棋子。西蒙是个素食主义者,身材瘦削,极度警觉。他希望除了作为背景的古典音乐,房间里没有其他声响。桌上摆着几杯茶和我妻子刚烤好的糕点,这原本是第一节课时她出于礼貌端上来的,但这种款待很快固定下来,甚至成了一套带有几分滑稽感的仪式。“我们需要给西蒙做糕点。”我妻子会在上课那天早晨急切地宣布。音乐、茶点及棋盘与棋子天然的优雅把我们的房子变成一场维也纳沙龙(至少,我喜欢这样想),在咖啡因的刺激下渐趋热烈,充斥着对国际象棋理论令人迷醉的讨论。 尽管当时我不曾想到,女儿和我其实是在进行一项认知实验,样本仅为两人:我们是两名新手,尝试学习一项新技能。 我们从同一起点出发,两人年龄相差了大约40 岁。 此前,在女儿的认知里,我一直是个专家,但现在,我们奇怪地来到了同一条起跑线,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我们俩谁能学得快一些呢?我们是以同样的方式学习吗?我们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谁最终会获胜? 但我很快就不再上课,因为我的存在似乎让人分心,我成了女儿和教练之间的障碍。开始的时候,她学得比较慢。当女儿努力在拥挤的棋盘上想出一步难下的棋时,西蒙和我会在对视后心照不宣地咧嘴一笑。 而我一开始似乎下得更好,哪怕只是因为我更认真。我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比较长,我有几十年的棋类游戏经验,也有身为成年人的骄傲。我们一起下棋的时候,女儿有时会走神,为了让她保持兴趣,我会故意亮出一些明显的错误,希望她能看到。在更广阔的国际象棋世界里,我是个新手——一个笨手笨脚、无可救药的新手,但在家里,至少我觉得自己像个贤明的政界元老。 然而,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女儿逐渐进步。她会平静地向我解释棋局里隐藏的复杂之处,或是告诉我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稳赢的在线棋局最终很可能打成平局,她学会了我完全不熟悉的策略和经验法则。她开始参加锦标赛:一开始是在本地图书馆地下室里举行的小型比赛,后来是全市范围的大型比赛。她拿到了很多奖杯,并在全国前100 名同龄女棋手中有了相当靠前的排名。突然间,要想下赢她,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有时还根本做不到。 回想起来,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只是一局接一局地在线上下棋,希望通过多对弈来提高水平——我认为“胜利是因为才华,失败是运气不佳”;女儿则在西蒙的指导下苦练开局理论和终局战术,每当她输掉一盘棋,她必须详细分析自己为什么会输,这通常比实际下棋花费的时间更长。 以心理学家安德斯·艾利克森(《刻意练习》的作者)的理论来看,她是在进行“刻意练习”。而且,我满足于“盲目重复”,尝试通过蛮力而非切实的目标提高棋艺。在某种程度上,我试图模仿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 的著名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零(AlphaZero)来下棋。阿尔法零只知道国际象棋的基本规则,在跟自己玩了4 400 万局之后,它掌握了这种游戏。a 它一路走来就学会了5,不靠教练的帮助6,靠着自学成为全世界最可怕的“棋手”。 我不想变成一个无聊的大人——任何人都可以在决定“做出改变”时变得更好! 《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等媒体热赞,《异类》《陌生人效应》作者格拉德威尔诚挚推荐! 为什么成为大人后,我们越发不敢试错,不敢让自己成为初学者去学习新事物? 我们是否忘记了从头开始的纯粹乐趣? 在get新技能的过程中,成人的大脑和孩子的大脑又有什么不同? 0~100岁之间的你,任何微小的好奇心与行动力,都将令生活充满魔力! 这本书可以帮你摆脱多年停滞不前、想尝试却不敢的窘境,再次打开新的人生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