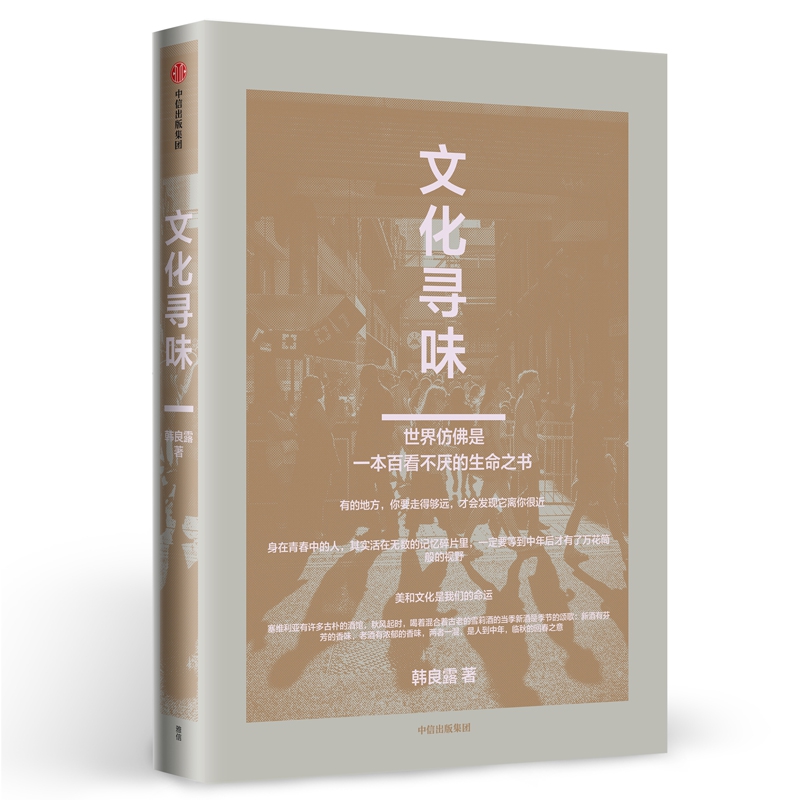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文化寻味
ISBN: 9787508690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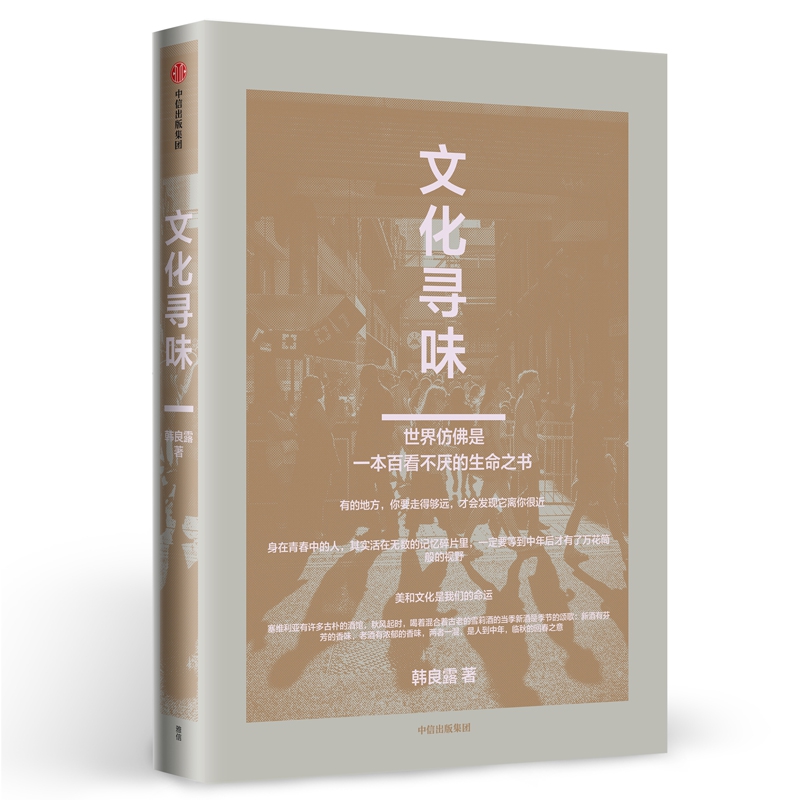
韩良露,丰厚多元的生活家。祖籍江苏如皋,生在**,*爱美食和旅行。她一生快意,丰富又尽兴:少时闯荡文化江湖,从诗歌散文到影视剧本,接连斩获大奖,声名斐然;后与夫婿全斌旅居世界,一边游学一边写书,享*了近十年逍遥时光;2007年夏至成立“南村落”,举办上千场公益活动,融合节气美食与在地风情,分享“慢食乐活”的生活美学。良露的文字,写尽一代才女*精彩的人生细节,藏着代代传承的人间情味。曾著有《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子·猫时间:韩良露伦敦旅札》《露水京都》《良露家之味》《台北回味》《文化寻味》,曾荣获**图书金鼎奖、台北文学奖等。
70年代,回头看见我 许知远说我像江湖百晓生,早年闯荡文化江湖,到处逢场作戏,只为二三十年后可以说,我在场、我知道、我记得的故事。 一、台南旧事 我喜欢台南那种缓慢的、懒散的、优闲的气息,潮湿的空气中飘浮着*木青味、黄昏时随着台南人**漫无目的地散步,入夜后沉静的暗巷浮动着花香、夜访郡王祠深夜的阴森,晨探赤嵌楼黎明的苍茫。 我站在台南火车站月台上,等着南下的慢车从永康开来,载我去保安村,我并不是想赶时髦,去玩一趟永保安康的火车旅行游戏,而是想回忆一趟二十多年前的逃亡路线。 那一年,把青春*子过得像写坏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我,实在厌倦了在台北的生活,突发异想地要到远方去念书,当年还不流行高中生出国,我只好在全岛选一个可以转学的地方。 父母当然希望我选离台北近的地方,虽然他们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我非要离家求学,一向只有南部的孩子离乡背井到台北唸书,哪有北部的学生一个人去南部唸书的道理。但我那一对开通或宽容到不可思议的父母,对我的青春浪荡生活早已不知如何是好了,高一念中山女中时,旷课加请假记录破建校历史,高二转去了辞修高中,依然不改本色,还闹过一次笑话,在全校朝会时(那**我还是不在,事后经同学转告),校长宣布高二上年度全校**名的奖学金得主韩良露,因请假加旷课太多,*行成绩只剩下了不到30分,因此被取消资格,当场引起全校哄堂大笑。 在台北其实也没什么压力的我,只是难耐那段想离家远远的冲动,想一个人过*子,想每天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向任何人交代地体会孤独和寂寞。 *后我选定了台南,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母系方面的亲人,虽然他们已经通通住在台北了,但台南对我一直有种神祕的牵引力量,长大后才明白当年我一定是听到了不明的、远古祖灵的召唤。父母说,考上了台南女中你就去吧!他们一定觉得我上不了,没想到两百多人考转学,只收了我一个人。 父母只好帮我租了房子,在府前路郡王祠旁的巷子里,两层楼的老式洋楼,屋主是在台电上班的**职员,太太在家教钢琴,有一个正在唸私立长荣女中高三的女儿,这一户保守的人家,肯把房间租给外地学生,看上的是要唸台南女中的我,会对他正要考大学的女儿激起竞争鼓励的作用。 事情**出乎他的预料,注册入台南女中高三后的我,**个星期摸清了学校有多少棵老榕树、*够了清晨朝会的团*,**不了台南女中古怪的**,*奇怪全班女同学为什么下课休息时都静悄悄的? 我又开始了逃学的*子,刚好认识了在台南美新处办画展的人,要我白天帮忙看画廊,反正是义工,我有空去时,就到图书馆借英文小说,画展看烦时,还可以丢下整屋的画,到门口的冰果室吃西红柿沾糖姜酱油和水果冰。 我旷课了一个月,认识了一些斯文秀气的台南男孩,一起骑单车去南鲲鯓,看还没开过画展只是传奇老人的洪通,一起在台南孔庙的大榕树下交换阅读彼此写的现代诗,这些男生都跟我的外公、大舅一样,会一种很柔软的台南腔及闽南话。很多年后,我去了京都及苏州,才了解到什么是古都人的声音。 旷课一个月后,学校开始查问了,我索性瞒着台北的家人,也骗了学校的教务主任说我水土不服,干脆办了休学,当时,我已经舍不得离开台南了。我慢慢地溶入了台南的古老灵魂之中,明白了台南人的压抑、保留、淡漠、守旧的外表下,潜藏着狂热、执着和骄傲。 休学了三个月后,父母终于发现了我的祕密,宣布要来带我回家。当夜,我四处联络台南的友人,凌晨带着行李偷偷离开租屋处,只惊动了客厅中正在打瞌睡的大狗。清晨,我从台南火车站搭上慢车,直赴保安村友人父亲的铁路宿舍落脚。父亲运气好,竟然等到了不知情的友人去找我,东打听西打听下,知道了我在保安村的藏匿之处。那**晚上,父亲领我从保安村回台南,却遇上台南全市大停电。一个城市会为一个人的逃亡终结而停电吗? 二、人生撞球台 整个人生像一场无止尽的撞球,大家撞来撞去,但都在一个撞球台上,有的球早撞到,有的球晚撞到,但也有的球一撞离了台子没了音讯。 高一高二都在台北逃学四处混,别人也许以为我在混太妹,但如今回头一看,就像那句广告词说的,“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我大概也可说成“爱文艺的少女不会变坏”。虽然不走正轨,却一直走正道,许多*子和男友逃学在西门町的“天琴厅”;也抽菸,奇怪的是抽了两三年后就自动不想抽了,大概是没吸进肺里,也喝未满十八岁的自由古巴*尾酒,但至今不酗酒;在天琴厅认识了一些办现代画会、剧场杂志的人,也开始去牯岭街找禁书看,看老舍、鲁迅、巴金、曹禺,还去记忆中小小的位于二楼的帕米尔书店买书,不知为何地深*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一书的吸引。 年轻的我,并不了解人生有如长河,随时会遇到生命河道转弯的时候,后来我的人生的确波澜起伏,也转过几次人生的大弯,但有些核心的情感却始终如伏流。 高三*终又逃回了台北,准备考大学,补习班也没去,常常去的是罗斯福路台大校门旁的香*山书屋,当时罗智成、杨泽都还在那做书店工读生,当时看了不少法国作家的书,纪德的《背德者》、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认识了一批在编《影响》杂志的人,当时会去一个叫谢正观的人家里聚会,还曾见到但汉章,因为《影响》的影响,我开始去西门町的台映看艺术电影,也促成了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暑假,竟然就一个人办起夏*艺术影展,每天从上午10点放电影到晚上10点,**放五至六部当时一般人看不到的电影。当时我手上有个小电话本,记录了台北各大专院校的艺术电影同好者的电话,一通电话随时可以招来数名至十数名的影客。在没有网络的时代,我也不知自己如何掌握了当时的动员能量,这样的能量*后我都不曾用在任何政治或商业领域,直到近几年在南村落举办文化活动时才重新启动。 小电话本后来在我搬家时遗失了,真可惜,否则还看得到不少人的老电话号码。我常说我如今认识的一半的艺文界人士的名字都记在那小本里,但其实大多数人当时我也不熟,反而在*后的二三十年间逐渐和其中不少人变熟。说来也怪,我和许多男人的江湖交情都是在三十多岁以后才能熟(例如倪重华、罗智成、杨泽等),为什么?也许是我对偶像型、才子型的男人有先天的抗拒,不想成为仰慕他们的女生,因此要保持距离,直到彼此可以自在平等相处。 三、动物园的歌声 听过当年动物园歌声的人,还有多少人心底仍然保留着那些可以永远播放的歌声?是否有些晃动的青春身影还在那流连不去? 我在大一到大三年间,和淡江一批住在“动物园”的人走得很近,当时我年龄还小,不到20岁,看到大了半轮一轮的李元贞、王津平、李双泽等,都当他们是长辈,和他们没有太多直接的来往,却记得他们说过的话和唱过的歌。 因为动物园的关系,我才亲临了几次**现代民歌发展**重要的现场。一次在淡江大学的礼堂,李双泽跳上台问“为什么不唱自己的歌?”后来他唱起了《国父纪念歌》,另一次是在中山堂,好像在陶晓清主持的西洋流行歌演唱会上,台下几位年轻的学生群起高呼“唱自己的歌”。对不起,当时真是年纪小,明明从高一就开始听齐柏林飞船摇滚的我也在那大呼小喊,这一次闹场事件,大概也促成了*后杨弦乡愁四韵的演唱会和校园民歌的兴起,但当年恐怕极少人明白,所有人类文明活动的本质都有左派右派之分,左派都想颠覆主流,右派却可以旧瓶装新酒。校园民歌后来成了流行音乐的主流,但左派民歌却消失了。当年左派民歌运动在广慈博爱院那场青*地演唱会中的杨祖珺,还有多少人记得?但因校园民歌崛起的歌手如蔡琴等人,至今仍红遍海峡**。 动物园的歌声后来沉寂了,人们也四分五散,70年代的歌声远了,在80年代人们唱起不同的歌,听过当年动物园歌声的人,还有多少人心底仍然保留着那些可以永远播放的歌声? 四、青春实验影片 电影梦恐怕还是在的,就像休眠火山不知何时爆发,我认识我先生朱全斌后,他曾经拿过一张黑白的老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竟然是他和当时我熟识的吴永毅、罗智成、张惠国等人的合照 当年,我身处的朋友圈子,有不少人在拍实验影片,记得在我升大二的夏天,就参与了几次制作,有一回在政大拍《竹林七贤》,参与的人记得有现在是画家的郑在东(他好像是导演),还有“给我报报”的冯光远,还有如今在美国教传播的张正平(好像拍摄的地方是他家或他邻居家),应该还有现在教文化研究的陈光兴,以及一些我记不起来的人了。这群人拍了快一个星期,一年多后看剪出来放映的影片,却只记得曝光过度不停晃动的人影和支离破碎的对白,如今回想起来,有趣的是当时这些20出头的年轻人,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对竹林七贤的题材有兴趣? 我也曾和一群淡**年在沙仑荒废公寓拍八厘米,那次人*多,现场有十几人,加上来来去去探班的人,记得主其事者是吴永毅、林洲民、李玮珉吧!记得还有罗智成,我和郑在东也去帮忙,也不记得在帮什么忙,常常拿着银色的打光板发呆,大家当时工作都很没效率,但每一个人都说出国以后要学电影,但是后来都没实现。 因为到处帮忙拍八厘米,在大二升大三的那年夏天,我竟然被东找去帮王菊金拍《六朝怪谈》,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部当年被喻为****部实验性的艺术电影?当时连侯孝贤都还在拍风儿踢踢踩吧!**的新电影运动也没开始起步。记得《六朝怪谈》在澎湖望安岛拍片的*子,我们这群副导、助导、场记都很快乐,常常收工后去夜间的海边游泳、唱歌。 **连数位相机都能拍出活动影像,大家是否已忘了那个年轻影友着迷拍八厘米实验影片的年代? 五、写在时代沙滩上的名字 在70年代末期,四方英雌豪杰群起,当时,对20岁的眼睛而言,许多的名字都是时代的象征,每一个名字都是自己城堡的主人,但隔了30年后回顾,才知道大部分的城堡都彷彿盖在时代的沙滩上,这些沙堡禁不起时代浪潮的冲洗而失去了踪影。 一直莫名其妙地会被时代能量吸引的我,*容易和朋友们混迹在一些时代磁场超强的地方,例如项子龙在罗斯福路开的“稻*人”,那里是遇见张照堂、张毅、余为政、舒国治的地方,来自屏东的陈达**次唱〈思想起〉也在这间位于二楼的小咖啡馆里。 稻*人的时代结束于项子龙把店搬到**的士林夜市那开了“异乡人”,却怎么也无法再兴文化的风浪。当年还不明白一切或和地理风水有关,罗斯福路在**还在台北文化重镇的温罗汀街区中心,士林夜市商业大发达,却造不了文化的风头。后来项搬去了东区,换了两三个地方开谈话头也一样,吸引的能量*多是非主流的娱乐圈,再也不是次文化、反文化帮了。 “紫藤庐”在开茶馆前,早已是一座公共茶馆,从不见锁门。记得《夏潮》的苏庆黎、郑泰安和林浊水在那时亲如姊弟,有一回我跟着苏和《夏潮》一帮人去**晶华饭店旁那两个公园做田野调查,从当时“禚家饺子馆”的小巷口进去访问了好几位从大陈来台的同胞,我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呢? 在紫藤庐会看到某*外杂志正在开编辑会议,不知我怎么也在场?也会听到不少政治八卦,谁跟谁如何又如何,许多人情世故也在其中学会,还会看到当时*外知名的好男好女吵架和大打出手,真是没人在乎隐私的时代。 那个时代真有风云际会之感,虽然大家的角色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总编辑、小编辑、作者等,却都有着仰望时代的巨大心灵,但等到*后其中不少人都坐过大位后,回头一看那些大位反而把人都坐小了。 许知远说我像江湖百晓生,早年闯荡文化江湖,到处逢场作戏,只为二三十年后可以说,我在场、我知道、我记得的故事。 其中各方人物,都像写在时代沙滩上的名字,有些名字至今都让人忆起昔*的风信,像奚淞、黄永松、白先勇、黄春明、尉天聪,但也有不少名字令人叹息扼腕。每个人一生,都有自己的玫瑰名字,写在时代的沙滩上,虽然*终都会消失,但名字还被人们记得时,希望仍像玫瑰一般美好。 六、终于向青春岁月告别 每个人青春期的结束,都有自己的时程与方式,不是大伙都在法定投票年龄宣告终止。 我对于自己青春岁月的告别,有着很清楚明确的时间意识,当时我的生活正面临几个事件的转折,分别和工作、金钱和关系有关,我原本是很没有责任意识的我于青春无悔的人,但之后就被迫长大了,开始学习负起责任。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刚好是我从初一到大四期间,所有影响我至今的重要人物、文学、艺术、政治、社会的思想和价值都在那十年中奠定,但当时的我哪里会明白自己一生的轮廓在彼时已打了底,身在青春中的人其实是活在无数的记忆碎片里,一定要等到中年后才有了万花筒般的视野,才可以不时转动焦距看到不同的碎片所组合出的各种人生图像。 ★许知远将韩良露比作“江湖百晓生”——“早年闯荡文化江湖,到处逢场作戏,只为二三十年后可以说我在场、我知道、我记得的故事”。 ★对韩良露而言,世界仿佛一本百看不厌的生命之书。她一向以热爱旅行、拥抱异国美食与文化著称,勇于尝试,无惧于表达自己的个性、主张与态度。《文化寻味》展现了韩良露的丰盛世界,书写了关于文艺、旅行、食趣、社会、记忆的精彩篇章。 ★舒国治作序**,蒋勋深情怀念。“韩良露生活美学系列”:《台北回味》《良露家之味》《文化寻味》《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子?猫时间:韩良露伦敦旅札》《露水京都》全面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