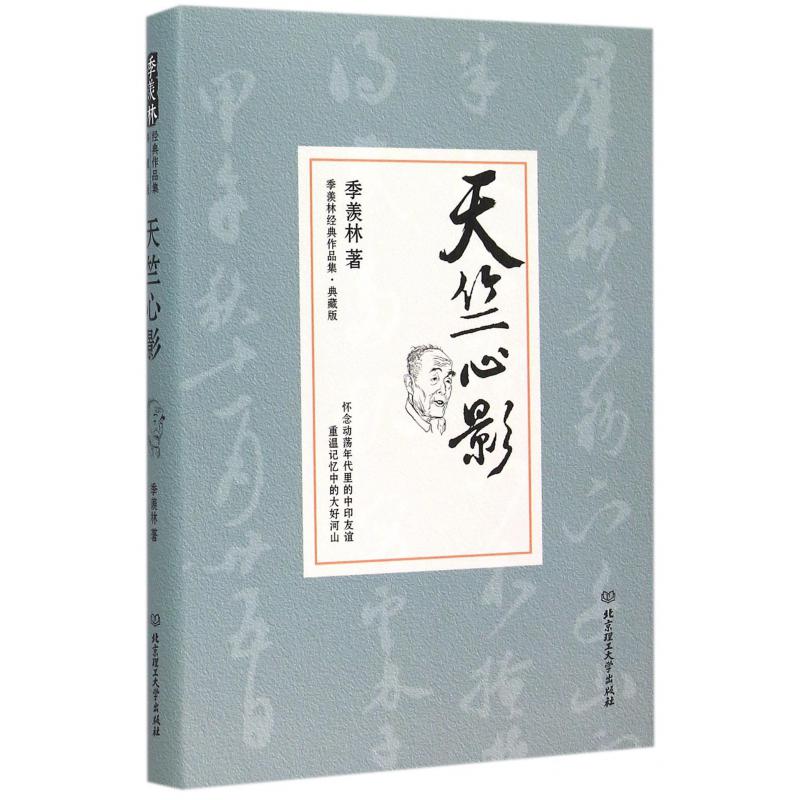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30.20
折扣购买: 天竺心影(典藏版)(精)/季羡林经典作品集
ISBN: 9787568203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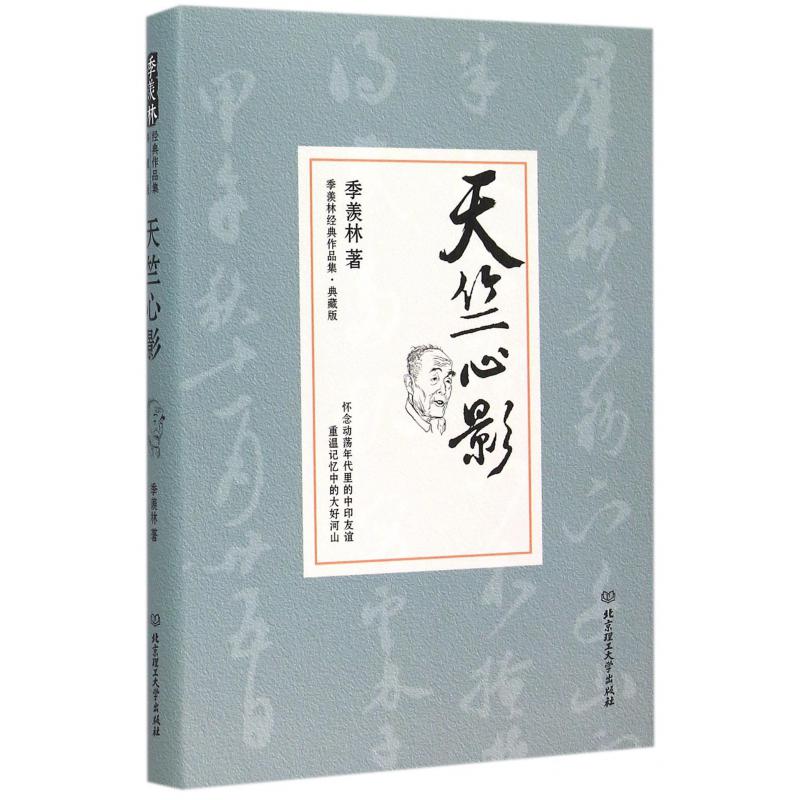
"季羡林(1911.8.6―2009.7.11):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代表作品:《牛棚杂忆》《天竺心影》《朗润集》《留德十年》《病榻杂记》《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 "
初抵德里 机外是茫茫的夜空,从机窗里看出去,什么东西 也看不见。黑暗仿佛凝结了起来,凝成了一个顶天立 地的黑色的大石块。飞机就以每小时二千多里的速度 向前猛冲。 但是,在机下二十多里的黑暗的深处,逐渐闪出 了几星火光,稀疏,暗淡,像是寥落的晨星。一转眼 间,火光大了起来,多了起来,仿佛寥落的晨星一变 而为夏夜的繁星。这一大片繁星像火红的珍珠,有的 错落重叠,有的成串成行,有的方方正正,有的又形 成了圆圈,像一大串火红的珍珠项链。 我知道,德里到了。 德里到了,我这一次远游的目的地到了。我有点 高兴,但又有点紧张,心里像开了锅似的翻腾起来。 我自己已经有二十三年的时间没有到印度来了,中间 又经历了一段对中印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不愉快的时期 ,虽然这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在中印文化交流的长河中 只能算是一个泡沫,虽然我相信我们的印度朋友决不 会为这点小小的不愉快所影响;但是到了此时此刻, 当我们乘坐的飞机就要降落到印度土地上的时候,我 脑筋里的问号一下子多了起来。印度人民现在究竟想 些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看待中国人民呢?我不 知道。我本来认为非常熟悉的印度,一下子陌生起来 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我以前已经来过两次 了。即使我现在对印度似乎感到陌生,即使我对将要 碰到的事情感到有点没有把握;但是我对过去的印度 是很熟悉的,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很有把握的。 我第一次到印度来,已经是二十七年前的事情了 。同样乘坐的是飞机,但却不是从巴基斯坦起飞,而 是从缅甸;第一站不是新德里,而是加尔各答;不是 在夜里,而是在白天。因此,我从飞机上看到的不是 黑暗的夜空,而是绿地毯似的原野。当时飞机还不能 飞得像现在这样高,机下大地上的一切都历历如在目 前。河流交错,树木蓊郁,稻田棋布,小村点点,好 一片锦绣山河。有时甚至能看到在田地里劳动的印度 农民,虽然只像一个小点,但却清清楚楚,连妇女们 穿的红绿沙丽都清晰可见。我虽然还没有踏上印度土 地,但却似乎已经熟悉了印度,印度对于我已经不陌 生了。 不陌生中毕竟还是有点陌生。一下飞机,我就吃 了一惊。机场上人山人海,红旗如林。我们伸出去的 手握的是一双双温暖的手。我们伸长的脖子戴的是一 串串红色、黄色、紫色、绿色的鲜艳的花环。我这一 生还是第一次戴上这样多的花环,花环一直戴到遮住 我的鼻子和眼睛。各色的花瓣把我的衣服也染成各种 颜色。有人又向我的双眉之间、双肩之上,涂上、洒 上香油,芬芳扑鼻的香气长时间地在我周围飘浮。花 香和油香汇成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 即使是终生难忘吧,反正是已经过去的事了。我 第二次到印度来只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不算是印度 人民的客人。停留时间短,访问地区少,同印度人民 接触不多,没有多少切身的感受。现在我又来到了印 度,时间隔得长,中间又几经沧桑,世局多变。印度 对于我就成了一个谜一样的国家。我对于印度曾有过 一段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现在又从熟悉转向陌生了 。 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陌生的感觉走下了飞机。因 为我们是先遣队,印度人民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因 此不会到机场上来欢迎我们,我们也就无从验证他们 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在冷冷清清的气氛中随着我们驻 印度使馆的同志们住进了那花园般的美丽的大使馆。 我们的大使馆确实非常美丽。庭院宽敞,楼台壮 丽,绿草如茵,繁花似锦。我们安闲地住了下来。每 天一大早,起来到院子里去跑步或者散步。从院子的 一端到另一端恐怕有一两千米。据说此地原是一片密 林,林子里有狼,有蛇,有猴子,也有孔雀。最近才 砍伐了密林,清除了杂草,准备修路盖房子。有几家 修路的印度工人就住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我们散步 走到那里,就看到他们在草地上升上炉子,煮着早饭 ,小孩子就在火旁游戏。此外,还有几家长期甚至几 代在中国使馆工作的印度清扫工人,养花护草的工人 ,见到我们,彼此就互相举手致敬。最使我感兴趣的 是一对孔雀,它们原来是住在那一片密林中的。密林 清除以后,它们无家可归,夜里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 。可是每天早晨,还飞回使馆来,或者栖息在高大的 开着红花的木棉树上,或者停留在一座小楼的阳台上 。见到我们,仿佛吃了一惊,连忙拖着沉重的身体缓 慢地飞到楼上,一转眼,就不见了。但是,当我们第 二天跑步或散步到那里的时候,又看到它们蹲在小楼 的栏杆上了。 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