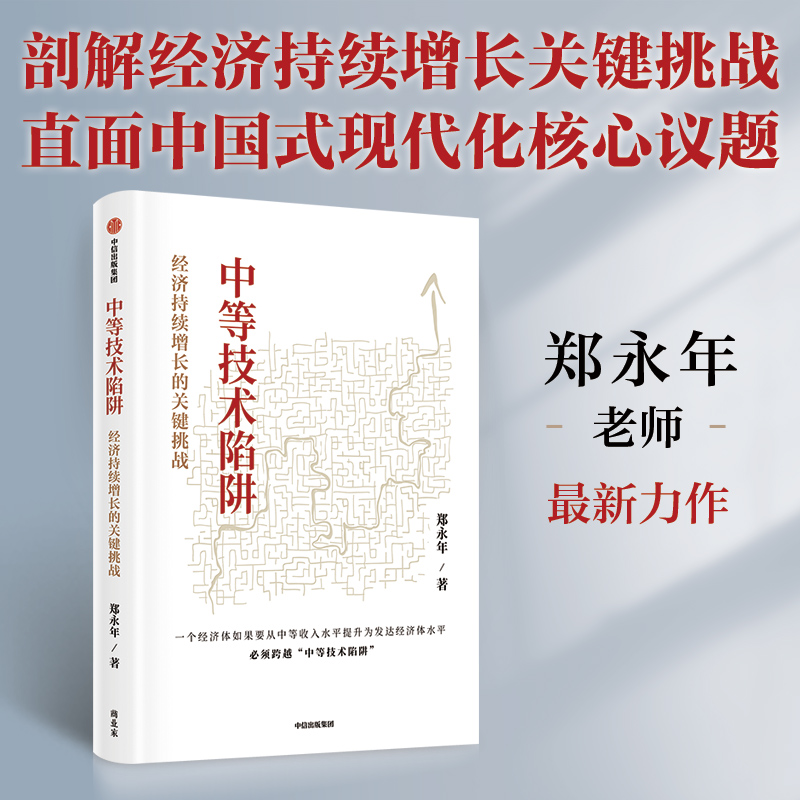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51.70
折扣购买: 中等技术陷阱: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挑战
ISBN: 9787521764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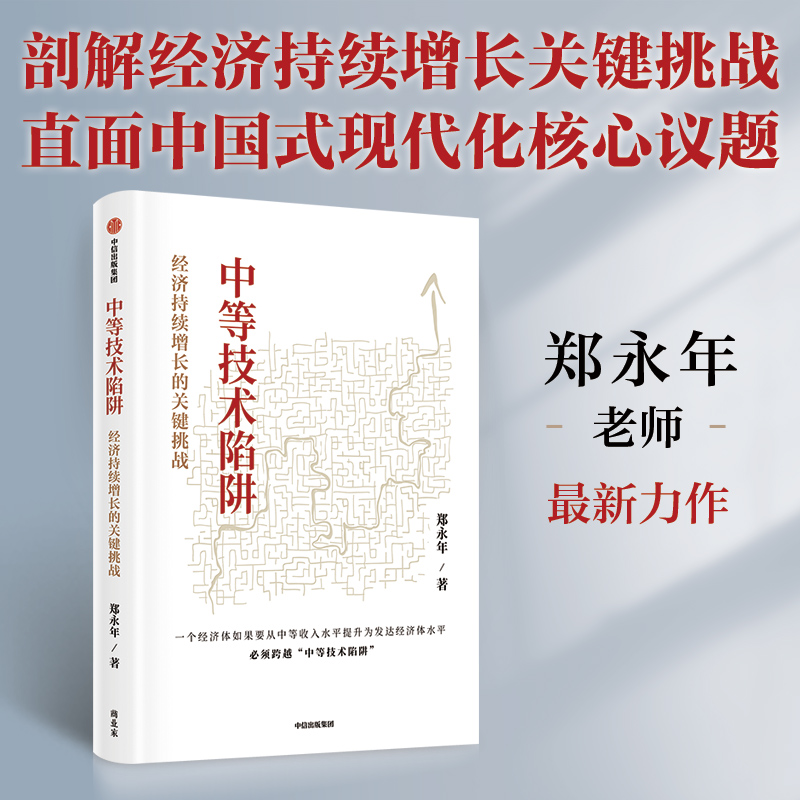
郑永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IPP(国家高端智库)专家。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World Scientific 《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
对我们来说,要回答的问题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行政当局和对华不友好甚至敌视的力量采取的种种做法,是否会把中国固化在当前的中等技术水平呢?我们又如何破解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围堵呢?我们如何实现从应用性技术到原创性技术的转型呢?我们如何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技术升级,从目前 4-7 的水平,提升到 8 或以上呢? 这些是我们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我国的科学家和政策研究者都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无论怎么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既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挑战和必须克服的困难,也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把自身提升为发达经济体的关键。技术领域是一个可以加以精准描述和检验的领域,我们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事实求是地看待问题,事实求是地解决问题。 (一)开放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呢?在宏观层面,开放政策是关键。前面已经讨论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开放和进步、封闭和落后之间的紧密关联。这里,我们需要把开放置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经验里来加以讨论。 在政策面,首先需要对近年来所强调的“新型举国体制”作科学的理解,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并且越来越开放。举国体制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以来,所有强大的国家都实行了举国体制。在西方,尽管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由资本主导,但一战、二战期间的战争动员,也促成了西方国家演变成为举国体制。美国更是如此。二战之后,随着《布什报告》(即《科学:无尽的前沿》)的出台,美国政府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找到了干预技术进步的领域和方法,即对技术和卫生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有组织的研发和转化。无论是技术还是卫生都和军事战场上的胜负有关,技术是用来针对敌人的,卫生是用来保障士兵的生命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更是举国体制。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公开叫出了要用“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法来对付中国。拜登政府以来,尽管美国没有再用这样的概念,但对中国的打压方法不仅没有变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基础上加上了“全世界”,即通过全球范围内的结盟打压中国;同时,拜登政府具有“新凯恩斯主义”特色的经济政策也在促成美国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改变了自 1980 年代里根革命以来的美式自由主义主义发展路径,也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面对今天美国对我们的“卡脖子”和系统脱钩,我们无疑必须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回应。但是,我们强调的是新型举国体制,它绝对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把大门敞开,在更开放的情况下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创新。 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世界科技发展内在逻辑的理解。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的世界科技看成一座山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处境。今天世界思想市场上一些人在谈论“一个世界、两个中心”的概念,即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心;也有人说“一个世界、两个市场”,即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在科技领域也有人在思考,中国是不是可以构建一个独立于西方科技之外的科技体系?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这样的思维方法不仅不符合历史经验的幻想,更是非常危险的。世界的科技只能有一座山,如果离开了这座山,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再去构建另一座山。世界科技的这座山是世界所有文明所有国家共同造就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阿拉伯世界的科技和西方古希腊以来的科技,都是对这座山的贡献。只不过, 因为现代化首先发生在西方,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霸占着这座山。二战前,欧洲国家霸占着这座山,到了二战以后,转变为由美国霸占着这座山。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动结束了以前的相对孤立状态,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成美国西方接受我们成为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加入了 WTO。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了世界科技这座山,并通过几十年的虚心学习和努力发展,在这座山上持续往上爬,对处于山顶上的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构成了竞争能力。这就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所说的“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今天,美国“卡脖子”的做法就表明美国不再允许中国继续在这座山上往上爬了, 而“系统脱钩”则更严重,表明美国意图把中国赶下这座山。中国不能上美国人的当,意气用事,自己主动封闭起来或者主动离开这座山,而是应当告诉美国,虽然美国现在霸占着这座山,但这座山既有美国的科技贡献,也有中国的科技贡献,它既是美国的,也是中国的。中国未来的选择不是离开这座山,而是要继续待在这座山里,为这座山增加更多的贡献。总有一天,不仅我们离不开这座山,这座山更离不开我们。 因此,我们今天提倡新型举国体制,就需要在开放的状态下搞科技创新,继续为世界科技这座山贡献中国的力量。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前面已经讨论过前苏联“关起门来自己创新”的历史教训,中国唐宋以后的“闭关锁国”政策也表明了这一点:不管一个国家以前的科技多么先进和发达,只要选择了封闭,就一定会变得落后。 根据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等人的研究,中国至宋代科技就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后来马克思承袭了培根的说法,提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尽管培根和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说出这三个发明来自哪个国家,但后来的史学家们不仅认同这些发明都来自中国,并且又加上了第四个发明,即“造纸术”,成为今天人们所说的中国“四大发明”。 中国的“四大发明”改变了西方世界,但中国本身在明朝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最终导致了技术落后。例如,火药从中国进入西方之后,演变成为“火药学”,但在中国本土火药一直停留在应用阶段。指南针也是如此,在西方被广泛应用于航海,但在中国本土则是用来看风水。明朝郑和下西洋所组成的船队用今天一些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母舰队”,而且郑和舰队的活动早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开辟新的通往东方的航线而发起的航海探索。并且,当时被称之为“倭寇”的海盗活动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东南沿海(主要是福建和浙江)的民间海上力量,这一力量也同样强大。但因为闭关锁国政策,航海技术付之一炬,中国先是失去了一个航海时代,继而又失去了一个由此引发的工业化时代。直到近代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自己发明的火药所炸开,国家被迫开放。因此,在 1980 年代,我们在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得出了“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习近平 2011 年 9 月 1 日在中央党校 2011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总结了中国的历史经验,再次强调指出,明朝末年,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近代更是陷入了列强欺凌、被动挨打的境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看不到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其他先进的东西。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教训是深刻的。1980 年代以降,我们实行主动开放,越来越开放,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奇迹。 因此,我们必须接受深刻的历史教训,不能幻想自己可以离开现在世界的科技系统,去造另一座山。面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政策,我们需要更大的开放政策,甚至是单边开放政策。也就是说,即使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闭政策,我们也需要继续向他们开放。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恐惧中国的科技崛起,对中国实行全面打压政策。但从长远看,他们不会成功,因为他们践行的是政治逻辑,而非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就西方本身发展经验而言,导致西方发展的并非是政治逻辑, 而是资本、技术和市场。近代以来,发生在西方的几波全球化就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冲破政治所设立的边界,而形成的国际市场。对我们而言,面对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打压,我们必须用资本、技术和市场逻辑来回应之。 实际上,从塑造科技发展的开放环境而言,今天的中国需要第三次开放。从近代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开放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的被迫开放,在国家被迫开放和被西方强权欺凌的情况下,中国开启了自强的进程,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第二次开放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主动开放,加入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就是第二次主动开放的结果。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第二次主动开放,我们能见到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一切。经过第二次开放,我们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开放所带来的变化说明了前述后发国家“比较优势”理论的正确性。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进行第三次开放。鸦片战争的时候,西方强迫我们开放;后来我们主动开放,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接受我们开放。但是现在开放的条件很不一样了。如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想要封杀中国,卡脖子,搞脱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们认为,第一,中国需要高水平开放。我们所说的“第三次开放”就是高水平开放。第三次开放就是以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精准的单边开放。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美国在其所需要的领域也始终是实行单边开放的,尤其是在人才、企业和金融领域。如果在这些领域,美国没有单边开放,那么难以解释美国在所有这些领域成为世界的高地,或者我们所说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世界上的优质资本、优质技术和高端人才都拼命往美国跑,主要是几个湾区,包括波士顿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变成了发达国家,条件优越,这些要素才会往美国跑。但问题是美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因素很复杂,但开放是核心,没有开放,就很难吸引到所需要的生产要素。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也是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实行单边开放的结果。概括地说,自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的开放政策已经走过了几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0 年代,当时被称为“请进来”。在那个阶段, 我们要发展,但很穷,不仅需要改革开放的政策,更需要外来的资本。“请进来”就是典型的单边开放。第二阶段是 1990 年代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被称为“接轨”。为了加入世界贸易体系,我们主动接轨,从中央到地方,我们修改了上万条法律、法规和政策。“接轨”也是单边开放。自本世纪以来,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即“走出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便是“走出去”的产物。我们把“一带一路”界定为中国为世界所提供的“国际公共品”,这也包含着“单边开放”的意涵。上海中国进口博览会更是单边开放的典型。 今天在美国一些西方国家封杀我们的时候,我们即使面对封杀也应该根据我们的需要坚持向他们实行精准开放,向他们的要素开放市场,包括资本、技术和人才。美国今天封杀中国、与中国脱钩是其国内冷战派和行政当局的逻辑。这样做不符合资本逻辑,因为资本是要走出去的;不符合科技逻辑,因为科技技术需要向外延伸;更不符合市场逻辑, 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如果中国践行单边开放,那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行政当局就很难封杀其作为市场主体的资本和企业。 精准单边开放就是根据国家实际发展需要的单边开放。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可以通过单边开放来推进落实因为政治问题而暂时无法生效的《中国—欧洲联盟全面投资协定》。在现在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如果对等开放,这个协议很难在短时期内实行。中国至少可以在一些自己所需要的领域先根据协议做起来。中国的单边开放可以利用资本逻辑、科技逻辑和市场逻辑来克服西方反华力量的政治和行政逻辑。 第二、对标 CPTPP、DEPA 等高标准规则,推动加入这些组织的进程。但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暂时加入不了,中国也可以以单边方式先实施起来。这犹如 1990 年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接轨”政策。 第三、建设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中国商务部在和东盟讨论 3.0 版的自由贸易区。的确,3.0 版比 2.0 版内容更广,但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一个数量上的不同。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把 RCEP、中国东盟 10 加 1 机制、澜湄合作等统筹起来,对标 CPTPP、DEPA 规则、规制、标准,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 第四、容许并且鼓励中国企业把供应链、产业链延伸出去。中国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一定要延伸到其它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必须意识到,在发达国家,企业卖整产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不合时宜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各个经济体都是卖整产品的,而在 1980 年代以后,经历了一波长达 40 年的超级全球化之后,如今很少有发达国家的企业还在生产整产品,而是选择了向外延伸产业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国际延申产生的是一种共赢经济。在地国家有了就业、税收,他们就会欢迎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同时中国的企业也可以利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和资源。现在在很多领域,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而产业链、供应链不能延伸出去,因此进入了内卷状态。如果内卷继续下去,整体经济就会恶化。现在一些决策部门没有意识到或者还不够清楚,把所有的产业链、供应链放在国内以确保供应链产业链安全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经验地看,如果一个企业生产全产业链是最没有效率的,也保证不了安全。 第五、尽量避免“替代”方法的扩大化,而全面替代战略更不可取。今天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一些技术领域封杀中国,在这些被封杀的领域,中国不得不实施“替代”方法。国内的企业也很有动力来实施“替代”战略,因为“替代”意味着这部分的市场从外资转移到内资(无论是国资还是民资)。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替代”是防御性的,不能扩大化。如果因为西方的封杀而实行全面替代,那么就会导向开放程度的减低甚至最终走向封闭。前面所讨论过的拉美经济体的替代战略的教训和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战略经验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出口导向,而非替代战略,未来除了被封杀的领域需要实行替代战略外,就整个经济体而言,还是要坚持出口导向的。 回应国家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百年发展目标的重要议题,创新性地提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议题,系统性地分解中国中等技术现状、问题,并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为跨越陷阱之路径建言献策。 全球视野,汇聚国际发展经验与教训,精准细分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格局与外部环境,重点立足于中国国内发展,让读者能够建立全局思维,站在未来看问题,理清科学政策的逻辑,更加透彻,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