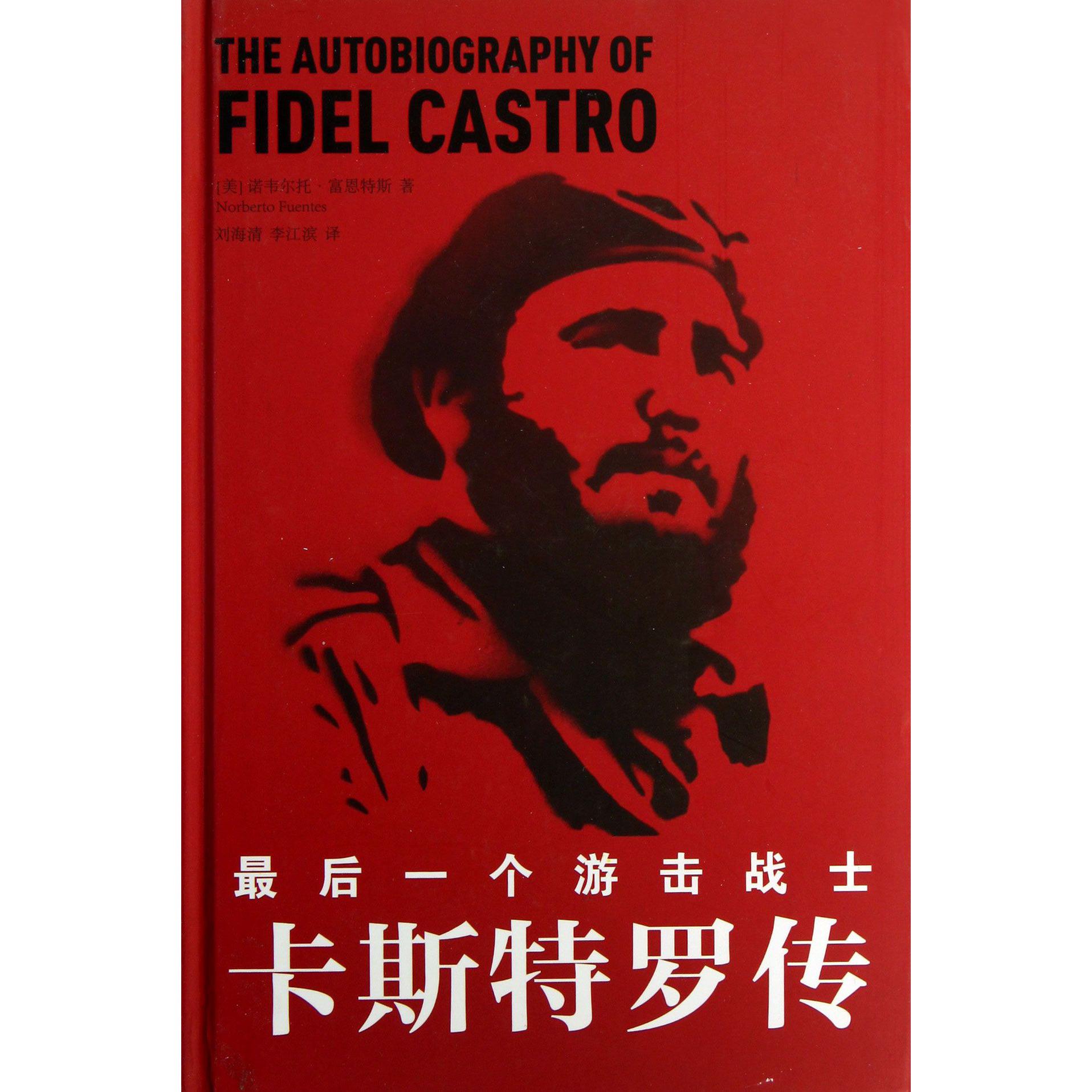
出版社: 法律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66.07
折扣购买: 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精)
ISBN: 9787511844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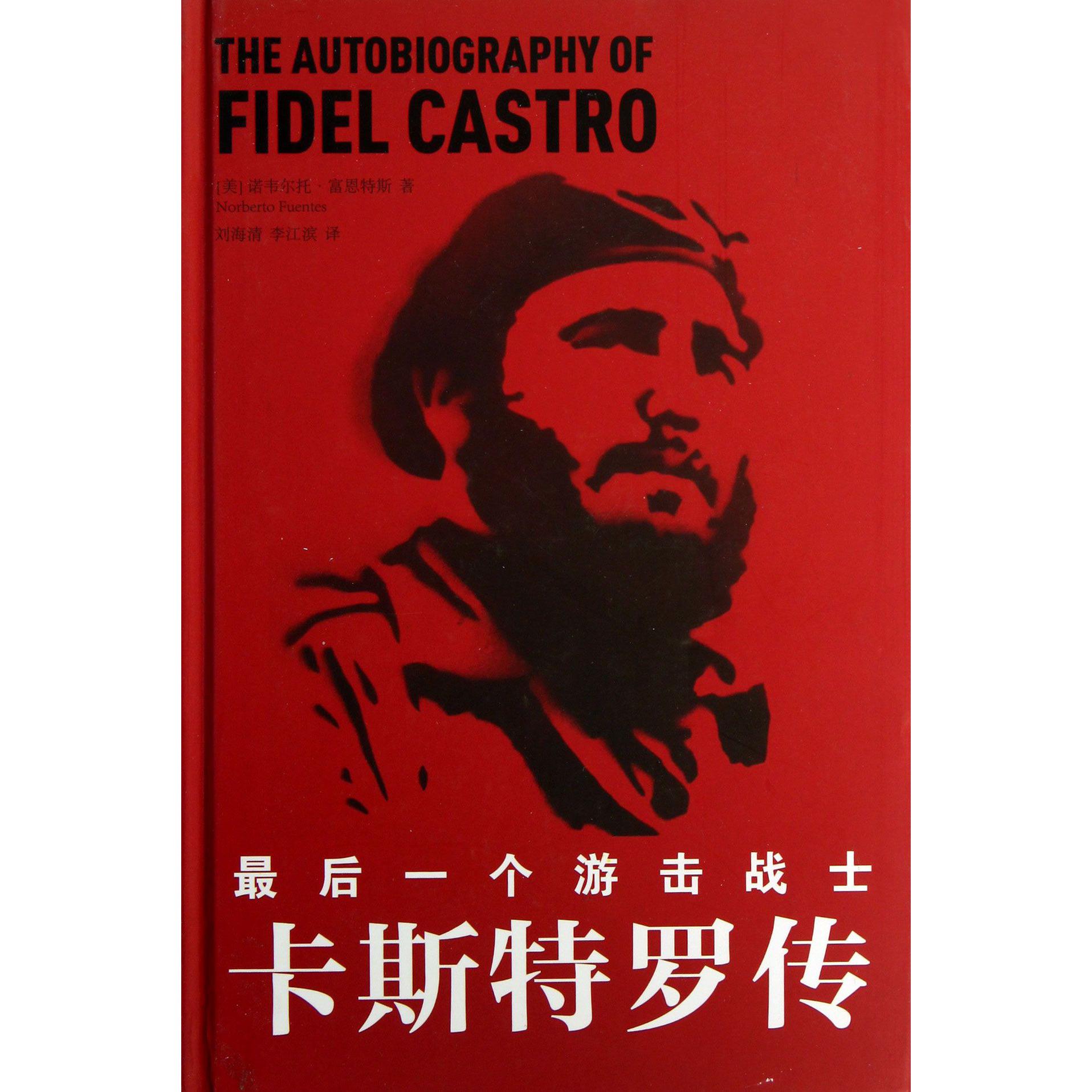
作为一位受人尊重的记者和海明威研究学者,诺韦尔托·富恩特斯是《海明威在古巴》等十部作品的作者。凭借其短篇小说集《孔达多的罪行》(Condenados del Condadoc),他曾荣获1968年卡萨德拉美洲奖(the 1968 Casa de has Americas Prize)。他的作品《非德尔·卡斯特罗自传》一书,更是使其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在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曾盛赞本书为“当代拉丁美洲文学的经典”,并称赞富恩特斯是“当代最杰出的古巴作家”。在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评论说,“长期以来,富恩特斯的作品也许是所有有关这位古巴领导人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如果说我消灭了一个胆怯而懦弱的世界,我又怎 么可能受那些我原来 反对的人的影响呢?我是为高尚之人写作的。 现在,请让我回忆一下我的童年。1926年8月, 一个暴风雨之夜的凌 晨两点,在马纳卡斯农场一座木桩支撑的吊脚楼中, 我出生了。我还希望向 读者介绍一下我的父亲。当时,他正在罗望子树下焦 急地等待着。 那棵罗望子树的鲜花正在开放。 他坐在那棵罗望子树下抽着烟,女人们则在剥动 物和木薯的皮。可怜 的人。我看到他坐在树下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这棵 树覆盖着整座庭院, 树干有二十五英尺粗,树枝上开满了小小的罗望子花 ,它的叶子给这座房子 带来了清爽和阴凉。它茂密的、亮晶晶的绿色树叶伸 展到了八十英尺的高 空,洒下一大片绿荫,似乎时刻宣示着自己的领地。 它的叶子永远是绿油油 的,即使在干旱季节也是如此。它橘红或黄色的花有 五个花瓣,并有红色花 环和紫色的花蕾。 我开始了解一个人和他所处环境的关系。我想, 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 个具体形象是我的父亲和那棵年龄估计超过一百多岁 的老罗望子树。这让 我确信,那肯定是夏季。甘蔗收割工作已经结束,农 场工人搭建的临时住所 已经消失,附近马尔卡内(Marcane)蔗糖加工厂的烟 筒也不再冒烟了。于 是,罗望子开花了,我父亲从他冬季一直待着的阁楼 中走出来。他手里拿着 纸烟,叉开粗壮的双腿站在树下,长时间地陷人了沉 思。从罗望子树开花这 个事实,你就知道夏天不久便会来临。农民们说这个 季节是La calor,即酷 热的意思。七月初,我父亲又开始了另外一项活动, 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是这 样的。他不断地赞美那棵树的产量,并一遍又一遍地 讲述他从树上摘到了 数量惊人的果实。 在粗大树干周围排列着四张长椅,就像罗盘的四 个基准点一样布置在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些年,父亲常常坐在那里休息 。在他附近的左后方 是一个建在四根水泥柱上的水池,稍远是支撑房子的 黝黑的caiguaran木 柱。正如我前面所说,这是我眼中看到的父亲。我看 到他拿着一只皮塔猎 人牌雪茄(Cazador de Pita),拿着雪茄的右手上有 一颗实心钻石。他不会让 雪茄熄灭,在烟头烧到商标前不会将它撕掉,并一直 放在嘴边吸着。皮塔猎 人是他最喜欢的雪茄牌子,马车小贩(carreros)常常 赶着整车的这种雪茄到 农场来卖——马车小贩是我们对四处游走商贩的称呼 。后来,我父亲在公 路的另一侧,也就是我们房子的对面,开了一家小商 店,这些小贩就将自己 的烟草和其他商品存放在那里出售。 我的父亲总是穿着高高的橡胶靴子,夹克衫上总 是带着淡淡的咖啡渍。 现在,你应该对我的父亲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了 吧?这就是我童年时 期的生活环境,田园诗般美丽而朴素的古巴农村,三 十年后正是我彻底改变 了这一切。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在这个国 家的每一个地方,任 何一个角落,我都能看到这种景象,然后我一个又一 个地把它们消灭。这并 不是因为我痛恨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出于早有预谋的 计划,也不是因为我认 为应该这样做,而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 程,当然这是我以后才 有的想法。这是我试图铲平的东西,它使我慢慢变得 越来越依赖残酷的力 量,这种力量是我创造的,然后又逐步释放出来。事 实上,从当时的情况来 看,我当时生活的环境并不是特别糟糕。所有为我编 写过传记的人都没能 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试图通过我在比兰马纳卡斯 (Manacas,Biran)童年时 期的生活经历发掘我发动古巴革命的根本动机,就好 像俄罗斯生物学家巴 普罗夫(Paylov)观察狗的行为一样。他们从来不想承 认这场革命是精神历 程的必然产物。首先,是一种平衡;其次,是一种权 力;再次,是一种控制。 此外,他们也都没有注意到我所推动建立的,或者至 少说是我发动革命产生 的政治制度,与我幸福的童年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五岁时,我亲眼见证了古巴农村的这些景象。爸 爸像酋长一样威严地 站在罗望子树下,用戴着耀眼光辉的钻石戒指的大手 ,喊道“儿子”或者“小 子”,招呼我走到他的身边。这就是我童年时期生活 的世界,是我眼中见到 的一切,是我的整个世界。虽然我还不能明确解释,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永 恒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眼中所看到的全部环境。我 必须承认,对于童年 时期的我来说,这就足够了。这是一片带有浓重中世 纪色彩的土地,自从我 父亲在这里建立了他的蔗糖生产殖民地,开垦了山地 ,砍伐了森林中的阿卡 纳树、牙买加黄槿、红木和caiguaran树以后,环境 就一直没有改变过。我觉 得自己就像陀螺一般,围绕着自己的轴线缓慢旋转。 存放罐子和粮食的库 房外墙边上靠着一个冰柜,屋里有一张很大的桌子, 年龄较大的女人们[包 括我的妈妈、姐姐安赫利塔(Angelita)和一些女佣] 用它来剥猪皮,稍后又会 把玉米磨放在上边。桌子上安了一个水槽,动物的血 可以沿着它流到地板 上摆放的一只桶里。没有人知道冰箱里放着什么东西 ,我们仍然可以说这 纯粹就是一个中世纪的家。 从我家的房子可以俯视外面的大路。这条路一直 通到奎托(Cueto),骑 马需要半个小时,坐卡车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房子 的窗户朝向东北,面对 着热带信风的方向,或许建筑工人当时就意识到了这 一点吧。爸爸抽着雪 茄把我叫到身边,说我已经五岁了,所以要奖励我一 个比索。他接着说: “今年,一个狗娘养的给了我三百五十磅。” 其实,是有人给了他三百五十磅重的罗望子。 他用手中的雪茄指了指头上的罗望子树,它所有 的花朵和果实都已凋 谢,必须等到明年春天才会再次出现。 我问,“但是爸爸,你为什么不给我五个呢?五 个比索。每年给我一 个。”爸爸说,“小子,一个比索等于五个比塞塔。 你怎么能要五个比索呢? 你还太小,用不了那么多钱。” 年轻女人们,包括我的姐姐胡安娜(Juana),可 能还有埃玛(Emma),以 及一个季节性女佣——一对海地夫妇的女儿,甘蔗收 获后他们继续留在了 当地——正在我父亲面前剥木薯。上面的厨房里,有 人正在筛选白米和黑 豆。我不知道是谁在做这件事,可能是一位姑妈,一 位祖母,也有可能是一 位女工。小劳尔(Raul)还没有出现,可能还在婴儿床 上,也有可能还没出 生。关于这一点,我要好好计算一下时间才行。 我之所以说“上面的厨房”,是因为它建在七英 尺高的立柱上。从院落 的前门,可以看到远处的邮政局,小学也建在这种立 柱式结构上。 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