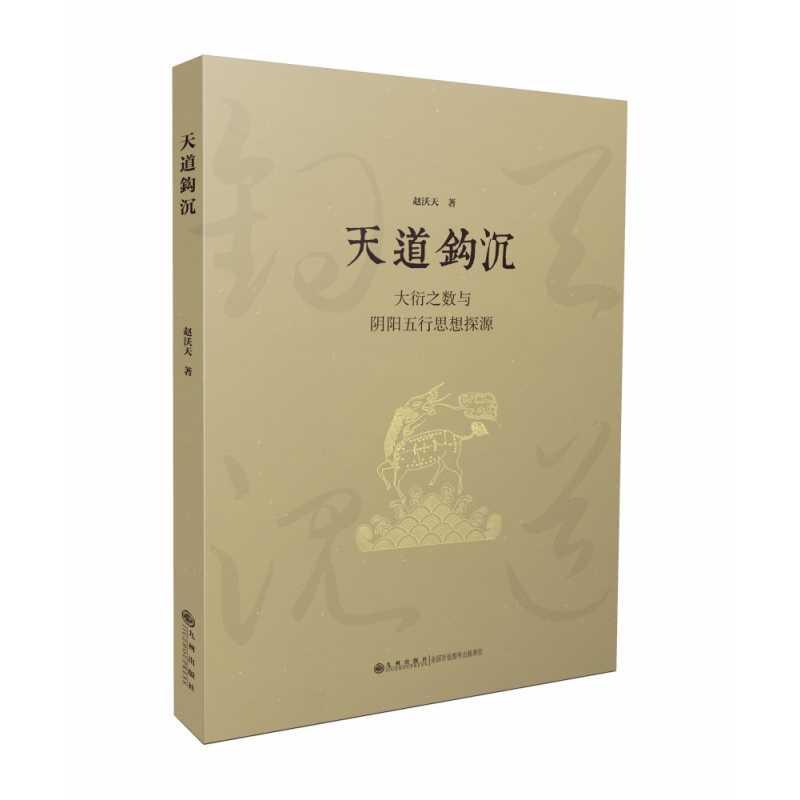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天道钩沉:大衍之数与阴阳五行思想探源
ISBN: 97875108855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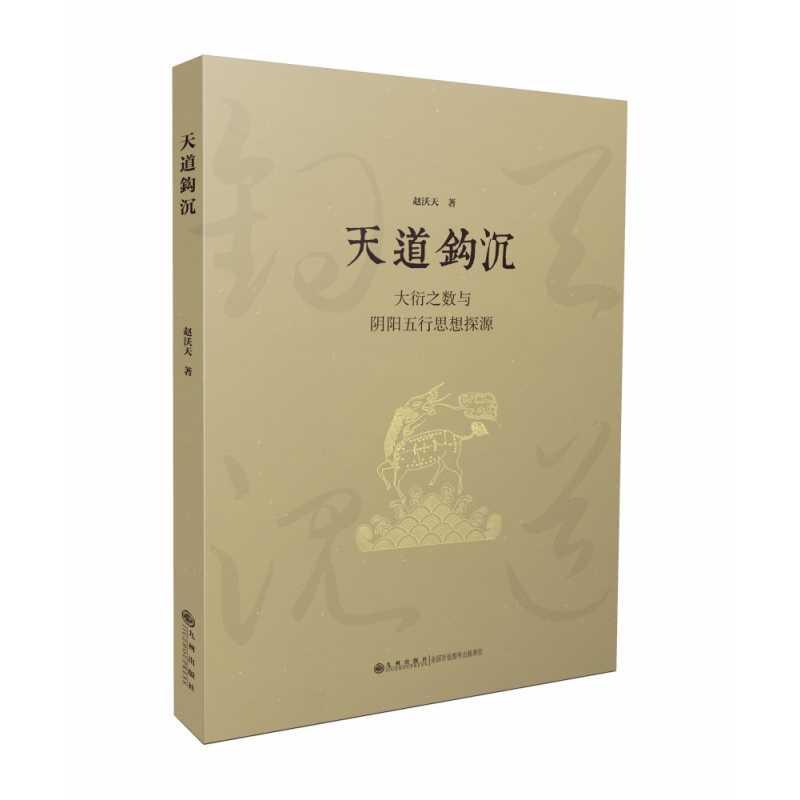
赵沃天,1942年出生于辽宁锦州正黄旗满族世家,1965年大学毕业,长期从事科研工作。自2016年开始,担任国际易学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擅长以古天文历法探索《周易》之奥秘。曾发表《论<周易>与古天文学之四象》《论“三五以变”》《综论<周易>大衍之数》等作品。
导 论 大衍之数乃《周易》锁钥,天道锁钥,上古文明锁钥,明察大衍之数,亘古洪荒之门将豁然洞开。 ——题记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在诠释《周易》大衍之数的基础上,通过发现和寻求大衍之数的历史渊源,完成对阴阳五行思想中的几个重要课题的探索。这些课题是周易筮法、西周历法、帝喾与阴阳合历、五行的起源等,它们都在“天道”的范畴之内,与古天文历法密切相关。就本书探讨的历史时代而言,是指从《周易》问世的殷周之际起,追溯到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因此,本书与上古文明有紧密的联系。 以研究和诠释大衍之数开篇,是一个特殊的研究视角,实际上成为探索“天道”的起点。有人说“《周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这一说法意在提高《周易》的地位,但我以为并不准确。又有人说“《周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其意是说《周易》不是“源”,而是接近于源头的、具有生命力的“流”。我以为仍然不够准确。因为在《周易》问世的数千年前,中华民族就已经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正是这一文明导致了《周易》的问世。 本书将涉及一系列学术界长期困惑或一直存在争议的课题,它们都是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的大题目。一是被称为“千古之谜”的《周易》大衍之数。事实上,她已存在了三千余年,虽然司马迁、京房、《周易乾凿度》作者等早就已经提出过答案,但由于没有对《周易》大衍之数诞生的历史大背景作出说明,也没有在文字学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诠释,以致有许多人连“大衍之数五十”都不能接受,另外提出所谓的“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之说。二是西周历法。一方面固然是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另一方面是若干重要问题上的长期争论,如西周是处于观象授时还是推步历法阶段,是否已经认识朔日,有没有实施颁朔制度,直到今天也没有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性意见。鉴于西周历法是解决西周王年的关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西周王年的任何方案都难以令人信服,“夏商周断代工程”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三是帝喾的贡献。现在对帝喾的研究虽然不多,但马王堆楚帛书《创世篇》以神话的方式将伏羲视为四神(黄赤道四象)之父,将帝喾视为日月之父。而在《山海经》中,帝喾又成为天帝。帝喾在神话中的地位,是后人将其非凡功绩神圣化的表现。因此,帝喾应该是继伏羲之后,又一位具有开创性伟大贡献的划时代人物。四是五行起源。五行起源关系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有人提出,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中华文明哲学基础的阴阳五行思想就是一脉相承的。过去,由于受到“古史辩”学派的影响,许多学者都认为五行源自战国时代的邹衍。尽管这一认识在今天影响甚微,但五行的起源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由于大衍之数是探讨上古文明的基础和支点,故要想解决上述一系列上古文明中的课题,解决大衍之数就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大衍之数是《周易》锁钥、天道锁钥、上古文明锁钥。 其次要着眼于研究方法。从古代文明的大视野来看,中华文明始于伏羲观象授时。渔猎社会向农耕文明的转变,观象授时发展为古天文历法,诞生了阴阳五行思想,诞生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阴阳合历,并产生了第一部集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古天文历法学、算学等大成的、对中华文明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品——《周易》。周人笃信,《周易》是受命于天的周天子与上天沟通的手段,其中必然涉及作为天命标志的古天文历法。古天文历法诞生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同时具有科学和宗教的两重性。正确地、历史地认识和运用它的两重性,对于我们研究《周易》,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和古代社会都有极大的益处。 第一,古天文历法的科学性。古天文学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一门自然科学,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因此,唯有借助古天文学的逻辑理念和方法,来研究《周易》筮法和破译大衍之数,才有可能实现大的突破。由于古天文历法兼具科学性和逻辑性,我们还可以从认识论的视角上来探讨它的演变过程。 第二,古天文历法的宗教性。古人在观象授时和创建历法的过程中,我国先民形成了对天的崇拜和敬畏,并将那些在古天文历法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祖先尊奉为天神。例如,楚帛书《创世篇》中的创世之神伏羲、女娲,《山海经》中的天帝帝喾,《尚书· 洪范》所谓“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中的大禹和多部文献中提及的“文王受命”等。这些都是基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神话故事和传说。宗教信仰导致人们要认识天意,创造与上天沟通的手段,于是在古天文历法发展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占星术。古天文历法和占星术的发展,又催生了祭祀,诞生了三兆和三易,它们都成为古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远古真实的历史是伴随着宗教信仰走过来的,可在传说、神话和祭祀礼仪中找到真实历史的重要痕迹。因此,我们就可以结合有关神话传说、祭祀礼仪、文献记载等,来还原和发现真实的历史。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就以古天文历法为主线,从研究《周易》筮法和破译大衍之数入手,来探索上古文明。其基本思路可概述如下: “大衍之数五十”之义为“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又称“日、月、星三辰”,或“日月星辰”。此处之“星”,即黄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座,又称二十八宿。古人通过观测日月相对于二十八宿的位置变化来研究他们的运动规律,进而创建历法。以十天干纪日,以十二辰纪月,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合之,成为天道运行的五十要素。古人认为,天道运行衍生万物,故此五十要素又称为“大衍之数”。又,殷周之际种种偶然事件的发生,使周人认为自己得到了上天的庇佑,由此形成“天命归周”的认识。于是,就像夏有《连山》、殷有《归藏》一样,文王创建《周易》作为天命归周的标志。这就是文王演《周易》的由来。文王在创建大衍筮法时,以五十枚蓍草拟比日月星辰运行,通过推演天道实现了与上天的沟通。所以,大衍筮法中的“大衍之数五十”的论述,实质上来源于西周历法。根据这一认识,并参照有关记载,就可以复原我国古代第一部推步历法——古《周历》的本来面目,进而对长期存在争论的西周是否认识朔日,是否建立了“颁朔制度”,是否采用“年终置闰”等一系列问题作出结论。 大衍之数和西周历法的厘清,为阴阳五行思想探源和上古文明的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并可由此上溯到五帝的帝喾时代。根据大衍之数对“三辰”的认识、《尧典》的“历象日月星辰”、《国语》的“帝喾序三辰”,结合《山海经》的有关记载,阐述帝喾对古天文历法的贡献。帝喾认识到是太阳的运行规律(按照现代科学的认识,是地球围绕太阳的运行,或者说是太阳绕地球的视运行)决定了大地的四时,据此提出了太阳年的理念,建立了日月的观测体系,创建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阴阳合历制度,同时又是阴阳思想的肇始。此外,帝喾还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律,建立了东、西、南、北四方,创建了二分二至,并且以黄赤道恒星作为星空背景,来观测和研究日月的运行规律,由此建立了后世长期使用的、相当于现代物理学中研究物体运动的参考系概念。帝喾是阴阳合历的创建者,在《创世篇》中被尊奉为日月之父,在《山海经》中被尊奉为“天帝”,又被称作古代中国的“哥白尼”。 五行与历法同出一源,二者都是在观象授时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在观象授时后期(由渔猎社会向农耕文明转型之际),农业生产催生了早期历法——星历。星历是以星象表示季节和物候现象,以便保证农业生产合于天时。在观象授时早期,主要是观测黄赤道四方的授时星座,大约不迟于黄帝时代又增加了北斗,形成早期的五宫(黄赤道四方的授时星座和北斗的合称)天象而建立了星历。帝喾创建四方(五方)之后,又以之匹配形成早期五宫—五方体系,成为五行的原初认识。这就是五行的起源。伴随着早期五宫—五方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又产生了管理五方的官员——五正、天上的五方帝和他们的辅佐——五佐。另外,还有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等多组五行要素的陆续加入。所有这些都起源于天文观测和创建星历的时代,与历法、占星术以及对天神、祖先的信仰和崇拜有关,故它们构成的体系,就被统称为“天道五行”。 古人出于对天人感应的认识和信仰,认为天上的日月星辰创造了大地的万事万物,并划分为水、火、木、金、土五材,归入地道五行体系,与天道五行合之而成为涵盖天地万物的五行体系。结合《尚书· 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的记载来看,应该是大禹完成了这一伟大的思想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中国古天文历法——中国最早形成的一门古代科学的发展过程,按认识论的哲学思想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在以伏羲观天法地为代表的观象授时阶段,古人认识到黄赤道四方恒星的出没规律与大地的四时相合,从而实现了观象授时。进入神农氏的农业文明之后,黄帝根据农业的需要,创建了星历——五行。属于古人对四时的感性认识阶段。 第二,帝喾认识到太阳的运行决定了大地的四时变化,由此提出太阳年的理念,创建了“阴阳合历”。这是古人对四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重要阶段。创建“阴阳合历”以后,古人又陆续探索、创建了一系列的历法概念、历法参数以及测量方法,建立了阴阳合历的历法规则等,完成了创建推步历法必不可少的一系列基础性工作。 第三,创建推步历法。确定岁首、历元和闰周之后,周文王创建了我国古代的第一部推步历法——古《周历》。这标志着古人对四时的理性认识进入了实践阶段。阴阳合历经过了数千年的演绎和发展,又吸收和融合了西方现代天文学历法,形成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历法:一是我国独创的历史悠久的二十四节气;二是太阳历法与朔望月历法的完美结合,也是中国的阴阳思想与西方自然科学的完美结合。 在观象授时和创建古天文历法的过程中,古人把寒冷和温暖、晴天和雨雪、白昼和夜晚、光明和阴暗等的变化归结为阴阳变化,形成了阴阳对立且互为消长的理念。又,在阴阳合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两个并行的纪时体系,一是由于观测太阳的周期性变化而形成的太阳年和节气的理念,二是由于朔望月纪时而形成的对晦朔弦望等月相的认识,这两个纪时体系具有不同的周期性,而在它们形成之初,人们就意识到需要建立闰月制度来协调两种历法体系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阴阳之间既相互对立又彼此协调一致的理念。上述阴阳要素的变化都可以归结为日月运行,归结为历法,由此可见,古人阴阳观念的核心是历法。 综上所述,阴阳和五行这两个概念都是古人在观象授时和创建古天文历法的过程中形成的,因为二者之间存在许多相同和相通之处,所以又被统称为“阴阳五行”。古人在认识宇宙、创建阴阳五行思想的同时,形成了对天的信仰。古圣人一方面将阴阳五行思想应用于治国理政之中,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将阴阳五行思想作为天人沟通的媒介,在夏商周三代分别创建了《连山》《归藏》和《周易》。 如果我们跨过五行的源头,沿着历史的足迹上溯而行,就会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步入更为遥远的上古。在那个洪荒时代,可以看到清澈的蓝天和巍峨的群山之间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一群手持木棒和石块的野人,正在呐喊着围猎和扑杀一群《山海经》中所描述的鸟头龙身的、庞然大物般的喷火怪兽。当白昼的繁忙和劳碌结束之后,晚霞的余晖没入远方群山的背后,一天的喧嚣归于沉寂,饱食之后的猎手们杂乱地躺在篝火周围进入梦乡,篝火旁是狼藉的兽骨。在夜幕初降的地平线上,悄然升起两颗亮星,那是苍龙之角,然后是跃起的苍龙……这不正是《乾卦》的六龙天象吗!刹那间,我从梦中惊醒,重新坐回书案旁,案上的书正是《周易》,翻开的那一页上赫然写着“大衍之数五十……” 丁酉之年仲冬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