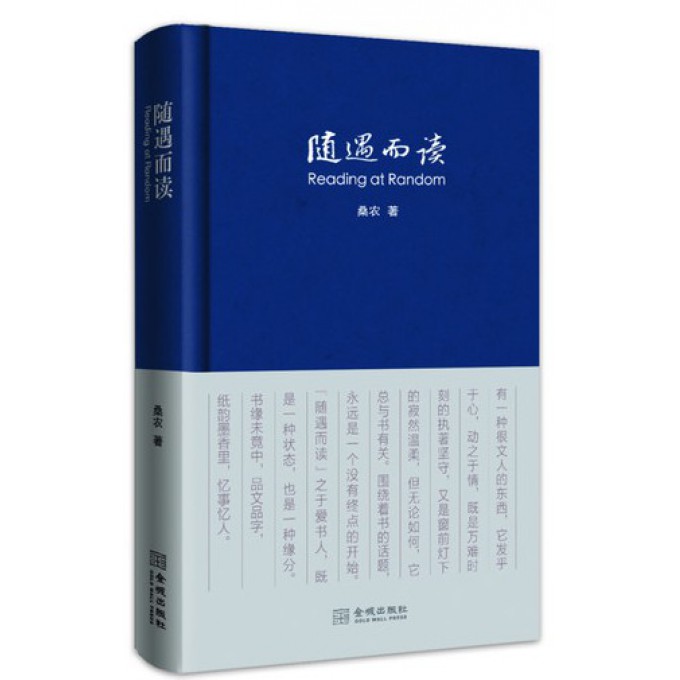
出版社: 金城
原售价: 39.80
折扣价: 29.00
折扣购买: 随遇而读(精)
ISBN: 97875155027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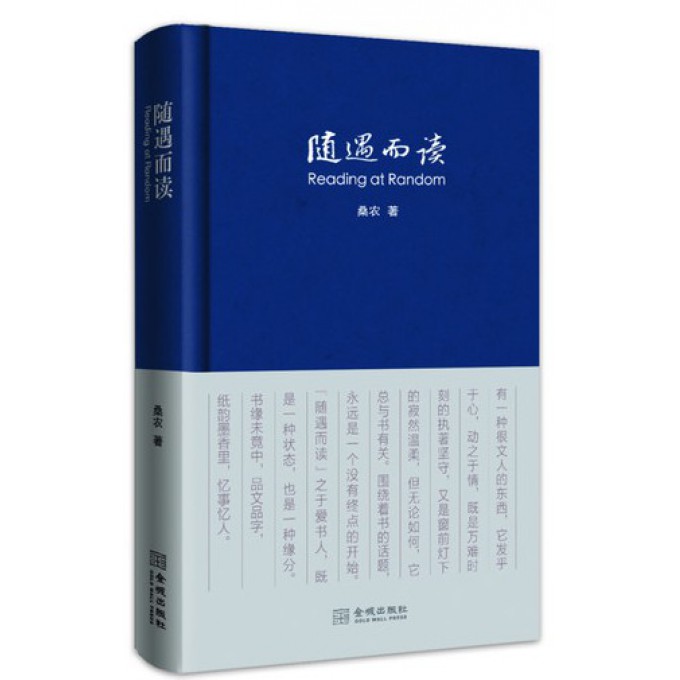
伤心图书馆之歌 董桥的《绝色》中有一篇《铁达尼里的一本培根》,说的是美国藏书家 哈里·威德纳的故事一一九一二年,年仅二十七岁的威德纳乘坐铁达尼号巨 轮回国,口袋里装着一本一五九八年版的培根《随笔集》。结果,自然是和 自己心爱的珍本一同葬身海底。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在爱德华·纽顿的《聚书的乐趣》里。当时印 象最深的是,大船开始下沉,救生艇放下去。“让妇女和儿童先撒”。威德 纳的母亲和侍女获救生还,而他和父亲从此失踪,一位富豪及其长子,把活 命的机会让给了太太和女佣,让人顿生感慨。如果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老 爷和公子应该先走,夫人和丫环理当牺牲才是。 据纽顿的记述,此前几天,威德纳在伦敦拍卖会上标下《随笔集》时, 曾对人说。“我还是等书到手以后再走好了,那么一来,万一我搭的船沉了 ,我才能和那部书一块儿葬身大海。”《聚书的乐趣》一书的译者,将这一 章的标题译为“一言难忘”,汉语表达不够到位。后来。陈建铭的重译本《 藏书之爱》里译为“一语成谶永难忘”,就好多了。 不过,陈建铭在注释里义指出,纽顿说的“一语成谶”虽然浪漫,却不 属实。他根据尼古拉斯·巴斯贝恩《文雅的疯狂》里提供的资料指出,这句 话应该是威德纳搀扶母亲登上救生艇,母子两人面临天人永隔时说的。“母 亲,那本培根小书已被我塞进口袋,它将和我一起葬身海底。” 某次一同散步时,威德纳跟纽顿说起,不希望只被人们当成拥有几部好 书的藏书家,不管那些书有什么了不起;而希望能盖一座最大的图书馆,好 让后世的读书人永远记得自己。纽顿讲,当得知威德纳的母亲为了怀念爱子 ,打算在哈佛兴建一幢藏书楼当做纪念馆,便屡屡想起那次对话。——如果 威德纳那句令人动容的谶言,是母子永别时所说,我们便更能理解一位母亲 的伤心和执著。 董桥的文章中也提到,可怜的妈妈知道儿子此生最爱的是书,最舍不得 的是书。悲剧发生一年之后,她写信给一位书商说。“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 日,人世间所有的欢愉都离我而去了。”为了抚平伤痛,她决定在儿子的母 校哈佛大学建一所纪念图书馆。她请书商为儿子的图书馆搜集更多、更珍贵 的版本,最终合计花了十二万美元。连威德纳的爷爷都花六千美元为孙子的 图书馆买进一批著名诗人的手稿。几经筹划,威德纳的母亲斥资两百万美元 ,聘用她指定的建筑师,用了两年时间,在哈佛兴建“哈里,埃尔金斯·威 德纳纪念图书馆”。“我儿子的书全部集中在哈佛了,”妈妈说,“我完成 了我儿子的心愿。” 图书馆于一九一五年建成,威德纳的三千多册藏书都陈列在馆内名为“ 超凡人圣”的特藏室里。现今,该馆仍是哈佛大学最大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 学研究图书馆,收藏历史、经济、语言、文学等各类文献。仅纸质图书即有 三百四十五万册,而且每年仍然以很快的速度增加。 威德纳图书馆的正门是类似罗马式的一排立柱长廊,巍峨雄伟。门前的 台阶有二十多级。拾阶而上,就像进行一种心灵上的登攀仪式。正门两侧, 各有一块石碑,分别刻着这样的碑文。“威德纳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在铁达 尼号沉没时去世。他生于一八八五年六月三日,死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这座图书馆由威德纳的母亲捐赠,这是爱的纪念。一九一五年六月二 十四日。” 爱书人的趣话 安妮·法迪曼的《书趣》一书,原名为拉丁文ExLibris意思是“某某的 藏书”国际通行的藏书票上,印着的就是这几个字母。翻译成“书趣”,或 许可以根据书的内容。理解为“爱书人的趣话”。 扉页上有作者的献辞,献给父母。父亲克利夫顿·法迪曼,就是那位写 过《一生的读书计划》的“费迪曼”。我以前读过该书的汉译本,是一份书 单,相当于必读书目。每种书的评点都很到位。言简意赅,对初学者很有用 。据说,当年十分畅销。现在,安妮来谈自己读书、藏书、爱书的乐趣,自 然是有“家学渊源”。 《书趣》里有一篇《我的祖传城堡》,说的就是她父母的藏书。四岁时 ,安妮喜欢玩搭建城堡的游戏,用的不是积木,而是父亲的一套袖珍本《特 罗洛普文集》,二十二册,每册有一盒扑克牌那么大小,正好用来做立柱、 横木或吊桥。 十四岁那年,安妮在父亲的书架上发现一本《芬妮·希尔》。这是英国 文学史早期有名的性爱小说,也是她第一次接触到的性书。成年后,她问过 几位作家朋友,还记得自己父母的书架上有些什么书,答案大多是带有性爱 色彩的。安妮写道。“我认为父母的书架是十几岁的孩子第一次和带有色情 内容图书相会的最好场所,不仅是因为这些书在这里容易到手,而且,孩子 们由此还会懂得,他们的父母也是有性的要求的,尽管有点难以相信。” 安妮的父母是一对作家、爱书人,安妮和她的丈夫乔治也是一对作家、 爱书人。两人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各自的书都是单独摆放,一个在阁楼 的北头。一个在南头。五年以后,才想到要将它们合拢起来。然而,按何种 方式排列,哪些复本应该剔除,又各执己见,打了许多无伤大雅的口角官司 =最后,夫妻二人的书终于融为一体。安妮写道。“我们是真正结婚了。” 安妮的境遇,让人想起李清照的前半生,父亲是位名人,丈夫趣味相投 ;只是后半生的情形不同了。安妮的父亲活了八十多岁,寿终正寝;丈夫也 没有外心,或英年早逝;更未曾遭遇外敌入侵。国破家亡。也许有人以为, 正是缺乏这些灾难的磨砺,安妮的文章不及《金石录后序》那样感人至深。 这是不错的。不过,国仇家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指责作者欠缺这种体 验,未免强人所难。况且,安妮和李清照的文字,应该说各有千秋。前者写 不出后者的忧郁、哀愁、悲凉,后者恐怕也写不出前者的轻松、幽默、风趣 。 《书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安妮的一个朋友,年轻时在牛津攻读文学 史。一开始就迷上了荷马,而一位男同学对她说,荷马比维吉尔差多了_两 人在咖啡馆里争执起来。其时,朋友尚未读过维吉尔,情急之下,说道。“ 如果你认为维吉尔那么了不起,干嘛不送我一本呢?”不久,她果然收到那 位男生赠送的一部《维吉尔全集》,扉页上还写了一大段表向爱慕之晴的题 词。“后来怎么样了?”安妮好奇地问道。“后来嘛,”朋友回答,“我从 来没有和那个男孩睡过觉,可是我爱上了维吉尔,我和那本书睡觉已经多次 了。”接下来,安妮又说,乔治曾将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她,扉页题词是。 “给我亲爱的妻子……这也是你的书。我的生命也属于你。”因此,这本书 成为她藏书中“最美好”的一部。安妮写道。“我不曾和那本书睡觉,但和 书的作者睡觉已经多次。” 如此俏皮的话语,李清照大概说不出口。 毛姆的文艺随笔 毛姆的文艺随笔,像他的小说一样,以故事性见长这一特征,以前读《 巨匠与杰作》时就见识过了最近,他的两部随笔集《观点》和《随性而至》 的汉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让读者再度领略到他独具一格的文风。 《观点》一书里,有一节谈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毛姆写道。“我不想 讲她的生平故事,但是因为她的小说大部分都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我还是简 述一下吧。”这是经典的毛姆句式。随后,是一段“打通了记人随笔和文艺 评论两个不同领域”的“妙文”。 毛姆说,凯瑟琳生于新西兰,当地的生活让她觉得沉闷无聊,于是说服 家人放她去英国。上学期间,她与一位舞会上邂逅的男子有了段露水情缘。 两年后回新西兰,又爱上一位大提琴家。随之再返伦敦,转而与他的弟弟, 一位小提琴师,共坠爱河。但不久即与一位大她十岁的声乐老师结婚。新婚 之夜,她拒绝同房;第二天便离家出走。她给远在新西兰的父母发了两封电 报,一封说要结婚了,一封说已经离开了丈夫。母亲赶来时,发现她已有孕 在身,便把她送到德国安顿下来,等孩子出生。在此期间,她读了不少契诃 夫的小说,自己也写了几篇,结集为《日耳曼膳宿公寓》。 后来,凯瑟琳突遭事故早产,生下死胎;等身体康复,便返回英国。在 伦敦,她遇到了米德尔顿·穆里。由于前夫拒绝离婚,两人只能同居。他们 一起到巴黎旅行,见到穆里的好友弗朗西斯·卡可。凯瑟琳与卡可交往频繁 ,回国后一直通信。终于有一天,她独自去了法国。可因为卡可已应征人伍 ,两人在军队安排的一个小房间待了三天后,凯瑟琳极度苦闷失望地离去。 穆里收到电报,去接她。一见面,凯瑟琳就说,她不是回到他身边,而是实 在没有地方可去了。毛姆写道。“凯瑟琳的这次出轨给她的小说《我不说法 语》提供了素材,她对弗朗西斯·卡可的描述非常苛刻,有失公允,把穆里 也写得很恶毒。她把初稿给穆里看,深深地伤害了他——毫无疑问,她的初 衷便是如此。” 读到这些,我不禁愕然。因为这与我记忆中的印象,截然不同。于是, 我找出一部《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印刷 时间是一九八三年,距今快三十年了。翻到书后附录,有一段“女作家小传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生于新两兰,青年时代在英国学习。十八岁回故 乡后,由于不满当地褊狭闭塞的风气,一九○八年再去伦敦。她遭受过不少 人生的挫折。首先是第一次婚姻完全失败,随即分居。她在德国生下的婴儿 又不幸失踪;她伤心之余,写下一系列带有苦涩味的速写(《在德国膳宿公 寓里》)。所幸的是,她在一九一二年认识了评论家和编辑墨利,二人志趣 相投,生活在一起,感情融洽。”——这是作家传记的常见写法,典型的八 股模式。比较而言,毛姆的叙述更为客观,尽管有些八卦 据说,八卦属于娱乐界,八股才符合“学术规范”。可谁会写这样的学 术八股呢?那作者不是不明真相,随意捏造,就是明白真相,刻意隐瞒。至 于能够欣赏学术八股的读者+不是蒙昧无知,就是情愿无知。这样的读者和 作者,便是陈寅恪说的“下愚面上诈”一个心智健全的普通读者,显然不希 望被瞒、被骗,而希望知道真相。承认这一点,就不难发现,要了解凯瑟琳 ·曼斯菲尔德的生平事迹,去读那些四平八稳、粉饰太平的学术八股,肯定 不如去读毛姆随性而至、毫无避讳的文艺随笔。P6-19